作家阿丁把聊斋写成当代小说
2018-04-10
文坛有很多弃医从文的人,从毛姆、鲁迅、郭沫若到如今的余华、毕淑敏、冯唐……文坛也不乏记者转型的作家,从海明威、狄更斯、萧乾到金庸、严歌苓……

2012年11月,作家阿丁在北京单向街书店。
作家阿丁身兼两种。他先是当了近10年的麻醉医师,辞职和父亲一起开诊所;然后又进媒体,当了近10年记者;最后真真正正开始写作,大器晚成,成为“70后”作家里的佼佼者,被称为“中国的亨利·米勒+理查德·耶茨”。米勒文风大胆而深刻,耶茨关注现实而富有洞见,阿丁如他们一般,目光“狠”,下笔更“狠”。
不久前,阿丁推出短篇小说集《厌作人间语》,挑选《聊斋志异》里的部分文章改写成现代小说,阴郁、温暖、苍凉……写尽了世间的种种况味。
让老古董闪出新光
阿丁特别推崇《聊斋志异》,认为“在世界短篇小说的殿堂里,其成色不亚于其他作品”。
小时候,阿丁的姥姥会给他讲各种鬼魂精怪的故事,把小家伙吓得瑟瑟发抖,却依然缠着姥姥讲下去。等阿丁大些时,姥姥失明了,为了陪她,阿丁就捧一本《白话聊斋》读给她听。姥姥很得意:“这不和以前姥姥给你讲得差不多嘛。”
在散文集《职业撒谎者的供述》中,阿丁曾分享过自己的文学脉络,讲述过胡安·鲁尔福、威廉·福克纳、伊萨克·巴别尔等大师对自己的影响。但算起来,和《聊斋志异》勾连在一起的姥姥的故事才应该是阿丁的第一位文学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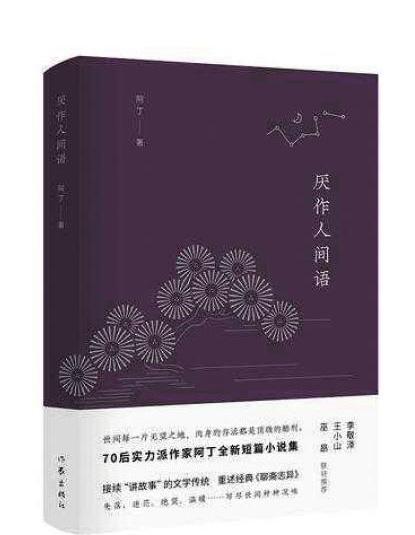
阿丁的新作《厌作人间语》。
在阿丁眼里,《聊斋志异》不输于任何一部西方文学殿堂的作品。因为“文学性即人性”,而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显然“多具人情”,就像福克纳等人笔下的狗狼鲸熊一样,“在其皮毛之上,同样泛着人性之光”。 “《聊斋志异》虽然是古汉语写就的,但也可归于现代文学,因为字里行间可以发现超越时代的光芒,比如对个体自由之憧憬、对僵硬体制之嘲讽,以及在婚恋问题上对女性之尊重,在当时都算是开风气之先,甚至在道学家看来‘大逆不道的。”此外还有蒲松龄在文学层面的想象力之瑰丽,也深深地吸引了阿丁。
吸引最终的结果是“新酒装旧瓶”,用阿丁的话说,是“以现代文学的叙事,完成自己之‘私欲 (即对《聊斋志异》的喜爱)”,“若能以当下的现实意义让这一老古董重新闪出些光来,就完美了。”阿丁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厌作人间语》里的短篇,源自聊斋,又不同于聊斋。比如《六指》,在原著的卷二·《阿宝》里,是一个长有六指的痴人迎娶白富美,考上进士的故事。阿丁吸取了六指、痴人、灵魂出窍的情节,但写了一个发生在“文革”期间因爱犯错,然后“坏人变老”的故事。
众多的改写里,阿丁最看重《蛩(音同穷)》,也即《聊斋志异》里的《促织》。“这篇我写的比蒲松龄的原文还要短,短是短了点儿,但我想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给了它可映照的现实意义和不同的叙述角度”。
其他短篇也是如此,同样的故事轮廓,不同的叙事方式,席方平、阿宝、王六郎……一个个人物“穿越”当代,构成一部新聊斋。李敬泽、巫昂等作家联袂推荐,有人评论其和余华的《第七天》一样弥足珍贵。
“郁”比无知无识好得多
《厌作人间语》跋文的题目,叫作“除了人我现在什么都想冒充”。当年的处女作《无尾狗》里,阿丁也写下过一句:“我对自己作为动物的肉身存在无计可施,因此希望自己拥有植物的思维。”

阿丁画作《生冻疮的Nepal(尼泊尔)天使》。
从想当植物到“厌作人”,是阿丁写作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可以把‘植物的思维理解成沈从文先生说的‘抽象的抒情,有现世的焦灼与避世妄想在内;‘除了人我现在什么都想冒充出自王小妮老师的诗,她想表达的正是有时我心里所想的,人的躯壳并不能给一个不安的灵魂以妥帖的庇护,有人‘物化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借助想象的逃避方式,哪怕是虚无的。”
为了这种虚无的安宁,阿丁已经从故乡逃离多年。
他是河北保定人,小时候就心怀文字梦。父亲是医生,希望阿丁能子承父业,端上“铁饭碗”。阿丁于是学医,十六七岁就参加工作,进医院当了麻醉师。阿丁很不“安分”,不喜欢日复一日的工作,也不喜欢可以想见的“有前途的”未来。
在一张处方笺上,他写下辞职信,确定了自己也不确定的未来。最初的日子彷徨而无措,靠写字当然难以为生。他开过诊所,做过小生意,都以失败告终。

阿丁所畫的卡夫卡。
网络刚兴起的时候,别的年轻人在玩游戏、聊QQ,他则在论坛上写文章。喜欢足球的他写了很多球评,凭借那些文字,一家媒体向他发出了邀请:要不要来上班。阿丁去了重庆,然后是天津、北京,10年里从一个小记者变成体育部主任。
真正写作也是在进了媒体之后。2007年,阿丁写出了《无尾狗》。他想要阐述的是:“当一条街被所有砍掉了尾巴的狗占有,偶然有一条长尾巴的狗闯入它们的街区时,它们就会扑上去,把后者的尾巴咬下来。于是,新的无尾狗也成了它们中的一员,一起奔跑、吠叫、嬉戏,狗的世界就此和谐,再无纷争。”显然,这是一个关于大多数人和异类的故事。
有书迷说,阿丁的作品是“致郁系”。他笔下没有那些空洞的鸡汤,有时甚至很不温暖,死亡、暴力,生冷不忌。阿丁不在乎自己被归为哪一类,“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但‘郁是好事,至少比天天活蹦乱跳、无知无识要好得多。卡夫卡说过要读那种‘捅我们一刀的书,大概就这意思。”
真绝望了就不会再写东西
只读其文,也许会把阿丁想象成一个对人性绝望的悲观厌世者。其实不然。作家王小山评价:“阿丁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威猛,但侠骨柔肠,基本上是个不会跟朋友说‘不的人。”
阿丁自己的说法是:“对见过的人,不管熟不熟,我都会以最大的善去揣测他,不认识的则相反。”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对人性)并不绝望,真绝望了就不会再写东西了。实际上我早就是个温情脉脉的人了,或者说,与人为善的人。只有在我极度讨厌的人面前我才会锋利,但这些年更多的表现也不再是锋利了,而是尽可能钝一些,比如干脆不说话。我能做到的极致,就是在碰到厌恶的人的时候不发一言,一走了之。”
他住在北京艺术家云集的宋庄,但既不混艺术家圈子,也不混作家圈。“现在我还是‘异类,一把年纪了还经常被长辈说幼稚,因为跟我不是一类的越来越多。不过不准备改了,我活我的。”
身在宋庄的他,唯一的影响是近年迷上了画画。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幅自己的画作。那是他刚开始画画时的作品,画的是大作家卡夫卡。背景是三原色: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原色是绘画里世界的构成。“我觉得卡夫卡几乎洞悉了整个世界,近乎神,因此这么画了他。”
阿丁说:“画画对我来说就是玩,而写作多少要严肃些,算事业,我会在写作上倾注我秘而不宣的野心,但画画不会。画画对我来说是某种药,治愈了我。写作没有治疗作用,却是灵魂的拐棍儿,我得拄着,到死。”
诗人、文学评论家霍俊明先生论述“70后”诗人的境遇时说他们是尴尬的一代,这也可以用来评价“70后”作家。在阿丁看来:“‘70后作家有些已经很优秀了,只是被时代和所谓的主流文学圈不承认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已。什么时候把这一代作家前面的代际数字去掉,就正常了,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有人把余华、苏童称作‘60后作家?”
至于他个人表现,阿丁觉得已算不错,“匹配我所得,人得知足”。他不怕挖空自己,“作家又不是采矿的,怎么会是容易挖空自己的职业呢?写作者只要还是活着的,就会生有触角,你我所生活的时代,现实素材俯拾皆是,不需要灵感。好好加工就是了”。
同时,阿丁也不想把自己的文字加工成那種迎合商业的文学,甚至不愿把自己的短篇变成适合碎片化阅读的通俗主流,“有人喜欢浅短薄小的通俗文学,就有人喜欢深长厚重的严肃文学,并推崇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做文学的意义。”
阿丁
生于1972年,原名王谨。河北保定人。当过麻醉医师、记者。现在以写作、画画为业。著有历史随笔集《软体动物》、短篇小说集《寻欢者不知所终》、长篇小说《无尾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