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杂货”的金克木
2018-04-09许晓迪
许晓迪

金克木(1912年-2000年)
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季羡林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计划讲课,绝不拖堂;金克木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例行拖堂。他的一大绝活是吟唱梵文颂诗。及至1984年,第二届梵文巴利文班重开,两位老先生已不再授课,学生们只能在录音带中聆听金克木的“天竺之音”。当时的学生之一钱文忠回忆:“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垂头丧气,他们平日练习梵文发音,被周遭人嘲笑为夹杂着马、牛、狗叫的“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
比较季羡林和金克木,格外有趣。上世纪80年代,两位老先生都住在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右边是季宅,左边是金宅,就像他们的学术之路,紧密相连又截然不同。季羡林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正途出身,金克木走的则是一条羊肠小道。他只有小学文凭,20世纪30年代到北京求学,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他就在这里自学成才,学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有别于科班训练的杂食口味。上世纪40年代,金克木到印度求学3年。他的梵文是和一位婆罗门学的,“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太阳西下时,就与陆续到来的和尚、居士结伴奔走,大步流星。
此時的印度,正从殖民时代走向独立。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远离文献,走近了活生生的人与文化。“‘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终其一生,金克木都在那些多变、复杂的知识中穿梭,从无序、混沌中摸清文化的底牌。
晚年的金克木,杂食主义的趣味更甚以往。他公开拒绝“专家”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金克木与张中行、费孝通、钱锺书等成为第一批“拓荒者”,由此开启了人文学界的黄金十年。在这些老先生中,金克木是最高产的作者。《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回忆,“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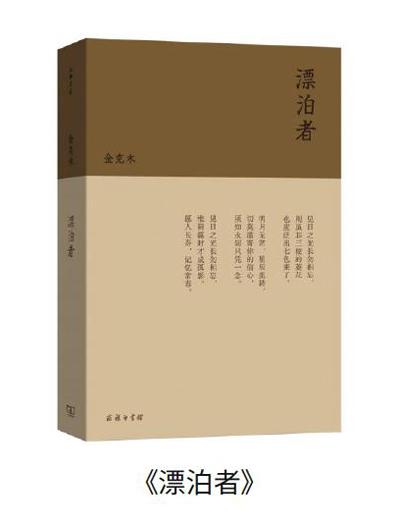
金克木的“杂货铺”里琳琅满目,有《十三经》《庄子》《文选》,也有张恨水、金庸、琼瑶;有弥尔顿、乔伊斯、普鲁斯特,也有围棋、天文、数学。除了这些“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杂学,他又花了数十万言来谈自己,尤其是成长时期的自己。这些文章如今收录在《漂泊者》中,各篇相互勾连,连缀出金克木孜孜以求的一生。这份坦诚自述,不是对岁月残渣的把玩、咀嚼,也不是依凭阅历和学识去炫耀伟业、抚摸伤痕、裁决历史,而是一个平凡人在时代潮汐中的自白:“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什么也说不上会”“于是以书生始,以书生终,其命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