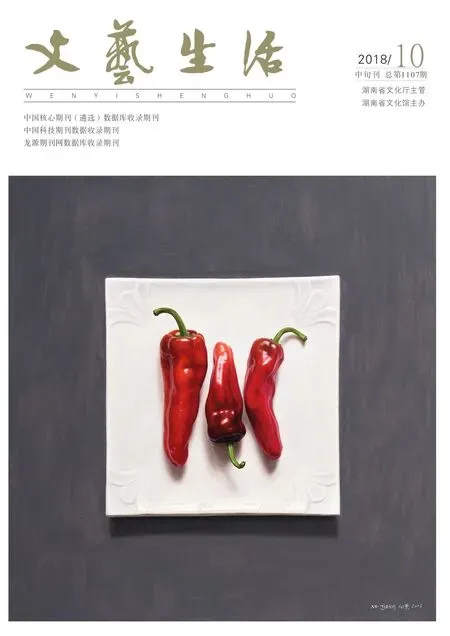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图书馆”研究
2018-04-08袁伟玲
袁伟玲
(浙江省诸暨市图书馆,浙江 诸暨 311800)
一、引言
文献所谓的“三坟”“五典”,是指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从这些文献的出现开始,就有了关于它们的收集保存活动,因而也就有了古老图书馆的管理业务。我国周代已有专门保存图书的机构“藏室”,并设有管理藏室的史官。老子可以视为我国最早的皇家图书馆负责人。《史记》载:“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
以两个广泛流传于诸暨民间并散见于典籍记载的神话故事“古代图书馆”为案例,通过整理和分析,论述了人们和神们对知识共享的强烈要求和实现方式,作为研究中国图书馆演变历史的先导性工作。
二、“宛委图书馆”及其对大禹实践的指导效应
“宛委图书馆”是越国建立之前的“图书馆”(或“藏书楼”),设立在虞夏时代的绍兴宛委山上,距今至少已有4000余年。当然,历史的久远难免会使这座初具雏形的远古“图书馆”蒙上一层神话的色彩,但我们从史籍记载的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强烈的古代文化灵光,依然能提取出不少有价值的有关古代“图书馆”雏形的信息。
东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在记述“大禹治水”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载:
禹“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在会稽县东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 瑑 其文’。……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古代“图书馆”的雏形。
众所周知,图书馆向有“三要素”之说,即馆舍、馆藏及馆员。馆舍者,藏书之所也。这所远在夏代的“图书馆”位于“东南天柱,号曰宛委”的“其岩之巅”,结构虽为原始,却也十分考究。它是一座“承以文玉,覆以磐石”的“石室”。“石室”就是当时最为高级的处所了。宛委山亦称玉笥山,其名自然亦与藏书有关。笥者,盛物之方形竹器也。其书藏于石室中的方形“玉笥”之内,可见古人对书籍的敬畏和神化。那部被称为《黄帝中经历》的“神书”,相传为“圣人所记”,“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瑑其文”。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以线贯穿的“简”,之所以用“金”“银”“玉”,均说明此简之贵重和稀有。这部书恐怕是这个夏代“图书馆”中唯一留下的让今人知其书名的“馆藏”了。而这里的“馆员”,无疑就是那位“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的人。当然要进该“馆”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借书手续”和“阅读规则”。先是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以接待前来预约的读者大禹(即文命);“非厥岁月,将告以期”,在确定具体日期后,才被允许进“馆”;阅读时,不得大声喧哗,不得作“无为戏吟”。
其次,需先“斋于黄帝岩岳之下”,择“三月庚子”吉日,登“宛委山”才能见到这部“金简之书”。大禹“案金简玉字”,经过认真阅读,积极探索,而终“得通水之理”,找到了治水的办法,明白了疏通江河的原理。这可以说是“文献资料服务于社会实践”的一条最早例证了。尽管《吴越春秋》没有记载《黄帝中经历》一书的具体内容,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其中必定有先人治水的经验总结。禹曰:“吾获覆釜之书,得以除天下之灾,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因此他始终没有忘记书籍给他带来的巨大作用。
这里的书籍被称为“金简”,意即金质简册,其实是古人对书籍的神化而已。有关“夏禹持简以平水土”的记载颇多。《越绝书》载:“禹至此者,亦有因矣,……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据《拾遗记》卷二载:伏羲“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并)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又如《尸子辑本》卷上载:“禹理水,观于河,……(河伯)授禹河图”。庾肩吾(487—553?)有《夏禹庙诗》云:“金简泥初发,龙门凿始通”。这些文章诗词虽然夹杂着经过渲染的古代神话,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古人对书籍的无比敬重。正因为大禹认识到书籍的重要性,他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越绝书》载:“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他“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清诸暨郭凤沼《青梅词》中“《山海经》传禹益时”句,所指即为此事。南宋著作家王应麟《困学纪闻》中说:“《山海经》,禹益所记,有……诸暨之名”。所惜古本《山海经》早佚,今已无从得见矣。
三、“天庭图书馆”及其对大禹实践的指导效应
沿着书籍的台阶不断地向上攀登,我们就会渐渐地走入“天堂”,因为“天堂”就是一座图书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斯(1899—1986年)曾经说过:“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中国的神话小说中,天堂上也“确实”是有着“图书馆”的;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玉帝管辖的天庭图书馆的负责人,可能还是诸暨人呢。下面我们不妨从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冯梦龙(1574—1646年)所著的《平妖传》说起。
《平妖传》是产生于明代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叙述神怪妖术为主,基本属于神魔小说。《平妖传》所写故事,其实是一幅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和生活的特征。这一点鲁迅(1881—1936年)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里已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事遍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夥”。
《平妖传》第一回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春秋周敬王时,吴越交争……南山有个处女,精通剑术,奉越王之命,聘请她为国师。那处女收拾下山,行到半途,逢着一个白发老人,自称袁公……(处女与袁公比试道术后,袁公)化为白猿而去。原来处女不是凡人,正是九天玄女化身,因吴王无道,玉帝遣玄女临凡,助越亡吴……越国成功(后),玄女带袁公上天,朝见了玉帝。玉帝见袁公好道,封为‘白云洞君’,教他掌管九天秘书。何为秘书?凡是人间所有之书,不论三教九流,天上无不具备,但这天上所有之书,人间耳未闻、目未见的,也不计其数,所以就总唤做‘秘书’,就金匮玉箧收藏。每年五月端午日,修文舍人来查点一次,此乃修文院之属官也。袁公虽然掌管,奉有天条禁约,等闲也不敢私自开发……(一天发现)一本小小册儿,面上题着三个字,叫作《如意册》,里面细开着道家一百零八样变化之法,三十六大变,应着天罡之数,七十二小变,应着地煞之数,端的有移天换斗之奇方,役鬼驱神的妙用”(《平妖传·第一回·授剑术处女下山,盗法书袁公归洞》。1980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本小册子被袁公偷偷地带回人间……
从这篇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玉帝也是有“天庭图书馆”的。“天庭图书馆”内藏书数量颇丰、门类齐全,不但“凡是人间所有之书,不论三教九流,天上无不具备”,而且还有不计其数的“人间耳未闻、目未见的”“天上所有之书”,这些图书都被收藏于“金匮玉箧”之中。“天庭图书馆”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天条禁约),“玉箧是天庭法宝,有三不开:无混元老祖法旨不开,无九天玄女娘娘法旨不开,无玉帝法旨不开”。即使像袁公这样掌管“图书”的人(九天秘书),“也不敢私自开发”。而且“每年五月端午日,修文舍人来查点一次”。可见玉帝对“天庭图书馆”的重视和对“图书”的敬畏。修文舍人“乃‘修文院’之属官也”。“图书”其实是知识的一种载体,各种知识都可在图书中得到体现,例如上段提到的《如意册》——小小册儿,“里面细开着道家一百零八样变化之法,三十六大变,应着天罡之数,七十二小变,应着地煞之数,端的有移天换斗之奇方,役鬼驱神的妙用”。“《如意册》乃九天秘法,不许泄漏人间”。说实在,这个“图书馆”当时也只是玉皇大帝的“私家藏书楼”而已。而袁公将那《如意册》上诸般“奇方”“妙用”、变化之法(知识),冒险带到人间,并整整齐齐地镌在白云洞两旁石壁上的做法,可说是体现了对知识共享的强烈要求。袁公说:“常闻说上帝无私,却不信有个‘秘’字;既说个‘秘’字,就不消留下文书;既留下文书,便是要留传万古。玉帝箧藏,我老袁石刻,同是一般意思”。袁公虽然犯了天条,但仍然说服了玉帝,最后“玉帝准奏,免其死罪,革去白云洞君之号,改为白猿神,着他看守白云洞石壁”(《平妖传·第二回·修文院斗主断狱,白云洞猿神布雾》)。
当然,神话只是一种美丽的民间传说,但通过神话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人们对知识共享的强烈渴望,而这个神话产生的源头或“流传中心”应该就在诸暨。清《光绪诸暨县志》记载了这一神话故事:
“牌头市,市旁斗子岩……上有龙王殿……三刘庙。庙左有白云庵,俗传有白鲎仙人掌雾于此。……王昙(1760—1817年,秀水人)《斗子岩暴雷澍雨纪事诗有序》:‘山有石门,土人谓猿公白姓者居此。误入者见眷属往来,洞房窈窕,有女子倚绣床。亦时摄人间好女入洞云。……处女白猿公,团 圞 一洞中;霓裳奔月冷,雷斧骇人红……’。
许瑶光(1817-1881年),善化人,其《白鲎仙人咏》:‘诸暨城南斗岩与天通,上有为云为雾之金龙;自言旧是白鲎老仙翁,前明洪武助战功。……人言诸暨本越地,铸刀疑出若耶铜。连宵宝气射斗牛,白鲎之刀应与白猿之剑同’”。
两书如出一辙,看来这个“多年修道的通臂白猿”袁公已流寓诸暨,成为名副其实的诸暨人了。所以才有玉皇大帝图书馆的负责人可能还是诸暨人的说法。《平妖传》中的这位“九天玄女”,不但帮助越国训练了一支军队,而且还向“天庭图书馆”推荐了一位图书管理员呢。
四、结语
陈桥驿(1923-2015年)先生在《吴越文化论丛·“越为禹后说”溯源》中说:“尽管这类传说……从事实上来说都是无稽的,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中,仍然不无价值。……历史上所有关于民族关系的传说,不管是信而有征的,或是荒诞不经的,在经过整理和分析以后,它们都将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宝贵财富”。这段对民族史研究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对图书馆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对“宛委图书馆”和“玉帝图书馆”的研究,虽然是无稽的,不是信而有征的,但对我们了解古代人们对知识共享的愿望和要求,以及指导今人熟悉图书馆史、正视图书馆功效和管理,应该有其宝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