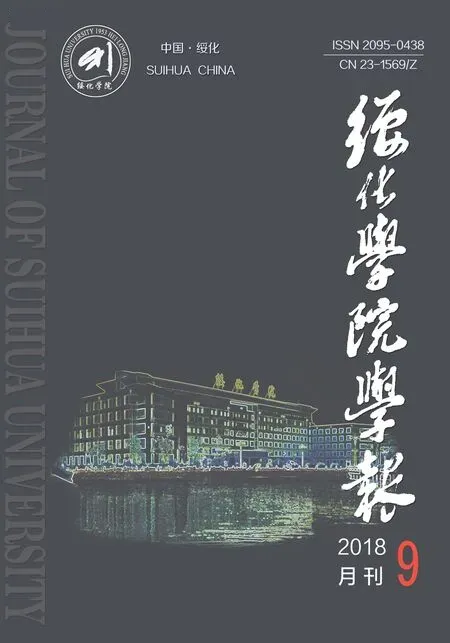梁启超与钱穆的历史人物研究观比较
2018-04-04孙鹏程
孙鹏程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将二者及《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合并出版,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则在1960年代于香港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在1980年代台北再版时又增加《略论治史方法》和《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两文。二人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们在各自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都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各自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
本文将以二者的历史人物研究为切入口,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中心,分别从历史人物的分类标准、历史人物研究的侧重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对梁启超与钱穆二人的历史人物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走进两位大师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世界。
一、历史人物的分类标准:“事功表现”与“心性道德”
关于历史人物,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做过这样的解释:“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1](P95)“所谓历史人物,则必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更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2](P98)
梁启超与钱穆二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首先解决的就是历史人物的分类问题。只有将历史人物进行合理地归类,在历史人物研究时才能更好地加以分析、比对。虽然关于历史人物的分类标准梁启超与钱穆想法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所把握的主要分类标准却是不一样的,这也造成了他们历史人物研究角度的不同,史学方法论思想的差别。
(一)梁启超对“事功表现”的重视。“人的专史,是专以人物作本位所编的专史,大概可分为五种形式:(一)列传、(二)年谱、(三)专传、(四)合传、(五)人表。”梁启超在《人的专史》中,就开门见山,把人的专史分成这五种形式。[2](P154)一定程度上来讲,梁启超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是相对正统的,很接近我国正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特点是重视历史人物的事功表现。紧接着《人的专史》,梁启超在《人的专史的对相》中就以“专传”“人表”为例子,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可以配做专传,什么样的人要归入人表之中。
历史研究者如果看重历史人物的事功表现,往往就会忽略了个人心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而先哲苏格拉底一直强调的“认识你自己”也有认识心性修养的含义。可见对心性修养的清楚认识,对于了解人物的人格精神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而梁启超对事功表现的强调,对心性修养的忽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研究的缺憾。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正是这样一种分类标准下的历史人物划分,对人物的时代影响力比较重视,对人物的叙述也更为清晰,更为强调历史人物身上发生的事件,也就能够让我们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各个细节了解得比较详细,更容易地了解到人物的生平细节,也更接近历史人物生活上真实的一面。
(二)钱穆对“心性道德”的推崇。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积极的活动、并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他也对历史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历史人物的高下、优劣得失的标准,一是人格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钱穆又认为首要和根本的标准是心性道德。
钱穆对历史人物的五种分法如下:第一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上的人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第三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第四种分法,是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关于第一类,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莫过于春秋战国时代,然而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一大批思想家都生于这个时代。汉代中国大一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汉代的思想家显然不如春秋战国时代繁盛。虽然孔孟他们当时个人的影响并没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德,丰富的思想而为后人所一直铭记、践行。第二类,成功得志的人物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所谓“得志者”是指在当时事业或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者,“不得志者”是指登不上历史舞台或登上了而事业最终失败者。[1](P99)钱穆认为:“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1](P100)这些历史人物往往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如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他们虽然未能改变宋朝灭亡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凭借个人美好的心性道德而流芳百世。第三类,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历史上的颜渊虽然是一个没有什么表现的人物,但是孔子却一直称颂颜渊,足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无表现的一面。由上可见,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心性道德而非事功表现。那些处于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均没有在事功上有突出和伟大表现,钱穆却十分看重他们,称他们在历史上有大表现。在他看来,他们的表现与价值即在其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并能够影响后世。
钱穆认为历史上的人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他们,然而他们却真实地活在历史中,他们的生命也将在历史里一直延续。但是,这里说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钱穆在书中说,《左传》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钱穆认为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道德重于事功,归根结底,还是道德第一。
而对于第三、第四、第五这三种分类,我们仅仅只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钱穆分类标准的倾向,那就是看重历史人物的心性道德,而不是依靠历史人物的事功表现。
纵观钱穆对历史人物的分类,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标准,政治事功仅是第二位的。而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也正如钱穆所提到的那样“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
二、历史人物研究的偏重:“巨细无遗”与“个人意志”
在分类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对这些已经分类好的历史人物该怎样去研究,是考虑自身外在的一切条件?还是从历史人物内在条件,即个人意志着手?这些都是一名史学家所要考虑到的问题,而研究侧重的不同,归根究底实际上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一)梁启超主张“巨细无遗”。历史人物研究有没有偏重?梁启超的看法是没有偏重,对待历史人物研究就要巨细无遗。在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年谱一类中,梁启超就认为:“年谱叙述一生事迹,完全按照发生前后,一年一年的写下去,不可有丝毫的改动。这种题材,其好处就在将生平时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4]可以说此时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全面研究,从而可以全方位地对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得不说,这是梁启超先进的地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提到:“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 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2](P147)所以,根据梁启超的这段话看来,在梁启超的研究方法中,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应与人物自身以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即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是要做到全面研究,巨细无遗。
然而,对历史人物巨细无遗的研究,却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细”的层面上。“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和环境变化。”[2](P147)在梁启超看来,研究历史人物,还要将历史人物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将当时的相关事件归入相关历史人物的身上,这是比较合理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加丰满的历史人物的形象。我们必须承认,也正是这种全面的研究,固然能很好地突出人物形象或者为我们揭露恶人的面孔。但是,因为巨细无遗,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记录到,却也有可能造成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历史人物研究的误差,这不得不让我们承认是一个研究的弊端。
(二)钱穆看重“个人意志”。无论是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的环境,还是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大大小小得、琐碎的事情,都可以说是外在条件。而在钱穆看来:“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个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与‘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身外,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1](P112)钱穆能有此看法,可以说是与自身经历有关的。徐国利教授在其著作《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指出:“钱穆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心性合一的历史本体思想, 既指出了历史文化本源上的自然性和发展中的客观实在性,历史文化的形成并非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又强调了历史文化在本质上的超越性,即人文性和道德性,历史文化只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是客观实在与主体精神的合一即,天人合一”[5]可以说,钱穆对个人意志的强调是与自身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是分不开的。
钱穆认为,历史人物的造就一方面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历史人物自身不断努力的结果。这就要求人发挥自己的内在条件,以使自己成为一历史人物。所以钱穆才会强调人的内心意志,强调这种个人可控的东西。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钱穆本身所接受的是浓厚的传统文化教育,尤其受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影响。因此,在研究历史人物时,钱穆更倾向于“个人意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钱穆研究历史人物时,强调人物内在的人格意志。与梁启超相比,有较大的不同。虽然钱穆的这种观点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钱穆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对”个人意志”的强调,的确也能够对传统历史人物研究的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
三、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英雄时势”与“英雄造时势”
观察他们有关历史人物的解释与阐释,我们不难发现。谈到历史人物时,都会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就是能够推动历史发展,影响历史进程的才能称得上是历史人物,即“英雄造时势”。但是,梁启超却在此之外也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倘使换了一个环境,成就自然不同。”[2](P200)在梁启超的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是“时势造英雄”的了。那么,之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英雄与时势之间的关系,梁启超与钱穆似乎有了一个大体上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逐一分析。
(一)梁启超在“英雄时势”中的纠结。首先,强调一下,这里的“英雄时势”与“英雄造时势”是完全不一样的。“英雄时势”是两个并列名词短语,所以“英雄时势”就有好几种可能:英雄造时势,英雄造于时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趋于中和的,梁启超恰恰就持有这样三种看法。
首先,对于英雄人物及其重大作用,梁启超有过很明确的阐述:“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6](P354)在梁启超看来,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英雄史,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时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启超在众多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杰出的英雄人物占据了相当重的分量,如《管子传》《李鸿章传》等。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到底反映了梁启超“英雄造时势”的观点。
但是,恰恰也就是这位提出“英雄造时势”的大学者,后来又有了与“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看法,即“时势造英雄”的观点。梁启超提出:“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2](P46)可以说,在这一看法中,梁启超强调了历史人物的研究在史料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对人物的记叙中, 从而了解此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这在一程度上足以表明梁启超持有“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当下,就有学者明确指出“强调时代、地点、条件等因素对人物的思想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时势造英雄”的观点。”
从以上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有关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英雄与时势之间关系的看法充满了矛盾。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史学观点。但是梁启超先后认同了这两种观点,最后,梁启超更是提出了一个中庸的观点。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长短,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能够把二者兼收并蓄,更加可以全面地、正确地解释历史的成因。就如同他所说:“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6](P341)
综上,我们发现虽然对待“英雄与时势”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持有的观点可以算做三种,而这三种观点实际上也都是对立的,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这是与时代巨变,社会形式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是梁启超祈求找到研究历史人物根本的解决方法时所作出的变通的举动。虽然,每一种观点都有其缺憾,但是却也都有其在当时的合理性。
(二)钱穆对“英雄造时势”的执着。和梁启超多变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钱穆则一直坚持“英雄造时势”的看法,即历史上少数人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谈到:“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 这是决然可知的。”[1](P90-91)而在《中华文化十二讲》中也提到:“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7]这都可以看作是钱穆对历史上少数人,即历史上的英雄推动历史发展、引领时代走向的一种强调,基本上钱穆对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历史观点就是传统上的英雄史观。在钱穆的观点看来,真正的历史人物,不仅仅只是在当今时代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推动历史发展;而且在他们死后,他们依然对历史的发展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并且作用发挥的越大,他们的形象也就越大。这种更深一步的见地实际上就更能反映钱穆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钱穆自然也发现了“英雄造时势”观点的缺憾之处,但是钱穆还是一直坚持“英雄造时势”的观点,这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具有相当的关系。在当时,中国社会上,尤其是在文化思想上一直被“全盘西化”的观念所笼罩,而钱穆又主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能够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中保留一点传统文化的生机,就坚持“英雄造时势”的传统英雄史观。虽然这种观念让钱穆陷于传统史观而难以抽身,也造成钱穆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研究的片面。但是不得不说,钱穆这种不为社会大潮流所裹挟,勇于坚守自我的治史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铭记与学习的。
四、结语
对于历史人物研究,梁启超和钱穆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各有缺憾,但也各有千秋。对于历史人物的分类标准,梁启超注重事功表现,而钱穆虽然把心性道德作为根本标准,但是也看到了事功表现的意义;对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偏重,梁启超主张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要做到巨细无遗,大事小事兼顾,钱穆则强调个人意志的重要性,而梁启超强调事无巨细,其中也就有了对个人意志的考虑;至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梁启超不断否定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其思想不断成熟、不断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扬弃的过程,钱穆坚定地认为是“英雄造时势”,虽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观点充满了矛盾性,但是钱穆的想法却是包含在梁启超的思想之中的,这就又不得不说是者二人不一样,但又有相通的地方。
梁启超与钱穆作为史学的大家,本身其史学思想以及史学方法论就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这就需要我们一代代不断地去发现,去挖掘。本文以历史人物为一个切入口,就是希望能够从一个小的突破口出发,探究二位史学大师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也希望对于两位史学大师,我们每一代人都能够从他们身上汲取治史的智慧,学习研究历史地方法,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