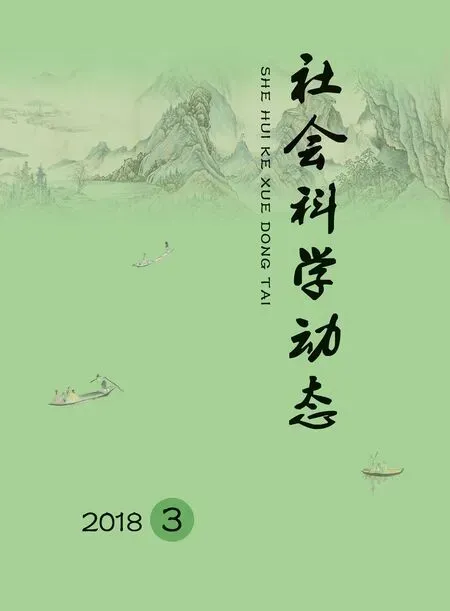文化体制变革的文化史探究
——读《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2018-04-03冯天瑜
冯天瑜
一般来说,政治事关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来源和使用,文化则为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提供解释框架和符号化的大众传播渠道。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与政治难以截然分开。《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傅才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一书,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轨迹放到近代社会基础结构和政治格局双重变奏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借助于“国家文化体制”的解释框架,描绘了近代政治精英集团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现代化旗帜的号召力,完成文化的符号化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展示出国家(政党)力量如何在“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下,通过重建社会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实现社会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国家化过程的恢宏画卷,这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把握方式。
一、公共文化领域的出现:近代社会动员方式的转换
近代中国,政党既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又是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民国时期的政治模式,历经多党竞争模式、国民党执政模式、国共两党竞争并存模式的复杂政治结构演变。清末民初精英阶层从“以欧(美)为师”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转向,对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形成和演进轨迹具有深远影响,形成了近代中国欧美价值系统、苏联价值系统和中华传统价值系统三者并存、相互影响的现代化道路。在政党政治发展及其模式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打断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自然进程,加深了1840年以来不断积聚的民族危机意识,造就了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社会变迁使得文化与政治、军事、社会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该书作者从这些复杂的变动关系中归纳出“文化体制”、“公共文化领域”和“文化领导权”等核心论题,试图建构对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及文化现代转型实践的解释模型,具有锐利的学术眼光。
作者运用公共文化领域的概念,将近代中国文化领域发展变化的特征与前近代的特征区别开来。前近代的革命或者社会政治运动,大多借助“神话或者符号”的制造和传播,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事要靠“鱼书”,元末红巾军起事要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革命或者政治运动的每一步均与某种“神话话语”或传说符号相关联。进入近代,革命或者政治运动业已转到靠政治精英集团组织的文化阵地和“意识形态话语”。如清季以《民报》为基地的革命派和以《新民丛报》为基地的维新派之间关于革命与立宪的论争;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学术论战,都对社会革命和政治动员形成深刻影响。这一社会动员方式的改变,与近代中国报馆、学校、剧场和文化组织等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由近代都市教育机构、文化场馆和文化组织为主组成的公共文化领域,提供了一个前近代传统农耕社会结构中不曾有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机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信息集成和信息传播中心,这也为政治精英集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动员民众,提供了新的价值整合和力量聚合基础。
二、“共同价值整合”: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
文化体制本质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理念上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结构化了的文化力量。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说:“力量问题的解决……包括通过制度化规范的合法性、行动的共同的最终目的和宗教仪式,以及各种形式表现出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所反映的个体整合事实这一共同参照系。所有这些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共同价值整合’的社会行动体系性质的一种表现。”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从1911年到1949年,在“以党建国”的目标下,国共两党逐步认识到社会文化动员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重要价值,并相继建立文化动员体系。由于文化与政治是一种相互关联、相互协同的系统架构,由文化体制所维系的意识形态整合力与政党体制相结合,助推近代中国政党发展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领导力量。这种文化体制结构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一体制所具有的文化整合能力,其自身也成为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力量。如约瑟夫·R·斯特雷耶所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是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并且相信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国家居民对国家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和对效忠国家的自觉认同。”
作者并未将文化体制看成一个由话语、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支撑起来的固定制度结构,而是将其形成和演进过程放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加以考察,体现出文化制度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同构。
三、追溯本末:为今之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书中考证,现代中国实施文化公有制,并非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早在1927年,民国政府就在汉口民众乐园进行公有制试验。作者提出,民国初年文化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正是近代中国从中古社会折向近代社会的标志。民初的中国社会进到一个“继承与开新”的十字路口。随着民国中期后国内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和日本全面侵华,文化转型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从民初开始的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折向文化专制的故道,导致“转型断裂”。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大潮下,知识阶层选择“集体沉默”,使近代中国失去一次文化转向现代性治理的历史机会。
得益于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傅斯年,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家融会中西文明的伟大贡献,自晚清民初开启的模仿西方社会的政治议程和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借鉴“范式”,业已奠定民国社会的大众话语、媒体框架和流行思潮,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议程设置”,并渗透于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里层结构。与此相对应,国家文化体制的表层结构的形态,则要受制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轨迹,包括政府组织的强弱,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弱,政党数量、发展程度和博弈结构,立法、司法能力与独立性等。对国家文化体制的里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论述简略,为其缺憾,从而也留下进一步研讨的空间。
百余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研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通过对历史发展进步的规律,即所谓“公理公例”的阐述,以启迪来者。才武教授的这部书符合这一旨趣,其对文化体制的“追溯本末,考镜源流”,应该能为今之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正可在旧邦新命的历史接续中,凝练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内涵,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