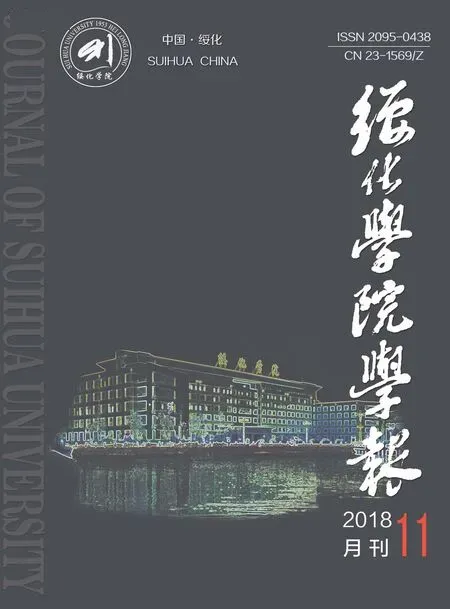从三重空间看《达洛卫夫人》中的空间政治观
2018-04-03黄佳丽
王 欣 黄佳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20世纪的“空间转向”掀起了一股广泛的,跨学科的“空间浪潮”,以列斐弗尔、福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理论学家对空间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空间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物质存在,而是一切权利运作的基础,是一种复杂的生产形式。“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1](P31)空间是由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因而空间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某种政治性。正因为空间具有生产性、政治性,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各种生活空间也应该被看作蕴含丰富文化意义的场域,而不是单纯的叙事背景。文学通过创造性的叙事手段,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丰富的意义和内涵,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其对社会现实的敏感性和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边缘位置,觉察到了空间生产所具有的政治隐喻,并将其渗透到文学创作中。本文基于空间理论,分别从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他者空间三个维度深入探讨《达洛卫夫人》中所体现的空间政治,揭示空间生产背后所隐匿的性别、阶级和民族层面的冲突,以及家庭空间中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地位、社会空间中暴露的阶级矛盾和他者空间中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歧视和压迫。
一、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家庭空间中的性别空间政治
亨利·列斐弗尔指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2](P48)家庭空间中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反映了父权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该空间中,女性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狭小的家庭空间成为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广阔的外部世界则与她们无关,而男性却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外部世界由他们来支配。父权制社会中性别空间政治是伍尔夫在创作中始终关注的主题,这种性别空间的意识形态使得女性的劳动被合法化地剥削,女性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达洛卫夫人》中的主人公克拉丽莎恪守着家庭空间中这样一种从属的边缘地位。年轻时,她放弃了情投意合的恋人彼得,恪守社会规则,嫁给了身份地位更高一筹的议员理查德·达洛卫,成为了高贵的达洛卫夫人。在她的意识里,女性依附于男性,女性地位的高低是由男性赋予的,所以她只能选择世俗,而放弃自己的爱情。克拉丽莎把自己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和爱情的渴望封闭起来,很快成为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对丈夫百依百顺,即便是要求她“午饭后安安静静地躺一会”[3](P107)她也会乖乖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本不愿请埃利·亨德森出席她的宴会,只因达洛卫先生一句“可怜的埃利·亨德森”[3](P107)她便立即邀请亨德森出席她的宴会。她不懂政治,不会思考,写作,“至今都不知道赤道是什么东西”[3](P110),对她来说为丈夫设宴,款待宾客就是她全部生活的意义。她格外关注宴会的成功与否,无论是窗帘的布置还是客人的交流气氛,她都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差池,因为宴会的成功程度代表着男性衡量女性能力大小的标准,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和地位并彰显自己的价值,她还是不得不出门去买花,筹备这一切,尽管在她的内心深处对宴会感到十分厌倦。
因此,从家庭空间政治的角度看,男性才是传统家庭的实权派,而女性则处于微不足道的边缘地位,她们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规规矩矩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像达洛卫夫人这样的女性角色数不胜数,她们的身份无法得到应有的认同,她们的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对男性奉献的程度上,她们作为一面镜子的存在,映射出男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中心地位。
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社会空间中的阶级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来源于列斐弗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空间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P62)是国家即支配权利“用来均质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工具”。[2](P53)马克思也指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4](P2)因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利关系都镶嵌到了一定的社会空间里,阶级空间政治也随之产生。在传统的文学评论中,伍尔夫的创作似乎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政治毫无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伍尔夫对社会的关注并不限于女性主义的角度,她还关注比男权社会和性别歧视更为广泛的问题,尤其是关于阶级空间的政治问题。在几乎每部作品中,伍尔夫都着力于凸显某一社会空间中的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价值观和秩序观,展现阶级差别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
在《达洛卫夫人》这部作品中的一个街头场景便能窥探社会群体中的阶级空间政治。邦德街上的一辆轿车突然发生爆炸,轿车里的人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然而顷刻之间,谣言便从邦德街中央无声无形地向两边传开”,[3](P13)人们的表情变得庄严肃穆,对那辆神秘的轿车肃然起敬,纷纷投去敬畏的目光,“可是此刻,神秘的羽翼紧紧地蒙着绷带,嘴巴张大着。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看到的是谁的面孔。”[3](P13)大家都在根据自己的想象揣测着,“是威尔士王子?是王后?还是首相?谁也说不上。”[3](P13)埃德加故作幽默地说到“所相(首相)的汽擦(汽车)。”[3](P13)直到那辆神秘莫测的轿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它仍然牵动街道两旁的人们的心,这些人既好奇有感到无比荣耀,而现实是“这些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君主、国家的象征只有咫尺之距。”[3](P15)这样一个戏剧化的荒诞场景显露出英国的阶级分化,尽管民众对乘车一族人的身份未知,但却莫名地集体生发出敬畏,因为“车子”代表着高贵、权威和地位,它于无形之中将社会空间中的具有不同身份不同认知的个体统一起来。这是英国普通民众对统治阶级的盲目崇拜,对权威的绝对遵从,是一种内心认知的理想化状态,这种体验和感受类似于列斐弗尔所说的对空间物质性的崇拜。然而现实是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离统治阶级千里之遥,但这种阶级的分化却并没有因此减退,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中,阶级秩序已然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和统一。他们怀着无尚的憧憬,渴望挤进更高一层的阶级空间,但是那层神秘的屏障——轿车的窗帘却将他们隔离开来。在这一空间中,统治阶级利用一种欺骗性的、幻想性的空间使普通民众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他们才是这一社会空间的生产者,掩盖了社会空间中的不平等关系。
三、繁荣与衰落的转变——他者空间中的民族空间政治
所谓“他者空间”是米歇尔·福柯在1986年的《论他者空间》一文中所提出的概念。福柯认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在本质上是异质的空间,我们不是生活在某种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整套勾画地点的关系之中。”[5](P65)他将这些空间分成乌托邦和异托邦这两类,详细阐述了异托邦的六种特征,并把殖民地描述为具有第六种特征的异托邦。在他看来,殖民地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具有他者性的空间。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暗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伍尔夫看来,“正是这种排他性,在内部与外部之间竖起了物理上和精神上的屏障,形成了‘自我’是文明的、先进的、优越的,而‘他者’是低级的、无知的、落后的这样一种认知模式,同时使得西方对殖民地的征服和排斥合理化、合法化。”[6](P119)要了解殖民地作为他者空间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必须进一步揭开伍尔夫作品中的殖民地空间面纱,挖掘他者空间中的民族空间政治,揭示大英帝国的繁荣对英国民族身份认知的主导作用以及帝国的衰落所引发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
从表面上看,伍尔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女性作家,在谈及民族政治,伍尔夫似乎不应该被列入研究对象。然而伍尔夫见证了大英帝国的兴衰荣辱,她在大英帝国繁盛时期出生,于衰败没落之时辞世,其作品中自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民族情绪。正如博埃默所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也可谓是帝国主义的态度与反殖民主义情绪并存。”[7](P160)《达洛卫夫人》一开篇克拉丽莎的旧情人彼得·沃尔什便把视线拉向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作为一个殖民地空间,印度这个场景的出现每次都会唤起不愉快的情绪及强烈的征服感。在英国人的概念中,大英帝国代表着世界的中心,支配着整个世界,“哈利街上的时钟,在一点点地咬啮着这个六月天,把它切成条,削成片,分了再分,钟声在劝人顺从、维护权威、并齐声指出均衡感的无比优越。”[3](P92)在帝国主义的空间背景下,伦敦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空间,始终是荒蛮、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是被殖民、被支配、被教化的对象,与之相关的人也被认为是愚昧的、粗俗的。当克拉丽莎得知彼得和他在去船上认识的一名印度女性结了婚,她想“那些印度女人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愚蠢、漂亮、轻浮的傻瓜。”[3](P7)彼得·沃尔什,作为一个殖民管理者,也因为他的身份而被边缘化,就连倾心他的克拉丽莎也难以掩饰这种情绪。因为他与印度的联系,他在克拉丽莎班级的眼中蒙上了阴影,被认为是彻底的失败者。
虽然他者空间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并没有失去存在感,也不总是沉默不语,相反,它于无形之中也在影响着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当帝国主义的统治“被当做传播文明的使命时,统治者社会的经验已经无可选择地依赖于殖民地和当地人了。”[8](P12)从克拉丽莎家里出来,走在大街上的彼得合着大本钟自言自语,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幸运者,“此刻他的身影正映现在维多利亚街一家汽车制造商的厚玻璃上。他的身后展现的是整个印度;平原、高山;霍乱流行;面积有两个爱尔兰之大的一个地区。”[3](P43)作为从他者空间返回帝国中心的文明人,他具有了一种能从边缘视审视中心的视角,他的言行和思想与当时英国的主流话语显得格格不入,并产生一种冲击,他重返伦敦,但是却尾随着深深的孤独和无奈,他的那些同胞们“凭着他们的权利,正聚集在东方俱乐部内,暴躁地谈论世风日下,道德沦亡。”[3](P152)他虽钟爱克拉丽莎,但却对她的宴会和贵妇人作风始终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他觉得现在的妻子黛西,“黑里俏”妩媚动人,“比克拉丽莎自然多了,没有神经质的激动,毫无麻烦,既不疙瘩,也不烦躁。”[3](P147)这种意识的转变,暗示着大英帝国的骄傲姿态在慢慢瓦解,其内部意识的分化和渗透,因为殖民关系总是矛盾的,生成自己毁灭的种子。伍尔夫通过对处于他者空间中“自我”人物的认知转变,批判了帝国权力阶级的傲慢、腐朽和伪善。对从外部环境看,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殖民帝国结构的瓦解以及一战的爆发,大英帝国也确实是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由此可见,伍尔夫对英国衰落的命运呈现出深深的忧思。
结语
显然伍尔夫并不是一个只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天马行空,耽于幻想,心理受到创伤借写作宣泄情绪的小妇人,她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她从固有的思维中超脱出来,通过独特的创作风格,把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场景提升到更为广阔的高度,体现的是她对家庭、对社会、对民族的政治意识和思考;揭示的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与边缘地位中显露出的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身份对立,是社会生活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阶级矛盾,是他者空间中映射出的大英帝国繁荣与衰落的民族情节;表达的是对女性、对普通民众、对殖民地人民等弱势群体的同情和诉求以及对英国由盛转衰的命运忧思。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背后深沉和宏大的政治关怀使伍尔夫的作品成为融进英国历史文化血脉的一部分,她所具有的时代艺术魅力和文化品格,深深地吸引并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因此,深入研究伍尔夫作品中所体现的空间政治对于揭示现代主义文学空间所具有的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将产生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