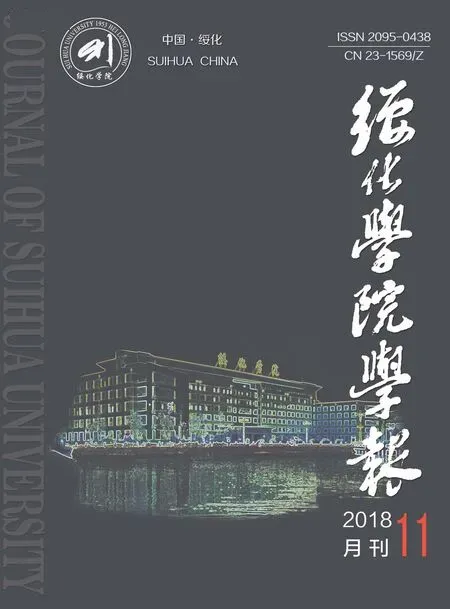略论中国古代嘲谑文学的流变
2018-04-03杨芃
杨 芃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100)
一、先秦时期:谐而不虐,寓庄于谐
我国最早关于嘲谑文学的记载,源于《诗经》。在此之前的文字记载,多为对重大事件的简单记录或求神问卜,绝少有调笑戏谑性的文字。由此可见,当时的上层社会是几乎没有嘲谑可言的,而在《诗经·国风》中则有许多作品具有诙谐幽默的风格。《卫风·淇奥》中以“宽兮绰兮,骑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来形容胸怀宽广,善于说笑,举止得体的君子才是惹人喜爱的;《邶风·终风》有“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描写青年男女见面后相互嬉闹的景象;《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更是记录了男女相谑,互赠芍药的情景。从中可知,在当时的人际交往中,打趣和玩笑已十分普遍,即便玩笑中附带一些嘲弄之意,也不失为一种对情趣的追求。《诗经》中的某些作品,还详细描写了这种调笑戏谑的情景。以《豳风·狼跋》为例,闻一多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公孙的妻子,意在嘲弄丈夫身袍宽大,体态臃肿,行动不便。他表示,诗人对于公孙的态度是“一种善意的调弄。”[1]这种无伤大雅的调侃与逗趣,将“谐而不虐”的风格发挥到极致,打造轻松欢乐的整体氛围。
不仅如此,“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后,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其中也不乏嘲谑性的文字:《论语》中既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教,也有“老而不死是为贼”之骂,前者严肃正理,后者不失诙谐;《孟子·公孙丑上》中有“揠苗助长”的可笑者,《滕文公下》有明知偷盗非君子所为却还要“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的攘鸡者;《荀子·非相》把儒家先贤的相貌写得千奇百怪堪称小丑,而将桀纣之君的仪容说得高大威猛玉树临风,令人啼笑皆非;《韩非子》中有人守株待兔,有人买椟还珠,尽显嘲弄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虽带有荒谬嘲讽之意,但最终都服务于诸子各自的思想态度和政治主张。孔子对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责骂建立在“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论语·宪问》)的基础上,可见孔子对“礼”的重视,与其积极有为的处世态度;孟子则是以“揠苗助长”说明“养气”须得循序渐进,用“攘邻鸡者”说明“去关税之征”不可拖拖拉拉;荀子通过圣贤丑貌而昏君俊颜的对比证明了“论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荀子·非相》)的道理;而法家作为战国后起之秀,提倡改革,谋求功利,所以韩非用守株待兔、买椟还珠来嘲笑刻板守旧、舍本逐末之人。很显然,这些思想家本无意专门嘲笑他人,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以一种“寓庄于谐”的方法更快地求得他人的认可和君主的任用。
除此之外,嘲谑性的语言还时常见于外交场合。晏子出使楚国,面对楚王的嘲讽,他用委婉玩笑的方式成功自卫,巧妙回击,既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齐国的国格,又不会伤了双方和气,阻碍两国交往。又有战国时秦宣太后公然对外交使臣讲黄段子:“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战国策·韩策》)意思是帮助韩国代价太大而好处太少,不是一笔好买卖。床帏之事本是夫妻私事,以房事喻国事,也是典型的寓庄于谐。不难看出,先秦时期的嘲谑文学除了调笑戏谑外,更加具有思想性与政治性。
另外,将调笑、戏谑作为本职工作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专门负责取悦统治者的俳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群以滑稽调笑为本职工作的人,却往往以“戏言”的方式实现了对现实的考察和干预,形成了意义深远、备受好评的“优谏”传统。当然,俳优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但其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对后世嘲谑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影响深远。
二、两汉时期:表达自我,追求娱乐
与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的嘲谑文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在戏谑、游戏的笔调中加入了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自我命运的反思,其二是对娱乐特性的自觉追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2]在这种大环境下,“士”的地位相比之前有所下降。他们不再需要滔滔雄辩,不再可能“为帝王师”,而只能做建言献策的参与者,或是吟诗作赋的调剂品。汉武帝时期以滑稽闻名的文臣并不少,东方朔更有“滑稽之雄”的称号。而在东方朔的文章里,除了机智调侃式的滑稽之语,更可以看到他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和尴尬处境的自嘲。
一方面,他在《上书自荐》中写道:“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责,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3]自认为是高大英俊无所不通的完美人才。这种大肆渲染极尽夸张的自我吹捧近乎戏言,让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他又因不被重用而写了《答客难》。在这篇以“怀才不遇”为主题的作品里,很难见到作者对社会的不满与鞭挞,反而对当今社会给予高度赞美:正是由于当今社会君主圣明,国泰民安,和春秋礼崩乐坏战国诸侯争霸不同,即使是苏秦、张仪、乐毅、李斯之流在今天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自己好歹官至侍郎,而这些名臣在今天可能还不如自己呢这种先自夸再自嘲后自慰,既满腹牢骚又歌功颂德的写法,本身便充满了调侃幽默的意味,其中更有在时移世易的环境下对“士”阶层处境和出路的思考。与此相似的是扬雄的《解嘲》,同样是以滑稽谐谑的笔调发泄心中牢骚,刘勰曾评价扬雄此文:“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4]在《逐贫赋》中,扬雄借乞儿之口与“贫”交流,描写了由“贫”带来的种种困扰和“贫”具有的种种好处,通过从“逐贫”到“留贫”的态度转变,表达了自己甘于清贫自守的价值选择,于诙谐谈笑中完成对自我的反思。
除此之外,汉代嘲谑文学也有对娱乐的自觉追求。《汉书·东方朔传》中,就记述了东方朔和郭舍人打谜互嘲的过程,其目的就是取悦皇帝,争取宠幸;[3](P2844)王褒《僮约》写自己与仆人的争执表现出一种脱离政治远离宫廷的生活化调弄。东汉时期儒学的神圣化和谶纬之说的盛行,一度使嘲谑文学归于沉寂。直到汉末时由于儒学礼教的松弛和统治者的娱乐需求,使得嘲戏之风又起,出现了一批篇幅短小的嘲戏形貌的作品,如戴良《失父零丁》、蔡邕《短人赋》等,都是拿别人容貌玩笑取乐的作品,这类作品没有什么深刻价值,但带有明显的游戏娱乐倾向。
三、魏晋时期:摆脱束缚,迂回反抗
《文心雕龙·谐隐》有言:“魏晋滑稽,盛相驱扇。”[4](P89)可见魏晋时期嘲戏之风大炽。此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笑话集《笑林》,《文心雕龙·谐隐》更是第一次对谐谑性的文字做出了理论总结。魏晋南北朝时依然存在大量篇幅短小的“嘲人赋”:如刘思真《丑妇赋》专门嘲笑女子貌丑;朱彦时《黑儿赋》嘲弄别人皮肤黝黑……这些作品与东汉《失父零丁》、《短人赋》等如出一辙。但是,魏晋时期的嘲谑文学又不单单是上一时期的简单复制,它有其自己的特点,即摆脱束缚,迂回反抗。魏晋文人的一言一行往往流露出一种“摆脱束缚,保持我素”的态度,即使在嘲谑时也不例外。这一点在《世说新语》里有明确体现: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5]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5](P494)
元帝喜得贵子,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9](P486)
从以上几则记载中不难发现,魏晋时期的人们早就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原则,妻子可以揶揄丈夫基因不好;孩子可以对长辈反唇相讥;甚至皇帝也会拿自己的子嗣与臣子开玩笑可谓毫不避讳,随性言语。曹丕与大臣之间的往来书信也不乏笑语,如《借取郭落带嘲刘祯书》和刘祯《答魏太子曹丕借郭落带书》完全以嘲戏为之,没有一般的君臣对话那样等级分明。甚至对可能改变天下局势的军政大事,也可调侃一番,裴松之注《三国志·钟繇传》引用了《魏略》中的一段记载:孙权向曹魏称臣后又献上关羽首级,太子曹丕在与钟繇的书信中提及此事,钟繇回信曰:“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妩媚。”[6]因孙权已经臣服又斩杀关羽,钟繇便用“了更妩媚”形容昔日敌人,字里行间充满笑谑,完全是有意拿昔日政敌打趣。
魏晋时期的散文创作也多嘲谑之笔。曹丕评价孔融的文章:“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7]刘勰也说他“但谈嘲戏”[7](P119),钱钟书先生也评价过孔融的嘲戏略似“《史记·滑稽列传》所载微词谲谏”[7],但两者虽在手法上有相近之处,前者却更具攻击性和反抗性。以《圣人优劣论》为例,其将圣人喻为“狗马”,用“狗马”之行有先后暗示圣人之中有优劣,手法高明,戏谑中可见其对虚伪礼法的反抗。
总体说来,魏晋思想解放,崇尚自我,许多文人都对动荡不安、虚伪黑暗的统治失望不已。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嵇康般慷慨任侠,更多的时候,“嘲谑”便成为一种手段,让他们在谑浪笑敖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相比较而言,两汉的文人常常以玩笑嘲弄的口吻发牢骚,而到了魏晋,牢骚渐渐变成了一种迂回曲折的抗争。但无论如何,从先秦到两汉再到魏晋,嘲谑文学一直在“自觉”的道路上快速发展。
四、唐宋时期:无所不谑,雅趣十足
唐宋时期作是封建社会物质精神文明之高潮期,嘲谑之风得以延续。这一时期的嘲谑文学数量丰富,包罗万象,几乎达到无所不谑的程度。
首先,嘲谑文学作品的体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几乎每一种文学体裁中都有大量的嘲谑文学作品。《全唐诗》中有“谐谑”四卷,几乎都是娱乐调笑性的作品对宋代谐谑词的发展进行记载的是王灼的《碧鸡漫志》:“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娱戏污贱,古所未有。”[8]韩愈散文亦有“以文为戏”的特色,他的《毛颖传》被认为是“以文滑稽”,《送穷文》被黄庭坚称为“谐戏”,《进学解》被看成“《送穷》之变体”;同期柳宗元也有此类名篇,如《愚溪对》《乞巧文》等,亦颇具“以文为戏”的风采。小说方面,唐代的很多笔记小说都为嘲谑性的文字设有专章,在《本事诗》中有“嘲戏第七”,在《因话录》中有“谐戏附”,《唐摭言》有“轻挑戏谑嘲咏附”,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中有“嘲诮”“诙谐”类,也记载了很多唐代的嘲谑故事。另外,戏剧领域也不乏嘲谑的内容。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所谓参军,便是戏中的正角……两者相互问答,其作用则调谑讽刺,兼而有之。”[9]
其二,参与嘲谑或从事纯粹嘲谑文学创作的群体扩大。《隋唐嘉话》中就记载了唐太宗宴请众臣,相互嘲谑打趣的故事,[10]《本事诗·嘲戏》记载有优人唱《回波词》调侃唐中宗怕老婆,还有长孙无忌和欧阳询两位名臣互相嘲弄对方外貌身材的掌故。[11]宋代欧阳修与众多礼部大臣的所写的唱和诗即“时发于奇,杂以诙嘲笑谑。”[12]在这里,王公重臣都是成了嘲谑性事件的发起人或当事者,而不再仅仅是中下层文人或俳优们需要取悦或谏言的对象。
再者,唐宋时期嘲谑文学的交游功能开始凸显,出现了大量的戏赠诗。这种诗唐前很少,唐初亦未成风气,但中唐白居易的诗集中多有“朋友戏投”之诗,到宋代广泛流行于各大诗人、诗派之间,有蔚然成风之势。[12]这种诗记载着朋友之间的交流往来,内容也就更加日常化、细碎化。如《圣俞坠马伤臂以其好言兵调之》《顺之将携室行而苦雨用前韵戏之》《闻曼叔腹疾走笔为戏》《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等。诗中描写坠马、下雨、生病、纳妾等多种场景,完全是对生活琐事的有心记录。总之,无论是从体裁、题材还是参与者的角度,都不难看出唐宋时嘲谑文学无所不谑的特点。
此外,唐宋时期的嘲谑文学体现出明显的“雅化”特征。首先是思想内容雅。韩柳散文中的许多戏言都是对自身经历和士人命运的一种感慨,带有浓重的“感士不遇”色彩。如果说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以文为戏”还可看作是对东方朔、扬雄等人讥时书愤、自慰述志风格的继承,那么兴于唐盛于宋的“戏赠诗”与前代“嘲人诗”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嘲人诗”几乎都是以嘲谑人的生理缺陷为乐,大有“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之嫌唐宋时戏赠诗则更能给人以风趣活泼之感。如李白自己嗜酒成癖,就调笑不喝酒的朋友,写了《嘲王历阳不肯饮酒》;李白作诗援笔立成,便用“离别之后太瘦生,仍为之前作诗苦”来调侃杜甫为作诗而折腾自己的身体;南宋杨万里和尤袤之间更有“尤杨雅谑”的故事传世。[13]于其他日常题材中,唐宋时人也颇见雅意。如岑参“道旁榆芙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将买酒赖账描绘得清新脱俗;罗隐“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流连风月也可自抒怀抱。即使面对“老之将至”这样残酷的主题,唐人都可以生出喜悦之情,写出《览镜喜老》《喜老自嘲》这样的诗篇,丝毫不见迟暮之悲。另外,宋人喜“以理入诗”,即使是调笑性的诗篇也不例外。如苏轼《薄薄酒二首并引》,虽然在序言中说明“可发览者之一噱”,但也充满了冷隽深沉的历史性反思和一种道家式的理想主义人生观。
其次是表现手法雅。唐宋文人嘲谑,除了常用的比拟、夸张等修辞外,在手法上加入了更多“书卷气”。时而拆解文字:唐时狄仁杰调侃同朝为官的卢献:“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乃是煮熟狗。’”[10](P134)时而歪解词句:“苏轼夜读《阿房宫赋》,二老兵事左右,不堪其扰,夜不能寐。一人抱怨:“知他有甚好处?”又一人曰:“有好句一者,吾独爱‘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14]时而引经据典:如某日尤袤对杨万里说:“杨氏为我。”(语出《孟子》)杨万里回应:“尤物移人。”(语出《左传》)时而运用典故:辛弃疾《卜算子·齿落》一词:“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借《世说新语·排调》之典故,《卜算子·用庄语》“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用《庄子·应帝王》中的秦氏故事……这些带有“书卷气”的手法,无疑更使唐宋嘲谑趋于雅化,尤其是“使典为戏”这一条,正是宋人好以才识学问作诗这一特点在嘲谑文学领域的体现。
五、元明清时期:由雅转俗,笑骂世情
元明清时期嘲谑文学由雅转俗的特征,从嘲谑文学的体裁上便可见一斑。元曲不仅使元代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古代俗文学的代表之一。嘲谑性的散曲在元代屡见不鲜,笑话作为俗文学的又一代表,更是嘲谑文学的集中体现,在明清两代取得了长足发展。笑话集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但数量不多,有些已经散佚,唐宋时期的笑话大多都是由文人创作,常常涉及真人真事,内容大都是当时的文坛掌故或野史趣闻,对民间通俗笑话记录不多,而明代文人则不避俚语笑谈,不废滑稽科诨,崇尚诙谐调侃。[15]而明清时期的笑话集往往“更具有通俗性,即使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也不能改变它作为民间文学的根本特性。”[16]元明清的小说戏剧中亦不乏嘲谑,但篇幅较长,本文中暂不讨论。
元明清嘲谑文学由雅转俗,在内容上表现为对“传统”的消解和对“浅俗”的自觉追求。元曲语言的通俗性自不必多说,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时期,文坛中出现了文学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追求真情与浅俗。嘉靖年间,徐渭、李开先等人都有意追求诗歌创作的通俗浅近,这种风格在戏谑性的诗作中体现得更加明显。[17]到万历时期,衍生出“以文为戏,适俗疗俗”的文学思想,[17](P809)冯梦龙《古今谭概》《笑府》等笑话集相应问世。明代笑话集中的部分笑话语涉猥亵,鄙陋下流,这一方面是作者本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迎合底层人民的娱乐需求,同时还是晚明淫逸世风的真实体现。
清朝时,性灵派诗人袁枚曾作诗嘲谑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天涯有客号泠痴,误把抄书当作诗。”[18]自己作诗也力求通俗:“手制羹汤强我餐,略听风响怪衣单。分明儿鬓白如许,阿母还当襁褓看。”[19]虽有点打油诗的味道,但玩笑之中亦体现人间至情。
同样是怀才不遇的牢骚诗,郑板桥曰:“教馆本自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下冤仇……”[20]直接表达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两汉、唐宋时期将不满与牢骚匿于歌功颂德、安贫乐道等情绪之下的含蓄风格大相径庭。即使同是使典为诗表达同一主题,典雅与浅俗也一目了然。苏轼和徐渭都曾经作诗嘲谑张姓朋友老年纳妾的行为,诗中均含有大量典故。试比较二诗末句,苏诗曰:“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徐诗曰:“正宜七十张公子,夜夜香衾比目鱼。”[21]虽都是用典,但后者更加直露浅白。
元代以后嘲谑文学的另一特点是笑骂世情。这段时期的嘲谑类作品的社会性和讽刺性较唐宋时期而言无疑大大增强。中国文学的讽刺特点早已有之,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便有“美刺”传统,《相鼠》言:“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硕鼠》曰:“誓将去女,适彼乐土。”甚至《尚书》中还有要和统治者同归于尽的愤恨,如“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然而这些诗文都毫无戏谑之意。而将讽刺与嘲谑相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必定介于强烈的攻击性与温软的调侃性之间,将“咒骂”变为“笑骂”。元代时散曲盛行,其中多有描述官员收受贿赂之作:“那的是为官富贵,只不过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箧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16](P144)表面好似为官家辩护之词,实则有揭露之意。明代诗文里也不乏诙谐嘲谑的讽刺作品。小品文领域,王思任、顾大韶、沈承等人也都有许多滑稽生动的讽刺之作,但是,最能体现“笑骂世情”这一特点的,还是明清之际的笑话。明清时期的笑话是谐谑与讽刺的结晶。除了上文所说某些粗俗猥亵的笑话反映了晚明纵欲放荡的社会风气之外,明清笑话还以嘲谑的方式,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心理。官府的黑暗,科举的弊病,世风的败坏,常常成为明清笑话的“笑骂”对象。描写官员贪得无厌:“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22](P315)描写不懂装懂的监生:“有督学策问“姚江学术”,监生回答“有谓江之学胜于姚者,有谓姚之学胜于江者,似难分其优劣。”[22](P519)在调侃戏谑的背后,反映出科举制度的僵化与变质。晚明的世风日下在笑话中也有充分体现,不但官员贪得无厌,商人唯利是图,就连普通百姓也吝啬到一毛不拔的境界。父亲溺水,儿子呼救。父亲命悬一线时仍不忘叮嘱:“是三分银子便救,若要多莫来。”[23]除了吝啬至极以外,更有和尚诱人妻女,道士坑蒙拐骗,娼妓只问金钱,道学先生顽固迂腐……农商百工、富人乞丐、盗贼无赖等都成了可笑之人,成了被“笑骂”的对象。这些笑话虽然也有批评讥刺之意,但少有“予与女偕亡”的强烈愤恨,而是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人看到其中荒诞丑拙的一面时首先感觉到可笑。
综上所述,嘲谑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各朝,直到今天尤未断绝。各代嘲谑文学因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在先秦时期可以说是嘲谑文学的萌芽期,在百家争鸣时期由于政治和学术的需要,常被当作申述主张的工具;汉魏时期嘲谑文学的娱乐功能开始体现,同时,已有文人将嘲谑作为表达身心情感的手段加以运用,使其走向自觉;唐宋时期是封建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高潮期,此时的嘲谑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内容更加广泛,手法更加多样,处处透着文人雅趣;及至元明清三代,封建社会高潮期已过,文人失去了优游生活的土壤,雅文学衰落,俗文学发展,嘲谑文学也不可避免地由雅转俗。再者,明清时期已是封建社会末期,各种弊端日渐显露,整个社会百病丛生。嘲谑文学在调侃戏谑引人发笑之余,亦发挥出投枪匕首似的刺世功能,体现出笑骂世情的风采。直到今天,嘲谑文学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嘲谑文学不仅是生活的调剂品,还是研究社会世情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