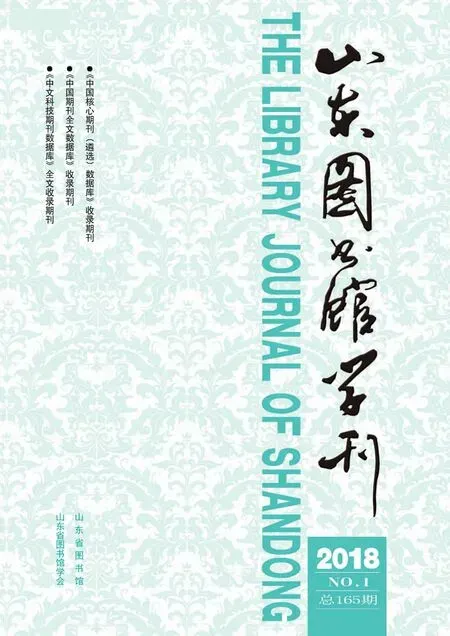阅读力的根本基础在于如何读书*
——关于斋藤孝《阅读的力量》与聂震宁《阅读力》的读书报告
2018-04-03张麒麟
张麒麟
(西南大学图书馆,重庆 400715)
我国的阅读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代表性著作如曾祥芹主编的《阅读学新论》、黄葵和俞君立编著的《阅读学基础》等,主要是从图书馆学、目录学、语文学、教育学等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的,进而推导出阅读指导活动与阅读教学的规律。
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阅读学研究引入了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阅读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和南京大学的徐雁教授撰写了大量的阅读文化学著述,从学理上论证了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人文素质阅读的文化价值。在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热潮下,近年来的阅读学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学者们对家庭阅读、校园阅读、社会阅读和数字阅读等细分领域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愈加注重与全民阅读推广实践的结合,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编写的“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王京生、徐雁主编的“全民阅读推广丛书”等等。
在近几年出版的众多阅读学研究著作之中,有两本新出版的图书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斋藤孝教授所著《阅读的力量》(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一是由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先生所著《阅读力》(三联书店2017年版)。其原因有三:第一,两本书避免了阅读学研究中经常存在的“泛泛而谈”,也不纠结于“读不读书”“怎样读”这种答案多元的议题,而着眼于个体“阅读力”的养成,这是阅读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第二,两本书虽然都以“阅读力”为基本出发点、在体例和结构上也十分相似,但基本观点却各成一家,可以互相参照,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第三,两本书的作者在阅读学研究领域都著述颇丰,但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阅读力”等类似的观点,这足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斋藤孝的日本版原著题为“読書力”,与聂著书名含义近似。笔者认为中文版书名“阅读的力量”有待商榷,因为“阅读的力量”更像在说明阅读行为所能赋予个人及社会的正能量,而全书实际上着眼于“提高读书能力”的方法,因此直译为《读书力》其实更为妥当。
1 “阅读力”:该如何读书?
斋藤孝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忧心现代日本人“阅读力”弱化的问题。他指出:“日本乃读书立邦之国”,“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期,日本不仅仅是识字率高,从读书内容上看质量也是颇高的”,“当时的庶民百姓对难度较大的汉字的过敏性反应,远远比现在的人们要少得多”,“现在五、六十岁的日本人在大学时代的阅读量,远比当下的大学生阅读量大得多”。[1]在斋藤孝看来,阅读量和阅读率固然值得忧心,但“阅读力”才是问题的本质,它是一个人能否坚持阅读的关键能力。
斋藤孝对“阅读力”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多少とも精神の伴う読書”[2],即阅读力必须是一种乐于耗费精力去阅读书籍的能力。在书中,斋藤孝不仅提出了“阅读力”训练的途径——“先排除连小学生都读得懂的那些既轻松又愉快的读物”“习惯阅读文库本图书”、随后阅读“知识新书”系列(日本出版的一类知识教养型图书),而且给出了是否具备“阅读力”的判断标准:至少读过文库本系列图书100册,并在四年的时间内读完知识新书系列图书50册(即每个月读完1册)。[3]斋藤孝认为,学会了如何读书,并且愿意在读书上花费时间、精力和脑力,才算真正拥有了阅读力。而达到阅读力检验标准的成年人,其理解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等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作家,聂震宁在2016年初决定“把对社会阅读问题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阅读力研究上来”[4],其自言原因有二:第一,在全民阅读推广的背景下,国内图书馆借阅量虽然在回升,但借阅量高的图书大多都是通俗易读的网络小说和类型小说,“当中存在着阅读力高下强弱的问题”;第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严重欠缺“阅读力”教育,以至于许多成年读者对提高“阅读力”有着强烈需求。
聂震宁将“阅读力”的概念阐释为:“阅读力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具体说可以包括这样几项能力:提取信息的能力、推断解释的能力、整体感知的能力、评价鉴赏的能力和联想运用的能力。阅读力其实是教育力、文化力、思想力的一部分。”[5]同时,相较于斋藤孝一刀切式的“4年·50册”标准,聂震宁认为阅读力存在一种“多层结构状态”,有“幼儿阅读力、小学阅读力、中学生阅读力、大学生阅读力乃至专家学者阅读力之分”。[6]
由此可见两位作者基本出发点之分野。在斋藤孝看来,“阅读力”是由内而外的,必须从个体的内心修行出发,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外化为人的品德和涵养,因而需要一个便于操作执行的硬指标。他写道:“伴随精神紧张的阅读,则是一种刚开始时让人非常疲惫的事情,哪怕读完一本书,也需要消耗相当多的精神方面的能量。但只要多读几本,就能跨过那道坎,并逐渐习以为常。”[7]“阅读就像长跑或步行一样,并不见得飞毛腿不可。只要每天坚持跑步,每次跑的距离一点一点延伸加长,相当多的人都能够锻炼出长跑的耐力……读书就是‘贵在持久’。”[8]
聂震宁的出发点则是由外而内的,一个社会必须具备阅读力,“社会的主流阅读力量可以引导、劝导、感召、影响社会中个人的好恶,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提高全社会的阅读力”[9],在社会整体、不同社群和少数专家的引导下,个人的阅读力得到锻炼和提升,个体的阅读力反过来又构成并提升了一个社会的阅读力。
在提升阅读力的具体方法上,两位作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聂震宁将读书方法归纳为“动口、动手、动心”,并探讨了朱子读书法、快阅读、慢阅读、浅阅读与深阅读所适宜的范畴。斋藤孝则探讨了发声朗读、划线阅读、变速阅读的技巧,并且认为读书可以通过转述内容、写作时引用内容来加深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两位作者的具体论述有所差异,但实际上都将“阅读力”视为阅读的核心问题,它是“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的立足点。培养阅读力、训练阅读力和具备阅读力的阅读,比“读不读书”更重要。同时,阅读力还可以解答“为什么要读经典”“找好书读重要吗”这样的问题,在两位作者看来,阅读经典和好书才是符合真正阅读力标准的阅读,才能够真正“开卷有益”,获取阅读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进而提升人生的软实力。
2 阅读史:一代人的阅读力
阅读史其实就是研究某一代人的阅读力。阅读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书籍史研究的分支,主要讨论六个基本问题:谁读,读什么,在哪儿读,什么时候读,怎么读,为什么读。[10]目前,国内阅读史研究大多从目录学、出版史、文化史及文学史入手,往往只解答了前四个问题。因此,聂震宁在书中第一章对阅读史后两个问题的尝试性解答就显得尤为重要。聂震宁认为:(1)人类的阅读先于文字,原始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不能没有阅读,因而阅读不应拘泥于文字而应关乎意义;(2)文字提升了阅读,但由于文献载体的笨重、出版的匮乏和语言本身句读的限制,朗读先于默读;(3)随着出版的发展,民众得以接触大量的文本,默读渐渐成为今天普遍的阅读方式。
因此,在聂震宁的眼中,阅读行为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那么今天“忙时读屏、闲时读书”“左书右网”等阅读习惯就是阅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当代人的“阅读力”。他在倡导阅读纸质书的同时,同样认可“大阅读”,并且提出应“善待一切阅读方式,坚守人类阅读认知规律,推动传统阅读与新兴阅读的融合”[11]。
斋藤孝则简要谈及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国人的阅读史,认为不单是长期以来高质量的学校教育保障了日本人普遍较高的阅读能力,而且日本人乐于“通过大量的阅读来促进自我性格和价值观的形成并提升对他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与聂震宁观点类似,斋藤孝同样认为读书与阅物、阅人、阅世密不可分。由此他也发出疑问:“当下日本人伦理观的低落现象是不是与读书能力下降有关呢?”[12]从这点来看,《阅读的力量》更兼有劝读导学的价值观指导意义。
了解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对于今天的社会阅读现状,聂震宁的态度显然偏向乐观,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分享和传播如何读书的方法,致力提升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力”。斋藤孝相比起来较为悲观,但实际上两人殊途同归,原因在于阅读方式的发展变化不可能抛弃阅读本身,而阅读能力下降的现实使我们更需要阅读。从阅读的历史上来看,阅读一直都是人类无法割舍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知行合一”的源头、一个社会构建价值观的基石,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无论某一代人的阅读力如何变化,人类的阅读史仍然会一直书写下去。
3 全民阅读:何为全民阅读的“最大公约数”?
全民阅读关注的是当代人的阅读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阅读率下降就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困境,全民阅读(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应运而生。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各国政府通过教育政策、阅读推广项目、出版基金和阅读促进法律等手段引导社会阅读。近年来,我国也将全民阅读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如火如荼。
聂震宁在《阅读力》中提出了全民阅读“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即读者中最广泛的阅读追求。他在总结“为什么要读书”时,以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致乐概括,但认为“读以致乐应当坚持放在阅读价值观的首位”。这种“乐”并不是“一乐而过”的“乐”,而是指“进入纯粹为读而读的状态时”所得到的精神乐趣[13]。而这种精神乐趣反过来又会促使人们养成坚持阅读、终身阅读的习惯,这就达到了全民阅读推广的目的。
而在《阅读的力量》一书中,斋藤孝分别以“塑造自我”“锤炼自我”“扩展自我”为章节标题,可见他将自我提升视为阅读的本质。这似乎与聂震宁“享受乐趣”的观点相左,通过阅读力的训练来使自己提高有些苦修的意味,但斋藤孝并没有否定阅读的乐趣,他也同样坚信只要阅读、就一定会给读者带来乐趣。不过,在斋藤孝看来,阅读给人生所带来进步的力量才是全民阅读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认为,寻找“公约数”比寻找“最大公约数”更重要。因为只要找到一个公约数,我们就能做些事情,就能把全民阅读推动一点点。例如,“好书”不就是全民阅读的公约数之一吗?在两本书的附录部分,两位作者都附上了推荐书目。聂震宁根据阅读力层次不同,分别推荐了“中学生语文新课标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中国文库”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书目。而斋藤孝则“精选文库本图书100册”,作为提高阅读力的基本书目。这些书目都是读者寻找好书的索引,也是两位作者多年来推动全民阅读的经验之选。再如,“如何读书”也是一个“公约数”,近年来畅销的阅读学名著《如何阅读一本书》其实已经说明了公众对学习如何读书、如何提升自己阅读力的期待,而两位学者关于“诵读”“笔读”、书屏结合等读书方法论势必也将进一步指导读者们如何读书、如何提升阅读力,进而品味阅读的乐趣、实现人生的价值。
总之,全民阅读的关键在于阅读力,而阅读力的根本基础在于如何读书。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都应该学会如何读书,努力让自己拥有“阅读力”,进而让“阅读改变人生”、让书香充满社会。在经过十年的阅读实践和思考后,聂震宁在《阅读力》导言中写道:“阅读力问题应当被看成是人类阅读研究的起点和归宿。”[14]诚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阅读学有许多种切入视角。但是,这些研究最终仍然要回归阅读的本质,即回答“为什么读”“读什么”和“怎么读”这样的基本问题。聂震宁先生和斋藤孝教授珠玉在前,可见“阅读力”的概念能够作为阅读学研究一个新基点,围绕阅读力的核心概念,对培养阅读力、提升阅读力、应用阅读力和评价阅读力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推动全民阅读事业继续发展。
〔1〕〔3〕〔7〕〔8〕〔12〕 [日]斋藤孝著,武继平译.阅读的力量[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序55-56,序19-25,序20,序42,序63
〔2〕 『読書力』(齋藤孝)は日本人的精神論が向きだしだった[EB/OL].http://1satsu3gyo.com/dokushoryoku-saito-2002,2015-12-29
〔4〕〔6〕〔9〕〔11〕〔13〕〔14〕 聂震宁.阅读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导语1-2,227,22,140,74-76,导语2
〔5〕 聂震宁.什么是 “阅读力 ”?[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7-05-05
〔10〕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15
〔15〕 刘浩冰.实践中的阅读力——聂震宁全民阅读的实践与理论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7(7):87-89
〔16〕 徐雁.读书永远是“进行时”——聂震宁《阅读力》与斋藤孝《阅读的力量》比较谈[J].图书情报研究,2017(4):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