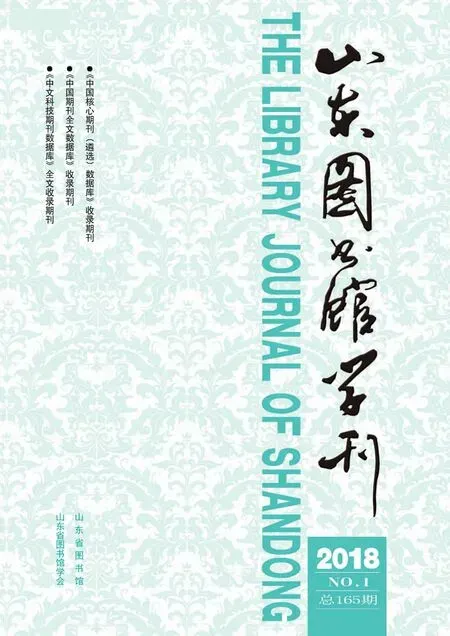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评述
2018-04-03郑永田
郑永田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 510006)
严文郁,字绍诚,1904年生于湖北汉川,2005年卒于美国林登市。严文郁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上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是我国“第二代”图书馆人才中的杰出代表。[1]他一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撰写了《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清儒传略》《中国书籍简史》等蜚声海内外的著述。而以他的亲身经历撰写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新竹:枫城出版社,1983年)的问世,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华人图书馆学界的学术地位,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人职业理想和事业精神的赞歌。
1 写作缘起
严文郁先生是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的先驱,也是早期留学美国的图书馆学家之一。他1921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前身),193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深造,两年后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从1925年开始,严文郁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并负责重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筹备建设工作。1949年赴纽约联合国图书馆主持中文图书编目,直至1964年退休之后受聘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目录学并主持该校东亚图书馆的工作。1978年返回台湾任教于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1981年被聘为讲座教授并兼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汉学资料及服务中心顾问。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以及其后的图书馆学教学经历使其重视图书馆学教育以及图书馆史的总结。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中央图书馆计划编撰《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鉴于严文郁先生在图书馆业界和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中央图书馆遂力邀严文郁先生担任《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第一章《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的撰写任务。严文郁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从萌芽时期、成长时期和抗战及复员时期三个方面分别概述了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
与此同时,虽然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学教育方兴未艾,但是有关图书馆史方面的中文教材相当缺乏,尤其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方面的教材阙如,这样既给授课的老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与困难,也让图书馆学青年学子无从学习与参考。为了改变中国图书馆发展史教材缺稀的尴尬状况,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决议邀请严文郁先生撰写《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书,以使图书馆史研究者明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沿革,并为图书馆建设者提供及时而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无论从专业学识、从业经验、学术地位和业界影响而论,严文郁先生无疑是编写此教材的不二人选,他的笔耕不辍、孜孜以求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亦促使其勇敢地去承担此次写作的重任。严文郁于是以《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第一章《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的文字为底本,埋头研究,奋笔疾书,不断地加以扩充和完善,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告成。此书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研究的文献空白,成为中国图书馆史教育领域必读的经典教科书。
然而,在述及编撰此书的初衷时,严文郁先生直言“笔者滥竽斯业,行将周甲,于图书馆大事,耳熟能详,近以年事已高,记忆衰退,惟恐时过境迁,许我茹苦含辛的史实为后世遗忘,故不揣浅陋,就所能得到的资料,益以个人见闻,编著此书,以备留心图书馆史者参考。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尚祈海内外同道,不吝指正为幸”[2]自序充分表达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谦逊与恭卑之情。
2 著作特点
2.1 体例完善
但凡一部优秀的学术作品,除了文字和内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之外,完备的体例结构也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即是这样一部结构合理、体例完善的经典之作。
从序言来看,《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成书之后,华人图书馆学界名流有感于此书的重要性以及将要在图书馆学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纷纷撰文评论严文郁其人的长处与其书的特点。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王振鹄称赞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不仅有利于同行了解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轨迹,而且有利于他们学习先辈之拓荒精神,益增惕励奋发之心。[2]王序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蓝乾章称此书的完成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件大事,它的问世必能有助于图书馆学之教学与图书馆之建置。[2]蓝序台湾大学图书馆学教授沈宝环盛赞此书的出版是我国图书馆界一件划时代和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这部填补了我国图书馆学文献空白的伟大著作不仅保持了严文郁一贯的“新”“速”“实”“简”的风格,而且更具有“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的三大特色。[2]沈序而严文郁的自序除了详细分析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的原因之外,更表露了编撰此书的初衷。众多的序言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严文郁其人其书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极大的完善了此书的体例,丰富了此书的内容。
在第一章“绪言”(绪论)部分,严文郁阐述了我国图书馆的历史演进,指出旧式藏书楼虽囿于静态的收藏管理(重藏),缺乏实际流通利用(轻用),但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实际支柱,藏书楼是图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严文郁认为我国旧式图书馆(藏书楼)的形态,大概可以分为宫廷藏书、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三种类型,并从周朝的守藏室谈起,概述了各类型藏书楼发展及其特点。严文郁分析我国旧式图书馆被称作藏书楼的原因,在于它们只是珍本的储藏所,而不是有用书籍的传布枢纽,并总结了近代图书馆是一种藏用并重、启迪民智的教育机构。从绪论中我们可以探究严文郁此书的写作思路——总论从萌芽、成长到抗战及复员三个时期阐述自清末至抗战胜利这一段时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再从有助于图书馆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的图书馆法令、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学术、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团体等五个方面分论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这种结构的安排显然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
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第二章“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产生的背景”,严文郁认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轫,始于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因此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改科举、设学校、开报馆、建藏书楼即是维新派的重要兴国主张)说起,探索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起源。严文郁继而从孙家鼐和李端芬的呼吁、以康梁为首创办的强学会等学会的推动、学堂图书馆之附设、东西洋图书馆观念的引入、图书馆行政的改进、大量西书翻译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西方新式图书馆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等背景,其中的许多观点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图书馆史分期是揭示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特点与差异的一种方法,也是图书馆学术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3]严文郁把自清末至抗战胜利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时期(1905-1911)、成长时期(1912-1936)以及抗战和复员时期(1937-1945)。萌芽时期以光绪31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以及图书馆运动的发端为起源,并以湖南图书馆的开办为标志,迄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成长时期起于民国元年(1912),迄于民国25年(1936);抗战和复员时期起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1937),止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1945)。
严文郁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划分既基于政治事件,又超乎政治本身——虽然严文郁认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轫始于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他并没有把维新变法运动发生的1898年定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之年,而是将其定为废科举与新式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建立为标志的1905年,为全文的叙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严文郁向我们描绘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荣辱兴衰、迭荡起伏的恢弘历史画卷;而对图书馆立法、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团体及其对外关系的描述则使我们加深了对清末至抗战胜利之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荣耀与辛酸的认识。
2.2 史料真实
图书馆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图书馆的过去,而且有助于我们把握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4]如果没有对公共图书馆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评判和鉴赏,就很难理解公共图书馆现在的地位。[5]图书馆史研究者应当把提供前车之鉴作为图书馆史研究的目的。而要保证借鉴的可靠性,就必须如梁启超所言,研究图书馆史必须“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以及“供吾人活动之资鉴”。[6]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可见,寻求和还原事实和真相是历史研究者的第一要务。虽然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可能会囿于思想和认识等方面的限制,但是相对而言,比起后来人受史料限制和主观臆想而得来的叙述总要靠谱得多。换言之,历史叙述者如果曾经作为当事人亲身经历过相关的事件,则可以保证历史资料的准确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严文郁先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也是早期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进代表人物。严文郁积极投身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参与了一系列图书馆的活动,并担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据严文郁《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封二介绍,严文郁曾经担任北平图书馆编目兼阅览部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主任、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创办人、台北辅仁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在国内的图书馆从业经历可谓相当丰富。
笔者根据对《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一书的不完全统计,严文郁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实践活动还包括:1929年1月28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被聘为《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编辑;1936年受中华图书馆协会之邀,以英文撰写《中国图书馆间之合作》,作为国际图书馆会议交流之论文;1942年担任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美国国务院文化部发起的“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的三位中方工作人员之一(其余两位是袁同礼和徐家璧);1942年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教授;1946年担任重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秘书;1947年4月19日担任重庆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1948年1月接待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克莱普(Verner Clapp)来华考察,并带领其参观浙江省立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
对于自清朝末年至抗战胜利这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撰写,严文郁先生无疑是理想之人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在其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称:“中国新图书馆事业开创迄今之经纬,余与绍诚兄皆身与其事,故其记述详明,论断悉中肯綮,凡所叙录,皆为史实”。[2]蒋序王振鹄亦在序言中说:“严教授五十余年来,孜孜矻矻,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由于在国内先后任职国家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并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各项活动,因之对我国前期图书馆发展经过,身临其境知之甚详。”[2]王序蓝乾章在序言中有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轫于逊清末叶,民国肇始,以迄抗战军兴,发展神速。当民国二十年之际,全国各省至各县,大多已设立图书馆,先生适值壮年,国中图书馆盛举,莫不躬与,以是先生所著,益增真实价值。”[2]蓝序这些序言都赞扬和肯定了此书史料的丰富性和叙述的可靠性。严文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教,保证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历史的真实性与史料的准确性,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真实的民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画面。
严文郁先生除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自清末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内中国图书馆从萌芽、成长到衰落的历史事实外,还大量引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等的图书、期刊文献以及图书馆调查报告的资料和数据,保证论述的真实性,除了让人感到信服之外,还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中山大学周旖通过研究认为,严文郁此书的重要价值,至少在史料方面是相当准确且可靠的;从史料角度衡量,《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专著中最好的一本。[7]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要比1998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严文郁《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要周全而合理得多。《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自始至终没有脚注和参考文献,所引用的事实和数据没有注明任何的来源,这样极不利于读者甄别资料和回溯阅读。[8]
2.3 叙述严谨
严文郁先生的文字朴实纯真,无虚华,不掠美,以实实在在的语句,真实地记录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其撰写的另一篇著作《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中得到进一步的感受和体会。对于入选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名人堂”(A Library Hall of Fame)的四十位杰出人物,严文郁都用平实的语言叙述其生平事迹、事业成就和学术影响。而对于《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来说,既具有文字朴实的风格,也具有叙述严谨的特点。
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其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严文郁用平白的语言,分析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背景,接着从萌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成长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抗战及复员时期的图书馆事业三个部分来叙述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历史,进而从创立、经费、建筑、组织、人员、推广及行政等方面对中国图书馆立法进行比较,最后概括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术团体和对外关系。沈宝环在序言中评价,“绍诚先生的文笔具有他独特的风格,没有一个虚字,没有一句空话,他的文章琳琳琅琅,令人读后有如玉山之行的感受,看绍诚先生的写作又有点像听绍诚先生的讲话,娓娓而谈,引人入胜。”[2]沈序
在第四章“成长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第三节“省市立图书馆”中述及“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的馆藏数量时,严文郁引用陈训慈“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一文的统计数据:“截至23年底止,有图书70056册”。对于这个数据,严文郁专门做了案语:“按:此据24年中报年鉴所载,另庄文亚所编全国文化机关一览,则称至该年5月底止,已有图书12万册,差距甚大,不知何者为是。”[2]83对于因不同的文献来源而产生的数据分歧,严文郁并没有采取武断的方法,而是留有存疑的态度,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严文郁治学的严谨以及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
同样是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县市立公私立图书馆”,严文郁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利用民国25年(1936)全国图书馆统计数据,列举了各县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内容包括省份和图书馆数量两项。对于表内所显示的安徽省只有17所、山东省只有6所图书馆的情况,严文郁表示“表内安徽只列17所,山东6所,足见填报不实,不足凭信”。[2]101虽然严文郁没有直接说明其中的原因,但表中明确显示,广东省的各县公私图书馆的数量为142所,江苏省的公私图书馆数量是78所,而以当时山东与江苏的经济实力,对比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甚至比山东经济薄弱的安徽的公私立图书馆的数量也比山东多,这或许是严文郁所不能接受的原因之一。严文郁觉得这个调查数据不准确,不足以让人相信,因此专门为此作了注释,这充分表明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存疑态度和严谨精神。
3 结语
严文郁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图书馆运动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图书馆学家。严文郁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光辉写照。以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为基础而撰写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学术巨著和文化遗产,虽然它的出版距离今天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所产生的学术价值和发挥的指导作用愈加显著。它使中国图书馆人尤其是广大图书馆学青年学子永远铭记那段光荣而屈辱的历史,激励他们养成图书馆职业精神与增进图书馆事业之心。基于上述的客观事实,笔者认为,《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应当列入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图书馆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课教材,使图书馆前辈的学术思想和职业精神薪火相传,以至千秋万代,永不熄灭。
〔1〕 程焕文.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2):35-42
〔2〕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新竹:枫城出版社,1983
〔3〕 郑永田,庞弘燊.吴稌年与近代图书馆史研究[J].图书馆,2012(1):36-39
〔4〕 郑永田,陈劲.论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性[J].图书馆,2012(3):27-29,33
〔5〕 Carleton B.Joeckel.The Governm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5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 周旖.如何书史——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J].图书馆论坛,2015(1):106-112
〔8〕 郑永田,罗木华.严文郁《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评介[J].图书馆建设,2015(3):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