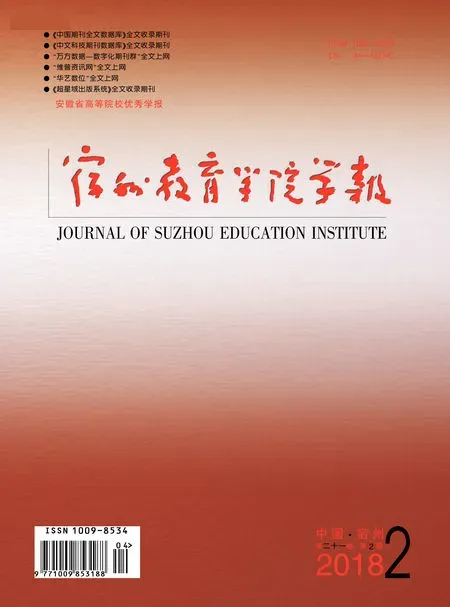论刑罚学的学科独立性—一种横向的比较
2018-04-03韩辰
韩 辰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一、问题的提出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在以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并由此诞生了多元化的研究层次,如比较刑法学,刑法教义学等。但是不仅仅是刑法学本身在随着时代需要转型,从刑法学科中也诞生了很多新兴的研究科目,如犯罪学。毋庸置疑,犯罪学在继近代刑法学研究转向实证化后正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学科门类,并在新时代背景下为社会发展需要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视角。但是作为另一门独立化的学科——刑罚学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种情形不禁使人扼腕。中国国内第一位对刑罚学独立展开研究的当属邱兴隆教授,然而继教授驾鹤西游后,对刑罚学继续深入研究的学者确实俩寥寥无几,更何况在其专著《刑罚学》中,对刑罚学做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论证也未加深入。本文就是想在此种背景下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思考的方式阐述刑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批判性意义,也借此表达对邱兴隆教授的纪念与哀思。
二、刑罚学与犯罪学
作为问题的开端,首先应当就刑罚学与犯罪学之间的区别问题作出说明。在近代近代龙勃罗梭出版了《犯罪人论》,此书标志着刑法学的研究逐步的从康德黑格尔时期的思辨化迈向了实证化,并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犯罪学。犯罪学在龙勃罗梭的后续研究者菲利、李斯特等人的深入钻研下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因为犯罪与刑罚总是一并出现的两个范畴,根据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为范畴出现的概念之间是有着先天联系的,因此犯罪学的独立也将预示着刑罚学的兴起,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刑罚学和犯罪学之间的区别阐述不清,导致了刑罚学与犯罪学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很多原本属于刑罚学研究的问题,落入了犯罪学的研究范畴,正如菲利对犯罪学的研究导致其将刑法学也归入犯罪学的范畴之中一样,最后形成的结局是刑法典的消解,使独立学科之间的互动和批判消失,这在学术上将造成很可观的损失。因此应当先就刑罚学和犯罪学之间模糊点作出如下说明,以便区分:
首当其冲的就是二者的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对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其研究对象是具有社会评价性质的犯罪,而不同于刑法中的从法益侵害角度定义的犯罪。而刑罚作为与犯罪同一范畴的概念却往往因为人们不假思索的逻辑推导而坠入怪圈,即如要对刑罚进行深入的研究,刑罚学首先需要解决什么是刑罚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要解决何为犯罪的问题,因为无犯罪则无刑罚,因此作为刑罚学,首先要研究犯罪,让对犯罪的研究成为刑罚之奥援。这一逻辑的背后体现了此种模糊性的本质,即对犯罪和刑罚之间的联系过于简单化,导致刑罚学的研究过于依赖犯罪学,甚至有一种先天的内化于犯罪学的趋势,其最终结果会消解其独立性。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应当对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从本质而言,刑罚的前提并不是犯罪,而是刑事责任。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承受刑罚并不是其必然结局,他仍然可能因为有责性的缺失而免于承担刑罚后果。可见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必然结果,而是犯罪的一种可能结局。若再往上追溯,正确的逻辑推论应当呈现为如下形式:犯罪?刑事责任?刑罚。这样理解不仅可以更加的契合刑法入罪判断的一致性要求,而且也能使刑罚学挣脱犯罪学的束缚,使其回归到针对刑罚本身的研究上来,不至于被形形色色的“犯罪前提”遮掩方向。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在研究方式上的相似性。对于犯罪学的研究目前而言主要分成两大类,即犯罪生物学和犯罪社会学。前者系用生物学的相关知识(包括心理要素等)对犯罪人进行研究,后者主要依据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将犯罪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疾病,对犯罪展开研究。从上述情形不难发现犯罪学的研究大多从实证处入手,无论是生物学的实验报告还是社会学的大数据调查,其研究结论必须有庞大信息实证的支撑。再反观刑罚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却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即从定性分析再到定量分析。前者即根据某一先念的原理和前提并综合刑罚学在现实中的研究素材进行深入的归纳和演绎,最后形成一套完整的从素材到论点再到论据的知识体系。后者则是从量上去研究刑罚,运用对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从而更精确的使刑罚得到合理配置并发挥出其最大效用[]。综合比对上述刑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方式,相似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二者的研究都体现了实证主义倾向,都需要运用大量的数据和调查来支撑论点。其实二者从刑法中的独立也就诏示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必然有着内在的实证化倾向,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二者的研究方式趋于混同无法鉴别。先从研究方式的广度来看,犯罪学与非刑事法学课的联系更加广泛,如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这就使得犯罪学能够更加简便的进行跨学科研究,而如果对刑罚学本身进行跨学科研究则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原因就在于刑罚学研究之刑罚在一定程度上与刑法条文的规定紧密相连,这就使其带有了天然的诠释学特征,想要轻易的进行脱离在理论上有着一定的困难。再从研究方式的逻辑结果上看,犯罪学的逻辑结果是呈现一个与研究方式紧密相连的结论,相比于体系性的建构更加注重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数据筛选的合理性。但是对刑罚学研究素材的演绎和归纳虽然逻辑结果也是呈现出结论,体系性的建构却更为重要,因为刑罚脱离不开对前述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逻辑推导,因此必须要注重结论在体系上的一致性才能彰显其合理性。
最后二者在研究目标上也存在隐约而含糊的联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是由这一学科的逻辑起点决定的,而且这一逻辑起点往往与研究目标重合。犯罪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即是犯罪的防治效果,可以说犯罪学的初衷和终点都是围绕着如何防治犯罪来展开的,如果达不到这一目的,那整个学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刑罚学的研究目的在表象上与犯罪学有着一致性,即关注刑罚的适用效果。造成这种表征上的一致性的原因就在于二者的实证化倾向决定了二者对功利化思维模式的依赖,如果无法从功利上对效果进行衡量,那二者的研究将难以深入,因为最重要的标准缺失了。但是刑罚学研究目的的深层次意味是更加值得挖掘的。诚然,刑罚学的研究的确在密切关注着刑罚的适用效果,但是如前所述,刑罚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性、体系性,因此刑罚学的研究目的与刑罚的目的又是紧密相连的。从康德第一次提出报应刑论到边沁第一次提出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可以看出刑罚的目的越来越脱离其本身的道德伦理韵味而逐渐转向作为刑罚承受的主体——人的本身。这种变迁与当代公民本位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刑罚学的研究目的自然而然也得从此入手考量。在现代国家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公民和国家处在难以逾越的两端遥望彼此,而犯罪的出现更是将这一距离拉大,将二者对立为敌我的厮杀。但是这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不相符合。从社会功能论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各个部分应如生物的各个细胞一样紧密结合且相互调和,和谐运行与整体之中。应此就需要一种手段机制的出现来调和公民与国家间的对立关系,而这种机制就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刑罚。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刑罚学的研究目的已经不仅仅在于刑罚的效果问题,其根本性的目的植根于调节国家与公民间的矛盾,使刑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能在社会运行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三、刑罚学与刑法学
划定了刑罚学和犯罪学之间的界限之后,再回到最初的分立起点:刑法学。无论将刑罚方向的研究深入到何种地步,都不可能将刑罚学和刑法学二者完全隔离,因为相关刑罚的概念依托于刑法体系的建构。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刑罚学的研究在刑法学面前完全失去了独立性,与对二者进行彻底分离相似,对二者进行无差别的混同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那么二者的界限到底在何处?或者说在刑法学极具包容性的庞大体系面前刑罚学又从何处找来自己的“安身之所”呢?正所谓存在未必合理,但存在一定有其原因,与其臧否其好坏不如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弄清楚二者之间模糊产生的根源为何。正如上述所说,刑罚的概念依托于刑法的体系建构,其本质就是因为刑法概念的界定与刑罚是脱离不开关系的。刑法理论界对刑法的定义不可胜数,但是总体而言可以进行以下归类:第一类是中国国内理论对刑法的定义。中国国内刑法理论界对刑法的定义大多是从犯罪和刑罚以及二者的关系出发的,如陈兴良教授在《本体刑法学》中写道“刑法,作为一门部门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二者间关系的法律。”。第二类是德国和日本理论对刑法的定义。德国及日本刑法理论对刑法的定义大多围绕着刑罚展开,如西原春夫教授对刑法作出如下定义:“刑法,是规定刑罚的法律。”,金德霍伊泽尔教授更是对围绕刑罚和安保措施对刑法做出定义:“所谓刑法就是人们利用刑罚或安保措施、矫正措施来进行威胁的那些举止方式,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会造成哪些后果。”从上述两类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本身概念的界定是脱离不开刑罚的,对此,罗克辛教授敏锐地指出“在形式的意义上,刑法是由它的惩罚方式进行定义的。”由此可见,在定义上的相互纠缠是两者界限不明的根源。
在弄明白模糊产生的本源后,笔者认为划分二者的界限首先需要从实质上即逻辑思考的模式入手。刑法学是一门体系性极强的学科,这也决定着其逻辑的贯穿具有一致性,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刑法教义学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划分刑法学的逻辑体系:刑法的根基与原则?行为论?犯罪论?刑罚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行为论应涵摄于犯罪论之中,但对该问题此处不做多余探讨)。这一逻辑体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单向性,每一个环节都是下一个环节诞生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此种推倒不可逆,究其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整个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定罪量刑的流程,如果逆推则会与实践割裂,背离刑法理论研究的初衷即说服法官。而反观刑罚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刑罚学对于刑罚的研究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某一逻辑体系单项推进的,更多体现的是从对结果的追求再到手段的探索,比起对理论一致性的追求,刑罚学更加注重社会效果的实现,因此在逻辑的思考方式上并不是学者思维,而是一种法官思维,即对某一结果有一个模糊的是非观,再去遵循这一直觉提供的方向反复验证,最终才得出体系化的结论。这一逻辑思考模式与刑法学研究中的模式有着显著不同,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实证化倾向。
最后再从形式的角度即研究方式入手去检视二者的界限。刑法的研究方式也有着广泛性,并随着近年来实证化的发展越来越开阔。但是刑法学的研究脱离不开一个基本点——刑法典的规定。正是因为刑法学对于刑法条文的忠诚和教义化的倾向[],所以使得刑法学的研究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展开,至少无法脱离太远。反观刑罚学,其研究对象和方式则不仅仅停留于对现存刑罚规范的解释说明,而是可以灵活的在规范与应然间进行视野的跳跃,从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四、刑罚学的逻辑体系
从以上横向的比较可以清晰的看出刑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内在逻辑,而这些都显著区别于刑法学和犯罪学,但是这仅仅在逻辑上通过什么不是刑罚学证成了刑罚学的独立性,对于刑罚学学科独立性的思考也应从其自身特性入手才更具有说服力。如上述对刑法学的逻辑体系的划分,每一个独立的学科都有着一个共同点的特征,即拥有自身的学科体系。刑罚学也是一样,至今为止,国内学者对刑罚学学科体系的探索不胜枚举,但总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种是由邱兴隆教授和许章润教授共同执笔的《刑罚学》所提出的刑法学体系。此体系分为四个部分即绪论篇、哲理篇、量刑篇、行刑篇。这四个部分逻辑紧密环环相扣,体现了刑罚学深邃的逻辑脉络。而且本书是我国大陆学者第一次攥写的关于刑罚学的学术专著,因此对我国大陆学者具体展开刑罚论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二种是由台湾林山田教授所攥写的《刑罚学》所开创的刑罚体系。本书讲刑罚学的体系划分为三部分,即绪论部分、刑罚理论部分以及刑罚制度部分。这一刑罚学学科体系的划分较为简便,但是基础理论奠基的意义极强。
第三种体系由美国学者约翰·维列斯·齐林在《犯罪学与刑罚学》一书中提出。他将刑罚学划分为三部分即刑罚史、近代刑罚制度以及司法上的工具。从这一体系可以看出他对刑罚体系的思考着眼点主要在于学术史的追溯,并且兼顾了比较研究的方式。
综合上述三种体系模式,笔者认为刑罚学的体系应当兼具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特点同时应尽量区分于其他学科,而这就要紧紧围绕研究对象进行展开。在逻辑起点上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刑罚,刑罚何以可能的问题,于是就引发了刑罚根据论的探讨。其次在刑罚诞生根据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才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刑罚,刑罚到底应当,于是就有了刑罚价值论的问题。再次弄清楚了刑罚存在和评价的问题后紧接其后就需要从实证的角度对刑罚配置的问题进行探讨,即刑罚该如何配置才能最大实现刑罚的功用呢?于是就诞生了刑罚配置论的问题。最后在合理配置刑罚的基础上,还应注意对刑罚适用问题的探究,即刑罚该如何执行才能发挥配置所期待的最佳效果呢?于是就产生了刑罚适用论的问题。应此,笔者认为整个刑罚学体系应当围绕一条逻辑主线上的四个基本点来构建,即刑罚根据论?刑罚价值论?刑罚配置论?刑罚适用论。如此既能保证刑罚学的体系性和逻辑性,又能保证刑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划分,使其具有独立的批判意义。
结语
前述通过横向的比对和纵向的探究在逻辑上完整证成了刑罚学的学科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笔者想对刑罚学作如下总结。
第一,刑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命题性。刑罚学专注于对各式各样的刑罚现像进行探讨,并且抽象出刑罚现象之间的关系再深入研究其中的问题,最后从不同的命题层次来揭示研究对象后隐藏的规律。
第二,刑罚学的研究方式具有实证性和逻辑性。不同于犯罪学的偏重实证研究,刑罚学不仅仅需要依靠实证的手段对刑罚进行大数据的研究,还需要在素材的演绎归纳的基础上形成逻辑体系,以保证自身理论的连贯性。
第三,刑罚学的内在逻辑具有灵活性。刑罚学的视野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灵活的在事实与理念之间轮换,做到以理念为指向,以事实为准绳。
综上所述,刑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其研究中不仅应留心其与相关学科间的相关性,更应当注重对其独立性的反思,在独立批判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剖析将更具有学术价值,也更符合刑事法科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谢青松.近代西方刑法哲学的追寻——从孟德斯鸠到李斯特[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166.
[2]邓晓芒.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78.
[3]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4]赖正直.机能主义刑法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6~77.
[5][日]西原春夫著,顾肖荣译.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5.
[6][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著,蔡桂生译.刑法总论教科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7][德]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3
[8]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J].中外法学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