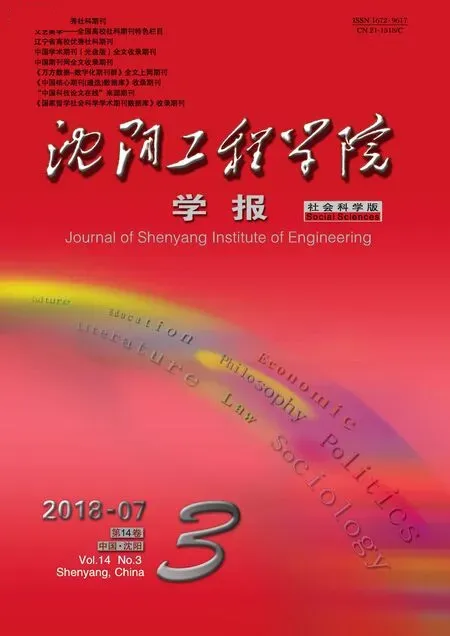经学体系建构与研究方法的转变
——当代儒学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
2018-04-03薛雷渊
薛雷渊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1]1。正如清儒皮锡瑞所说,研究一门学问不仅需要了解其发展历史,这样才能全面把握思想演变的脉络,而且需要对其发展过程中所损益的内容进行辨别,这样才能知道自己该从何处切入并且展开自己的学术思想。当代儒学的发展需要寻本溯源,才能找到其传承的方向与目标。历代学者在回顾儒学的发展历程时,经常会面对经学与子学的划分问题。而经学与子学又有许多难以分清的内容,如《孟子》,既是十三经中的一部,又是子学的组成部分,由此便又涉及诸经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当理清了儒学传承演变的源流之后,接下来将面临的课题就是用何种方式来研究传统经典,这是当代儒学创新发展最为重要的一步,乃至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传统儒学可以分为经学与子学两个部分。所谓经学,是指信仰儒家经典的一类人,通过注疏与义理阐释等方法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不断传承的学问。子学的构成则较为复杂,它在广义上本来泛指诸子之学,刘歆《七略·诸子略》就曾把诸子分为儒、墨、道、法等十类,而本文在这里主要探讨的则是狭义上的子学,即儒家诸子的学问和思想。
关于经学与子学的关系,蒋伯潜先生认为:“如《诗》辑诗歌,《书》辑史料,《礼》记礼仪,《易》论卦爻,各有其内容;而诸经所含的哲理,各寓于其中。至于诸子,则各就所见,奋笔书写,把作者底主张直接发挥出来。这就是‘经’与‘子’的不同。”[2]4因此可以说,儒家诸子之学乃是从经学中衍生并独立出来的部分,它们始终是以经学为轴心而生发演变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董子(董仲舒)”“二程子(程颢、程颐)”“朱子(朱熹)”“阳明子(王阳明)”等后代儒门诸子,其学说皆是在六经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姜广辉先生说:“有关传统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3]91由此,可以看出姜先生对于经学与子学关系的态度,也是认为经学是核心,是中轴。
回溯历史,几乎每一个文化兴盛的重要时期都得益于经学的研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等都根源于五经,并且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先秦时代最为明显,儒家哲学的创立者孔子即直接以五经作为教材,《礼记·经解》曾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两汉时期的儒学,更被直接称为“两汉经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董仲舒就是以公羊经学成名。奠定宋明理学辉煌基础的两大儒者周敦颐与张载,也都是通过对五经的研究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的代表作《通书》和《正蒙》均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不难看出,儒家历代诸子的思想几乎都是在对于经的研读中形成的,儒学亦是以经学为核心而发展演变的。
然而,与以往经学蓬勃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反,当代社会和学术界却呈现出子学更为兴盛的状况。因为子学相对经学来说,更多地表现为抽象的逻辑推理和意义阐发,这些思想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较容易地被重新诠释和解析;而五经则明显带有特定时代的具体特征,对于时代背景不甚熟悉的“时过境迁”的当代学者们,很难超越往圣先贤业已对五经做出的详尽的阐发。由于当代经学的研究难出成效,大多数学者便被迫选择了较为简单的方法,即略过经学而着重于子学研究。姜广辉先生就曾对此批评到:“经学的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3]91这样的尴尬局面需要学界同仁积极地扭转,重新将研究的重心回归更为本源性的传统经学上来。
二、经学内部的关联系统
传统儒家经学的发展,也曾经历过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经典的种类和数量由先秦的五经演变至隋唐时期的九经,到宋明时期则最终确立为十三经。对此,蒋伯潜先生曾指出:“《春秋》类底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严格言之,是传非经。《礼》类的礼记,是记非经。《论语》也只是附于‘经’的,本身也不是正式的‘经’。《孟子》一书,就其体裁论,和《论语》一样,又和其他诸子不同。《论语》既可附于‘经’,则《孟子》自然也可以作为‘经’底附属。但其直接发挥己见,则又和五经不同,而类似诸子,故也可以列入诸子。”[2]7也就是说,汉代之后由五经扩充而来的其他这些经典,严格来说只可以看做是经的附属类作品。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曾言及:“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1]39所以严格说来,除五经(六经中《乐》遗失)外,其余的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赞《周易》始,六经乃定,其后扩充入经的都是因为“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1]39。
研究经学时,不仅需要辨别上文所述的五经与其余诸经的区别,同时也要注意五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初春秋战国儒家所尊奉的经典有六种,《乐经》不幸在秦汉时遗失,只在“三礼”中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有关“乐”的记载。为了弥补《乐经》的缺失,学者应该在研究《礼》的同时考查“乐”的思想,因为礼乐原本就是相互紧密关联的一对事物。《礼记·乐记》有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以和同人心走向社会大同;礼乐的功能也具有互补性,所谓“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记·乐记》),有德君子须礼乐兼备。但是,礼乐之间也存在区别,“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由此可见,礼别同异,乐同民声,礼乐同行才能长治久安。同时,“乐”与《诗经》亦有紧密的关联,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乐”乃是诗舞乐一体的综合形式。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可见诗与礼乐一样,对于塑造儒家君子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荀子在《儒效》篇中曾指出:“《诗》言是,其志也。”杨倞注曰:“是儒之志。”[4]84《诗经》除了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期望之外,更体现着儒者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承载着儒者的志向与期许。
五经中的《尚书》与《春秋》,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部史书,二者最主要的差异是《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左史)主要记载了统治者的言论,承载的是圣人治理天下大事的功德与智慧。而《春秋》(右史)原则上以记事为主,但至孔子笔削褒贬之后,乃有微言大义存乎其间,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荀子·儒效篇》有云:“春秋言是,其微也。”杨倞注曰:“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4]85这其中最直接的就表现在《春秋》对于各国人物的称呼,有尊称、敬称,也有贱称。自此《春秋》具有了威慑诸侯的力量,从简单的编年体史书,开始变成了为后王立法之书。钱穆先生就认为《春秋》大义最突出地体现在“立一王之法,为素王改制”,并举汉昭帝五年一个京兆尹根据《春秋》毅然将太子判罪的例子,证明《春秋》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力。“可见要窥见孔子生平的心事和志向,自然应注意到《春秋》……要认真研究孔子平日之微言大义言,则非《春秋》莫属。”[5]264
在五经内部,《易经》乃为统摄群经之书。《易传·系辞传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传·乾·彖传》)又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儒者认为《易经》通过乾坤二卦的变易来推演天地生成万物的过程,因而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都已包含其中,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传·系辞传上》)。金景芳先生对此解释道:“《易经》之写作是与天地相准的,按照天地来作《易》。例如,《易经》的乾坤两卦象天地,其余各卦象天地的变化。全部《易经》,是与天地准的,与天地一样。因与天地一样,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弥纶’的意思就是概括”[6]34-35。所以《易传·系辞传上》才赞叹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由此可见,儒者认为天地之间的道理在《易经》中已经尽显完备了,而其余诸经则只是各执一理:《诗》道志,《书》道言,《礼》道行,《乐》道和,《春秋》道名分,而《易》却涵盖天下诸理。《易》乃是统摄五经的根本,它与其余诸经共同构成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
三、当代经学研究的创新方法
既然以《易》为宗统的五经乃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和根本,那么当代儒学的发展就需要大力继承经学研究的传统,并以现代理论视野开辟睿智深刻的原创性思想。而这一工作的前提,则是要选择恰当有效的研究方法。近百年来,学界对于经学的研究可谓是起起伏伏、一波三折。从民国初年废止读经的禁令,到与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的“国故”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儒学,到不久之后“文革”时期对儒家的“革命批斗”。这样一路波折,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儒学研究才开始趋于稳定。这近百年来儒学研究的发展虽然几经起伏,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民国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经学史的构建,其中的代表作有周予同先生注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范文澜的《群经概论》、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等等。而建国后,儒学研究界开始更多转向子学和专经研讨,诸经之间以及经学与子学间的关联多被割裂开来,历史上的经学家和诸子往往只是被按照历史顺序进行编撰和孤立分析,基本上忽略了对于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的把握。鉴于当下这种孤立片面的经学研究现状,建议运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重建经学史的研究框架,我们不妨称其为“经纬法”。
所谓“经纬法”,首先是以五经的传承与发展为“经”。儒家经典从先秦的五经扩展到隋唐的九经、再到宋明时期的十三经,这很好地显示出经学在面临时代问题时的机动变化和自我调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构筑了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各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也都是一脉相承、彼此相连的,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罢了。以五经为基础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正是直面这些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而提出的,因而对于传统儒学的整理和研究,不仅需要理解历代儒者自身的学术思想,更需要把握他们所面临时代的社会问题及其寻求解决的方式。这样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每个时代的经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相回应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也就可以充分地阐明经学发展过程中,五经与其后扩充的诸经典之间因社会变革而形成的连接关系。
所谓“经纬法”的“纬”,则是各个时期儒者对于经典的解释以及自身形成的独特思想。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儒者对于儒学的研习几乎都是先从读经开始,并在经典注疏与义理阐释过程中注入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这些理解都是以诸经为依据并结合时代问题而形成的,故而从横向上扩充了经学思想的内容与范围。因经典诠释而形成的思想之“纬”,可以被理解为每个时代儒学思想铺展开来的横截面。而儒家思想的繁盛与否,往往与特定时代的整体文明程度相一致。如果一个时期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繁荣,那么这个思想的横截面就会相对大一些;相反一个时期社会混乱、文化凋敝,这个面就会相对缩小。由于历代儒者的学说大多可以在五经中找到源头和归宿,因而特定时代的儒学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代经学的发展水平。运用这种“经纬法”,不仅可以了解历代经学研究的情况,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历代儒者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想。
综上所述,当代儒学的发展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寻求其源头和根本,即以五经为核心演变而来的经学体系,就像我们研究汉字的演变一样,应该从甲骨文开始,分析汉字各个阶段的变化,才能透视中国文化的根源[7]91。而对于经学思想的分析研讨,除了必须梳理其发展的历史,更需要还原其时代与社会语境,考察历代经学所直面的社会问题及其通过自身的损益来应对社会问题的方法。这一研究态度和方法,应该具有不断传承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期待传统经典的体系框架和核心观念,也能够适应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理论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