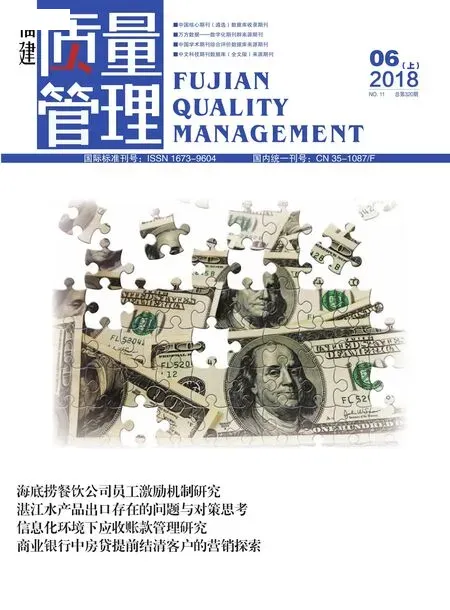浅析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
2018-04-02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被分为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合法证据会被采纳,非法证据会被排除。但在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外,还存在一类证据——瑕疵证据。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属于不合法证据的一部分,二者相伴而生,划分界限也会随着法律规范的完善而发生改变。正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将瑕疵证据通过补正证明进一步转化为合法证据有助于实现这一类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体系。
一、瑕疵证据认定和补正证明实践中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是我国最早开始涉及瑕疵证据的法律规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又进一步完善了瑕疵证据的立法内容。虽然在立法上赋予了瑕疵证据较为明确的法律地位,也规定了较为完备的瑕疵证据效力补正体系,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致使瑕疵证据的效力无法确定,同时也凸显了立法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现象。
(一)瑕疵证据规则不明、概念理解不清
《刑事诉讼法》第54条对于物证、书证的规定属于对瑕疵证据的一般立法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司法解释》)则在第四章“证据”章节规定了多样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瑕疵证据情形,证据类型也限于物证和书证,而且还包括证人证言、辨认笔录、供述、被害人供述等,瑕疵的严重情形也不是仅指“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因此《刑诉法司法解释》基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了扩张性解释。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普遍认为没有明确规定瑕疵证据的法律规范,他们更多地会选择通过司法实践经验、领导批示的方式来认定瑕疵证据。对于瑕疵证据的概念也存在模糊,实践部门有自己的认知,并且在个人和部门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法》和《刑诉法司法解释》等对于瑕疵证据的规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规范价值。
(二)瑕疵证据情形繁多、突破立法规范
实践中的瑕疵证据可以分为以下情形:取证主体不合法;收集的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范;收集证据的手段不合法;收集证据的程序不合法;收集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存有异议;证据本身以及证据之间存有矛盾等。虽然《刑诉法司法解释》对于瑕疵证据的类型进行了扩张性解释,但实践中瑕疵证据的情形远远超出了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范围,瑕疵证据情形繁多,既涉及证据的性问题,也存在违反法律规范的情形,还有些属于技术操作失误的情形,更有甚者,实践中工作人员借用瑕疵证据的补正证明措施对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材料进行补正。
(三)瑕疵证据处理方式多样、随意性强
目前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主要为:(1)直接退回;(2)自行补查;(3)直接排除;(4)不予处理;其中直接退回又分为四种处理方式:(1)重新取证;(2)补充完善;(3)解释说明;(4)不告知怎样做。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具有多样性,但是不予处理的方式表明实践中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随意性很强;直接退回中不告知怎样做的方式也是不符合瑕疵证据相关法律规范的。
(四)瑕疵证据补正机会不限、补正成为常态
瑕疵证据在公、检、法三个机关进行补正的情形都有发生,补正次数从1次、2次、3次到不限制的情况都存在。相比之下,瑕疵证据在法院不限制补正的情形更多。瑕疵证据补正次数不限的情况表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缺乏对于瑕疵证据补正次数的明确规定和限制,致使实践中补正机会不限成为常态,实务部门利用瑕疵证据补正的方式来加强证据的效力,这和瑕疵证据法律体系最初设立的目的相背离。
二、瑕疵证据司法实践问题的原因分析
瑕疵证据补正证明体系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但其缺乏相应的实施规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其在实践中并不能得到良好的运行效果。我国理论界目前对瑕疵证据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效力、补正方式、补正程序等方面,学说众多且繁杂;其次,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瑕疵证据的理论层面,对于瑕疵证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极少,致使研究的成果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司法实践。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认识偏差,较多矛盾的存在冲击了立法规范的实际效力。
(一)瑕疵证据规范体系逻辑不清致使概念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三种类型的证据: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二是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三是收集时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对于这三种类型的证据,第54条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其中哪些属于非法证据,哪些属于瑕疵证据。如果将《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中规定的可以给予补正机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和书证认定为瑕疵证据的话,《刑诉法司法解释》则给予了瑕疵证据更为广泛的范围,类型不限于物证和书证,同时也不限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这一个情形。但是在《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章第八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又进一步对“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进行了解释。从这一点来看,《刑诉法司法解释》又是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证”物证和书证当作非法证据来看的,并且在这一节中给予了法官自由裁量证据影响司法公正“严重程度”和是否应当予以排除的权力。瑕疵证据法律规范体系的逻辑不清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瑕疵证据的认定标准模糊,司法解释给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也造成了“瑕疵证据”排除思想的出现。
(二)理论界的研究繁多学说林立致使认识混乱
我国关于证据的立法中规定了“证据材料”、“定案的根据”、书证、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被排除适用的“非法证据”、收集时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经审查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及依法可以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瑕疵证据”等多种类型的证据。法律规范中这么繁多的证据类型,很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淆。与此同时,理论界也进行了理论性的概念界定和分类解读,像万毅先生在《论瑕疵证据——以“两个<证据规定>”为分析对象》中“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的三分法;还有“广义的非法证据”和“狭义的非法证据”之分;“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证据资格待定的证据”也是常用的称谓。另外,根据证据不同的排除方式,陈瑞华先生在《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中又提出了非法证据的“不可补正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的“可补充排除规则”,而“不可补正排除规则”又可以分为“强制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排除规则”两种类型。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我国立法中的证据概念、类型等有所帮助,但同时也因为理论界的分歧导致实践中对瑕疵证据的概念、属性、类型等产生混淆。
(三)立法与实践之间存在偏差冲击规范实效
2010年出台的《两个规定》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采取承认和接受司法实践经验性的做法来对瑕疵证据进行规范,即通过法律来认可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和纠正功能以及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发现证据瑕疵要求公诉人员进行补正和解释说明的习惯性做法,使之合法化。但这种相对比较妥协的立法方式却会使得通过对瑕疵证据立法来提高司法证明合法化的立法目的与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通过诉讼阶段不断补正证据效力的做法相互矛盾,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的追诉犯罪的职业观念导致司法人员为了追诉犯罪而不断追求形式性的合法化的证据资格,即不断地通过予以补正和解释性说明的方式完善证据资格,这和最初的立法目的背道相驰的。司法实践中更多地选择通过司法实践经验或通过领导批示来对待瑕疵证据的做法不断冲击相关法律规范的实际效力。
三、完善瑕疵证据补正证明体系的建议
在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瑕疵证据的存在不可避免。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有别,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帮助作用。目前的瑕疵证据补正证明体系仍然存在问题需要理论去探索,需要不断通过实践去解决。基于目前的研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在立法层面,应当明确瑕疵证据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我国的证据体系,提高瑕疵证据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逐步减少瑕疵证据的出现,进而提高司法质量。瑕疵证据虽然可以帮助认定事实,之前的立法也规定瑕疵证据可以通过补正效力或是作出合理解释的方式完善证据资格成为定案的依据,但其存在本身就带有不合法性。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明确瑕疵证据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瑕疵证据的存在,而不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而放弃程序公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推动我国证据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2.在实践层面,统一公、检、法三机关瑕疵证据认定标准,界定诉讼证明职能分工,发挥瑕疵证据法律规范的程序性价值。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司法实践由注重实体性价值逐渐向关注实体性价值也重视程序性价值转变,针对证据的程序性规范也逐步完善起来,但是针对瑕疵证据的程序性规范却很少。公、检、法三机关在认定瑕疵证据时标准不一,法官在认定瑕疵证据资格时的裁量权也较大,最终导致瑕疵证据的处理方式随意性强。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当统一公、检、法的认定标准,将证据瑕疵的认定与瑕疵证据资格的最终认定职能进行合理分工,将瑕疵证据的情形具体化,通过瑕疵证据的程序性规范保障瑕疵证据效力的合法性。
3.在制度层面,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之上完善我国的瑕疵证据制度体系。瑕疵证据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瑕疵证据的认定和效力补正、资格完善制度。为了更好地实现瑕疵证据的认定和证据资格完善的目的,还应该建立一些具体制度。首先,建立瑕疵证据举证时效制度,通过确立一定的举证时限来减少实践中瑕疵证据补正次数不限的情形,让证据效力补正不再成为常态。其次,建立瑕疵证据补正责任制度,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和检查机关瑕疵证据效力补正的权力,同样也应当设立相应的责任制度,法律责任的设立可以更好地监督侦查主体和检察主体的行为,不断推进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化。
【参考文献】
[1]吕泽华.我国瑕疵证据补正证明的实证分析与理论再构[J].法学论坛.2017(4)
[2]任华哲,郭寅颖.论刑事诉讼中的瑕疵证据[J].法学评论.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