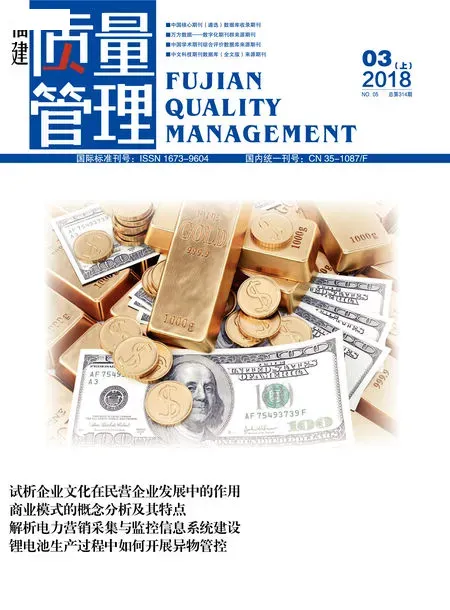关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问题的思考
——兼评《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
2018-04-02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快到令人咋舌。隔几天就会出现一个爆炸性的话题,网民们争先恐后地隔着手机或电脑屏幕发表意见。在这些话题中,有一类话题令笔者感到最为沉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问题。人一生之中最脆弱、无助的时期莫过于幼年和迟暮之时,尊老爱幼也因此成为我们所宣扬的传统美德。但是,该传统美德在当今是否得到有效传承,尚待考证。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例不胜枚举。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李吉顺强奸、猥亵儿童案,董琦潜入中学宿舍强奸多名女生案,魏连志采取哄骗等手段猥亵多名男童案,李沛新猥亵继女案等典型案例。更有湖南省永州市一名十二岁的幼女被强奸后怀孕,为取证被迫生子案等。以上现状引发思考,在性侵案件中,民法能够给予未成年人什么保护呢?
一、民法上的保护——评价《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
刑法是法律最后的、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其中的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等均是针对相关性侵犯罪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司法部四部门也于2013年10月2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通知,以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的恶劣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我国的民法为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提供了什么样的保护呢?
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文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该条款是诉讼时效制度的特殊规定,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体现。但是,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刑事追诉时效的规定已经能够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民法总则》再做这种规定有越俎代庖之嫌,并且规定在《民法总则》之中也与整个总则的体系不相协调。还有观点认为,当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时,如果不能正确表达意志,其法定代理人就应该代替未成年人行使权利。如果法定代理人怠于履行相应的职责,那么未成年人从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故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给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成年后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
对此,笔者认为每个法条都应当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其背后的立法目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的立法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其旨在使未成年人得到更加合理的保护,从而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外,民法上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针对该条本身的内容,即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笔者认为确有不妥。诉讼时效自身存在的理由是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不要躺在权利的阳光下睡觉,本质是一种对权利的限制,是一种反权利的制度。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在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下,争议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使权利人的实体权利真正得以落实。反之,不受诉讼时效约束的民事权利恰恰造成对权利的保护不及时、不充分,拉长了主张权利的时间。加之,我国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特点之一就是被害人低龄化,待成年之后再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应证据的采集变得极其困难。因此,从《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本身角度而言,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方式来达到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恐怕很难。
二、民法上的保护——明确性自主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如果要真正实现《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立法目的,笔者认为更应当着眼于其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后在民法上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权利,值得肯定。不过,笔者认为该项请求权究竟是什么种类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成年人又具体是何种权利受到了侵害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相应的民事法律中应加以明确。
性侵未成年人一般会侵犯未成年人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从而产生不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一是侵犯未成年人的身体权或健康权,这两种权利在我国民法上均有明确规定。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权人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受害人应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二是侵犯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权,该权利在我国民法的民事权利中尚未明确。该项侵害主要是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受害人应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人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现有的法律中,未成年人因遭受性侵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何种民事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呢?笔者认为,在法律还没有将性自主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规定时,可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和第一百一十条关于“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和“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相关规定,以一般人格权作为基础。从一般人格权的角度来讲,其具有补充人格权立法不足的作用。当具体人格权规定不充分时,一般人格权应发挥功能,担负起人格利益保护的作用。因此,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权,属于人格尊严的一般人格权保护范畴。
笔者认为,可明确性自主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后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区别于一般的精神损害赔偿,出台相关的解释,予以特殊保护。此外,《民法总则》的第一百零九条和第一百一十条并没有明确性自主权。希望将来,性自主权能够在民法中得以具体化。
三、结语
笔者曾看过一本心理纪实书籍,主人公比利因童年时期父亲因故自杀,母亲改嫁,后继父对其实施残忍虐待及性侵的悲惨经历,分裂出了包括比利在内的二十四个不同人格,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并因其他人格的行为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剥夺自由,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受到社会的排斥。事实上,比利是一名天才少年。一名作家想要写比利的故事,比利应允后说“希望人们认识到虐待儿童的后果”。从比利身上,大致可见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不良后果的缩影。希望法律对未成年人能够有更加全方位的保护。
[1]蒋丽虹,论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特殊保护,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2]钟维松,关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问题,法制与社会,2017(10);
[3]谢登科,论性侵未成年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学术交流,2014(11);
[4]杨立新,民法总则给予未成年人诉讼时效特别保护,检察日报,2017.4.5;
[5]周杲,未成年人受性侵特别诉讼时效条款之商榷,人民法院报,201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