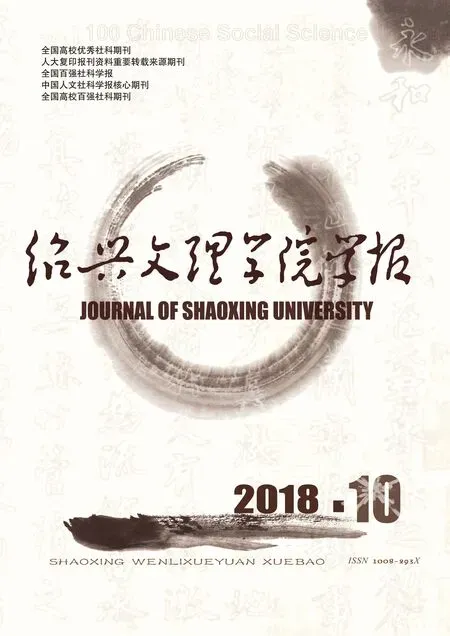儿童数字-空间编码的证据及教育启示
2018-04-02李梦霞
李梦霞 任 强
(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是感知-运动的结果[1-3]。在数字认知的研究中,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建立在基础的感知-运动之上的典型表现就是抽象的数字认知是建立在具象的外在空间之上[4-6]。从表面上看,数字认知可能是脱离客体的纯数字符号加工,并不需要任何空间信息的参与,但诸多事实都表明了数字和空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在学校教育中发现,那些数学成绩相对优异的学生往往都具有相对较好的空间能力,这一空间能力具体表现为空间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这些事实似乎都意味着数字的加工和编码方式可能与空间信息的加工和编码方式之间有着某种关联。1980年Galton在《Nature》上发表了关于数字具有空间特性的文章,从科学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了数字的加工和编码方式与空间编码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7-8]。
众多研究证据也证实了对抽象数字的加工可以自动地激活它的空间编码[4-6]。例如,Deheane等人的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对数字进行奇偶判断时,被试会表现出对相对较小的数字(如1或者2)用左手反应快,对相对较大的数字(如8或者9)用右手反应快的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存在一种空间-数字的反应编码联合效应(the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SNARC),即SNARC效应。SNARC效应是指个体在看到相对小的数字和相对大的数字时,其动作反应会引起内在的空间反应偏好。SNARC效应反应了大脑中存在着小数字位于左侧,大数字位于右侧的一条自左向右方向的心理数字线[4]。SNARC效应即是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位置表征和空间位置反应一致性的结果。
来自不同研究的证据甚至显示,人类先天拥有联合数字与空间的能力[9-10]。如de Hevia和Spelke研究发现婴儿可以将增加的点的数量与增加的线段长度联合起来,而不是将其与减少的线段长度联合起来[9]。实际上,涉及数字表征的大脑区域与涉及区分空间维度,如大小,长度的部分重叠,意味着数字表征和空间表征共用了相同区域的大脑皮层[10],或者说数字认知和空间表征之间可能具有共同的脑机制[11]。
数字认知与空间的联合方式也会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对数字的空间表征方式会受到已有阅读和书写习惯的影响。例如,以西方主流文化为主的阅读和书写习惯为是自左向右的方向。Moyer和Landauer使用了简单的大小分类任务对西方主流阅读和书写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进行研究,即,要求被试对同时呈现的两个数字进行大小判断,并指出相对较大的那个数字。结果出现了数字与空间表征关联的两个基本的效应:距离效应和大小效应。距离效应即是两个同时呈现的数字之间相差越大,判断并选择较大数字所用的反应时(RT)越短;大小效应即是当两组分别同时呈现的两个数字之间距离相同时(如1-2,或8-9),需要判断和比较的数字组越大,反应时(RT)相对越长[12]。数字认知中的距离效应和大小效应等研究了从不同侧面验证了人类数字认知的表征方式是基于心理数字线(metal number line,MNL)的观点[13]。根据心理数字线隐喻,大脑表征数字的距离的方式就像是物理空间上表示距离的方式一样,对在大小上接近的数字的表征,也像是物理空间上的重叠方式一样。
一、数字-空间编码的具身认知证据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通过身体的经验以及身体的活动方式而形成的。通俗地讲,具身认知理论主张把“把心理放入大脑里,把大脑放入身体内,把身体放入环境内。”叶浩生将具身认知观归纳为:认知既是具身的,又是嵌入的;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构成了一体的认知系统。此处的“身体”概念不仅仅是指脑或神经机制等身体的生理解剖学结构,而且还包括了身体结构、状态、活动方式、以及特殊感觉-运动通道等。具身认知理论非常强调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对认知活动的影响,由于具身认知本身从三个层面反映心理现象的产生,即,大脑与身体的特殊感觉运动通道对认知的影响;身体状态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以及环境对认知的影响[14-16]。因此,不同层面的具身经验对数字-空间编码均有影响。
(一)身体姿势对数字-空间编码的影响
双手的姿势可能会影响数字-空间联合的方向。Dehaene等人采用奇偶判断任务,但是打破正常的左、右手空间顺序,要求被试交叉左右手进行反应,结果仍然出现了典型的SNARC效应。也即是说无论左、右手是否交叉,SNARC效应似乎是以身体中心为参照的,均是表现出身体左侧对小数字反应相对较快,身体右侧对大数字反应相对较快[4]。Wood等人复制了Deheane等人1993年的研究。这两个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Wood采用了相对较大的样本(32人)使用了四种数字符号(阿拉伯数字、文字数字、声音呈现的文字数字和骰子)。研究结果发现,双手交叉后没有出现SNARC效应。这是因为双手交叉以后,除了交叉以后过的左、右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是自左向右的。因此,身体的表征与数字的空间表征一致;而交叉以后的左手和右手需要表征的则分别是数字线的右侧和左侧,这时左、右手的表征与数字的空间表征特性是相反的。同时,由于双手交叉以后左、右手的空间表征与除去双手之外的其他身体的空间表征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没有出现SNARC效应[17]。
Riello和Rusconi要求被试分别使用单手(左、右手)手掌向下的姿势和手掌向上的姿势进行大小比较任务和奇偶判断任务,这些被试的两只手数数的方向均是从大拇指到小拇指。结果发现,当手掌向下时,右手出现典型的单手SNARC效应,但左手未出现SNARC效应;当手掌向上时,左手出现典型的单手SNARC效应,但右手未出现SNARC效应。这一单手SNARC效应的研究证实了数字-空间联合的心理数字线解释。支持了以手为单位的左、右空间参照,但是否定了以身体为单位的左、右空间参照[18]。
Eerland,Guadalupe和Zwaan研究表明身体的物理状态会影响数量的表征。该研究要求被试处于不同的身体倾斜姿态下去估计埃菲尔铁塔的高度。结果表明,当要求被试身体左倾时其对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估计明显低于要求被试身体正立时和身体右倾时对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估计[19]。张丽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被试当前身体的物理状态对其数量表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参与任务的身体状态与数字表征的空间特性相一致时,即两者均与自左向右的线性表征规则一致时,才会出现SNARC效应。当要求被试单手完成反应任务时,身体没有形成自左向右的空间线性表征,单手的空间特性没有与数字的空间特性对应起来,所以没有SNARC效应出现。当在两个被试一个人使用左手,另一个人使用右手的合作情景实验时,虽然每个被试只能使用一只手进行按键反应,但是由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与其合作的被试的动作也被表征。所以,在合作情境下对被试的空间表征而言,实际上就跟一个人同时使用自己的两只手进行的实验是一样的,因而也出现了SNARC效应[20]。
Crollen,Dormal,Seron,Lepore和Collignon通过分别对早盲被试、晚盲被试和正常被试进行了大小比较任务和奇偶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在大小比较任务中,仅有早盲组被试在双手交叉反应的条件下,出现了反转的SNARC效应,其他两组均没有出现反转的SNARC效应。而在奇偶判断任务中,双手交叉反应条件下,三组被试均未出现反转的SNARC效应[21]。因为奇偶判断任务被认为更基于数字的言语-空间联合,而大小比较任务更基于数字的视觉-空间联合。说明了具身的视觉经验促使了数字的视觉-空间表征的外在整合系统的发展。
(二)手指数数的顺序对数字-空间编码的影响
Fischer最早用手指数数的顺序来解释SNARC效应。Fischer先用使用问卷调查得出445名成年被试中无论他们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有三分之二的人习惯从左手开始数数。其次,分别将53名从左手开始数数的被试分为一组,将47名从右手开始数数的被试分为另一组,进行了奇偶判断任务。结果从左手开始数数的被试组出现了SNARC效应,从右手开始数数的被试组未出现SNARC效应。因此,Fisher认为,手指数数的习惯可能促成了成年人的数字-空间的联合效应[22]。Lindemann等人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900个中东国家(如,伊朗)和西方国家(如欧洲和美国)的被试,调查当用手指数1-10的数时,他们的手指和数字空间表征之间的映射关系。结果发现,被试的双手数数模式揭示了手指数数顺序和开始手指的明显的跨文化差异。大部分的西方被试从左手开始数数,并且将数字1与拇指相联合;大部分中东被试从右手开始数数,并且将数字1与小拇指相联合。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种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感知运动习惯。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手指数数过程中,两只手转换中的对称策略(即两只手或者均从大拇指开始数数,或者均从小拇指开始数数)和空间方向一致策略(即两只手均是从相同的方向开始数数)对数字-空间表征方向的影响作用相同[23]。
Fabbri和Guarini选取了184名一到四年级的儿童和42名成年人,分别通过外显实验任务(数字线估计任务)和内隐实验任务(数字线分半任务)进行了手指数数顺序考查了手指数数顺序对儿童和成年人数字-空间表征的影响。结果表明,手指数数顺序没有影响到外显数字-空间实验任务的成绩,但是影响了内隐数字-空间实验任务的成绩[24]。这些研究一方面似乎证实了手指数数顺序对SNARC效应中数字-空间表征方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SNARC效应数字-空间表征方向中的单手左右空间参照证据的存在。
(三)身体运动对数字-空间编码的影响
身体运动同样也可能会影响SNARC效应产生影响。Loetscher等人采用要求数字生成任务(demanding number generation task),该任务要求被试闭上眼睛,并随机报告1到30之间的数字。每个被试需要完成两次随机数字报告任务,其中的一次是作为基线水平,要求他们头部保持垂直,另一次则是要求他们的头部向左或向右转。对所有被试而言,一半的被试在生成随机数字时要求他们想象直尺上1到30之间的数字;另一半的被试没有要求。因变量是被试生成小数字(1到15之间)的频次。结果显示,若被试头部是向右转时,其随机报告的小数字频次相对少于其头部向右转时报告的小数字频次。尤其是当要求被试想象着直尺上1到30之间的数字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要求被试想象直尺上1到30之间的数字时,他们在头部左转条件下报告的小数字频次显著多于头部右转条件下报告的小数字频次。另外,当同样是头部右转条件下,当要求被试想象直尺上的数字时,报告的小数字频次也显著多于没有想象直尺条件下报告的小数字频次。Loetscher等人认为头部运动刺激了心理数字线上不同位置的数字的激活。因此也表现出头部向左运动与小数字联合,向右运动与大数字联合的趋势[25]。
随后,Loetscher等人招募了12名右利手男性被试,通过随机数字生成任务和眼动研究来考查生成的数字大小与眼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实验要求被试随机报告1-30之间的数字,并同时记录被试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当被试随机生成的数字比前一个数字小时,会表现出向左或者向下的眼动运动;当随机生成的数字比前一个数字大时,会表现出向右或者向上的眼动运动。同时,Loetscher等人进一步通过统计考查了随机生成的数字和前一个数字之差与眼动运动的距离之间的关系。他们以随机生成的数字与前一个数字之差为因变量,以水平或者垂直方向眼动运动的距离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眼动运动的距离越大,被试随机生成的数字与前一个数字之差越大;当眼动运动的距离越小,被试随机生成的数字与前一个数字之差越小[26]。可见,通过眼动实验,也表现出了大数字与身体运动的向右或者向上相联结,小数字与身体运动的向左或者向下相联结的趋势。
Hartmann等人通过3个系列实验同样证实了身体运动对数字-空间联合的影响。实验1使用随机数字生成任务(random-number generation task),结果发现,身体向左移动或者向下移动可以易化对小数字的生成;当身体向右移动或者向上移动时,可以易化对大数字的生成。实验2采用以听觉形式呈现的大小判断任务的也表现出身体左转和右转对数字认知的影响。实验3中,被试被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并且在要求被试探测运动方向的同时,向其呈现小数字或者大数字。当探测运动方向有难度时,被试听到小数字对向左移动的探测反应相对较快,听到大数字对向右移动的探测反应相对较快。Hartmann等人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对SNARC效应进行验证,但是也同样反映出典型的SNARC效应的趋势。即表现出身体左侧移动或转动与小数字相联合,身体右侧移动或转动与大数字相联合的趋势。同时,这一研究既证实了身体运动对数字认知的影响,反过来也证实了数字认知对身体运动辨别的影响[27]。
二、儿童数字-空间编码研究的证据
目前儿童数字-空间编码的研究主要集中SNARC效应研究以及数字线估计研究两个领域。
(一)儿童SNARC效应研究的证据
第一个关于儿童SNARC效应的发展研究是Berch等人所做的研究。该研究使用奇偶判断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上呈现的数字是奇数还是偶数),研究发现,9岁之前的儿童存在SNARC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SNARC效应逐渐减弱[28]。第二个关于儿童SNARC效应的研究是Bachot等人所做的研究。该研究选取的是9岁有视觉障碍的儿童和匹配组儿童作被试,采用大小对比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上呈现的数字比5大还是比5小)。研究结果发现,匹配组儿童显示出了SNARC效应,视觉障碍组儿童组没有出现SNARC效应[29]。第三个关于儿童SNARC效应的研究是由Van Galen和Reitsma开展的。该研究选采用大小比较任务,对7、8、9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7岁儿童在大小比较任务中显示出了SNARC效应,表明7岁儿童表征数字大小的方式与成人相同,即他们把小的数字与空间位置的左边联系在一起,把大的数字与空间位置的右边联系在一起[30]。与西方儿童的研究结果不同,中国儿童早在5岁就表现出了SNARC效应。例如,周广东等人以中国儿童为被试,采用相对简单的数字颜色判断任务以及数量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当采用相对较为简单的颜色判断任务时,中国儿童在5.5岁时就呈现出显著的SNARC效应。但当采用数量判断任务时,中国儿童在5.8岁时才会出现显著的SNARC效应[31]。Hoffmann等人以及Patro 和 Haman随后的研究也发现了儿童数字空间表征的SNARC效应出现在学龄前或者幼儿园阶段[32-33]。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7个月的婴儿也表现出随着数字由小到大的递增,也出现了从左向右的空间反应偏好,但这种空间反应偏好并不稳定[34],它可能会受到情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35-36]。
(二)儿童数字线估计研究的证据
数字与空间关系的研究的另一个小的领域集中在数字空间表征模式领域。测量数字空间表征模式的经典的方法是,给被试呈现一个带有两个端点(如0和100)的线段,让被试画出某个数字(如68)在数字线上的位置。儿童最初仅是凭直觉将数字和空间表征联合,他们没有将数字线以精确的线性方式表征,更多地是以不精确的对数方式表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数字线的表征越来越倾向于精确的线性方式。
诸多的研究也表明年幼的儿童对数字的直觉表征是对数形式的,即将数字对应在心理数字线段上时,小数字之间的间距大于大数字之间的间距[37-39]。如,Siegler和Booth的研究发现,一年级儿童的1-10的数字空间表征是线性的,对0-100的数字空间表征是对数的。大部分二年级儿童对0-100的数字空间表征变为线性的,但是对0-1000的数字空间表征仍是对数的。对0-1000的数字空间表征大部分儿童直到小学四年级才变为线性表征[38]。国内周广东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儿童数字估计的发展模式与上述Siegler和Booth、Booth和Siegler以及Siegler和Opfer研究结果相似,并且我国儿童对数字的线性表征的出现要早于美国儿童[31]。Barth和Paladino认为,所有年龄的个体在估计数字在心理线上的位置时,均使用一个相同的比例策略,年长的儿童使用了更接近线性的策略是因为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数字经验的积累,拥有了更准确的数字线端点知识[40]。
当儿童发展出线性数字表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丢失对数表征;在不熟悉的情景中,如表征更大的数字时,儿童仍使用对数表征并且数字的线性空间表征仅在使用阿拉伯数字时使用。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成人也不能对非符号的数字(如点矩阵)进行线性表征,而只能进行对数表征[11,41]。
三、数字—空间表征与儿童数学能力的关系及启示
个体的数字-空间表征能力可能对数学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大小分类任务中表现出强的SNARC效应的学龄前儿童具备了相对更好的数字知识和数字认识能力,例如,他们可以按照顺序写出更多的阿拉伯数字[32]。数字-空间表征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表明,个体对于数字任务的线性表征能力可以预测其数学能力的发展;在数字线任务中呈现出线性表征的儿童,其在数学计算任务中的成绩好于对数表征的儿童[37]。相反,数学学习困难儿童在数字线估计任务中的表现相对较差[42-43]。此外,通过感知-运动训练不但可以提高学龄前儿童的数字-空间表征能力,也可以提高他们在数字加法任务和数字转换任务的成绩[44-45]。同样,通过感知-运动训练提高儿童的线性数字表征能力也会促进其数字推理成绩的大幅提升[37]。
数学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数学学习的基础认知机制的理解同样非常重要。综上可知,当前研究已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介绍了数字-空间能力对数学能力的影响,或者说数字-空间表征可能是数学能力的认知基础。现实的教育情境中经常会出现儿童在学习数学时感到困难,但通过学校教育或者题海战术并不能有效提升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现象。儿童的数学能力不能有效提升的现象可能是学生早期更为基础的数字-空间表征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致。对于这类儿童,可以尝试通过对其进行感知-运动训练以促进数字—空间表征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儿童的数学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SMITH L B. Cognition as a dynamic system: Principles from embodiment[J]. Developmental Review,2005,25(3-4),278-298.
[2]SMITH L, GASSER M. The development of embodied cognition: six lessons from babies[J]. Artificial Life,2005(11):13-29.
[3]WILSON M. Six view of embodied cognition[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2002(9):625-636.
[4]DEHAENE S, BOSSINI S, GIRAUX P.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parity and number magnitud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1993,122(3):371-396.
[5]DEHAENE S, COHEN L. Cultural recycling of cortical maps[J]. Neuron,2007,56(2):384-398.
[6]HUBBARD E M, PIAZZA M, PINEL P,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number and space in parietal cortex[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05,6(6):435-448.
[7]GALTON F. Visualised numerals[J]. Nature,1880,21:252-256.
[8]GALTON F. Visualised numerals[J]. Nature,1880,22:494-495.
[9]DE HEVIA M D, SPELKE E S. Number-space mapping in human infants[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21:653-660.
[10]PINEL P, PIAZZA M, LE BIHAN D,et al. Distributed and overlapping cerebral representations of number, size, and luminance during comparative judgments[J]. Neuron,2004,41:983-993.
[11]DEHAENE S, IZARD V, SPELKE E, et al. Log or linear? Distinct intuitions of the number scale in Western and Amazonian indigene cultures[J].Science,2008,320:1217-1220.
[12]MOYER R S, LANDAUER T K. Time required for judgements of numerical inequality[J]. Nature,1967,215(5109):1519-1520.
[13]RESTLE F. Speed of adding and comparing numb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70,83(2):274-278.
[14]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5):705-710.
[15]陈巍,汪寅.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教育:新“神经神话”的诞生[J].教育研究,2015(2):92-101.
[16]陈巍,李恒威.直接社会知觉与理解他心的神经现象学主张[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46-58.
[17]WOOD G, WILLMES K, NUERK H C, et al. On the cognitive link between space and numb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SNARC effect[J]. Psychology Science Quarterly,2008,50(4):489.
[18]RIELLO M, RUSCONI E. Unimanual SNARC Effect: Hand Matter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1,2:372.
[19]EERLAND A, GUADALUPE T M, ZWAAN R A. Leaning to the left makes the eiffel tower seem smaller: posture-modulated estim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1,22(12):1511-1514.
[20]张丽,陈雪梅,王琦,等.身体形式和社会环境对SNARC效应的影响:基于具身认知观的理解[J].心理学报,2012,44(10):1309-1317.
[21]CROLLEN V, DORMAL G, SERON X, et al. Embodied numbers: the role of vi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umber-space interactions[J]. Cortex,2013,49(1):276-283.
[22]FISCHER M H. Finger counting habits modulate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s[J]. Cortex,2008,44(4):386-392.
[23]LINDEMANN O, ALIPOUR A, FISCHER M H. Finger counting habits in middle eastern and western individuals: an online survey[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11,42(4):566-578.
[24]FABBRI M, GUARINI A. Finger counting habit and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in children and adults[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2016,40(2):45-53.
[25]LOETSCHER T, SCHWARZ U, SCHUBIGER M, et al. Head turns bias the brain's internal random generator[J]. Current Biology,2008,18(2):R60-62.
[26]LOETSCHER T, BOCKISCH C J, NICHOLLS M E R, et al. Eye position predicts what number you have in mind[J]. Current Biology,2010,20(6):R264-265.
[27]HARTMANN M, GARBHERR L, MAST F W. Moving along the mental number line:interactions between whole-body motion and numerical cogni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2012,38(6):1416-1427.
[28]BERCH D B, FOLEY E J, HILL R J, et al. Extracting parity and magnitude from Arabic numerals: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number process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1999,74(4):286-308.
[29]BACHOT J G W F. Number sense in children with visuospatial disabilities: Orientation of the mental number line[J]. Psychology Science,2005,47:172-183.
[30]VAN GALEN M S, REITSMA P. Developing access to number magnitude: A study of the SNARC effect in 7-to 9-year-old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08,101(2):99-113.
[31]周广东,莫雷,温红博.儿童数字估计的表征模式与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4):21-29.
[32]HOFFMANN D, HORMUNG C, MARTIN R, et al. Developing number-space associations: SNARC effects using a color discrimination task in 5-year-old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13,116(4):775-791.
[33]PATRO K, HAMAN M. The spatial-numerical congruity effect in preschool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12,111(3):534-542.
[34]DE HEVIA M D, GIRELLI L, ADDABBO M, et al. Human infants' preference for left-to-right oriented increasing numerical sequences[J].PLoS One,2014,9(5):e96412.
[35]MCCRINK K, SHAKI S, BERKOWITZ T. Culturally-Driven Biases in Preschoolers' Spatial Search Strategies for Ordinal and Non-Ordinal Dimensions[J]. Cognitive Development,2014,30:1-14.
[36]NUERK H C, PATRO K, CRESS U, et al. How space-number associations may be created in preliterate children: six distinct mechanism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5:6.
[37]BOOTH J L, SIEGLER R S. Developmental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re numerical estim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6,42(1):189-201.
[38]SIEGLER R S, BOOTH J L. Development of numerical estimation in young children[J]. Child Development,2004,75:428-444.
[39]SIEGLER R S, OPFER J E. The development of numerical estimation: Evidence for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numerical quantity[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3,14:237-243.
[40]BARTH H C, PALADINO A M. The development of numerical estimation: Evidence against a representational shift[J]. Developmental Science,2011,14:125-135.
[41]THOMPSON C A, SIEGLER R S. Linear numerical-magnitude representations aid children’s memory for numbers[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21:1274-1281.
[42]GEARY D C, HOARD M K, NUGENT L, et al. Mathematical cognition deficits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persistent low achievement: A five-year p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2,104:206-223.
[43]GEARY D C, HOARD M K, NUGENT L, et al. Development of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s in children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sability[J]. 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2008,33:277-299.
[44]LANDERL K. Development of numerical processing in children with typical and dyscalculic arithmetic skills—a longitudinal stud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4: 459.
[44]LINK T, MOELLER K, HUBER S, et al. Walk the number line: An embodied training of numerical concepts[J]. Trends in 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 2013, 2(2): 74-84.
[45]FISCHER U, MOELLER K, HUBER S, et al. Full-body movement in numerical trainings: A pilot study with an interactive whiteboar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ious Games,2015,2(4):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