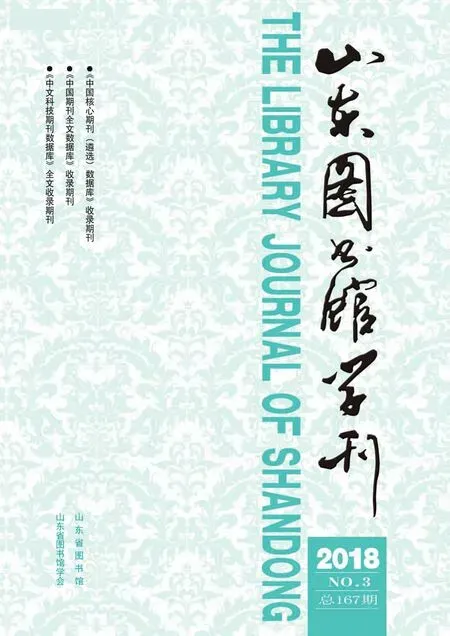《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考辨
2018-04-01赵嘉
赵 嘉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明末以来,编刻丛书之风日盛,种类繁多,延续至有清一代,方兴未艾。书坊所刻丛书本,因数量众多而又往往疏于校勘,所以长期以来少有人从版本学、刻书史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秘书廿一种》即为其中之一。
1 汪士汉对吴琯《古今逸史》本《白虎通》的修改
汪士汉,清初人,字闇然,婺源城西人,岁贡,著述有《四书传旨》《易经集解》《古今记林》《祖书存余》《集古山房文集》[1]。其所刊刻之《古今记林》《秘书廿一种》被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汪士汉清初所印《秘书廿一种》不仅在内容上不出明代万历年间吴琯所刻《古今逸史》之范围,而且还直接使用了这些书版。后来这些版片最终损坏,但汪士汉及其后人仍依照原来的行款加以翻刻,可见《古今逸史》本对汪氏《秘书廿一种》影响之深。
汪士汉在直接使用《古今逸史》本版片之前,对其中一些地方进行了修改,就《白虎通》而言,主要有以下几处:
1.1 撤下原书前《白虎通德论序》《题白虎通德论》两篇序文,换上《白虎通德论》《〈白虎〉〈风俗〉二通合编总论》
吴琯所刻两篇序文虽然署名与元大德本《白虎通》序作者相同,分别是严度和张楷,但细审内容,在篇名和内容上都与元本有差异,却与明嘉靖年间傅钥本相同,说明吴氏当时并未见到大德本,参考的是之前的明本*按,元大德本《白虎通》又称无锡州学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现藏上海图书馆,所用为《中华再造善本》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所用为民国间《景元明善本丛书》本。两本在序文上的区别在于:第一篇序文,前者并无篇名,后者作《题白虎通德论》,且文字较前者多出首一段;第二篇序文,开篇第二句,前者作“然不知出于何代”,后者“何”作“止”,前者篇名作《白虎通序》,后者作《白虎通德论序》。。
汪士汉换上的《白虎通德论》,前半部分截取自明刻《题白虎通德论》的后半段,后半部分的按语则是对班固生平介绍以及王士贞《读〈白虎通〉》中评语的引用。另一篇《〈白虎〉〈风俗〉二通合编总论》则略显牵强,因为在《古今逸史》《秘书廿一种》中,《白虎通》和《风俗通》都不是相连的,中间都隔有他人著述,因此并非合编关系,或是汪氏参考其它与合编相关版本的序跋而来*按,明末钟惺编有《秘书九种》,其中第二种、第三种分别为《白虎通德论》和《风俗通义》,此书现已稀见,汪氏或即以此书为参考。。
总之,原先的两篇序文占书版一片,换上的序文亦占书版一片,汪士汉此举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给读者以此书出自其辑校之功的错觉。
1.2 依据他本,将《古今逸史》本《白虎通》书版中原作墨丁之处,补足刻字
吴琯在刊刻《古今逸史》本《白虎通》时没有真正看过大德本,除了上文中所说的序文差异外,在正文方面体现的更为明显,特别是全书中有6处文字作墨丁,和之前的元本、明本截然不同。
笔者查阅了《古今逸史》早期的四十二种本以及后来的增订五十五种本,发现相同书籍所用书版都是同一套,墨丁在这两种本子里都是存在的*按,《古今逸史》四十二种本,国图索书号T00676,是本书中钤有“吴琯”(朱文)圆印;《增订古今逸史》五十五种本,国图索书号T00675,民国间《景元明善本丛书》本即据此本影印。。具体情况如下:
①卷之上 第十一叶上半叶第五行第五字 元大德本作“寇”
②卷之上 第十三叶上半叶第九行第九字 元大德本作“宗”
③卷之上 第二十八叶下半叶第八行第十三字 元大德本作“孙”
④卷之上 第三十五叶上半叶第六行第十九字 元大德本作“彼”
⑤卷之下 第十二叶下半叶第四行第六字 元大德本此处字句有异
⑥卷之下 第五十叶上半叶第六行第六字 元大德本作“涂”
以上6处,在元大德本和明代万历前刻本(诸如傅钥本、蒋杰刻本)中都是有字的。特别是⑤一处,元本和诸明本皆谬误且相同,唯吴氏本谬误处与其不同:
此处应作“师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伯,鲁臣者亡。”*按,此处校勘依据新编诸子集成本《白虎通疏证》。[2]326
元大德本、明代傅钥本、蒋杰本、杨祜本、程荣《汉魏丛书》本舛误同,皆作“师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鲁臣者亡不行。”
吴氏《古今逸史》本独作“师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臣者亡不行。”另外,笔者将吴氏本与元大德本加以校勘,发现文字多有异同。
以上差异说明吴琯在整理《古今逸史》本《白虎通》时,既没有亲见元刻,也未盲从明代诸刻本,有可能是又加入了己见的原因。
汪士汉在得到《古今逸史》的书版后,依据明代刻本,将《白虎通》中的墨丁全部刻成字以补完,但并未对字句的差异加以修改,这一程序较为简单*按,笔者比对了文中提及的几种明刻本,以上6处吴氏本空缺处,后5处诸明本所刻之字皆同;惟中傅钥本、程荣《汉魏丛书》本作“冠”,其余本作“寇”。汪氏当据傅、程二本以外本补字。。
1.3 将《白虎通》中署名吴琯之处剜改成汪士汉
《古今逸史》本《白虎通》卷端第二行为“汉 扶风班固纂”,第三行为“明 新安吴琯校”。汪士汉《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卷端则将此两行合成一行,“汉班固纂 后学新安汪士汉校”,第三行加“德论上”以补足书版原行款。
仅据笔者所见,《秘书廿一种》之《白虎通》卷端,除署“新安汪士汉”外,亦有署“星源汪士汉”者。此中之区别差异则涉及到汪氏《秘书廿一种》在清代的刊刻问题,其版本复杂程度在清代刻书史中较为复杂,或可作为清代书坊刻书的缩影。
2 汪氏《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举隅
黄丕烈有言“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至今益信。”[3]182汪士汉《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即是如此,现将所见各种版本条列如下:
2.1 清初本
此本为汪士汉用明万历年间吴琯《古今逸史》本《白虎通》版片正文为主,正文前换上汪氏《白虎通德论》一文,署“新安汪士汉考辑”。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书前皆无《〈白虎〉〈风俗〉二通合编总论》,或是此本最初本无《总论》*按,国图所藏两本索书号分别为T00691,版本著录为“增订古今逸史重编后印本”;T01713,版本著录为“清康熙七年(1668)刻本”,扉页有“新安汪士汉校白虎通 居仁堂梓”,书中钤有“大兴冯氏赐书堂藏书印”(朱文)、“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记。前者版片漫漶处多于后者,刊印当晚于后者。抑或此本原有《总论》,后佚去,如此则当属康熙甲种本,见下文。。
仔细翻阅此二本,发现正文所用万历年间书版虽然整体上保存尚完好,但个别版片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断裂,如卷上第二十三叶下半叶及第二十四叶上半叶书版中下部出现横向断裂,贯穿整个书版,已经影响文字内容的阅读。
此本版心处尚有残留《古今逸史》本《白虎通》刻工痕迹之处,如卷之上第三十八叶版心下方有“荣 四百”,明吴琯《古今逸史》四十二种本即有之。
另外,因为汪氏所补刻之字最初为明版墨丁处,所以字体较原版正常字尺寸略扁而不舒展。
此本无《总论》,而《总论》结尾有汪士汉署时间“康熙戊申”(康熙七年,1688),故此本之刊印当不会晚于康熙七年。
2.2 清康熙甲种本
此本与前一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序文处增加了《〈白虎〉〈风俗〉二通合编总论》,其余并无差异,正文仍然使用的是万历年间的书版*所见版本有二,一为国图藏本,索书号38204,丛书首部《汲冢周书》卷端钤有“飞青阁藏书印”(白文)、“朱师辙观”(白文)、“松坡图书馆藏”(朱文),曾为杨守敬旧藏,《白虎通》扉页有“新安汪士汉校 秘书廿一种”;另一本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扫描本,丛书第一种扉页有“新安汪士汉校 秘书廿一种 本衙藏板”,并附有丛书简目。。
2.3 清康熙乙种本
所见本为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本,此本虽然正文部分为明万历年间书版,但修补和局部重刻的痕迹已经较为明显,应当是这套明代书版被印刷使用的最后阶段*此本为《秘书廿一种》之一,但已成单种流传,装为上下两册,已经佚去书前序言及目录,开篇即为正文,卷端钤有“河北天津师范学院藏书”(蓝文)及伪造黄丕烈诸藏书印。。此本与之前两种版本的主要差异有:
①版心处已有变化。明刻版片上原来的刻工被全部铲除,同时又加刻“四种”二字。这里的“四种”指《白虎通》是《秘书廿一种》中的第四种,说明河大所藏此本为丛书本之残本。
②此本正文虽整体上依旧为万历时版片,然而字画多已被修饰描画,明版风格顿失。如卷之上第八叶上半叶第四行第十字“称”较原刻字画明显有别,二十叶下半叶第二行末一字“鼓”亦与原刻有明显差异,此种状况在此本中较为常见。
另外,此本卷之下第二十四叶因书版损坏严重,整块书版被重新描刻,与原书版差别极为明显,大相径庭。
③版片年久磨损,部分文字无法辨识,因此出现了新的墨丁。万历末年距康熙初年已有半世纪之多,对于书版而言已属年久,出现此种情况在所难免。如卷之上三十八叶下半叶首行第十六、十七字,之前的刻本作“为”“子”,而此本则作墨丁。
④因版片字迹漫漶,产生了新的讹误。版片字迹漫漶的问题在上文提及的清初本中就已经出现,如卷之上第四十二叶下半叶第九行、十行首字,当作“臣”“忠”二字,但仅残存字体下半极少部分,已不可辨识*此漫漶处指上文提及的国图藏本,T00691,“增订古今逸史重编后印本”。;之后的康熙甲种本亦是如此。而此本则加以补刻,作“国”“忠”,“国”字属于因版片漫漶而导致的讹误。
另外,此本曾经书贾作伪以冒充黄丕烈藏本,卷之下尾叶伪造有黄丕烈及顾千里题跋各一则,又钤有“复翁”“千里”“荛圃”诸伪印。观题跋字体、内容及钤印,作伪手段较为低劣粗浅,故不赘述。
至此,以上三种版本皆是以万历书版为主的清代印本,此后明版彻底损毁,汪氏于是便依照原版行款重新刊印,于是以下版本皆为清刻本。
2.4 清康熙丙种本
所见为国家图书馆藏本,此本正文版片已全部据万历版行款翻刻,字体风格已有明显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汪士汉在两篇序文的籍贯由“新安”改成“星源”,颇有移花接木之嫌*国图藏本索书号T02041,著录为“清康熙刻本”。卷端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朱文)及“一九四九年武强贺孔才捐赠北平图书馆之图书”(朱文)藏书印。按,古徽州亦称新安,下辖六县,婺源为其中之一,而星源为婺源所辖。。
此本虽是翻刻明万历版而来,但疏于校勘,有两处因形近而产生的谬误:
①卷之上第十八叶上半首行第二字,之前刻本均作“喜”,此本误作“善”;
②卷之上第三十四叶上半叶首行第一字,之前刻本均作“萌”,此本误作“明”。
此刻本给人以生硬粗疏的印象,经历鼎革之后的沧桑可见一斑。
2.5 乾隆本
所见为国家图书馆藏书,依旧为明本的翻刻本,此本字体与康熙本风格不同,且文字又有异同,为重新刊刻之本,汪氏籍贯为“星源”*国图藏本索书号38296,著录为“乾隆七年刻本”。扉页有“秘书廿一种 新安汪士汉 居仁堂藏版”,钤有“旴台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白文)。。
此本首次在丛书的第一种前加以序言,《重镌廿一种秘书序》,为江永所作,落款所属时间为乾隆壬戌(乾隆七年,1742),但其中《白虎通》序文仍沿其旧为康熙七年,所以只看单行之本而不与他本比较,容易被迷惑。
通过江永《重镌廿一种秘书序》,我们可知:
①“隐侯汪先生尝取《汲冢》以下廿一种校而梓之”,汪氏及其后人仍旧未曾言及所刻《秘书廿一种》与《古今逸史》的关系如何;
②“版寖蠧漫,其孙勋偕弟谟、照、升、杰、烈暨再从子德昭复新之,以承先志”,之前所用书版已经损毁,汪士汉已去世,新刻丛书由汪氏后人协力刊成*按,康熙三十八年(1699)《徽州府志》中即已有汪士汉,则其去世当在此前。。
此本在校勘上更正了上文中提到的康熙刻本的两处谬误,但依旧产生了新的讹误,同样是因形近而误:卷之上第二十八叶下半第八行第十四字,之前诸本均作“首”,此本独作“自”。
另外,此本还有一处墨丁,卷之下第四十三叶上半叶第六行第十九字,作■;此前诸本均作“名”。
2.6 嘉庆本
所见本为国家图书馆藏书,依旧为明本的翻刻本,汪氏籍贯为“星源”*国图藏本索取号38917:4,著录为“清嘉庆九年刻本”(1804年)。。此本虽刊印于嘉庆年间,但文字风格及异同却更接近康熙时刻本。
此本丛书第一种前仍冠以《重镌廿一种秘书序》,但文字已有修改润色,与乾隆本《序》有别,结尾处仍署江永,时间是嘉庆九年(1804)。江永卒于1762年,此序或并非江永所亲改。《白虎通》书前序文依然与乾隆本相同,时间还是乾隆七年。
该本在字体风格上更接近于康熙时刻版,且文字讹误之处亦与康熙丙种本相同,误“善”为“喜”,误“萌”为“明”。
另外,书中还产生了新的讹误,与以上诸本不同,卷之上第二十八叶下半第八行第十四字,当作“首”字,讹作“百”。
针对嘉庆本的以上版本特点,笔者猜测,此本书版或是和康熙乙种本为刊刻时间较为接近,抑或为乙种本之修版,故而原版之讹误因循未变而在修版时又产生了新的讹误。即便书版非康熙乙种本原版,但距离时间接近,所以带有康熙本的风格和特点。汪氏一族为书坊刻书,刻工粗疏且多有讹误,但历经康熙直至嘉庆已有将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更换书版当属常事,所以这一猜测亦有合理性。
汪氏在道光年间仍然继续刊印《秘书廿一种》,但已是巾箱小字本,与以上版本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故不再赘述。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汪士汉几种《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的梳理,我们大致上对其版本情况有如下了解:
第一,汪士汉在清代初年最初刊印《秘书廿一种》使用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吴琯所刻的《古今逸史》本版片,其中《白虎通》将书前的两篇原序加以替换,同时又据他本将原版中的墨丁补足刻字。这一版本最晚在康熙七年开始刊印,当时版片就已经多有磨损,其间屡经修补,已渐失原貌。据后来所见汪氏新刻之康熙版判断,此本最后的刊印时间当不出康熙初年。
第二,上文中所见康熙本三种,序文所属时间均是康熙七年,与其所用明版序文时间一致。极有可能说明汪士汉在使用明代书版刊印的同时,已经着手刊刻新的书版。这一版本虽是对明版的翻刻,但产生了些许讹误。从此本开始,汪士汉的籍贯由之前的新安变为了星源。
第三,乾隆本在刊刻质量上要优于康熙本,纠正了康熙本产生的讹误,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舛误。由于汪士汉本人已经去世,该版由其族人合力完成。
第四,嘉庆本在字体与内容上与康熙本较为接近,或为康熙本之修版,而乾隆本所用之书版未曾再见刊印,或许毁于天灾人祸亦未可知。
第五,汪氏所刻《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非同一般官府或是私家刻书。以上版本可以汪士汉籍贯作为判断依据,凡序中署“新安”者,则为明版清印;凡署“星源”者,则为清刻无疑。但笔者后来又见到序中署“新安”,但正文为清刻的本子;还有的清刻本,卷端作“后斈新安汪士汉”*按,所见署“新安”汪士汉之清刻本为书友藏书,残存上册,无藏书印记或题跋;所见“后斈新安汪士汉”之清刻本为拍卖网所见书影。两本字体均接近康熙本风格。。这些版本的存在,无疑使得汪氏所刻《白虎通》的刊印顺序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对此,笔者以为,汪氏一门以书坊刻书为业,首先具有的是商业盈利性的特点,因此其在刻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盲目随意的特点,不似官府和私家刻书那样严谨细致;其次汪氏族人众多,仅从江永所作序文中就可知汪士汉的孙辈及再从子就有7人,他们共同出力完成了新书版的刊刻,而这其中可能有人就是继承了祖辈的事业继续以刻书售书为业;再次,作为家族产业,各家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祖上的书版各家分别重刻售卖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有年代不同、风格各异的版本流传开来。这些版本之间在时间上可能以平行关系居多,而非简单的前后继承关系。
汪士汉《秘书廿一种》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之中,但后人整理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并未收录此书。此书作为当时较为常见的丛书,加之又是平常书坊所刻,所以长久以来并未受到过多关注。但是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书坊所刻丛书具有与同时期官府、私家刻书所不同的复杂性,汪氏《秘书廿一种》从康熙初年刊印至嘉庆初年为止,刊印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其间历经多次翻刻、重刻,在版本学和刻书史研究上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通过对此本的浅显分析或许能够为今后明清书坊的刻书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清)丁廷楗,等.徽州府志·卷十五[Z].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
〔2〕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M].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8
〔3〕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