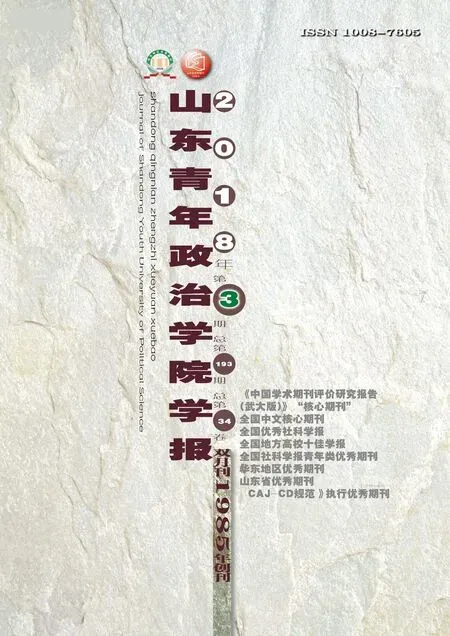幻魅世界的另类想象
——齐文化影响下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塑造
2018-04-01王美春
王美春
(山东财经大学,济南 250014)
故乡、梦幻、传说、现实是莫言的文学资源,故乡是他心灵不灭的精神存在。莫言的家乡在山东高密,高密地处古齐国,齐文化对莫言影响甚大。高密偏处胶东半岛一隅,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民情朴素。莫言有营造原味乡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面对高密的莽莽苍天,莫言借助非凡的想象,巧为穿插,使一则则传奇故事浮现其间,他的神思奇想在虚构与现实、遐想与历史间微妙互动。
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鬼里鬼气、古灵精怪的女性人物。这些介乎人鬼之间,身上带着仙气、鬼气、灵气、妖气的女性人物,反映了莫言在幻梦世界的另类追寻。作家阿城说:“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1]
莫言小说中的神秘氛围,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很大。莫言如蒲松龄一般,对中国本土的神话、鬼怪故事很感兴趣。《聊斋志异》对莫言的影响从他的《学习蒲松龄》中可看出一斑:作者先后给蒲师爷磕了九个头拜见、认师、谢恩。由于青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听到的流传的鬼怪故事,也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这种作品有民间传说的影子,其中离奇古怪的情节和散发着鬼气的人物似乎是从古老的传奇中走出来的。
莫言笔下的很多女主人公是非常神秘的人物,她们的诡秘莫测一点都不逊色于蒲松龄小说中的花妖狐魅。莫言曾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也算看了不少文学作品,让我难忘的女性形象,不是貂禅也不是西施,而是我们山东老乡蒲松龄先生笔下的那些狐狸精。她们有的爱笑,有的爱闹,个个个性鲜明,超凡脱俗,不虚伪,不做作,不受繁文缛节束缚,不食人间烟火,有一股妖精气在飘洒洋溢。你想想那几个世界级名模吧,她们那冷艳的眼神,像人吗?不像,像什么?像狐狸,像妖精。……我认为跳孔雀舞的杨丽萍算一个可以与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媲美的小妖精,她在舞台上跳舞时,周身洋溢着妖气,仙气,惟独没有人气,所以她是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2]
文学的永恒魅力在于作品显现出的人的精神深度,这是作家关于生命存在的独特发现,也是作家思想的一种艺术折射,莫言在内心世界中自觉地探索着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怀抱鲜花的女人》、《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等作品都揭示了人在荒谬处境中的荒谬存在,关注着个体生命如何实现在荒谬处境中的精神超越和精神突围。
一、怀抱鲜花的怪女人
齐文化潇洒风流,莫言受齐文化影响很大,他的小说多具有“聊斋”韵味。不过,少了蒲松龄“聊斋”中强烈的讽喻和劝世色彩,呈现给读者的只是如烟如梦、如雾如云的惊鸿一瞥。莫言的很多小说不刻意经营情节的合理性,运用夸张和想象的手法虚构出变形的奇怪景遇,并因为与现实的脱节而使小说有了寓言般的多义性。如《怀抱鲜花的女人》中鬼魂般的美丽女人对男人的无止境的纠缠,《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遭遇两位古代男女,试图追随他们弄个明白等,亦真亦幻、实中含虚的叙述中,蕴涵了无穷的象征意味。
中篇小说《怀抱鲜花的女人》就表达了一个引诱与拒绝主题的准鬼怪故事,海军上尉与怀抱鲜花的怪女人的偶然邂逅,反映了作家的一种理念,以及芸芸众生的一种生存状态,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一种无奈的状态,如被一个狐魅般神秘漂亮的女人追赶……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人在世俗生存中的一种尴尬的两难状态,拼命追求一种东西,追求到了又试图抛弃它,刚想抛弃却又犹豫起来,人性的复杂性正在这里。
《怀抱鲜花的女人》中海军上尉王四在回老家结婚的途中,邂逅了一位怀抱鲜花的奇异的似人非人的女人,她的面容姣好,微笑迷人,身着质地很好的绿色曳地长裙,好象从古典油画中走下来。心中充满邪念的王四对她一见钟情,一念之差便情不自禁、鬼使神差地吻了她。从此,王四的命运便与这个素不相识、莫名其妙的女人纠缠在一起,他始终摆脱不掉这个女人。他走到哪里女人便跟到哪里。上车时她跟着上车,下车时她跟着下车;过桥的时候她跟着过桥,回家的时候她跟着回家。气急败坏的王四用“打你一炮也不过五十元”的下流语言污辱她,拿出刀子恐吓她,甚至后来双手掐住她的脖颈。可这奇怪的女人、迷人的微笑、水灵灵的鲜花和诡异的黑狗 ,却如冥界中的鬼魅一样紧紧尾随着王四到了他家。在这中间,上尉心中的矛盾、欲望、柔情、道德此消彼长;最后,人性反复、犹豫、不可遏止的激情和一点点善良、温情互相交织的结果是,在准备与“钟表姑娘”结婚的洞房中,上尉与赤身裸体的鲜花姑娘紧紧搂抱在一起死去了。
在王四即将走向幸福婚姻生活的途中,在县城的立交桥下的雨中的黄昏,女人的美丽令他过目不忘。他以对艳遇抱有幻想、却又无力摆脱平庸的朴实姿态上去搭讪,从此惹下祸端。等待着洞房花烛的父母和未婚妻对这个怀抱鲜花的女人当然不欢迎。他们甚至以中国人惯有的道德观念来想象上尉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并且迅速把这种不欢迎转换成了对军人的愤怒。可怜的军人哀求过、恐吓过、愤怒过,但也感动过,女人依旧和他如影随形。在拥挤的开往乡下的公共汽车上,在夕阳下的原野和池塘,女人双手搂着鲜花,脸上的笑容永远,墨绿色的长裙飘飘……黑狗一直跟着这个女人,如一个忠实的奴仆。
王四和怀抱鲜花的象征着诱惑的虚幻女人进行了一场诱惑和反诱惑的角逐。诱惑就像幽灵一样追随着、考验着人性深处的欲望,欲望的过度放纵会使沉迷其间的人付出代价。王四的父母、未婚妻和堂弟代表着世俗的伦理道德的力量,他们没能阻止住王四内心的非理性因素。最后,王四和女人同归于尽。莫言在这个传奇中传达了自己对人性和世俗生活的感悟,欲望的渴求和满足是世俗生活的重要内容,无止境的纵欲会将人推向毁灭的边缘。小说运用象征手法描摹了人性深处的非理性因素,虚虚实实的艺术世界为小说蒙上神秘与哲理的色彩。
小说中怀抱鲜花的女人是一个虚化的为情而生的符号,作为上尉脑海中的一个幻像,这个梦想中的情人只不过是一个幻影。王四在现实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依然是家乡俗气的“闹钟姑娘”,罗曼蒂克的爱情只不过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幻象。或许,每一个男人的脑海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在他的婚姻危机和世俗生活的苦恼里,她不时会神出鬼没地出现、诱惑他,使他的生命脱离正常人生的轨道。怀抱鲜花的女人的虚幻指向的是人生的苦恼,俗世的现实生活拒绝了男人身上固有的浪漫情怀。
人类不能脱离既定的生存秩序或环境而独立生存,必须依托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存在为基础。同时,人类又是一种个体的生命存在,生命本身又有着许多庞杂的非理性因素,它们时不时地冲破理性因素对人类自身的预设或规划,制造出许多难以言说的尴尬和荒谬。《怀抱鲜花的女人》中上尉因一念之差,把自己即将到手的幸福毁于一旦。他抵挡不住诱惑,致使个人的命运脱离了自身预设的轨道。人类的兽欲本能和善良悲悯的天性,促使王四远离理性因素的控制,无法预测和掌握命运,一步步滑向死亡的深渊。
莫言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他对人性、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怀抱鲜花的女人象征诱惑,经不起诱惑的人在触及诱饵后,便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诱惑会缠绕、跟随着他,考验他的毅力,折磨他的身心。最终,他在错失一个个良机后,与诱惑同归于尽。这种象征的手法给这个传奇蒙上了一层人生哲理的色彩。小说要表现的或许是人性的弱点,致命的诱惑永远会缠绕着不甘平庸的人,灵肉挣扎的结果是悲剧性的;或许是生命的醒悟,命运的无奈总在折磨着人类,导致他们情爱的绝决。小说如同一篇寓言,具有浓郁的反讽气息。
二、长安大道上的古典美人
莫言经常借用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创作技法,如用说书人口吻讲述故事,用幽默、戏谑的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推进情节发展,《天花乱坠》将三个有关女人与麻子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丰乳肥臀》中化为鸟仙的三姐,让我们既看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又看到了莫言在有意识地向中国传统的传奇文学学习。
莫言小说中的种种传奇的生活现象,是他对中国社会、历史乃至人性反思和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不仅反思历史,还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等。
中国传奇叙述中经常用的模式是奇事或奇遇,生活中的奇遇会让人卷入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件中。《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乡间的奇人奇事征服读者,侯七们遇到一对天外来客般的古代男女,因整日身处枯燥、单调、平庸的精神状态,对这对奇异男女的现身无限关注和迷恋,奇遇情节激活了他们的日趋单调、物化的生活模式。小说以清闲典雅之笔风将现代社会人类的好奇欲望描摹到极致,对普通人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做了恶作剧般的打趣和调笑:一男一女骑着一驴一马来到长安大道,“侯七”们一路跟踪,但跟踪、围观的结果是白马黑驴分别翘起尾巴拉出几十个粪蛋子,然后像电一样地往前跑去。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的女主人公是那个身穿红裙的少妇,她骑着一匹油光闪闪的小墨驴,旁若无人般地闯红灯、过马路。她的身后,跟着一个骑白马、披挂着银灰色盔甲的男子,他右手握一枝木杆的长矛,矛尖闪闪发光,他浑圆的头盔上竖着一个尖锐的枪头,枪头上高挑着一簇红缨。就这样,一驴一马驮着一女一男,在下班高峰期的长安大道上闯了红灯,大家用平时少有的平静和肃穆看着他们过了马路。有好多骑自行车的人都调转了车头,跟着这一男一女想看热闹,侯七就是其中的一个。春寒料峭,人们有的穿着羽绒服,侯七穿着毛衣毛裤,驴上的女子却只穿着一条红稠裙,腰里扎着一条棕色的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柄镶着钻石的短剑,她的胳膊很长,红袖肥大,腕上套一只玉镯。侯七和大家尾随着那驴那马从鸿宾楼门前到了六部口,正碰上红灯,原以为他们还会闯红灯,没想到这回他们停下来等绿灯了。一个警察看到了骑驴、骑马的男女,跑过来,刚想说什么时绿灯亮了,那女子一驴当先,率领大家过了斑马线。有的人好奇,问那男女是干什么的,没人回答他们。有的人想挤到前面,看那女子的脸,结果被骑马男子用长矛拦住了,但大家都往前冲,把他的矛杆冲歪了,他拔出了悬挂在腰间的长剑,将一个人的头发削去,人们再也不敢逾越。六部口的那个警察骑着摩托车追来,要求骑马和骑驴的男女站住,他们没有反应,警察用警棍敲了一下骑马人的头盔,结果他自己被狼狈地挂在了道路隔栏上,倒地的摩托倒在了路中央,制造了一起几十辆汽车撞在一起的交通事故,所幸没有死人……侯七和大家跟着驴马穿过了府右街路口,过了新华门,骑驴的女子被路边的花朵吸引了,她掐了一朵蓝花叼在嘴里,人们把他们围在了墙边上。有两辆摩托和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要求人们解散,骑马人三下两下就把警察用长矛拨到一边了,然后,他和美人继续前行。很多人都散了,但侯七及少数几个人还是一直跟着,并在天安门前面追上了驴马。过了南池子大街,过了王府井大街,过了东单路口,过了国贸大厦……一切都没变化,只是跟着的人越来越少,当只剩下侯七一人时,白马和黑驴停住脚步,他的心中一阵狂喜,没想到马和驴各自翘起尾巴,拉出几十个粪蛋子后,像电一样向前跑去。故事到此结束。
骑驴美人在这里是个虚幻的影像,我们不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知道她的出现让大家神魂颠倒,她的惊鸿一瞥般的美丽现身,充满神秘的浪漫色彩。她身上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她可以代表善良的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或理想,也可以代表人类虚幻的不可知的未来;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就是她自己。
愚人节侯七们在长安大道上的奇遇是莫言为现代人精心安排的一次惊喜,他们需要奇遇来调节、激活单调乏味、机械重复的生活模式,小说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进行了探寻。苍白、平淡的日子里,在大街上遭遇一位骑黑驴的红裙少妇,空虚、无聊的侯七们猛然被一种强烈的期待攫住,开始了执著的追随之旅。最后希望却落空了,幻想着一种外来激情的拯救的他被抛弃在城市的大街上,行为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是一种无聊与落寞的感觉。
莫言的小说中,传奇多是作为主题、动机来推动小说的叙述,或是充当一个细节来增加小说的怪异色彩。奇遇作为中国传奇叙述中常见的模式,奇遇之奇往往是因为超出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和逻辑。《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侯七遇到了天外来客般的骑驴美人和古典骑士。身穿红裙的美貌少妇和披挂盔甲、手握长矛的骑士,出现在车流涌动的长安大道上,侯七之流们不由自主地尾随着他们。这对来历不明的古典男女,就像古代侠士一样旁若无人地在长安大道上穿行,这不能不激起现代人的兴奋、好奇和骚乱。时空的交叉和错位是这篇小说的“奇”之所在。古典男女不可抗拒的魅力反衬出当代社会中人的平庸和乏味,他们超凡脱俗的气质是对现代社会中世俗、功利的一种反讽。小说通过现代人的好奇心被一对古代的男女牵引着掉起胃口,结果却只得到“一堆驴粪蛋”的故事,揭示荒谬无处、无时不在。小说结局表明,程式化的平庸生活状态、常规的工作生活秩序不会被轻易打破,它总是压抑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渴望,迫使人们无奈地向现实让步、妥协。但只要人对自己的生存际遇心怀不满,还不想彻底放弃对命运的掌握,人类就还有希望。
三、飞翔的神秘女郎
借助鬼怪是莫言传奇叙述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中,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小说中的出现,总是寄寓了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或理想。在叙事层面上,可以帮助作者实现小说情节上的转折;在内容上,作者还可借鬼怪表达他对人事的态度。
莫言用鬼怪志怪建构了一个想象的世界,以此表达他对世俗生活中的不幸的女人的同情和怜悯。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领弟,由于心爱的男人鸟儿韩被一群来历不明的匪徒抓走,痛失爱人的悲伤和绝望击垮了她,她从此变成了一个人形鸟性的鸟仙;小说中还曾写道,高密东北乡短暂的历史上,曾有六个由于恋爱受到阻碍、婚姻不和睦的女人,顶着狐狸等动物的灵位度过了神秘而让人敬畏的一生。
短篇小说《翱翔》中逃婚的女人燕燕用飞翔来保护自己,她像鸟一样在夜晚的松林上空飞翔……关于燕燕的故事是这样的:燕燕生得很美,修长的双臂、纤细的腰肢,容长的脸儿,细眉高鼻,双眼细长,像凤凰的眼睛;但她的哥哥是个哑巴,年纪很大了还没找到对象,于是家里人便做主用燕燕给她的哑巴哥哥换了个媳妇,名叫杨花。杨花是高密东北乡数一数二的美女,她的哥哥一脸大麻子,四十多岁了还是个老光棍,为了麻子哥哥——黑大汉洪喜,杨花委屈自己嫁给了燕燕的哑巴哥哥。他们几个的婚姻方式,俗称换亲。燕燕一开始不知道家里人把她嫁给了一个麻子,新婚当天,“她看到了洪喜的脸,怔怔地立住,半袋烟工夫,突然哀嚎一声,撒腿就往外跑,两个女傧伸手去拽她的胳膊,嗤,撕裂了那件红格褂子,露出了雪白的双臂、细长的脖子和胸前的那件红绸子胸衣。”[3]跑了新媳妇,高密东北乡的人们都帮着追,一群人马上就要捉住燕燕了,“突然,一道红光从麦浪中跃起,众人眼花缭乱,往四下里仰了身子。只见那燕燕挥舞着双臂,并拢着双腿,像一只美丽的大蝴蝶,袅袅娜娜地飞出了包围圈。”[4]后来,燕燕降落在村东老墓田的松林里,落在墓田中央最高最大的一株老松树上。她最后被人们用弓箭射了下来,铁山老爷爷拎起一桶狗血浇到了她身上……
想逃婚的燕燕没有成功,虽然她无师自通地用飞翔来逃避捉她的人们,但终究还是被逮住了。她的结局,注定是要带着满身的伤痕隐忍地在这世界上生存;因为,她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会有很多人看守着她,不让她自杀的;也许,她会回心转意,为洪喜生个小麻子传宗接代。总之,作家想象的浪漫的反抗失败了,残酷的现实占了上风。
《丰乳肥臀》中的三姐上官领弟,深爱着威风凛凛的扑鸟专家“鸟儿韩”,鸟儿韩被日寇捉去做劳工后,她承受不了打击,变得神经错乱。
鸟儿韩被捉走后第三天,三姐从炕上爬下来,赤着脚,毫无羞耻感地袒露着胸膛走到院子里。她跳上石榴树梢,把柔韧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母亲急忙去拉她,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我认为,如果不是母亲请来樊三等一干强人,用黑狗血把三姐从屋脊上泼下来的话,三姐身上就会生出华丽的羽毛,变成一只美丽的鸟,……去寻找她的鸟儿韩。[5]
这是三姐领弟在鸟儿韩被抓后神经错乱,变为“鸟仙”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描写,充满了神秘的、匪夷所思的色彩。由于战争的灾难,人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异化为类人非人的生物,三姐领弟就是人性异化的佐证。她因大悲痛而迷失人性,变成半人半鸟的生灵,后来嫁给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因为得了“幻想症”,看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的跳伞飞行表演,试图效仿、练习飞翔的她摔下悬崖而死。
莫言的创作中具备了许多浪漫主义的要素,比如夸张、幻想、超现实的离奇故事等,与西方魔幻主义作品相似。莫言继承了齐地作家蒲松龄的一些品质,他的小说颇有《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以乡村百姓的自由想象为基础,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出发,超脱现实,沟通阴间和阳世,连接花鸟禽兽,建构出一个不同于世俗世界的审美空间,创造出一系列传奇小说。莫言的超越之处在于他从个体的世俗生存出发,直面人类的悲剧性宿命,展示历史和人性的冲突。
《红高粱家族》中的二奶奶恋儿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奇女子,在与余占鳌的猎捕和反猎捕中,她甚至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日本鬼子残忍地糟蹋了恋儿,小说通过恋儿自己的视角来表现那场令人发指的悲剧,她遭到的凌辱通过她痛苦的灵魂和肉体感受表达出来,惨无人道的情形震撼人心。小说后来写道,二奶奶在遭到惨无人道的凌辱后,死后起尸狂语不止,灌湾水,往心窝上压钢火镰、压犁地的钢铲等都无济于事,二奶奶怨气冲天的怒骂持续数天,情形恐怖,充满神秘、诡奇的气息。最后,我爷爷请来“山人”作法,二奶奶才咽了最后一口气……二奶奶以她那诡奇超拔的死亡过程,结束了她那短促的绚丽多彩的一生。
鬼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通常暗示事件的不正常,或者人们心理的恐慌不安。中篇小说《司令的女人》中鬼魂显灵让坏人得到了惩罚,为好人洗去了罪名。结尾:深夜,范小鬼子揭穿了吴巴是杀人凶手的面目,死去的女人小唐的阴魂在窗外飘荡。小说化用了民间传奇中冤鬼复仇的模式,小唐的阴魂不散是为了讨取真凶吴巴,鬼魂现身为司令洗去了罪名。
四、诗意的浪漫女子
莫言的小说包含着两个世界,现实的小说世界和超现实的小说世界。童年回忆、家乡生活、时代变化带来的苦恼与冲突等是写实的;超现实的小说中,神秘的色彩弥漫开来,给小说中的人物蒙上一层传奇色彩。莫言的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偏离了简单的现实,偏离了静止的日常生活,偏离了写实主义,将生活的另一面——神奇性展现出来,拓展、创造了故乡的“现实”概念。短篇小说《夜渔》、《秋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夜渔》的写作时间为1991年,作者写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故事。小说中的女性神秘、高贵、善良、漂亮,如同《聊斋志异》中的狐仙,色彩迷离、令人惝恍。乡村少年“我”跟随捉蟹能手九叔,穿越密密层层的高粱地,来到离村很远的小河沟捕捉螃蟹。深夜雾气渐浓、月光幽幽,九叔吹出一些唧唧啾啾的怪声,他的目光绿幽幽的,对“我”的呼唤毫无反映,“我”戳他的脊背发现凉得刺骨。九叔的怪异、周围的怪声使 “我”毛骨悚然。
“我”是个十来岁的男孩子,有了朦胧的性爱意识,或许还有“恋母情结”。在极端惧怕的条件下,心有所想就出现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这个女人亭亭玉立、面若银盆、满脸微笑、香气袭人。“她回手从身后拖过一根带穗的高粱杆,往河沟中的两道栅栏间一甩,那些青色的大螃蟹就沿着秆儿飞快地爬上来。她把高粱秆的下端插入麻袋,那些螃蟹就一个跟着一个钻到麻袋里去了。”[6]有如此超现实的能力的她,突然而至,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那她是仙女是鬼怪?还是狐狸?少年对女人的兴趣,是他朦胧性爱意识的表露。
小说结尾,天亮了,村里的人们、父母、叔婶、哥嫂、九叔在野外找到我;原来,在深深的高粱地里,九叔摔了一跤,我和九叔走失了,九叔回家找我,我则在高粱地里迷失了方向。可是,梦幻中那位仙女一样的女人帮我捕捉的两麻袋螃蟹就在我身旁。那个女人留下的乩语以及 25年后东南大海岛上再相遇的话,后来果然应验。小说的奇异性就在这里,把幻象、幻景当作生活的真实来写,并寓以某种观念、某种哲理;虽然使用了虚幻假定的幻觉幻化艺术,但它揭示的情理是美好的令人信服的。
《夜渔》中,九叔的怪异、少年的恐惧、荷花的灿烂、女人的美丽及其超人的魅力,少年身旁那两麻袋螃蟹及乩语的应验,都令读者遐想。少年在迷离的自然面前,忘记了恐惧、自身,身体仿佛化作一种虚幻的情绪飘动起来,内心抑制不住的忧伤、感动。那个漂亮的女人似妖非妖、似鬼非鬼,25年前曾出现在 “我”的梦中,25年后又与“我”再次相见,在新加坡的一个大商场。小说在幻觉幻化中融和着作者的情感、想象,带着关于生命意义、生存思考的特殊的领悟……
《秋水》中的爷爷、奶奶在蛮荒之地的高密东北乡努力开拓着他们的家园:方圆数十里的一片大涝洼,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突然有一天,黄色的浪涌如马头高,一切都被淹没了。一位神秘的紫衣女人从洪水中来到我爷爷的窝棚,我奶奶当时正要生孩子,但是一直折腾了两天一夜了,还没有生下来……紫衣女人知道后,从草铺上抽出一把草撒到地上,接着闪电一样拿出枪逼着我爷爷的胸脯,要求我奶奶弯下腰,把草一棵一棵拣起来。我奶奶弯下身子捡草,起伏了四五十次,透明的羊水从腿间流出,我爷爷如梦初醒,原来紫衣女人是要帮助他给我奶奶接生,我奶奶终于产下了一个男孩。接生完毕,紫衣女人身子一歪,睡了过去。不久,从洪水中来了一个黑衣人和一个白衣盲女,黑衣人是个神枪手,对白衣盲女非常照顾,对紫衣女人却很戒备。紫衣女人闪电般的一枪打死了黑衣人,“他一头栽倒,慢慢地翻过身,露出一个愉快的笑脸:‘……侄女……好样的……你跟你娘像一个模子脱的……’紫衣女人哭叫着:‘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爹?’黑衣人用力抬起一个手指,指着白衣盲女,喉咙里响了一声,便垂手扑地,脑袋侧在地上。”[7]
《秋水》将大水之中,人的希望与失望、侥幸与绝望、生与死,精疲力尽的恐惧和面临死亡的混沌茫然,在意与象的融合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弥散着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氤氲,神秘的氛围,使得小说背景冲淡、笔触迷蒙、轮廓模糊,整体上具有一种空灵朦胧之美。莫言吸收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手法,在冷静、从容的叙述中反思历史,融入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意蕴,透视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非自由状态,现实主义中有现代主义的味道,幽深、扑朔迷离。
参考文献:
[1]阿城:魂与魄与鬼及孔子[J].收获,1997,(4).
[2]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159.
[3][4][7]莫言:苍蝇·门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64,265,49.
[5]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83-84.
[6]莫言:莫言文集(卷5)·道神嫖[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