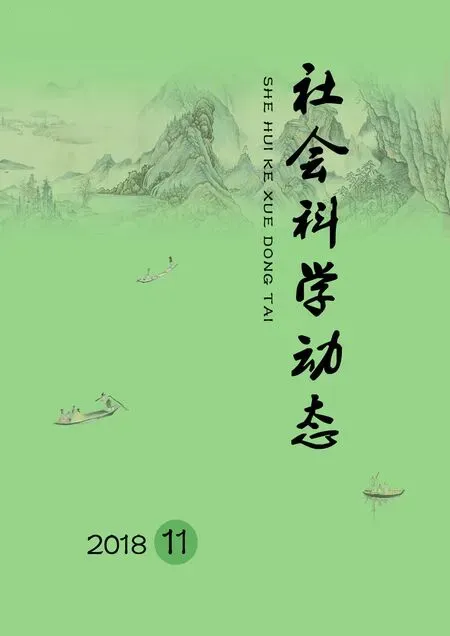边界写作与文本建构
——张翎的《劳燕》论说
2018-03-31钟梦姣沈思涵
钟梦姣 沈思涵
一
中国小说学会作为最权威的小说推评机构,对年度小说进行排行已历15载。2018年1月7日,“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江苏兴化揭晓。刘庆的 《唇典》、鲁敏的 《奔月》、张翎的 《劳燕》、石一枫的 《心灵外史》以及范迁的 《锦瑟》入选长篇小说排行榜。
张翎的 《劳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收获殊荣,确为实至名归。可兹佐证的是,第十四届 《当代》长篇小说论坛获奖名单中,《劳燕》荣登 “五佳作品”榜首。其他如 “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专家榜”、 “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读者人气榜”、 “新浪中国好书榜2017年度十大好书”等,都有 《劳燕》的身影。
《劳燕》可以看作是一部 “战争题材的小说”,但它又不是传统的战争题材作品。这里没有惯常的民族仇恨血债血偿,尽管日本鬼子杀死了诸多四十一步村民众并残忍蹂躏了女主角阿燕;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风花雪月卿卿我我,尽管美国牧师比利、机械师伊恩和中国大兵刘兆虎都深爱同一个女孩,这足可以写成跨国的三男一女多头恋故事;没有明确的线性结构,没有最终胜利属于我们的 “光明尾巴”——相反,初读张翎的《劳燕》,让人不知所云。因为,这个所谓的 “女主角”,在军人刘兆虎那里,她是 “阿燕”;在牧师比利眼中,她是 “斯塔拉” (Stella,星星);在机械师伊恩的心中,她又是 “温德” (Wind,风)。身份不明的附加值就是:人物形象似乎 “游移不定”。更令人感到陌生的是,小说并不是从生者的视角去观察世相,叙写人物,而是在三个亡灵的 “回看”中建构起那个曾经的中国乡村女孩形象。
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故事吗?作者缘何如此?作者意欲何为?
二
“边界写作”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籍印度裔作家塞尔曼·拉什迪提出的。拉什迪的 “边界写作”所 “称颂”的是 “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等令人惊异的混合和变形,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新生事物”。哈佛教授芭芭概括 “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母题是: “不确定的流散身份”和 “无法调和的、杂糅的边缘文化”。在中国,说到 “边界写作”,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阿来的 《尘埃落定》。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年在文化学者李建军看来, “是封闭的、混乱的、破碎的。他仅仅满足于叙写 ‘我’的飘忽的想像和怪异的行为”, “给人一种单调、沉闷、虚假和陌生的感觉”①。其实,李建军的 “误读”正在于他没有意识到阿来所采用的是一种 “边界写作”策略。是文化的激荡造就《尘埃落定》这部作品,用阿来自己的话说就是“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阿来多次言及自己作为汉化藏民的独特民族身份和穿行于汉藏两种文化之间的奇特感受: “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 “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②独特的民族身份,藏汉、中西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化根基,奇特的想象和灵异的思维等,共同造就了阿来的诗性叙事,也暗合了塞尔曼·拉什迪所提出的 “边界写作”。
回到张翎。张翎生为中国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其后在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最终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可以说,英语世界是她的 “第一世界”,但她却一直 “坚强地抵抗着用英语写作的诱惑”。何以如此?盖因为“用英文写作时,我会时刻考虑语法正确与否,应不应该这样使用某个词语,如此一来,故事就只能讲得平顺而不是精彩”。③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张翎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特殊 “身份”以及由此“造就”的边界写作思维: “地理距离的阻隔对我的写作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破坏作用,我失去了根的感觉。……我对当下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深切的体验。我很难和北美新大陆完全贴心贴肺,因为它不是生我的故土。而我的故土也不见得认我——我已经错过了中国最热闹最跌宕起伏的三十年,我很难精准地抓住中国当下的精髓。这是我无法规避的短板。”④正因如此,张翎曾经一度回避对中国当下题材的叙写。好在事物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从一位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却定居在外国的作家的角度说,中国与海外的桥梁并没有中断,相反给她提供了独特的 “他者”视角和异质想象的可能。 “在两个大陆之间游走的好处是多了一双眼睛,打开了一些原本不及的视野;多了一段审美距离,少了一些 ‘人在此山中’的迷惑。”⑤回国,出国,再回国,再出国,不仅仅是自然的旅行,更多的是文化的纠结和人性的碰撞。换言之,较之于寓居国内的作家来说,张翎有了更多的机会从中远距离、从外部、从异质文化去观察中国社会和人生世相。 “我意识到旁观者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我可以写出另一种版本的中国故事。”⑥“当我回望故土时,有了一个审美空间,局部细节渐渐演化成了整体感。在诸多的不利中,我只能尽量运用这个可取之处,争取写出一些视角不同的东西。”⑦
三
那么,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张翎,在 《劳燕》中写出了哪一种版本的中国故事,又表现出了哪些不同视角的东西呢?
“不同”是从 《流年物语》开始的。张翎曾在回答 《中华读书报》记者访谈时指出: “在我过去的创作经历中,我一直很关注故事,会花很多功力去营造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内核,例如乱世中阴差阳错的人生,灾难如何把人逼到墙角,绝境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等等, 《阵痛》 《金山》和 《余震》,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流年物语》是一部有故事的小说,但故事是个寻常的故事,只是我在里边尝试了一种我从前未尝试过的讲故事方法。很难界定具体是哪一样东西给了我灵感,但近期我阅读了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君特·格拉斯、库切等人的作品,他们在叙事方式上的多元和创新使我心存景仰,我无法想象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如此灵动而没有边界。这些作家可能启发了我叙事方法上的灵感。”⑧
如果说 《流年物语》是张翎 “变阵”的开始,《劳燕》则可以看作是张翎的华丽转身。在作者家乡浙江玉壶地区,历史上曾有一个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在抗战的最后一年时间里,“玉壶班”培训了4期共3000名中国优秀士兵。对于写作者而言,这该是怎样的一片历史富矿啊!从政治意义上说,其时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里有中美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有玉壶地区人民对抗战的生死支持……无论怎样,凭着张翎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她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中规中矩、既能得到官方首肯又能获得读者青睐的传统长篇小说。何乐而不为呢?
实际上, 《劳燕》备受业界推崇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小说中选择了文体杂陈的述说方式,具体说就是将书信、报纸新闻、日记、历史记载等有机地揉入小说之中,使得小说在虚构的背景下予人以 “真实”的感觉;就阅读来讲,读者在阅读虚构文本的同时, “故事”被人为地中止,从而“被迫”对故事性进行比照和验证,最终将作为“第三方”的读者带入 “场域”之中。另一个广受好评的就是所谓的“亡灵叙事”——如前所述,阿燕的故事铺陈和形象建构,并不是作者张翎运用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以线性逻辑形式一一展开的。相反,是中国士兵刘兆虎、美国牧师比利和机械师伊恩共同建构起 “阿燕”的形象与人生,准确地说,是从三个方向 (受难者阿燕、女神斯塔拉和自由之风温德)一点点 “复原”那个已经沉入历史深处的中国女孩 (女人)形象。三个侧面互相印证,互为补充,通过亡灵视角 (三个视角)的不断转换,最终为读者呈现了张翎笔下 “那一个”中国女孩 (女人)形象。
这让笔者联想到此前同样受到强烈关注的作家方方关于土改的长篇小说 《软埋》。 《软埋》所引发的震荡,除了对 “土改”历史意义的不同认知外,就在于作者所采用的“双线逆时叙事”——深度昏迷的丁子桃顺着地狱的十八层台阶拾级而上,一层层梳理来时之路,对家族在土改这个历史事件中的灭顶之灾进行深切回忆;另一方面是作为大小姐的胡黛云 (也就是后来的丁子桃)之现世生死与爱恨情仇。最终,在历史的断裂处,两条线索合二为一,破碎的历史记忆由这个既叫丁子桃又是胡黛云的女子缝合,从而呈现出有异于正统历史和传统历史小说叙事模式的别一种境界。
我们将方方与张翎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她们同为女作家,同样钟情于塑造女性人格,都习惯叙写人性之痛尤其是女性之殇,而且都有着女性作家少有的理性。方方的 “理性”表现在其小说写作时 “观念在握”,并不注重细节描写,她总是将女性在这个由男性掌控的时代里的 “受压迫与被损害”境遇推到极致;而张翎的理性更多的来源于两种文化的隔膜与融通。在北美做过17年听力康复师的她,曾接触过一战、二战、越战、阿富汗战场、中东战场的诸多老兵,因而对于战争对人的伤害她早已不仅仅从民族、阶级、国家、正义与邪恶等维度上思考,更是超越到 “人性”的普世层面上问诊。诚如张翎所言: “关于抗战,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但我觉得远远不够。我想关注的是史书和纪念碑上没有记载过的名字。在《劳燕》中,与其说我想探讨战争本身,其实我更想探讨的是灾难带给人性的裂变与创伤。”⑨女性作为 “美”的极致,尤其是少女 (阿燕其时十六岁,母亲被日本人杀死,父亲被炸死,自己惨遭蹂躏),更是让人欲罢不能;而从亡灵视角对悲惨世界的一点点拼贴,更能引发对战争的深层次思量。诚如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利民对获奖作家及其小说给予的高度评价: “在承接现实关怀的同时,作家们也普遍拓展了思想的视界和景深,力图在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审美空间,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包括在今年集中涌现的一批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也显示出多元化的人性视野、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的交织互补。与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相伴随的,是作家们的文体创造意识的增强。”此言可谓切中肯綮。
注释:
①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 《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
② 阿来: 《自述》, 《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③ 张黎姣、张翎: 《最强烈的震撼是沉默》, 《中国青年报》2014年3月25日。
④⑦⑧ 舒晋瑜、张翎: 《“疼痛”是贯穿我近期作品的一条隐线》, 《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20日。
⑤江少川:《攀登华文文学创作的高山——张翎访谈录》, 《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⑥ 邹雅婷、张翎: 《书写另一种版本的中国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11日。
⑨ 蒋肖斌: 《〈劳燕〉: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人性温暖》, 《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