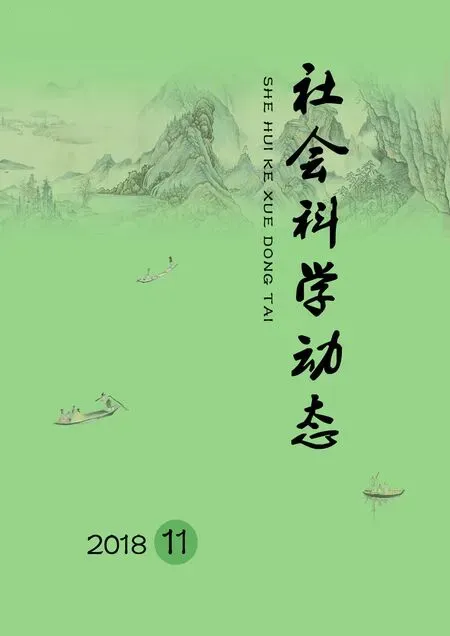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2018-03-31刘风
刘 风
从提出概念到形成与发展理论,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已有百余年时间。社会资本理论最初被用来强调复兴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其表现形式是社区邻里之间的善意、伙伴关系、同情心以及家庭、邻里之间交往等形成的社会网络。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理论被逐渐建构起来,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制度化因素,强调行动者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理论获得经济、文化等资源。由此,社会资本理论得以系统发展,应用范围逐渐扩大。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现代意义的扩充,学术界出现了社会中心论和个人中心论的研究取向,学者分别从不同取向阐释社会资本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一种新型资本类型。进入21世纪,社会资本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内容的逐渐丰富和完善,国内外诸多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移民、流动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行动研究中,并从社会网络、信任、组织和规则等要素出发来描述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经济获得渠道等需求状况,解释他们的流动性动因。
一、社会网络:人口流动的动力型社会资本
从18世纪至19世纪,欧美多数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先后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劳动力逐渐发生转移。有学者从亲属与群体网络的视角出发,研究现代化因素对迁移人口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过程中的调适与同化。于是在人口流动过程研究中,社会网络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研究视角,这为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研究提供了支持。
1.国际移民中的社会网络研究
移民是当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针对移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将国际移民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例如,欧美的外籍移民研究、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等。
第一,欧美等国家的外籍移民研究。欧美国家对移民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移民融合的视角来看,欧洲的社会融合理念是由政府驱动的,在公共政策的推动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多元与平等,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 “自上而下”的模式。美国在学术力量的推动下,经历了同化、熔炉、多元、区隔性融合以及边界重构的过程,形成 “自下而上”的理论驱动性模式。①概言之,欧美等国家的移民都历经了复杂且漫长的融合过程。面对国际上大规模的人口运动,20世纪后半期被称为 “人口迁移的时代”。波特斯是最早认识到社会网络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将社会网络引入移民研究中的学者。他认为,移民迁移行动中的每个环节都与社会网络紧密联系。社会网络是移民由成员身份而获得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社会结构中,可调动稀缺的资源。比如,移民可以借由成员身份获取工作机会、低息贷款、廉价劳动力等资源。②桑德斯等以美国移民为分析对象,讨论了移民的家庭社会网络对其获得 “自雇”地位的影响。③马丁根据社区网络系统论和推拉理论分析了移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为 “供给—推力”因素将劳工推出国门, “需求—拉力”因素吸引移民前往发达地区或国家。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后来的移民借用亲友或本民族同乡建立信息网络,确定迁移目的地。④拥有可支配数量和质量的社会网络对移民行动的可能性具有显著影响,它能够帮助移民获得 “自雇”地位。在特定条件下,社会网络可促进年轻一代移民顺利适应新的生活,可以说社会网络在此时比人力资本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⑤还有学者以移民澳大利亚的索马里女性为例,分析了其社会网络,发现她们存在社会网络缺乏以及社会关系缺失的状况,这不仅限制她们创造新的社会网络的可能性,还限制她们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融合。以上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社会网络对于移民的重要作用。
根据欧美等地的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事实,可将国际移民分为三类:一类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移民。这类移民在流入国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受当地人尊重,可以较快地融入主流社会。例如,移民的父辈在国外顺利实现社会融合,能为其后代争取更好的资源。另外一类是资源贫乏型移民。这类移民拥有的社会资源很少,影响其稳定的就业和体面的生活,最终只能融入当地的底层社会。例如,当移民的父辈生活艰难时,其后代获得丰富资源的可能性较小。第三类是选择性移民。这些移民对其下一代的教育有鼓励,也有限制,对其子女是否愿意继续留在迁移国家或地区没有要求。总体看来,社会网络在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华人华侨的迁移研究。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主要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如广东的恩平、台山、开平、南海、新会、番禺、中山、顺德等地,这些地方的居民试图通过到海外淘金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于是,以获得更多经济收入为动力,中国人漫长的海外迁移行动一直延续至今。学者对迁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所展开的研究,为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从移入地来看,迁居美国的华人受到了当地社会的排斥,拒绝他们进入白人社会。刚入美国的华人被认为是带来天花等疾病的群体,且犯罪的可能性高于本土国民。美国人认为华人都是干苦力活的,如当保姆、洗衣服、从事餐饮服务等;华人不讲卫生,妨碍了本土国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以上种种排斥行动导致迁移者很少与本地人往来,如果美国人不主动来往,华人基本不会主动与美国人交往。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移民发觉最初的人际关系网络大部分都已消失,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尚未建立,且生活习惯与移入地主流社会形成鲜明的差异性。他们在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逐渐被“边缘化”,出现没有归属感和依靠的心理,从而表现出困扰、不安、愤怒、后悔、退缩、忧伤或思乡等情绪。⑦这种 “边缘化”造成的社会空间隔离,势必会影响移民的社会参与机会,阻碍他们在移入地的社会融合。但是华人在这种被排斥的环境中还能生存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原因。
周敏和林闽钢通过研究纽约唐人街早期的移民发现,移民的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都较为薄弱,社会网络为促进他们在移入地的社会融合起到了带动作用。⑧我国在外的移民文化背景与移入国家或地区完全不同,两类群体之间的语言、饮食起居、传统习惯皆不相同。唐人街的存在,使得东方的制度能够在异国他乡得以保存,为那些在异国打拼奋斗的中国移民提供适应生活且不断生存下去的熟悉环境。⑨赵定东等在进行中哈移民的研究后也发现,移民初期移民缺少向上移动的渠道,社会关系可以促进或加快他们适应异国他乡的环境。⑩王春光针对非精英阶层的温州移民展开调查发现,巴黎温州城的温州人凭借其具有乡土性特征的社会关系资源,在巴黎最边缘的经济层面确立了生存、发展的战略,从而实现了最大的融合效果。⑪很明显,社会网络为移民适应移入地社会发挥着促进作用⑫,对海外移民的生存、生产和发展具有积极效应。
2.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研究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其对国内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开始在农民工问题研究中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可以说,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具有差异性。
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研究取向归纳起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流动人口群体内的社会网络特点。例如王毅杰指出,流动农民社会网络有其独有的特点,即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⑬渠敬东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所构成的,其影响着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⑭二是对社会网络工具性特征的关注,即农民工在流入地再建构关系网络的过程。如曹子玮认为,流动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后,在其初级关系网络之上,再建构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网络具有工具理性取向。⑮彭庆恩认为,建筑业包工头进城之后是通过有意识地构筑关系网络,并利用关系网络获得和巩固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⑯李汉林认为,农民工群体是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具有 “强关系”的特点,群体成员间的同质性是构成这种 “强关系”的纽带,非制度化信任则是 “强关系”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国乡土社会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具有乡土特色的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空间的变动、职业的变动而改变。⑰在李培林看来,流动农民工在生活空间和职业变动中所依赖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对其降低交易费用、节约流动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就流动农民工能使用的资源而言,血缘和地缘关系是相对理性的选择方式。⑱三是强调关系在流动人口生存、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刘林平的研究表明,平江人在深圳的发展是充分利用了社会网络的结果,而不是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⑲赵延东也提出,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连人力资本也对其有依赖性,即要在社会网络良好的基础上人力资本才可以充分发挥作用。⑳张连德从关系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民工的熟人关系网络得以延续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他认为,信任是群体间联系的润滑剂,它可以促使群体间合作,维持社会关系的持续性需要。社会网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并维持着群体间的社会网络,其中包括对他人的期待。因为信任的存在,信任感、安全感让农民工倾向于跟亲戚、老乡交往,这就是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得以延续的内在原因。㉑
二、组织、信任与规则:人口流动的要素型社会资本
人口通过流动、迁移进入陌生的环境,不仅体现了地域间的流动、迁移,更体现了精神空间的流动。换言之,流动者在陌生的环境中,其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与流入环境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文化风俗等呈现差异性,两个主体间充满了结构上的张力。有鉴于此,流动者的精神空间得以转移。当地域与精神环境皆出现异质性时,相似的生活、共同的行动规则创造了他们所极度需要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这种信任感和依赖感会通过社会团体等组织形式建构起来。此时,这种组织成为他们抒发内心不适、获得安全感的载体,信任是他们互动联结的内在机制,规则则构成了他们之间互动的约束性资源。
1.流动人口互助互依的组织要素
在社会实践中, “强关系”、 “频繁关系”通常以组织形式加以固定,如家庭组织、企业组织、社团组织等。家庭组织体现的是血缘与亲缘关系,企业组织体现的是业缘关系,社团组织体现的是群体间的组织关系。在陌生人空间,组织要素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交流平台。
第一,国外移民对社会团体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迁居海外的移民本身来看,他们通过社会网络建立起各种社会团体,以维护同胞的权益,相互帮扶、共同发展。以美国华人社区的 “六大公司”为例,就其职能来看, “六大公司”类似于急救团体和互助会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移民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所存在的 “六大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会馆,会馆名称前面还以县冠名。例如,当华人初到旧金山时,他们只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即只要是头上有辫子的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当更多的华人到来时,他们都能在这个组织里找到先来的亲属或同乡,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不同的华人维护不同分支机构的情况。会馆的职能非常多,其主要功能是互利互保。新移入的移民或者生病的老乡能够得到会馆的指点或帮助。因此,这类组织不是法院更不是商业类机构,而是互助互惠的团体。会员之间不谋求、也不施行任何法律权威。
除了 “六大公司”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团体,他们为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靠。例如中华公所 (同业公会,类似于我国的异地商会)、庙堂、布道会等。在中国移民心中,信仰上帝和求神拜佛没有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讲,首要的是学会讲英语,因为许多华人不会讲英语,这阻碍了他们在当地的交流。㉒因此,大量的民族主义组织、中文学校、同源会等组织也相应诞生,以帮助中华同胞更好、更快地适应海外生活。同源会是唐人街最新成立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各大城市都有支会。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反对不公平的、歧视华人的法案。由于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有选举权,所以他们希望能有效地利用这种特权。在城市选举中,各个支会会采取行动,使所有的会员投他们所拥护的候选人。在国家选举中,总部或总局会聚集所有有选票的会员,促使他们全力支持同源会所拥护的候选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标志着华人开始参与美国政治。这也是华人在美国的一个同化的标志。㉓华人在移入地从被排斥到参与当地选举,在某种意义上都体现了其主体性的不断提升,这一转变得益于华人在移入地的关系网络的不断完善与拓展。
另外,同源会这类社会组织非常重视维护华人群体的声誉。它经常敦促成员尊重和遵从美国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使别人对他们无可指责。这种态度同那些老一代华人是根本不同的。对老一代华人而言,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和美国的传统,正如在中国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也没有兴趣研究它一样。这些移民保持着狭隘的家乡观念,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代表的就是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整个华人的声誉。然而,新一代华人的新态度表明他们的思维更加超前、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建构社会组织,并在这些组织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为中国移民的海外生存提供了组织保障。
第二,国内流动人口对社会组织的依赖性转变。自上而下的现代性谋划,体现了中国制度层面的流动人口流动轨迹,流动人口对政府组织的依赖程度之大即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性谋划的表现。然而,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流动性社会转向,流动人口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不信任到逐渐信任的过程,表现出人口流动自下而上的现代性谋划。帕特南把这种现代性谋划看作是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他认为众多社团组织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之间密切的、横向的社会互动,为民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载体。㉔齐心在研究新生代农民时提到,很多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 “我”为中心来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由此产生了流动人口的 “结群”与 “自组织”现象。例如,流动的农民工建立了具有同质性特征的社区——都市村庄。㉕老乡会作为一种 “自组织”支撑着流动人口的精神空间,赵光勇等人认为,老乡会这类草根组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组织一系列群体性活动来促使流动人口获得相应的权益保护,这成为了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组织 “外壳”。㉖总而言之,组织要素对流动人口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在流动人口需要归属感的时候,同乡会、老乡会这些由流动人口以户籍为条件所建立起来的草根民间组织,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情感支持。其次,在流入地作为异乡人,流动人口的各项权益或多或少受到侵犯,他们或者需要在生活和工作中寻求一些渠道,或者需要实现自己的一些诉求的时候,提供维权服务的社会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再次,流动人口想要展开一系列生活和娱乐活动、享受一些社会服务,专业的社会组织能为其提供疏导压力的服务。最后,流动人口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对于其了解社区、了解所生活的城市、了解周边的邻居以及当地的文化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2.流动人口互动联结的信任要素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是信任程度和信任范围。㉗胡荣、王晓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信任能够缩短社会距离,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间的信任度越高,社会距离越近。㉘唐兴国、王可园指出,信任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等功能。作为转型期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信任缺失的结构中。㉙张康之认为,这种信任是一种习俗型信任,而在现代社会还会兴起契约型信任。㉚其实,丁未的研究中就指出了契约型信任的特征,他认为攸县出租车司机对于因耽误了朋友的时间,以金钱作为补偿的 “现代”方式,缺少了 “人情味”。这是因为这种补偿虽然是在熟人之间进行的,不乏感情的成分,但这是一种即时的、对称性的偿还行为,具有更赤裸裸的工具性。㉛用林南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经济交换,而不是那种具有长期性和非对称性,包含了彼此承诺、信任、感情的社会交换。㉜于是,这种补偿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情社会所固有的循环式的 “报”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从金钱换人情变成了金钱换时间㉝,这是流动人口工具理性选择模式不断成熟的表现,也是流动人口适应现代社会规则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流动人口之间的契约型信任逐渐建立起来。
在一个分层系统中,社会位置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是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在占有一些资本方面的差异。㉞流动人口既有边缘性的特征,也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这种双重属性让他们不断正视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合理流动。流动人口的成长性是本质属性,边缘性是过渡属性。成长性属性对激发流动人口的生命力和经济、社会功能具有基础性作用。边缘性属性则会不断削弱,最终走向消失。㉟当流动人口的地缘关系等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之后,防范心理就会出现,防范心理使整体性的社群关系产生裂痕。初级关系虽然仍具有很多的道德义务,却附加了大家都能理解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虽然没有契约,但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某种默契,一种新的互动秩序悄然产生。㊱
3.流动人口约束性的规则要素
规则自人类社会的产生就一直被孕育着,群体生活、生产的有序进行离不开规则。就规则的起源而言,规则源于群体合作自治的需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治规则。自治规则的产生与自治共同体的演进密切相关。规则成为群体成员必须遵守的一项约束机制,这主要是因为规则在群体成员展开行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自发生成的规则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霍布斯所言,正义的、公道的自然法并非一开始就能够让人们遵守,人们能够遵守它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共同权力,这种权力是能够令大家畏惧的。㊲其次,人为定制的规则具有重要的合法性意义。就公共事务治理而言,哈丁、奥尔森等学者强调, “公地悲剧”的产生也可能给利维坦规制规则提供了相应的合法性。立足于对治理公共鱼塘等小群体的分析,奥斯特罗姆认为,当国家制度性安排不能发挥其功效时,为了能够避免“公共悲剧”的发生,自主制定、执行、改进规则等一系列自主治理规则具有必要性。㊳再次,自发规则和人为设置的规则共同维护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埃里克森认为,同质性较强的群体内成员在规则的开发和保持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种规则在于为群体成员获取最大化的福利。㊴
秩序是规则的具体表现,流动人口边缘化空间秩序的形成源于其生存理性自发倾向的秩序论,即流动人口在流动中所依赖的乡土资源,如地缘、血缘关系,这些关系激发着老乡群体的 “集体行动逻辑”,并在现代社会空间中维持着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一旦生存问题不再重要,包括其他的需求得以满足、自己的合理性存在得以确立,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中就会体现出一种由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人类理性选择的自发倾向,也正是这种对利益的理性追求促进了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这为流动人口的在现代社会实现边缘性空间秩序的转换提供了一种能够运用的理想性资源,也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保持合理的空间秩序中的集体存在逻辑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㊵
三、关系: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内核
张鹂从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来自温州的流动人口通过社会网络完成空间转移,以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成功地推动其商业发展,建成属于温州人特有的商业圈和商业模式。㊶这种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带到现代社会,并加以改造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再生产模式,为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生产、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定支持。李汉林、渠敬东对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并从问卷结果中分析了农民工的关系网络,描述了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状况。㊷李培林借助对济南农民工的调查,得出农民工可以依靠血缘、地缘为基础的 “强关系”来获得相应职位的结论。㊸刘林平以深圳的平江村流动人口为例,阐述了流动人口之间所存在的四类关系类型,分别是 “强关系”、 “弱关系”、 “弱强关系”和 “强弱关系”。他指出,在流动过程中,关系可以给流动人口带来更多收益。㊹王桂新、武俊奎认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社会距离,农民工拥有的关系资本越多、越广泛,就越有利于消除自己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㊺彭庆恩在对农民工 “包工头”所开展的个案访谈中发现,这些社会网络构成了关系资本,并被个人所拥有,其作用超过人力资本等其他结构性资源。㊻另有大量调查数据显示,乡土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而言,意义重大。有学者在访谈同村人一起务工的537个被调查者时发现,63.3%的人说他 (她)和同村人 “经常见面”,16.5%的人说 “偶尔见面”,20.2%的人说 “很少见面”。㊼虽然流动人口的职业、生活方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他们仍然依赖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初级关系。陈燕祯研究发现,虽然新移民在台湾已经有了新根,其子女也获得教育、成长和工作的机会。但是他们所受到的社会排斥也非常明显。主要是因为他们封闭性的社群网络系统,给当地社会产生了很多影响,形成了新移民文化和经济产业聚落。但多元文化和社会包容的模式并未呈现出来。㊽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可知,社会资本建立在对收益和回报的预期基础之上,本质在于获得效率和效益。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类型一样,具有同样的地位和性质,都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资本不同于其他资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他所在群体可有效利用的社会网络的范围。他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及社会网络的广度,决定了他所拥有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㊾组织是社会资本的第二个要素,它可以被视为社会网络的实体或表现形式。一方面,流动人口成立各种组织,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络通过组织形式被建构出来,成为一种看得见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组织要素发展成为流动人口赖以生存、工作的载体。信任和规则作为社会资本的第三和第四个要素,对流动人口而言,能够增加组织关系、网络关系的可靠性和规范性。因此,不管是欧美等国际移民还是我国华人华侨迁移研究,亦或是国内的流动人口研究,迁移人口在迁入地从进入到适应、再到立足,社会网络、组织、信任和规则都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迈向流动性的社会资本研究新视野
从整个人类迁移的历史长河来看,流动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不仅体现了一种地域空间的迁移和转变,更体现了流动人口原始社会资本的重新建构。流动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其自身携带的社会网络面临着巨大冲击,每天感受的、参与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在传统社会生活时的规则和氛围。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差异,让他们不知所措又无法抗拒。由此,他们只能充分调动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对在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资本进行消解或解构,重新建构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社会资本类型,增加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社会资本内容,为实现在现代社会的立足和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更有价值的资源。
吉登斯认为, “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来’”。正是这种把社会关系从地方场域中提炼出来,再使社会关系网络在更大的空间中进行 “再重组”或 “再联结”的 “脱域”方式贯通了社会生活与其所嵌入的具体场域之间的特殊关节点,使得与具体场域不匹配的制度在极大程度上扩展了延伸的范围。㊿从这一角度来看, “再联结”或 “再重组”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扩大了社会关系资本的建构范围,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进一步融合的空间。
1.流动性转向与能力
当今社会,全球化时代的突飞猛进加剧了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流动性,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不再具有封闭性特性,而呈现了流动性特征。鉴于此,西方研究出现了流动性转向的新趋势,并使流动性成为观察和解释社会变迁的新维度。流动转向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开始呈现和建构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表征和形塑着人的身份与认同,人所获得的权力结构也在流动中不断实施和展现。在鲍曼看来,流动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在资源稀缺和分配不平等的社区中,持续流动的自由很快成为了晚期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分层因素。他将流动层次的上升视为现代生活的建构元素,正是这种自我的 “流动性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在这一层次体系中的位置。流动的能力就是在社会中存活的能力,流动权力的掌握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群体、社区和城市的发展和生存。流动能力越高,流动速度越快,就会在社会各种关系和事物的运作过程中占据越有利的位置。对于个体而言,是否具有一定的流动能力,已成为其是否能够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流动能力既是参与社会过程的条件,也是社会权力的表现。从流动性转向与能力来讲,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假若具有流动能力,就会在流动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这些资源和权力可以提升其在流动社会中的位置。
2.流动性与社会资本
社会系统的封闭性对于规范的出现十分重要,如果信任关系建立在合理基础上,即受托人已被证明值得信任,系统封闭与否便十分重要。这种封闭性可能导致极端信任或极端不信任,除去此种不稳定性,一定程度的封闭为系统内部的个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封闭的系统内部给予成员的社会资本必然是有限的,那些维系社会资本不会削减的社会网络、组织、规则要素必定缺少再生产或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在封闭性系统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基本不会出现,甚至会出现“内卷化”倾向。
流动性是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流动空间弱化了城乡区域空间的行政边界、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限制作用,促使人类活动溢出固定的地理空间。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时间、空间限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代社会已然成为一种流动性的社会,因此形成了流动的空间、时间或社会等相关概念。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流动性特征打破了原本固化的常态和社会秩序,流动性转向成为当代社会必经的过程。流动性包含的就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在流动转向过程中,不同主体间开始呈现和建构复杂的社会关系,表征和形塑着人们的身份与认同,人们所获得的权力结构也在流动中不断实施和展现。在流动性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将会具有更多、更新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对于流动性社会中的典型群体——流动人口而言,他们的社会资本将会发生更多的转变,甚至可能对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较大影响。
注释:
① 杨菊华、贺丹: 《分异与融通:欧美移民社会融合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②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1).
③ J.M.Sanders,N.Victor,Immigrant Self-Employment:The Family as A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2).
④ Martin Philip,The Migration Issue,in King Russell ed.,The New Geography of European Migrations,London:Belhaven Press,1993.
⑤ Zhou Min,C.L.Bankston,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Case of Vietnamese Youth in New Orleans,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4,28(4).
⑥⑨㉒㉓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筑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 E.P.Robert,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
⑧ 周敏、林闽钢: 《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 《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⑩赵定东、许洪波: 《“关系”的魅力与移民的 “社会适应”:中哈移民的一个考察》,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年第4期。
⑪ 王春光、Jean Philippe BEJA: 《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⑫ 任远、陶力: 《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⑬ 王毅杰、童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⑭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柯兰君、李汉林主编: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⑮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⑯㊻彭庆恩:《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以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包工头的个案为例》, 《社会学研究》1996年4期。
⑰李汉林:《关系强弱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⑱㊸㊼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⑲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⑳ 赵延东、王奋宇: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㉑ 张连德: 《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何以延续?——基于信任视角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5期。
㉔ 转引自胡荣: 《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㉕ 齐心: 《延续与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㉖㊾ 赵光勇、陈邓海: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㉗ 颜晓峰: 《信任:一种社会资本》, 《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㉘ 胡荣、王晓: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㉙ 唐兴国、王可园: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㉚ 张康之: 《论信任的衰落与重建》, 《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㉛㉝㊱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㉜ 边燕杰: 《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㉞ 李路路、边燕杰主编: 《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㉟ 宋林飞: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㊲[英]霍布斯:《利维坦——论国家》,张妍、赵文道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㊳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余逊达、赵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㊴ [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 《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㊵ 潘泽泉: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㊶[美]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㊷李汉林、渠敬东:《关系强弱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李培林主编: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㊹ 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家庭与家族网络支持——深圳“平江村”的调查与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㊺ 王桂新、武俊奎: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㊽ 陈燕祯: 《台湾新移民的文化认同、社会适应与社会网络》, 《国家与社会》2008年第6期。
㊿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