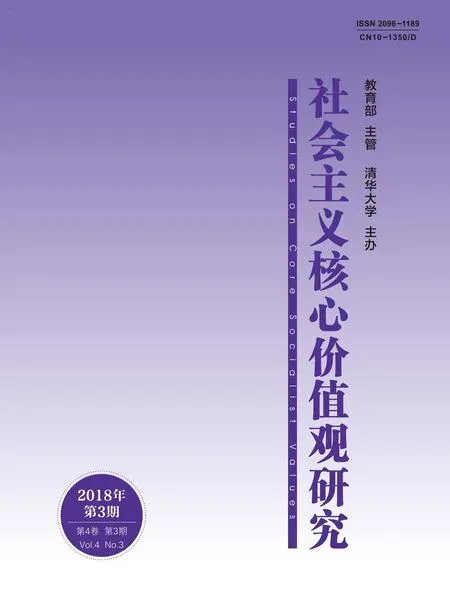新时代师德建设的伦理进路①
2018-03-31李建华
李建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同时,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等,特别是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对师德建设提出更加明确、更加系统的要求。具体说来,习近平关于师德建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四有”“四统一”“三路径”:“四有”就是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四统一”就是教师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第1版);“三路径”就是实现教书育人要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这构成了新时代关于师德要求与实践的完整体系,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必须突破原有囿于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路,使之置于更加广阔和深远的伦理空间。因为,现代性伦理文化无须争辩的事实是伦理与道德之间的撕裂与弥合,西方伦理学中“规范论”与“德性论”争论和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好人无好报”怪象就是例证。师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来协调有序推进。
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进行师德建设,就是要解决教师的责、权、利如何统一的问题
职业就是由于社会分工和劳动内部分工,使人们长期从事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业、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活动。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职业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伦理意义:由于职业是社会分工或劳动内部分工的产物,所以职业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职业歧视都是不道德的;职业是社会职能的专门化,所以从事某种职业就是为社会分担某种责任,不爱岗敬业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职业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所以职业回报所获得的工资待遇是基本人权,随意剥夺他人劳动权或克扣、拖欠他人工资的行为都是侵犯人权,也是极不道德的表现。
从西方伦理学的演变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元伦理学由于对现实道德问题的远离与回避而逐渐退出主流,被规范伦理学所替代。而规范伦理思想一直存在两种传统:一个是权利论,另一个是义务论。以权利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学直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论证道德规范的目的在于引导公共权力为公民权利和幸福提供保证,并对公民权利负有道德义务,这一传统由古希腊柏拉图开启直到罗尔斯。以义务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学则将社会个人作为道德规范约束的对象,通过制定道德规范来引导个体行为符合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麦金太尔。规范伦理学的两种传统尽管存在分歧,各自的侧重不同,反而印证了现代伦理学的整体性,在社会权益保障与个体行为自律之间,忽视任何一方都不可取。而中国伦理学传统是义务论范型,将权利论规范伦理思想介入中国现代道德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基于职业自身所蕴含的伦理要求,职业伦理应该属于权利论规范伦理范畴,教师道德虽然因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而区别于其他职业道德,但就其普遍性伦理要求而言,应该遵循职业伦理的一般性要求,进而自然地导出师德建设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全社会要真正形成“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良好环境,给教师一个人道的态度和待遇;二是要平等地充分保障无论作为公民还是作为一般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或足够的依据来要求教师遵守职业道德。换言之,如果社会或其他职业群体对待教师是极不人道的态度,那么教师有权拒绝任何的道德要求与评价。六安教师讨薪事件就暴露出对待教师的职业伦理严重失序的问题,无论是拖欠工资还是对讨薪教师进行动武,都是极不人道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试想,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教师如何恪尽职守?如何安心教书育人?
从德性伦理的角度来进行师德建设,就是要解决教师自尊、自强、自律、自利的问题
与规范伦理学相反,德性伦理学强调德性是人类道德之光升起的地平线,具有优良德性的社会个体一开始就具有天然的道德信仰,能够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种类事件中坚守道德,保持道德上的完整性和神圣性,哪怕是在伤害自身利益的条件下也能甘愿作出自我牺牲。如果说规范伦理学强调公平、正义、应当是优先于善的,强调善的行为和善的人格只有在正义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证,那么,德性伦理学则强调所谓的公平正义规则只能存在于以德性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之中,在德性之前或之外不可能有普遍的正义规则。其实,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构成了分析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完整框架。当代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争,不是告诉人们解决道德问题只存在非此即彼的方案,而是提醒人们不能忽视和遗忘某些方面,或者强调某一领域而忽视另一领域。我们在强调从具有规范伦理性质的职业伦理视角进行师德建设的前提下,还应该从德性伦理的视角,讨论师德建设如何做的问题。
由于职业是基于自由自愿而选择的契约性行为,所以人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内生出理想、技能、态度、纪律、良心、荣誉、作风等要求,形成一个道德自律体系,这就是职业道德,对于教师而言就是师德。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是“爱国守法,敬业爱生 ,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要求:“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从职业道德出发,教师就不能仅仅把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而应该把教育责任扛在肩上,把既当“经师”又当“人师”作为职业理想;技能是自身完成职业责任的必备条件,这个技能就是扎实的学识和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决定事业高度,态度是对职业的充分尊重,就是对教育事业的恭敬,不敢苟且,不敢轻视,必须认真;纪律就是行业规矩,要求教师遵纪、守法、照章,特别是不能搞行业腐败;良心就是教育责任的内在化,要求教师要有仁爱之心,有教无类,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克己慎独;荣誉就是要求教师以职业为荣,爱岗敬业,知耻辞让;作风就是道德品质的行为化和个性化,在工作中做到热心、细心、耐心、诚心。这些德性要素构成了师德的整体性要求,并且这种要求是不会也不能因外在条件是否具备而能放弃或放松的,也正是这种自觉的、无条件性的内在要求,显示出教师道德的独特价值,教师才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师德建设是教师自身的事业要求,必须“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
从教育伦理的角度来进行师德建设,就是要解决把教育目标与立德树人结合好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就是我们大学的伦理目标。中华民族是重视德育和志趣高尚的民族,“立德”为我国古代所谓“三不朽”之一。《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立德有德、实现道德理想,其次是事业追求、建功立业,再次是有知识有思想、著书立说。这三者是人生不朽的表现。把“立德”摆在第一位,是因为万事从做人开始。“立德树人”也几乎是历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理念。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使受教育者能够提高主体意识,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达到自我发展。
育人之道,德字为先。在社会大变革的现实情境下,强调“立德树人”显得格外迫切。爱因斯坦曾经在名篇《培育独立思考的教育》中谆谆告诫:“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0页]这话是对受教育者说的,更是对教育工作者说的。大学要善于化知识为德性。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教育的根本是灵魂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知识之所以就是力量,是因为它蕴含了德性,所以在西方,德性和力量是等义的。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大学应该是最圣洁的地方,老师应该是灵魂工程师。遗憾的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极个别教师既不学高更不身正,成了道德的缺席者,比如见利忘义、吃拿卡要、弄虚作假、违背学术良知,等等,以如此形象示人的教师,怎能使学生服膺?又怎能教育好学生?“师有百行,以德为首。”师德犹如教师的生命,是为师之本、教育之基。应严格考核管理、健全制度规范,促进良好师德师风的形成。高校师德建设首先需要广大教师应淡泊名利、志存高远,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以人格魅力、学识魅力赢得广大学生和全社会的尊重。在此意义上讲,师德建设离不开教育活动,离不开教育过程,或者说,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就是师德建设的过程,离开教育本身谈师德建设,无疑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