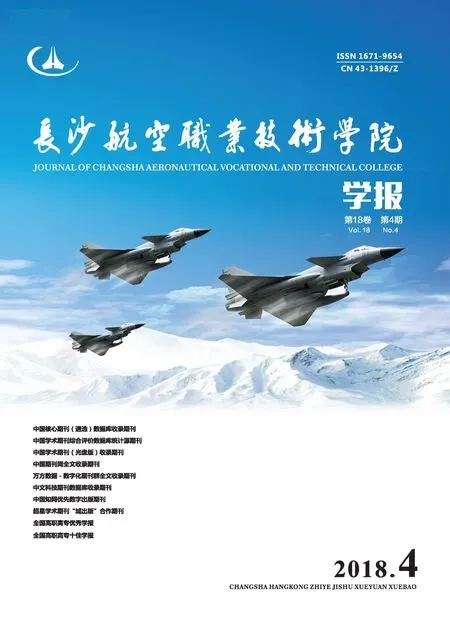在迷乱的现实中“呐喊”
——方方《白梦》解读
2018-03-30杨珊珊
杨珊珊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小说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的同时,方方早期的作品也被评论界视为新写实小说的重要代表。从《在大篷车上》到《风景》再到《祖父在我心中》,可以说,方方的创作风格是多样的,观察生活的角度也非常独特。小说《白梦》是方方1986年3月写于武汉的一部中篇小说,1986年发表于《中国》第8期,与她198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的《白雾》以及1989年发表于《长江》第1期的《白驹》合称“三白”。从作者1986年的自述中可以看出,1986年是她创作风格转型的分界线。小说《白梦》在表现手法上带有很强的反讽意味,小说的主题也有多重含义,剖析《白梦》所蕴含的主题,对理解方方转型时期的创作风格有重要意义。
一、图解“荒诞”的现实
“荒诞”一词多运用于哲学层面和美学层面,在文学中,“荒诞”作为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而被人们所关注。“荒诞”哲学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多表现为对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的探讨,从而与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有巨大的渊源。在方方前期的作品中,“荒诞感”并不那么强烈,反讽意味也不那么浓厚,大多都是作者在冷静地观察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间段里,其作品就明显具有荒诞意识和反讽意味。小说《白梦》对现实图景的描绘恰如其分地例证了这一点。《白梦》主要描述的是文化圈的生活现状,整部小说是由众多生活的“点”合成的生活的“面”,小说叙写的故事也是由一个个的人物经历合成的整体。小说《白梦》通过主人公“家伙”的视角,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家伙”在电视台工作时所接触到的人以及与她们(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小说以“家伙”从小贩手上买到一件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血衣为开场,一开篇便将商业界的混乱场景展现在读者眼前,迷乱的各类场景由此铺开:“家伙”去医院看病,医院里却也分“三六九等”,医生皆是一副“性急”的嘴脸;“家伙”去坐公交,还未到站,就遭列车员“驱赶”;“家伙”坐公交,公交车熄火,“家伙”和车上的人下来推车,车发动了,结果司机却扔下她和推车的人跑了;“家伙”去住酒店,清洁员拒绝换干净床单,声称床单十天换一次……无论是医院、餐厅还是普通的出行,作者都描绘了极尽荒谬的生活景象。这种荒谬的生活透露着无奈的同时,也带着挥之不去的“灰色”映像,正是类似的“灰色”映像构成了小说的基本色调——“灰暗”。小说在形式上通过医院、餐厅、作协、影视界、电视台、会议室等场景的自由转换,显示出一种“走马灯”式的效果,在内容上则通过苇儿、丝瓜、吴猴子、老头子等人物的对话、动作、内心独白等凸显出由内到外的荒诞和反讽。
《白梦》是方方“三白”系列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方方创作风格转型的重要分界。小说《白梦》在叙写真实的基础上,还有着现代主义中对“世界荒诞”这一观念的表达。如果说方方1987年发表的《风景》叙写的是一种生活的真实,那么小说《白梦》则叙写的是一种社会的真实,且这种社会真实与理想中的社会真实相去甚远。在方方笔下,社会仿佛没有规则可言,一切场合都充斥着“瞒”和“骗”。小说主人公名为“家伙”,与其说是人名,不如说是个简单的代号。在日常生活中,“家伙”是我们对别人的戏称,有时还带有轻蔑的意味,而将这样一种不明确的指代赋予女主人公,则产生一种模糊感。小说借“家伙”之眼,细致地观察了文化圈及医院、影视界等其它圈子里的人和事,用观望和调侃的态度图解着另一个社会现实。在“家伙”看来,这些都是真实而荒谬的:丝瓜作为一名医生,却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丢弃在郊外的农田里,还义正言辞地说是为了顾全大局;老头子拍电影《山上的海》,为了增加场景的“艺术感染力”,宣称演员要无条件“为艺术献身”,甚至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全;瑛瑛本是男性,却因自己以前的笔名“天雄”没有吸引力特意取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随后便声名大震……这一切让人感觉荒谬的事实透露着作者对混乱社会现实的讽刺。作者通过“家伙”的个人印象来关照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人物语言、人物形象还是人物命运都在图解“荒诞式”的现实。这种“荒诞式”的现实主要以“展览”各色人物的方法来展开叙述,在描绘人物形象时,作者力图在细碎生活背景中画出人物的“魂灵”:小说女主人公“家伙”作为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却仅凭一张大学文凭和发表过的几篇小说就进入了电视台;比“家伙”小7岁的低年级同学苇儿,凭着一副“清纯可爱”的模样便在一流作家面前获得称赞;“家伙”去医院找丝瓜看病,丝瓜建议照X光,结果诊断说她肺上有个4×5的阴影,而到了大医院去找别的医生检查时,却查出只是一块伤湿止痛贴,并没有所谓的阴影……“家伙”身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她的观察结果是失望的,而“家伙”本身与其生活的环境也有着难以调合的矛盾:为了创作一部能获大奖的作品,“家伙”嫌弃宿舍太吵,请求作协给她安排一个安静、宽敞的房间,结果到了那里,“家伙”又忍受不了内心的孤独,后又决定住在一个小黑屋里。而医院、作协、影视界、官场皆是乱像丛生:医生在其位却不谋其职,把病人的生命当做儿戏;作家创作并不是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是出于利益和成名的需要;制片人为了获得大奖而弄虚作假……小说从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她的生存环境,一切的存在都显得荒诞而无意义:模糊不清的人物关系、碎片化的故事情节以及贯穿小说始终的“梦”。小说笔调平静而诙谐,但这类诙谐却包含着深刻的“反讽”意味,一方面加强了人在迷惘现实中的无法捉摸之感,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当下环境中,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荒诞”。
二、揭示痛苦的人生经历
方方的小说创作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温暖还随处可见,到了中、后期,凝重而充满讽刺意味的作品就增加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方方的小说都与她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作家的创作大多有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来自童年还是来自成年后。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于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经历的理解就会不相同。1986年作为方方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分界,“1987年的《风景》被认为是方方风格成熟的标志,而1986年的《白梦》恰是她创作变化的重要转折点”[1]。从作家的经历上看,1986年,方方经历了好友的“背叛”,对方是一位同行,比方方小7岁,且私底下还称呼方方为姐姐。在好友大学四年将毕业之季,方方不顾烈日,不辞辛劳帮她搬行李、买车票,没有一句怨言,可到最后,那位好友却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小说中套用了方方的经历来污辱她,这让方方对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产生了怀疑。也就是经历了1986年的“背叛”之后,方方的内心便充满了痛苦,对好友的冷漠态度更是伤心。方方曾经在《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当时觉得1986年的日子是难过的,我觉得很不舒服。”[2]从作者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强烈感受到了人存在于世界中的孤独感。
与作者1986年的经历相对应,小说《白梦》从另一角度也记录了这种真实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在小说中苇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说《白梦》中,苇儿是“家伙”的师妹,且比她小7岁,这也恰好对应了作者在创作《白梦》时的自序。小说中的苇儿极善伪装,靠着自己伪装出的单纯、天真赢来了很高的人气,而“家伙”却对苇儿的做法鄙视不已。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讽刺,透露出作家对真实的渴望。从苇儿的整体形象塑造上来看,都与1986年的那位好友一致。小说《白梦》中,苇儿讽刺“家伙”为了稿费故意把小说写得很长,自己却向《花都》杂志投了一篇很长的小说《男仙儿》,还在小说里“编了个下流的故事,在介绍女主人公时套用了家伙简单的历史,这又与1986年的“背叛”是一致的。纵观整部小说,作者看似是借“家伙”的眼来看,实则是将个体潜藏在文本背后,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进行回忆,而这种回忆在方方的笔下则是痛苦的。作者通过揭示自我人生经历当中的痛苦记忆,对人心的质询和真诚的期盼也浮现出来。
三、探讨人的生存困境
自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至今,以人为本的文学思想就可以在现代、当代的众多小说中得到印证。以人为中心进行文学创作则大多表现为对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在方方的众多新写实小说中,《风景》表现出了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照,而小说《白梦》则体现出了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小说题名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句有着相似的表达。整部小说虽未对“梦”的实质作出诠释,但却从文本中那些细碎的人物经历中揭示了《白梦》所暗含的观念:人生如梦,充满了痛苦的记忆,在迷乱的现实中,一味地逃避只能陷入深深地孤独中,只有正视迷乱的现实,才能避开“无意义、无价值”的人生。方方的《白梦》创作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处境是不可把握的……人们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不得其解的问题”[3]。小说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活在不同环境下要遭遇的难题:作为病人,遇到不负责任或没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很有可能顷刻间把你从“人间”拉入“地狱”;作为工作人员,为了领导能获大奖,随时随都要熬夜“奉献自己”;作为演员,遇到贪图名利的制片人,只能“为艺术而献身”;作为朋友,任何时刻都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在背后给你致命的一击……作者在观察这广阔的社会现实时,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览出来,她们的存在以及对他人存在的影响正是作家对人生存困境的探讨。
仵从巨在《灰色幽默:方方小说的个性与评价》一文中,总结方方小说中的幽默色调是“灰色”,这种“灰色”有异于海勒的“黑色幽默”,它并不在于用崇消解人生的意义,而是在排遣人生些许悲哀的同时,照见人世的迷离与悲欢,从而探求现实背后的症结所在。小说《白梦》借“家伙”之口说出对真实世界的深思和焦虑:“我若带了眼镜,把世界的底细看得一清二楚便会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在干无聊的事还是在干无用的事”[4],“家伙”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是看清了的,但看清之后却更加迷茫,这就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和人生价值的溃散世界对于身陷于信任危机中的人类而言,是充满疑惑的,人们甚至有时找不出原因究竟在何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家伙”对自身及他人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她深深感到自己是在为了稿费而榨干自己,最后只剩下满纸空话,“家伙”也看得清苇儿对她的迫害,但却仍旧陷入“背叛”之中。在真实逐渐褪去的现实面前,女主人公也尝试着一种观望的态度仍他们去折腾,这也是“家伙”的“呐喊”和“反抗”,但却在无形之中被“梦”质询着。小说题名呈现出一种模糊、难以捕捉的人生状态,也充分表现出主人公内心的迷茫,在这迷茫的生存状态下,又有着对自我存在状态的清醒意识,因此形成对比,产生了对意义的质询和对生存困境的探讨。小说中虚而不实的人生状态让“家伙”感到了自身与世界的隔离。对真实世界、真实情感、真是人生的追寻,恰似“家伙”用双眼去看“荒诞”的现实之后的渴望。
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思潮中,萨特的存在主义
深深影响到了方方的创作,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在《白梦》中寻到踪迹,即集中提现人存在于世界的荒诞感。方方在1986年到1989年这一时间段里创作的小说大多具有荒诞感,“在表现对客观世界的无奈思绪时,方方强调环境决定命运,强调物质世界、外部环境对人的异化”[5],从小说内容上看,《白梦》在倾诉个人痛苦记忆的同时又揭示了一些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利益问题、真实性问题等,从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上看,《白梦》则是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生经历的“另类”写照。小说女主人公“家伙”的形象塑造充满了象征意义,象征着沦陷于混乱现实中的“清醒”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思考。“家伙”的生存状态及人生遭遇冲击着人关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思考,传递出现代人的一种内在焦虑。方方在《白梦》中书写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图景,在表达主人公对迷乱的现实的无奈与痛苦感的同时,又探讨了造成这一现实的关键原因,那就是:对谎言的伪装和对道德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