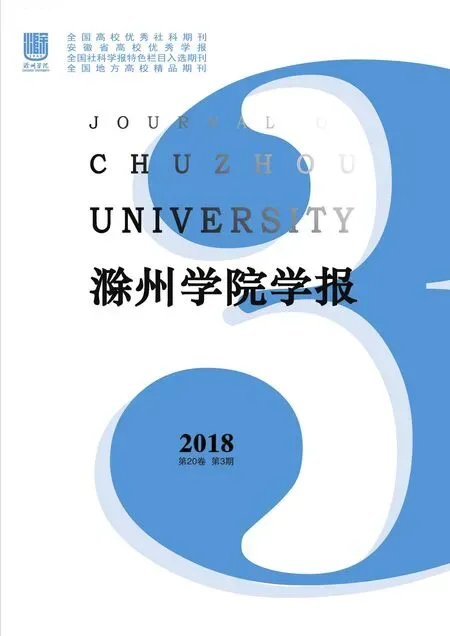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公共育儿支持体系构建初探
2018-03-29闫静
闫 静
二胎政策施行后,我国0-6岁幼儿激增,很多家庭面临经济方面、教育方面、职场方面等较大的育儿压力。这些问题在二胎家庭中尤为突出,二胎家庭的父母年龄较大,面临着两个孩子的抚养压力和教育压力,在生活和工作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宽容和支持,这一群体面对的诸多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笔者对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的6岁前幼儿育儿家庭、社区、早教机构、幼儿园、幼儿教育培训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了大量的问卷和实地走访调查,依托社会支持理论,分析家庭育儿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社会支持理论概述
“社会支持”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社区心理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社会支持”被定义为:作为供者与接受者的两个个体之间所感知到的资源的交换,目的是增进接受者的健康。[1]
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者开始将社会支持理论引入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中,这一理论得到充分发展和普遍认可.美国社会学者卡普兰(Caplan G) 在研究家庭支持系统时指出社会支持的主要作用是汲取个体之外有效资源来促进个体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这些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2]社会学家林南,阿尔弗雷德等人( Nan Lin,Alfred) 将社会支持来源分为三类主体,即其他个体,社会团体和社区。[3]
截止到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支持理论没有统一的概念,对于社会支持的理解在不断的发展中。从我国研究学者的观点中来看,殷世东、朱明山认为从国家的政策法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系统由国家、社会、社区、学校和家庭等方面构成。[4]邹泓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支持源、支持行为和被支持者对支持行为的主观评价。[5]
总的来说,社会支持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体系,由其支持主体对支持客体提供多方面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各支持主体和支持客体之间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的总和。
二、家庭育儿的社会支持系统构成
社会育儿支持体系的建立并非是某些部门或某些人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中的个体和机构应该共同承担的任务。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支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社区、家庭、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
在此,我们将育儿家庭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将育儿家庭特别是幼儿父母作为支持客体,分析社会育儿支持体系的构成主体包括为以国家层面为引导,以家庭和早期教养机构为核心,以社区和其他社会机构为辅助的基本结构。
(一)政策引导主体:政府
政府在体系中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观念引导、监督施行等方面。应从法律层面重视社会育儿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各层次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划分,引导社会中科学育儿观念的养成,增加早期教育资源建设的投入,监督社会育儿体系的实施情况。
(二)育儿实施主体:家庭
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角度,对家庭的理解更为宽泛,除了父母之外还应该包含能够为育儿提供支持的其他家庭成员。家庭作为社会育儿体系的主体,应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家庭各成员的作用。
(三)科学育儿的引导者:早期教养机构
早期教养机构既包含幼儿园、早教机构等教育类机构,还包括为家庭育儿提供支持的婴幼儿保健机构,如社区医院、各地妇幼保健医院等,此类机构能够为幼儿的科学喂养、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早期教养类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为幼儿提供教育、保健、医疗服务,为家庭提供教育和婴幼儿保健咨询,为家长提供科学的教育和养育知识。
(四)社区
社区是仅次于家庭的幼儿成长的重要环境,社区的文化环境建设对幼儿有重要的影响。社区在社会育儿支持系统中的主要任务包括提供适宜的公共活动场地和游戏设施、营造适宜的文化氛围、提供简单的早期教育资源。
(五)其他社会机构
其他社会机构包含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所有的与幼儿相关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它的主要任务是在自己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家庭育儿的需求提供各种的协助。
三、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公共育儿支持体系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政府机构、育儿家庭、早教机构、幼儿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的走访调查,结合社会支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政策引导力度较弱
现有的政策更多是针对3-6岁幼儿园教育的相关法规政策,针对家庭教育指导、3岁前幼儿教育等方面缺少政策方面的支持。
在政府引导和投入方面,多集中于3-6岁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引进了多所优质的社区幼儿园,为社区幼儿园的建设提供了各种政策上的支持。3岁前的幼儿教育机构政府投入相对较少,公立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多以民办、私营机构为主,且缺少科学规范的国家标准,存在机构数量较少、服务能力差、质量参差不齐、收费较高等问题。
在家庭教育的科学指导方面,多依赖于公立幼儿园来承担,政府机构对于科学育儿的宣传参与的比较少。
(二)家庭育儿的保育支持力度较大,教育引导相对缺乏
在调查中,有90%以上的幼儿父母表示有其他成员会为家庭育儿提供人力或经济上的支持,有一半以上的父母表示在自己上班期间,家里的老人承担保育孩子的任务,在照顾孩子方面,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力度很大。
调查发现大部分3岁前幼儿的主要照顾者是祖父母和保姆,祖父母的年龄、自身教育水平都对幼儿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保姆群体的素质参差不齐也是很多家长顾虑的因素。
另外,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对于如何教养孩子有迫切的学习愿望,但缺乏便捷的学习途径,往往依靠熟人间的传授、长辈的指导等来获取。调查中发现,新一代的家长善于运用网络这一学习途径,会有意识地登陆育儿类网站、教育公众号等,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教养孩子的相关知识。但此类网站和公众号的教育知识多为经验总结类知识,缺少总结提升,还存在参差不齐、宣传口号性强、缺少科学性等问题,这些原因也导致父母接触到的知识较为零碎,没有科学体系,大部分父母不具备对于知识的判断能力,容易走入误区。
(三)优质教养机构普遍缺乏,尤其是3岁前阶段
一为早期教育资源量少,社会上存在很多的教育培训类机构,多集中于中小学阶段,面向6岁前幼儿的较少。在较少的面向幼儿的教育培训机构中,有大多集中于3-6岁的幼儿,针对3岁前的少之又少;二是免费的社会早期教育资源少,现有的社会提供的早期教育资源多为高收费的,少数的社会公共机构提供的早期教育资源能够免费向公众开放,但又存在受众面广,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四)社区和其他社会机构的育儿支持意识淡薄
社区和其他社会机构是社会育儿环境的重要组织部分。在调查中发现,只有少数城市高端社区中设置了幼儿活动区域,提供少量的幼儿活动设施,大部分社区只是配备了健身器材,并不适合幼儿使用。
总体来看,在社区建设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建设方面,针对婴幼儿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较弱、社会基础设施未能满足0-6岁幼儿的需求。现有基础设施更多的是面向所有人群的,并未进行精细的划分,这就使得家长带幼儿出行时遭遇了诸多的不便,如很多公共机构并未设置哺乳室和婴幼儿休息室,在公共交通方面没有建设方便婴儿车等的专用通道和设施配备等。
四、关于公共育儿支持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社会育儿体系的建立
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法规和措施来对0-5或者0-6岁幼儿家庭育儿提供各种支持,如日本从1994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天使计划”,内容包括改善雇佣环境、发展低幼儿童保育机构、提供家庭育儿的健康保障支持、改善育子家庭的住宅和社区基础建设、推进宽松式的学校教育、改善家庭教育、减轻育儿费用等方面,旨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建构起全社会对于育儿提供支援的网络与系统工作;芬兰政府机构Kela会为每个准妈妈提供婴儿礼盒或者140欧元的生产补贴,政府为0-18岁的儿童每月提供生活补贴和免费的医疗服务。
综合分析各国的相关政策法规,主要包含以下方面:改善雇佣环境,保障育龄父母的育儿时间,如母亲的产假和哺乳假、父亲的育儿假、保障育龄妇女的就业机会等;为早期家庭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可以通过减税、专项教育经费、育儿生活补贴、发放婴幼儿用品等多种方式;完善婴幼儿早期教养的保障机构,主要集中于早期教育机构(如幼儿园、托儿所等)和婴幼儿健康保障机构的配置建设和完善,以能够满足婴幼儿的教养需求;良好社会育儿环境的建设,目的在于为婴幼儿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充足的婴幼儿活动场地、适宜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既为社会育儿支持的构建提供方向引导,也是社会育儿体系建立和与运行的有效保障。
(二)增加优质幼儿教育资源,提供育儿教育保障
加大对于早期教育资源的投入,扩充早期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是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基础条件。增加优质幼儿教育资源主要依赖于有质量保障的幼儿教育机构(包含3岁前的早教机构)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建设两个途径。
幼儿教育机构的建立我国一贯坚持多种渠道办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幼儿教育机构的建设中来。我们以为在0-6岁幼儿早期教育机构的建设中也应充分的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参与到建设中来,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增加公立幼儿教育机构的同时,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标准(特别是3岁前幼儿教育机构),引导幼儿教育行业的科学、规范运行。
公共教育资源的建设在0-6岁幼儿教育方面重点在于教育资源的开发、教育资源的推广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建设开放。6岁前是幼儿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提供丰富的刺激有助于其健康成长,增加对于早期教育资源的开发力度,丰富早期教育资源的类型,提高早期教育资源的适宜性,能为幼儿教育提供有效地支持。公共教育资源的建设更多从政府层面来进行,包括提供幼儿活动场地、幼儿图书馆、儿童乐园、幼儿科技馆等科学文化的公共免费场所,为家庭育儿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
(三)提升婴幼儿保健服务,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婴幼儿时期身体的免疫能力较差,良好的医疗保障非常重要。2015年日本政府分配1.36万亿日元(约合114.77亿美元)用于支持育儿家庭、改善育儿护理工作环境,并提高医疗服务及护理水平。目前我国已经提供免费的孕期检查和新生儿检查,检查项目多由各地的妇幼保健医院和计划生育服务部门来承担,覆盖率较高。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和预防保健机构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卫生服务体系也已初见成效。
从婴幼儿保健角度,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加大婴幼儿家庭护理知识的宣传力度,让父母了解婴幼儿的护理常识,具备基本的护理能力;二是在孕期检查和婴幼儿的成长检查方面能够更有针对性,由相对固定的人员负责,如芬兰从母亲怀孕三个月到孩子7岁前妇幼保健中心会安排一位固定的护士,免费负责检查,跟踪孩子健康状况,比如身体发育、认知发展、社交能力等。
(四)强化家庭教育指导,为家长提供教育支持
家庭教育是6岁前幼儿的主要教育途径之一,家庭教育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幼儿教育的质量。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者,父母的教育水平至关重要。如何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是各国育儿支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可以从多种途径来进行,具体包括:
1.政府层面。从政策方面来规范家庭教育指导,建立家庭教育的指导体系能更为有效的保证家庭教育指导的质量水平。如法国在1999年3月建立了 “倾听、援助、陪伴父母网络”,给予政府和社团对父母家庭教育进行干预、援助的空间,在建立与家庭联系、促进父母承担教育责任、提高能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6]。
2.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合作方面。学校教育是专门性的教育机构,拥有更为丰富的、专业的教育资源。我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在建设初期就担负着教育孩子和服务、指导家庭教育的双重任务,在2016年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再次强调了幼儿园应给予家庭教育以科学的指导。
3.社会公共团体及组织。社会公共团体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是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主体,还包括家长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因其背景相近,内容针对性强,效果更有保障。如英国的家庭教育信托机构是研究家庭破裂的原因和后果的国家教育信托基金。它没有政治或宗教关系,完全由自愿捐款提供资金。它既不要求也不接受政府的资金。它们的任务只要包括出版关于家庭有关问题的书籍等材料,生产用于学校的教育材料和在线资源,为政府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对父母、老师和孩子的教育提供各项支持。
4.自媒体等网络媒介。网络方面可以借助于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和网站等多方位的为家长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信息。如美国在教育部网站上进行政策、项目的宣传介绍,设立了“父母”栏目,向父母提供教育资讯,包括:入学前准备、寻找学校和放学后照看、帮助孩子阅读、学业成功、孩子的特殊需求、孩子的大学等板块。
(五)优化社区育儿环境,构建周边育儿支持网络
幼儿期的孩子活动范围较少,基本以社区为中心,建设良好的社区环境,完善社区育儿支持网络也是构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育儿环境的优化主要集中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层面。
物质环境的优化主要集中于幼儿活动场所、幼儿医疗场所、幼儿教育机构、幼儿托管中心等的配套建设。社区规划中应包含宽敞的幼儿活动空间,建筑和道路规划应充分考虑婴幼儿的需求,建设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幼儿医疗服务和幼儿教育服务机构,并对医疗、教育服务机构的建设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真正为家庭育儿提供有效地帮助;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大型经营场所的婴幼儿设施要建设完善,如公共汽车、火车上可以建设专门的母婴坐区,提供放置婴儿车的区域设置;商场提供哺乳室、母婴洗手间、尿布台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为婴幼儿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社区文化环境建设是较为薄弱的方面。在建设社区文化环境方面,一是要重视环境建设的教育因素,可以创设一些低幼图书类的阅读区域,也可以在社区环境的布置中增加教育性成分,对幼儿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鼓励家长参与,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可以定期的组织家长教育交流活动,借鉴英国的学前游戏班等形式,也可以组织家庭间的交流共享教育资源,图书漂流等。
构建面向6岁前幼儿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家庭的教育需求和幼儿的年龄特征,从政策机制、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社区建设和公共基础建设等多方面来进行共同的努力,以满足家庭育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