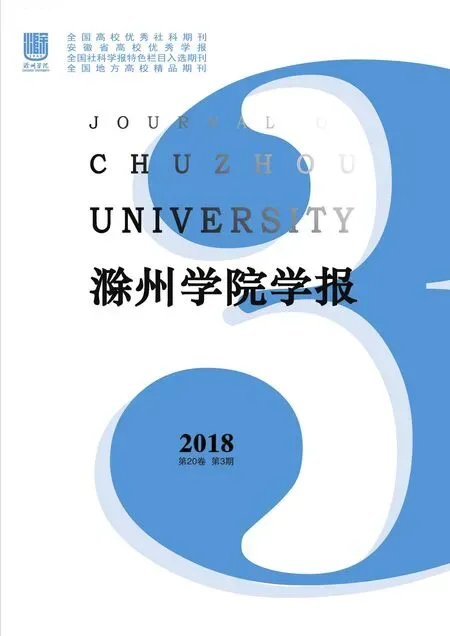与现实建立幽默的关系
——论余华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2018-03-29张敏,李静
张 敏,李 静
在文学随笔《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利特〉》中,余华谈到了“幽默与现实”。余华说,虽然布尔加科夫是现实的敌人,但他却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做出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语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的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1]387事实上,余华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他在创作中用幽默缓解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至少达成了与现实表层的和谐。余华选择幽默同样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余华的幽默导源于他对现实的深刻怀疑,他在用幽默彻底颠覆现实(也可以理解为余华所说的“日常经验”),以逼近不为经验所拘囿的内心真实。余华认识到:与现实剑拔弩张只会使声音失去力量,变成一堆漫骂、一堆哭叫。幽默令余华的作品获得了看似轻松实则坚毅的力量。
自1986年以来,余华逐渐构建起一个充斥血腥、暴力和死亡的阴冷诡异的小说世界。虽然90年代之后的创作有所转变,流露出越来越多的世俗温情,但余华从没放弃他所擅长的暴力和死亡的描写,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都不乏苦难、死亡和血腥场景的描写。余华对惨烈瘮人的血腥场景的“欣赏态度”和“工笔重彩”的描绘是典型的黑色幽默笔法,这些内容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常常是触目惊心和忍俊不禁,当然,这种笑决不是释怀大笑,而是恐惧、绝望的笑。其实,从黑色幽默的角度解读余华的作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阅读策略,这倒不是说余华的小说是黑色幽默小说,而是笔者认为,黑色幽默的意识和创作手法一直潜在地贯穿于余华的创作之中。
一、精神上的高级反叛
(一)对荒诞现实的反叛
黑色幽默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面对死亡的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小说流派,其后现代性首先体现在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彻底绝望和否定。黑色幽默作品中的社会是一个虚幻、混乱和充满欺诈的庞大体系,“千人一面”的人物都辗转挣扎于“千人一命”的圈套和陷阱中。现实的灾难、不幸在黑色幽默作品中只是一个中介符号,只是表明人类处境的荒诞性和宿命性。[2]余华对“现实”的理解与黑色幽默派是相通的。他一再强调:生活是荒谬、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文明、秩序、经验和常识尤其不可靠!灾难、死亡在余华的小说中俯拾即是,死亡构成了余华小说世界最真实的部分。每个人随时会遭到死亡的袭击,怎样地挣扎和逃避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只能以轻松、幽默的态度去对待它,这便形成了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的基调。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是建立在对现实荒诞本质的清醒认识之上。
从成名之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就彻底粉碎了人们对世界的美好憧憬。这篇具有寓言性质的作品昭示了余华此后的创作将执着于对生存暗夜的揭示。短篇小说《死亡叙述》试图通过司机两次撞死人的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遭遇,引发人们对既定秩序和固有道德的思考。那个肇事的司机第一次撞死人后逃之夭夭,没有受到惩罚,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第二次撞死了人他没有再逃,怀着赎罪的心理极力挽救将死的一条生命,但这一次他却被受害者的家人毫不含糊地用各种农具打死,这就是荒谬的、毫无理性的现实人生。从作品对死亡的描述来看,主人公似乎是以一种解脱之后的轻松来面对这次意料之中的死亡。中篇小说《偶然事件》讲述了这样的“偶然事件”:素不相识的陈河与江飘在“峡谷”咖啡馆偶然地目睹了一起凶杀案,之后陈河偶然间发现江飘与自己的妻子有染,便以通信的方式与江飘讨论那起凶杀案,密谋实施报复。相信读者能够猜到江飘被陈河杀死是小说必然的结局,果然,同样的情景又一次在咖啡馆上演。有意思的是,江飘一直是以游戏的语调与陈河津津有味地讨论着别人的死亡,而实际上他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自己将要到来的死亡。作品名为“偶然事件”,但人物最终走向死亡却是“必然事件”,一切皆属偶然,只有死亡才是必然,也许这就是对荒诞宿命人生的注解。
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具有更加深沉的“黑色幽默”色彩。《活着》中的福贵是一次又一次死亡的见证者。看着亲人一个又一个地离去,福贵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没有绝望的号啕,只是默默地、麻木地忍受,他甚至还能苦中作乐:让那头老牛充当逝去的一个个亲人。“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3]6这是作者对《活着》的评价,也是《活着》的核心寓体。《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别无所长,只能靠出卖身上的血来化解生活中接踵而至的苦难。每次卖完血,一盘炒猪肝、二两温的黄酒便足以使许三观乐在其中。当我们无法逃避生活苦难的时候,不妨保持平静,在苦中做乐。余华对苦难和死亡戏谑性的描写除了给人无奈中短暂的解脱之外,更重要的是逼使人在恐惧、压抑中思索人类的困境和命运。
余华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抽去了时代背景和确定的环境设置,刻意追求文本情境的虚拟化。余华淡化小说的时空背景是出于这样的意图:强调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性。灾难是永久和普遍存在的,它如影随形,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一笑了之,以轻松自然的态度面对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
(二)对荒谬历史的反叛
历史可以看作是“过去的现实”,是一种被权力所叙写的现实,历史含有虚构的成分。余华对历史的揭示采取的是黑色幽默的方式,即:在看似不经意的嬉笑中剥落历史荒诞的本质。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这段历史留给国人的是百感交集的复杂体验。对于作家来说,生于其中既是不幸又是最大的幸运。余华在谈起《兄弟》时表达了这样的感触:他们那一代中国人经历了两个特殊的时代,前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文革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现在这个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中国人四十年就经历了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4]有这样弥足珍贵的经历,余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这充分说明余华是一个有自觉历史意识的作家,虽然他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被抽去了确切的时空因素,但他的长篇小说的背景却是具体、写实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都是把人物放入社会历史的具体苦难境遇中考察其生存状态。
以《活着》为例,人物的命运被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所裹胁: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直至“文化大革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都在福贵家庭中留下了悲剧性的烙印。洪治纲先生认为:“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在叙事中却显得非常平淡,似乎只是人物无意中碰上的一种灾难,或者说,只是命运自身的一种潜在安排,至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悲壮冲突并不明显。这也说明,余华的叙事目标不是强化历史的悲剧性,而只是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5]不错,这段文字的观点是契合《活着》的主要创作意图,但与此同时,当我们洗耳恭听作者对“活着”一词解释的时候,是否忽略了这么一句话:“〈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3]6这句话在体现了一种悲悯情怀的同时是否潜藏着作家对“这几十年历史”的某种态度?这句表述也适用于《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只不过在揭示历史本相的时候,余华放弃了严肃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立场,而改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剥去历史神圣的外衣,将历史的严肃性消解在它的非严肃性之中。明明是残酷的战争,但在余华笔下却演变成这样可悲又滑稽的场面:福贵、春生因为气力不如人抢不到空投的大饼,只能趁别人忙着抢东西时扒人的鞋子煮饭吃;明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在许三观看来这是“报私仇的好机会”,平时恨谁就糊他的大字报,别人就会把他往死里整;明明是为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的全民大炼钢、开办大食堂,结果却是全民大饥荒,读者恐怕怎么也不会忘记《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让家人一起打嘴巴牙祭的那个精彩片断,我们在抹着眼泪的笑的时候体味到阵阵的酸楚。《兄弟》中作者对宋凡平入棺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由于那口又短又薄的棺材根本放不进宋凡平高大的身躯,妻子李兰无奈之下只能任由别人砸断丈夫的膝盖、把小腿弯过来装进棺材。相比较于生前受到的虐待、殴打,宋凡平死后经受的这番折腾又算得了什么?这何尝不是对“文革”那段疯狂荒谬历史的一次令人震撼的揭示?余华在评论布尔加科夫时说:“他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1]196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其实说的也是余华自己。
二、可悲可笑的小人物
余华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悲可笑的“反英雄”式的小人物形象,其精神气质近似于黑色幽默作品中的歪斜抽象的人物形象,世界的荒诞、历史的悖谬、人生的乖误在人物形象的歪斜、欠缺中得到充分地凸现。
让我们分析一下余华小说中的这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河边的错误》中的马哲、《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以及《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
《河边的错误》通过描写警察侦破发生在河边一连串凶杀案的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常识的谬误以及对人的残害,并进而揭示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世界的荒谬本质。最富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是小说的结局:一直清醒冷静的刑警队长马哲为了终结惨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抉择——击毙疯子,自己装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主人公被作者冠以“马哲”这个象征性的名字,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常识怪圈的荒谬错乱的世界之中。在办理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马哲可能是唯一没有陷入常识怪圈中的“局外人”,但偏偏在案件真相大白的时候,马哲发现自己面对法律常识无能为力,只能以荒诞的方式对待现实的荒谬。精神病院里的那一幕着实让主人公和读者哭笑不得,一个原本智慧理性的探案英雄的形象被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或许这个名字就是意味着理性在现实世界中是无处藏身的。
阮海阔的形象与马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虽然客观上陷入江湖的恩怨仇杀之中,但主观态度上却始终游离于矛盾旋涡之外,也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这种主观态度与客观境遇的断裂把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本应具有的英雄主义完完全全消解了。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羸弱少年身背一把传世宝剑,其实不会半点武功;他游走江湖口口声声说要寻找杀父仇人实在迫于无奈,因为他已无家可归;母亲对仇人夸张的仇恨与阮海阔的心不在焉形成了巨大反差。他对于人生的感受正如他对前方道路的判断:“十字路口并不比单纯往前的大道更显出几分犹豫。”他行走在江湖,“如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树叶,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1]39人物行动的茫然对应的是他内心世界的茫然。而到了最后,当阮海阔知道杀父仇人已被别人杀死,自己无仇可报时,他却突然感到内心一片混乱,同时怅然若失,因为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从最初被迫踏入江湖到此时流连江湖,阮海阔的主观意愿总是与其处境背道而弛,阮海阔化解这一矛盾的妙招则是茫然——浑然——怅然。借助于主人公略带滑稽的人生经历和感受,作品表现了生命的虚无感和现实总是背离精神的命运观。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普通送茧工许三观卖血为生的故事。与福贵麻木地忍受苦难不同,许三观面对人生磨难总能以夸饰的小市民趣味将之化解,因而这个人物也就更多了几分黑色幽默的色彩。卖血本是一件残酷的事,用许玉兰的话说,“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6]但这一事实与普通老百姓艰难的生活相比,其残酷性竟被淡化了许多,至少许三观是通过卖血实现了人生的预想目标,卖血还能证明“身子骨结实”,能名正言顺地去饭店犒劳自己一顿。如果说黑色幽默是人类超越窘境的一种无奈的态度的话,那么,许三观便是深谙此道,他始终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对抗着病痛、饥饿和贫穷的煎熬。而就在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无需卖血的时候,许三观又再一次走进医院卖血,原因是他嘴馋想吃盘炒猪肝。这一次医院里年轻的血头不但不要他的血,还嘲笑他的血是猪血只配作油漆,许三观支撑生活和希望的唯一招数被彻底否定了,“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许三观绝望无助地嚎啕大哭起来。十二次重复的卖血经历在许三观的意识中已经被镂印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遇到灾祸只能靠卖血来逢凶化吉,卖了血之后才能吃猪肝、喝酒,要吃猪肝、喝酒就必须卖血,甚至大热天的许三观还按照以往的惯例要把酒“温一温”。深重的苦难迫使人们选择不正常的行为,也造就了人不正常的生存意识和心理。
传统小说中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演变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中自身难保的“反英雄”式的小人物,其背后对应的是人的主体价值的丧失。曾几何时,人被看成是由高贵的理性所构建的主体,是历史甚至是宇宙的主宰,但现代工业文明、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摧毁了人关于自身乌托邦式的想象。当人被取消了主体地位,成为了一个无动机、无目的的存在,当个人这个“角色”不再成为小说的中心话语时,人就必然退回到被忽视、被伤害的角落里,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就不能不是卑琐、可笑的了。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7]123
三、“零度”与“重复”的写作策略
余华的小说诉诸于人类形而上的灾难命运,揭示人生苦难,其美学风格本应该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但余华藉助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将悲剧转化成了喜剧。余华采用的写作策略:一是以冷漠的叙述方式描写许多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极力表现出一种见怪不惊的寻常心态;二是运用“重复”的手段对悲剧进行稀释。
余华在其作品中常常用“零度情感”的叙述语言描述死亡和悲伤惨痛的遭遇。《死亡叙述》对死亡过程和死亡感觉的描绘可谓触目惊心:“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的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的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我仰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往四周爬去。我的鲜血很像一颗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我死了。”[1]196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小说中恐怕很难找到如此富于想象力的死亡叙述。而最能体现余华冷漠叙述特点的莫过于《现实一种》,作品对暴力和死亡的描写更加令人目瞪口呆。这是发生在亲兄弟之间的连环仇杀:先是哥哥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然后是山峰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又用残忍的手段虐杀了弟弟山峰,山岗被判死刑,山峰的妻子把山岗的尸体献给了医院供解剖之用,于是,作品便在肉体解剖过程的细节描述中结束。余华描写起血肉横飞的场面偏偏如此地“唯美”和“幽默”:“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1]197外科医生在肢解尸体时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动手术时他得小心翼翼避开它们,给活人动手术他感到压抑。现在他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他对身旁的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这话使身旁的医生感到妙不可言。”[1]21-22黑色幽默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约瑟夫·海勒)和《五号屠场》(库尔特·冯尼古特)对于战争的描写,还记得《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个恐怖而传神的经典比喻吗?从楼窗跳下匍伏在地的尸体“象只装满草莓冰淇淋的毛呢口袋”。在《五号屠场》中,库尔特·冯尼古特将一群被押送的俘虏比喻为“液体”,将僵硬的尸体比喻为“石头”,“‘液体’开始流动,大量‘液体’积在门口,然后‘扑通’一下流在地上。毕利是倒数第二个到达车厢门口的,流浪汉是最后一个。流浪汉不能流,不能‘扑通’落地,他已不是流质而是石头了。”[9]这两位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家都是用轻松滑稽的笔调揭示了战争这种反人类行为的荒谬和残酷。同样,余华的这种喜剧性的叙述也是针对现实的荒谬,针对那些虚假的道德、伦理、文明和秩序。
众多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余华对“重复”叙事手法的偏好,这几乎成了余华小说的一个显著标志。重复是余华结构小说的主要手段,也是构成细节的方法之一。拿本文前面提及的几部作品来说,都具有“重复”的特点。《偶然事件》描写了两起发生在咖啡馆里的相似的凶杀案,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物沿着命定的路线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河边的错误》也是运用事件的重复来表现主题:疯子在河边制造了一连串手法一样的杀人案;刑警队长击毙了疯子后被逼成了疯子,一个疯子死了,另一个正常人又成了疯子。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重复仍是主要的叙事手段。《活着》是以主人公身边的亲人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作为主要叙事内容的。重复地叙写死亡,不但没有导致悲剧的累积,反而消解了死亡的悲剧意义。随着亲人一个一个的逝去,不但福贵渐渐地麻木了,我们读者恐惧悲痛的感知也在逐渐地丧失,从而不由自主地认同了小说结尾对死亡的寓意:死亡,就像“女人召唤着她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死亡无所谓悲,无所谓喜,只是平凡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罢了。《许三观卖血记》以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经历为主要事件进行重复叙述。而许三观每次的卖血过程也都大同小异:先是拼命喝水,然后找血头卖血,卖完血到胜利饭店吃上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并且“酒要温一温”。为了冲淡卖血事件的悲剧色彩,作者还在许三观的卖血历程中注入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因素,比如: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是出于好奇,第三次卖血是为了报答林芬芳与他偷情,最后一次是因为路过胜利饭店,“炒猪肝的气息拉住了他的脚”。许三观卖血并非次次为生活所迫,而是被人的本能欲望(好奇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食的欲望)所驱谴。这样,余华就将一幅融合了苦难与欢乐、平庸与琐碎的世俗人生图景展示出来了。另外,该部小说还在一些细节上运用了重复,最典型的片段就是:饥荒年里,许三观用嘴给三个儿子炒菜吃,他给一乐做的是红烧肉,给二乐做的还是红烧肉,给三乐做的仍然是红烧肉。这样运用重复手法的细节描写在该作品中不止一处,大大增强了作品诙谐、幽默的情趣。
重复的叙事手法体现了余华小说形式探索的成就。通过不断地重复叙事,余华模糊了传统文学悲剧、喜剧泾渭分明的界限,展现了悲喜剧交织的最为本真的人生状态。“重复”令余华再一次地接近了“真实”。
余华的创作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小说的评价,它将我们“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喜剧的恐怖之处”。[7]123余华的创作还让我想起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弗里德曼的一段话:“黑色幽默可能早已存在于我周围,只要现实中还有伪装需要剥掉,只要还存在没有人肯关心去思考的问题,它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永远在我们周围流荡。”[10]余华最初以先锋作家的姿态登上文坛,他的创作一直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一派的“黑色幽默”在余华的创作中时有闪现。黑色幽默的意识使余华实现了精神上的高级反叛,更透彻地揭示现实和历史的荒诞本质;黑色幽默的技巧使余华的小说在展现小人物的悲喜剧时获得了看似轻松实则坚毅的力量!
BuildingaHumorousRelationshipwithReality——OntheBlackHumorinYuHua'sNovels
Zhang Min,Li Jing
Abstract: Yu Hua's avant-garde novels were born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an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st-modernism, "black humor" often flashes in Yu Hua's creation. Yu Hua mocked society and life with desperate humor, forcing people to face up to the cruel reality and absurd history; He also used "anti-hero" type of small figure image to highlight the world's absurdity, historical paradox and life's perversion;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techniques of "zero" and "repetition", Yu Hua turned the tragedy into comedy, making his works seem easy , but actually achieve the strength of perseverance.
Keywords:black humor;Yu Hua's novels;absurdity;anti-hero;zero; re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