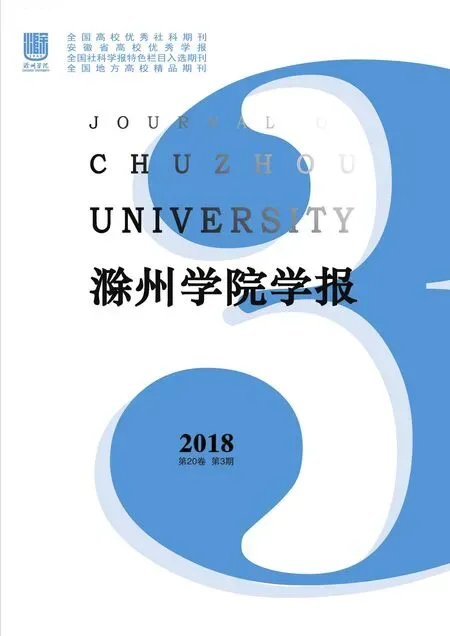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滁州荒政探究
——基于《叩阍书》《请免津粮疏》视角
2018-03-29李应青
李应青
荒政是中国古代政府因应灾荒而采取的救灾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废除行省,在全国设13个承宣布政使,下设府、州、县。皖境设有49个县,分属南京所属7府(含7个散州)、4直隶州。所属7府(含7个散州)分别是:凤阳府及泗州、寿州、宿州、颖州、亳州,庐州府及六安州、无为州,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4直隶州分别是: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1]263-267。
滁州升为直隶州,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直隶六部;永乐元年(1403),属南京,治今滁州市区,领全椒、来安2县。和州升为直隶州,是在洪武二年(1369),治今和县县城;洪武十三年(1380),领含山1县[1]267。明代在经历了前期的全盛时期之后,中后期的统治日趋腐朽,社会矛盾激化,各地灾荒频仍,滁州也不例外。《滁州志》记载:
嘉靖元年秋七月,大风发屋。二年秋,大旱,民流离饿死无算。三年春,大疠,死者相枕藉。七年冬,白气亘天如练。八年,蝗自西北来,蔽天日,丘陵坟衍如沸,所至禾黎、崇祯辄尽,男妇奔号蔽野。十四年,州西诸山夜鸣如雷。十五年,大旱。冬十二月初五日,夜大雷电。三十八年夏,大水,圩尽破。万历十四年夏,大水。十八年春,大饥,米价涌贵,请发大赈。四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大雨连昼夜,洪水暴涨,溺死男妇近千。四十五年,蝗旱交作,流殣载道。四十六年秋,斗米银三分。天启7七年,大旱。崇祯八年,闯贼来犯滁州。九年正月,卢象升来援,大败贼于珠龙桥,河水为赤。十三年大旱。十四年,疫疠盛行。[2]41
滁州频繁发生的各类灾荒,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苦乱。
一、明代中后期滁州灾荒频仍的主要原因
滁州从地域上介于长江与淮河之间,滁州的灾荒最常见的是水灾、旱灾、蝗灾和疫疠,其中尤以水旱灾害的交互发生为最。
(一)自然原因
1.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泛滥。长江流域年降水量为800毫米,淮河流域年降水量为770毫米,相差不大。但明代中后期这两大河流河道的排水能力减弱,泥沙淤积。长江径流系数达63%,上游水土流失,在下游河床上形成很多沙洲群,排水不畅,径流受阻即易致泛滥;而淮河上游陡峭,下游平坦,中游无湖泊,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高达750倍,一旦上游突然涨水时,下游便不能充分地排水,也易致泛滥。“如果遇上暴雨促使黄河泛滥,大量黄河水流入淮河,更易导致大洪水暴发。尤其是从6月至7月中旬梅雨气团的形成,必然带来暴雨性的降水”[3]。滁州梅雨期长约20多天,“每年梅雨气团向北移动时遇到北方冷高压的阻碍,就将形成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暴雨性集中降水”[4];反之,梅雨气团移动时如果无冷高压阻碍继续向北移动,又会造成严重干旱。正所谓“五年水灾,三年旱灾”。
2.滁河河道的迂折阻塞。滁州在隋朝因滁河(涂水)贯通境内始得名。滁河从南京六合汇入长江,是长江下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滁水由庐州经全椒入州境,下游至六合瓜步口入江,迂折三百里。一遇淫霖,宣泄不及,往往横决为患。距浦口二十里,有孟子嘴阻塞”[5]157,虽然明代“操江丁亲勘滁河,水利当兴,题准疏凿,委州判尹梦璧督工挑挖。自张家保至孟子嘴,已开十分之八”[5]157,可惜“为六合所阻,中止”[5]157。
3.滁田半在山,厥土亢。滁州属于当代“江淮分水岭”区域,该区域的特点:易旱缺水、降水不均、土壤贫瘠、地形破碎、西北山水盈涸不常。百姓殷勤始能有渠有陂,“惟因地之高下,潴以为塘,为沛,引以为沟,堵以为坝,为堰”[5]157,否则,“率仰给天雨。设天少旱,即依倚墙树高坐,又不善节缩敛藏,故一旱即破产失业不可支,可哀也可疾也”[5]158。
(二)社会原因
明朝到了中后期统治阶级激烈的利益争夺,官府加重徭役增派,湖田植被的滥垦,流民匪盗四起。崇祯八年(1635),乙亥,正月,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东进攻克凤阳,挖掘皇陵,兵抵滁州。崇祯九年(1636),丙子,年初,农民军主力高迎祥等部纵横于豫、皖、川、陕各省,滁州蒙难,兵燹弥野,旱蝗频年,疫疠交频。人祸加重了天灾的严重程度,严重影响着滁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1.徭役赋税繁重。国家赋役挽输,酌定山川道里,准之民情物力,以期久远可循。然明代中后期的田赋徭役盐课,地瘠民贫的滁州除了要与大州一样依旧例按丁口缴纳摊派外,反多有桥梁等杂税添加,甚至将死亡绝丁的摊派任务加到现丁身上。《滁州志》记载:
先是,滁兼全椒、来安,地计三十有一里,其后析置二县,州[才]十二里,户又减耗,而诸岁杂派,犹仍旧贯,计里科算,常与他大州等。[6]245
桥梁原为利涉。六合接壤全椒,中通一河,距有浮桥一道。不知起自何年,创立桥税,岁益苛加。岂但商旅,即扁舟担物,必取盈焉。江口旧有巡检,亦以缉盗,私设佹封,稽验税票,彼此攫利。[7]101
崇祯丙子(1636),流寇之乱,城郭仅存,丁口杀伤者以数千计。顾其时,上台督征方严,有司不敢报减,至摊绝丁于现丁户下。较之万历年间每丁征银三钱一分之数者,后几至五钱二分有奇。[8]
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以供应新设立的环山营需要,增加江南赋税,其中征收滁州三千石米。常年的赋税已经很难缴纳,何况加赋?不仅加赋,加征三千石米的环山营赋税,因为滁州本山城,陆路梗阻,水路干涸,却要求从海上运输。滁州人心惶惶,纷纷商议离家外逃。
2.起运大州,漕运津粮。滁州自古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称,于中都(今凤阳)、南都(今南京)之间,官员公务往返两京,皇族返葬中都凤阳,滁州都是南北必经之道,官府车马过往频繁,滁州成为起运大州,马价忽增,又为民累。《滁州志》记载:
马数多至百匹。滁下湿,故不宜马,率使之买诸北地。……诸屯所养马田地,岁久率多干没,滁民病之。……时民谣传:“有马有驴,大都取给”。丁田马丁岁赋银九分,驴加于马[不啻]倍。[6]245
盖部议专为本色,马价太昂,倍金以购耳。若折色,自当循旧。而一概增之,三饷并征,尚经如伤轸,视此又在饷银外矣。民脂几何,能当层剥?骏骨虽高,料不重于民命。垂毙余生,胡以堪此?恐年来新额削民者,更不止马价一事也。”[7]101
不仅如此,在加征三千石米的环山营赋税嗣后,天津巡抚又以江北粮饷不能如额,令滁、和二州动支新饷。区区滁、和二州所属凋残,寇荒已极,米豆万难促征,总领小小3县却又遭摊派天津米菽一万四千七百石漕运之征。《滁州志》记载:
臣乡滁、和,向无米豆召买,派自十四年之津运。夫他处以灾荒而减所本有,滁、和独以灾荒而增所本无,疲累实甚。[7]101
议者谓以滁、和补江北之乏,裒多益寡,缓急可需,不知滁、和俱在江北,同受数载灾伤,尚多两番残破,惟正[赋]之追呼尚难应手,额外之敲扑孰不惊心?且他处漕舰各以定制征兑运解,尚竭一年之力始得如期,今以滁、和山城,去天津三千余里,素无运道,又无运船、运军,仓卒檄征,即催前诣,自非神输鬼运,何以咄嗟而办?[9]101-102
原本是山城的滁州、和州,相距天津三千余里,没有运船、运军,山溪小船,怎能过黄淮大川。丧乱余生,何能堪此?
3.湖田植被的滥垦,水土流失。一方面,由于长江、淮河、滁河的沿岸湖泊泥沙淤积,为解决粮食问题,农民围绕淤滩造田开垦湖田或圩田日渐增多,“往昔蓄水之湖荡以及滨江滩地与沙洲,多已圩垦成田”[10]。更有甚者,农民为保护自己的湖田而私自筑堤,致使水流受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混乱,农民对水土保持,漠不关心,乱伐林木,对灾后的恢复计划,也没有集体观念。“每遇大水时,乡民们不知集中力量共同护卫官堤(大坝),只顾私利,分集各小圩,自行保守,迨官堤一决,江水如潮,向内直灌,而各自单薄之圩堤亦无一幸免。”[11]这种把私利摆在第一位的一时性补救办法破坏了江河湖泊的自然生态,最终使其丧失调节排蓄能力,进一步造成水患。
4.土地兼并,盗寇并起。天时不齐,早涝时作,饥馑接踵,流离死亡,实无纪极。一方面,灾民外出逃荒,尤其是大量青壮年的逃荒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耕地荒废,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另一方面,灾民为维持生计,不是卖子鬻妻,便是卖地或借债抵押土地,“土地借贷为最通行之借贷方法……如到期借款未能清偿,即作卖绝……使土地集中于高利贷者之手。”[12]故水灾一过,必随之出现土地大量集中的现象,农村灾后社会经济的残破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失地农民离乡成为流民,有的甚至当了匪盗,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开门揖盗,匪盗们的暴行,破坏了社会秩序,带来恶性影响。
5.蝗疫交濒,战乱四起,水利损毁。旱灾常常引起蝗灾,灾荒之际,粮食缺乏,灾民只好以树皮、粗粉、水藻、草根、树叶、观音土等充饥,草木俱尽,甚至人相食。这些代食品经过灾害期的污染,灾民健康受到很大威胁,疾病蔓延。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疫……死人弃孩,盈河塞路”[13]。灾荒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冲击是很大的,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激发了民众的觉醒,各地民变不断爆发。社会动荡,百姓生灵涂炭,水利损毁严重。《滁州志》记载:
“尔来寇势披猖,流民勾应,皆缘岁事不登,旱蝗频年,兵燹弥野,疫疠交濒……献贼肆逞,庐郡又复沦失。破巢、破含、破霍,攻同堕卵;陷六、陷舒、陷庐,摧如破竹。金斗巨镇,跨楚豫,吭江淮,去陪京不数舍地,俨然贼瞰而取之,狡志不少。……献贼陷庐之后,哨拨四出,滁、全紧与庐邻,旦夕莫保。三月以来无雨,人忧播种之艰。咫尺之地皆贼,”[7]100
“崇[祯]八年,忽罹寇变,和州城社丘墟,滁州村落灰烬,士民杀戮存者十不二三,风鹤时闻,靡有宁处。”[9]101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百姓全膏已竭,瘠骨何堪吮肌?明朝末年政府对人为因素的控制和预防重视不力,导致江淮地区更严重灾荒。保定巡抚徐标在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觐见时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14]。
二、明代中后期滁州救荒安民之策
由于灾荒频仍对封建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故自先秦以来历朝均重视救荒安民,采取多方面赈救措施,对于抵御自然灾害、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有积极意义。史载:
“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物资),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放宽力役),五曰舍禁(取消山泽的禁令),六曰去几(停收关市之税),七曰眚礼(省去吉礼的礼数),八曰杀哀(省去凶礼的礼数),九曰蕃乐(收藏乐器,停止演奏),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向鬼神祈祷),十有二曰除盗贼。”[15]
历代帝王、封建士大夫是古代社会荒政活动的主持者和倡行人,地方官吏对荒政建设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乡绅等其它群体和普通民众在救荒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中后期,滁州尤以知州陈则清、王邦瑞、郑庆、林元伦、叶露新、丁士奇、陈允升、戴瑞卿和南太仆寺卿李觉斯、冯元飚、李一鹏,以及郡绅金光辰、郡掾盛大朝、民众孙孜的救荒安民之策最有成效。
陈则清,嘉靖二年(1523)知滁州,三为州守,俱有惠政;王邦瑞,嘉靖五年(1526)知滁州,施行善政;郑庆,嘉靖九年(1530)知州事,治蝗得力。林元伦,嘉靖十五年(1536)知滁州,廉明恺悌;叶露新,嘉靖四十四年(1564)知滁州,端方严毅;丁士奇,万历十六年(1588)知滁州,仁爱百姓;陈允升,万历二十七年(1599)知滁州,端重寡言;戴瑞卿,万历三十八年(1610)知滁州,体恤百姓;李觉斯,崇祯八年(1635)任南太仆寺卿,守御有备;冯元飚,崇祯十三年(1640)任南太仆寺卿,同情百姓;李一鹏,崇祯十四年(1641)任南太仆寺卿,士民德之。郡掾盛大朝上《叩阍书》;郡绅金光辰,字居垣,左佥都御史,滁州全椒人,上特疏《请免津粮疏》,惠及乡里[16];民众孙孜,义行救荒。他们的救荒安民之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散利赈济
陈则清知滁时,“岁大旱,发仓赈贷。……逾年,厉大作,民病不能兴,量地设厂,为糜食之,活者甚众”[17]245丁士奇知滁时,“岁饥,捐俸倡赈。城镇分设粥厂,饥民赖以活者甚众。”[18]246嘉靖三年春,滁大疫,死者相枕籍。民众孙孜“率众置义冢,出粟授贫人,使收骼瘗瘗之”[19]。
(二)蠲免薄赋
明太祖深知“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的道理[20],休养生息,蠲免田赋,国力强盛。明代中后期统治腐朽,财政状况恶化,江南田赋加重,百姓生活艰难。
陈则清知滁时,“请免输凤阳仓麦二千石,每石折银四钱,民免输运倍收之费。”[17]245王邦瑞知滁时,“是时,民罹大饥,继以疫厉,生计甚艰。催积逋符檄如雨……滁民病之。邦瑞具列上,一曰蠲逋欠,二曰均科派,三曰平马政,四曰减重征”[6]245。请求朝廷作增减调整,并提出解决办法,朝廷准奏,核准施行,民参军者,也不再缴纳费钱。郡中百姓称其公平。
丁士奇知滁时,“时监司取锾金逾额,积欠帑数百金,自鬻家枣园代偿之”[18]246。
陈允升知滁时,滁田瘠粮重,尝有弃产去者,“允升履田清丈,计额均赋,人丁以三钱为则。百姓赖之,立祠以祀”[21]247。
戴瑞卿知滁时,“查乡保街坊征收的丁粮,使贪占隐匿者暴露出来,取其查获出的费用充公,供驿递之急需。每马岁加十余金。……体恤百姓,田赋钱粮,丰年不增”[22]97。
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以供应新设立的环山营需要,增加江南赋税,其中收滁州三千石米。由于陆路梗阻,内河干涸,要求海运。是时,百姓苦乱,田地多荒芜,正额尚优无法完成,海运更添费用。郡诸生相约到南太仆寺卿衙哭诉,南太仆寺卿冯元飙心生恻隐,给漕抚朱大典写了封文书,“滁本山城,舟楫商贾之所不至。今又苦寇、苦荒、苦疫,残黎几何,难概责以海运”[23]251-252。海运之役得免。第二年,李一鹏任南太仆寺卿,“公赍表北上,特为滁题免海运米三千石”[24]252。入朝觐见得到户部答复:“奉旨:滁阳今岁暂解本色,以后照旧。免其召买,不许再行混派,钦此。”李一鹏为滁请免了供应环山营的三千石米赋税,士民德之。
在加征环山营赋税不久,朝廷又令滁、和二州召买米菽一万四千七百石,漕运入津。郡掾盛大朝挺身上《叩阍书》,《滁州志》记载:
“方今市价,每米一石,准银三两三钱,菽亦称是。伏承据派米价连运每石九钱,菽价六钱,此九钱六钱之数,即以之充水程运费未足抵半,何况市平物价不足供三分之一乎?似此征赔行于荆棘瓦砾之场,则鹄面鸠形之众不至尽填沟壑不已,将来正赋何以征输……官吏加征诸色虽在厘毫,犹切详慎。而此次召买抑配浮于正供者四万余金,比旧日条编,不啻倍蓰。伏乞饬下户部,熟议善策。或酌减斗斛,或就其所便,听以二麦抵额。又山溪小船,不能过黄淮大川,令其漕至淮安,听漕运衙门附入海运。召买部价从公准销,此后仍还旧赋,输银解京有司,不得拘为故事。民生幸甚!国计幸甚!”[9]102
盛大朝言辞凿凿,陈请召买和漕运的难度,请求酌减斗斛,或以二麦抵额。最终加派津粮蒙恩得以麦抵,但只于全椒免派。
崇祯十四年(1641),郡绅金光辰再向朝廷上特疏《请免津粮疏》,《滁州志》记载:
“揭为滁、和寇荒已极,米豆万难促征,谨冒味沥请,仰乞圣鉴,敕部酌议减免,并罢私税厘马价,以宣皇仁,以保民生事。……且椒邑免派既荷俞纶,而部疏仅米减千石,豆减千石,则数百石之零数何归?欲洒派滁、来,是非徒不减,又益之也,不几失邀免之德意乎?况和、含屡经蹂残,含山新遭失事,粒米如珠,差使如虎。狡贼佯言赈济,岂催收反为盗赍,鉴兹生命阽危,实非他处可比,敕部免其本色,不失原额,仍旧输银,或另行酌议。此非第为一方之民而保障,可固以锁钥陪京,非细也。谨疏。……伏望敕部一并察议,宜罢者罢,宜厘者厘,还旧赋以苏残喘,则众志成城,潢池永靖矣。”[7]100-101
最终,加派滁、和的津粮,以郡绅金光辰请免。士民感之,入乡贤祠。滁州连续三年免除了额外的负担。
(三)治蝗浚流
大旱之后,虫灾肆掠。嘉靖八年(1529),滁州蝗自西北来,蔽天日,丘陵坟衍如沸,所至禾黎辄尽,男妇奔号蔽野。知州郑庆“从州衙选挑勤敏精干的官吏数十人,分部到各处,捕打蝗虫。百姓摇旗敲锣,举火开堑,又严加禁防,使其不得侵扰,蝗虫衰灭。第二年春天,蝗虫又蕃衍成灾,郑庆按照上年的方法殴捕,并下令按捕捉蝗虫的多少,官府给等量的谷子作为奖励。因此,人人争相捕捉,蝗虫被捕灭,秋收有成”[25]。万历四十五年(1617),滁州蝗旱交作,城东出现蝗灾,知州戴瑞卿亲率衙卒亟赴驱蝗[22]97。
面对灾害,人们在救灾的过程中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浚流排涝,蓄水防旱。嘉靖四十四年(1564),知州叶露新“创修上下水关,建珠龙桥,经费出入,悉有成算,民不知劳,精明综核,至今人尚称之”[26]。万历三十八年(1610),戴瑞卿知滁,“广树艺,浚清流”[22]97。崇祯九年(1636)南太仆寺卿李觉斯,“疏双凤桥之水灌溉北濠”[27]。
(四)除盗贼索鬼神
明代中后期灾害频仍,人民无资生产业可为,化为盗贼。匪盗们的暴行,破坏了社会秩序,带来恶性影响。历任地方官都重视社会治安的治理,防治社会秩序混乱。陈则清“民有窃人资者,一切治之以严;其以病自戕诬人者不问,郡用安戢。”[17]245。王邦瑞“奖善嫉恶,击断无畏,供张稀间,民当甲者无费钱[6]245。丁士奇“城四隅建敌楼,以备了望,盗贼莫敢伺”[18]246。
在大灾大害面前,尽管地方官尽职尽力地救荒安民,但由于社会的衰败和科学的荏弱无力,大多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为焉,犹竭其而不得已”[28]于是各阶层寄希望于顺天应人的弥灾思想向鬼神祈祷,祭神祈雨和驱蝗。嘉靖十五年(1536),时滁州大旱,知州林元伦组织州民抗旱无力,无奈之下,“徒步祷于柏子潭,有百龟浮水上,甘澍辄应”[29]。万历四十五年(1617),滁州蝗旱交作,知州戴瑞卿亲率衙卒亟赴驱蝗,并作《驱蝗报祭文》,“愿神其默垂荫佑,俾我民永无后灾!”[30]。
虽然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荒政中顺乎天命,但这种社会心态在民众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其原因是导致了民众的逃避心理,这种逃避心理又导致了民众缺乏直接向灾荒挑战的勇气,这是中国社会灾荒心态的一种典型表现。最终只能造成灾荒的加重和频发”[31]。当然,明代中后期不论是虫害治理,还是赈灾的相关记载,都是我们研究滁州抗灾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几点启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荒政建设,他在继承传统荒政思想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荒政思想和实践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各方面得以发展。“在备荒上,他知道有备无患的道理。为了提高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多次下诏要求有司积极发展水利事业;诏谕各地有司因地制宜地兴修水利,蓄水防旱;修复因战争损坏的水利工程,加固江河的堤岸,防止大水冲决,淹没粮田。同时令各地设置预备仓,并多次对灾民进行蠲免和救济。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在有明一朝极为罕见”[32]。
明代中后期,滁州屡遭战祸,田地贫瘠易旱涝而征粮的赋税又重,民穷财尽,一些农民对灾荒无防备能力,弃田而去,田野荒芜,境内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地方官同情百姓疾苦,致力于灾前备荒、临灾救灾、灾后重建,滁州人口逐渐增多,社会总体安定,生产迅速恢复。明代中后期滁州的荒政治理总结起来,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综合治理有几点启示:
(一)兴修水利,保护生态
江淮分水岭地区地形破碎,若循旧例全由官府进行,势难长久维持。因时制宜兴修水利,主张官民分理,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凡民力可办之工,不妨交地方官督劝田主,令其自为修理。惟民力不能为者,方许动帑,官为修理。”[33];培修长江、淮河、滁河堤防;添建江淮分水岭区域涵洞工程;疏浚江淮分水岭水利浅段工程;重视生态的恢复与保护;加大水利方面的投资,实行持续性水利建设。不能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发展生产,与民温饱
民生问题最基本的是与民温饱。面对水患、灾荒,古今地方政府同情民众苦难,关心百姓温饱,致力于发展生产,发展特色生产。不能盲目地围湖造田,破坏江河湖泊的自然生态,影响江河湖泊的调节排蓄能力。不能滥伐森林植被,生态环境变迁影响气候的异常。由于江淮分水岭的易旱缺水、降水不均、土壤贫瘠、地形破碎、西北山水盈涸不常等的特殊地形造成了存不住水和缺水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要害。如何“把水留住、把树种上、把路修通、把结构调优,促进农民增收”[34],除了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解决“水”的问题之外,还要改造农业生产本身,选择耐旱品种、实施节水灌溉等手段来适应当地少水、缺水的环境,致力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特色生产。
(三)及时救灾,重建家园
灾情发生时,一方面,组织得力的骨干队伍,迅速、及时地救灾,保护灾民的生命财产,降低损失。另一方面,重视灾后重建,建设美好家园,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余论
中国古代完备的荒政制度在救荒安民的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救灾效果,但在“荒政”思维的指导下,政府被动地解决水患、灾荒等民生问题。“因为缺乏科学性,有的时候越救越荒,‘治理’最后也会变成‘无理’:为了对付水灾,大兴水利工程,结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大量的林木被砍伐用于工程,使得原本就不算广袤的丘陵地带森林更加稀少,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为了发展农业,提高产出,进行大规模垦荒,结果过度的土地利用与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等问题,破坏了自然环境,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35]。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江淮分水岭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发挥政府的主体和社会力量,农田水利有所建设、生态环境有所改观、灾害发生频率有所下降、因灾而荒的程度有所减轻,但随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而来的人水争地、水土流失、水体污染问题越发突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由于整治的目的性较为被动,所以措施上也较有局限性。
荒政乃“一国兴亡之所系”,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引发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日趋重视。既然自然灾害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灾、救灾,尽量减轻因灾害带给人类的危害。真实了解明代中后期滁州的荒政,真实了解政府、社会如何对受灾地区进行蠲免、赈济,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AStudyontheFaminePolicyofChuzhouintheMiddleandLateMingDynasty——Basedon"TheBookofKnocking" "AnAppealingLetterforExemptingfromTaxingGrain"
Li Yingqing
Abstract: The famine policy is a reliving policy adopt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famine perio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reign became more and more corrupti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were intensified, and famine struck quite often. Chuzhou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Huaihe River, and the most common disasters are floods, droughts, locust plagues and epidemic plagues.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floods and droughts ranked as the wor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auses of the severe disaster in Chuzhou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ollects the local officials, the county gentry, and civilians to resist the natural disasters, stabilize the people's lives, restore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stabilize the ruling order, and draw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of the watershed of Changjiang River and Huaihe River.
Keywords: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huzhou; famine relief; "the Book of Knocking"; "An Appealing Letter for Exempting from Taxing G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