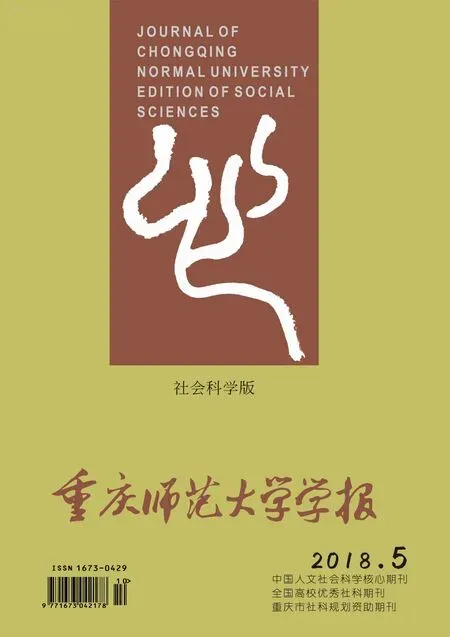《论衡》个人性语法现象探析
2018-03-29葛佳才
葛 佳 才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论衡》是东汉时期的代表性语料。刘盼遂序《论衡集解》云:“王氏自有其字典也。世谓西方大学人均有个人字典,予谓我国周、秦、两汉诸子亦莫不然。试取一编阅之,即可知。”其中“王氏自有其字典”,即指《论衡》中有不少王充自创独用的个人言语。不言而喻,绝大多数文献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个人特色,从而形成个人言语。在我们看来,作为汉语史研究基础的文献语料,所反映的都不是一个共时的、静态的、同质的语言系统,其中不乏带有仿古、新兴、地域、语体、外来、个人等色彩的“异质”成分,对这些成分加以剥离、分析,是进行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的前提。
迄今为止,对汉语史语料中个人性语言现象加以剥离、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何志华专文考证了仅见于《论衡》而属于王充自铸的新词,溯其源流,揭示王充创制新词的原因和具体方法。[1]126-140在东汉语法的调查、比较中,我们也注意到《论衡》的一些富有个人特色的语法现象,也拟就其中的虚词、句法略作讨论。
从严格意义上说,个人性必须体现为显著的封闭性或限定性。如果一种语言现象新兴于某一时期的个人作品中,既没有由点到面的共时扩散——不见于同期其他文献,也没有由点到线的历时流播——也不见于后期文献,我们才能确定其个人性。也就是说,要对个人性语言现象加以鉴定、剥离,共时、历时比较缺一不可。不过,一来个人性言语现象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中有可能上升为通用性语言现象,从而使个人性与新兴性在特定时期同时呈现,二来相对于共时扩散,要证明历时流播的未发生或不存在,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因此,我们主张侧重于以断代文献来确定语言现象的个人性,毕竟一种语言现象产生之初如果没有共时扩散,使用范围限于专人专书,一般也不会发生历时流播。有鉴于此,对于《论衡》个人语法现象的离析,我们侧重于东汉碑刻(《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繁体版,第一、二册),毛远明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孟子章句》(《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汉书》(班固撰,中华书局1962年)、《论衡》(《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黄晖撰,中华书局1990年)、东汉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伤寒论》(《伤寒论校注》,刘渡舟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太平经》(《〈太平经〉正读》,俞理明著,巴蜀书社2001年)、东汉译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东汉八种文献的统计、比较,至于历时比较方面,则是基于共时比较结果的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尽可能参考。
一
通过对东汉八种文献中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的统计比较,我们剥离出一些极具个人特色的虚词现象,如:实/若设令假设连词,如果、当/行/遭/遇/偶/遭适/偶适/偶适然/偶自/适当/适自语气副词,恰好、阶/阶据/据见方式介词,凭借,依据、就方式介词,凭借,依据/对象介词,针对。举例分析如次:
【实】
(1)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艺增》)
东汉文献中,假设连词比较发达。单就《论衡》而言,单音节的有“必、诚、当(傥)而、苟、或、今、即、令、乃、其、如、若、使、实、设、向、则”等,双音节的有“假令、如或、如令、设或、向令”等。汉语中,在句首表示确定语气的副词,一旦进入假设复句,就容易沾染、获得假设用法,“必”“诚”即是其例。例(1)“实”表假设的用法也应该属于类似引申,只是《论衡》始见,而同期、后期文献未见,当是王充的个人创造。
【当、行、遭、遇、偶、遭适、偶适、偶适然、偶自、适当、适自】
(2)王莽姑正君许嫁二夫,二夫死,当适赵而王薨。(《偶会》)
(3)天非为囚未当死,使圣王出德令也,圣王适下赦,拘囚适当免死。(《偶会》)
(4)卜谓女相贵,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实不然。次公当贵,行与女会,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门。偶适然自相遭遇,时也。(《偶会》)
(5)天道偶会,虎适食人,长吏遭恶,故谓为变,应上天矣。(《遭虎》)
(6)二令参偶,遭适逢会,人事始作,天气已有,故曰道也。(《寒温》
(7)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幸偶》)
(8)或时杞国且圮,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变动》)
(9)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时,偶适相遇,非气感也。(《偶会》)
(10)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风寒发盲,围解之后,盲偶自愈。(《福虚》)
(11)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变动》)
《论衡》中恰幸副词十分丰富,其中“幸”“邂逅”表示恰幸语气比较特殊,只是东汉诗、《太平经》也偶见其例,故不作为王充个人性言语现象加以讨论。在此之外,《论衡》除了沿自先秦的“属”“方”“会”“正”“适”以外,更多使用新词新义:一是新兴的单音词如“当”“行”“遭”“遇”“偶”,一是新旧单音词复合或附加成词,如“遭适”“偶适”“偶适然”“偶自”“适当”“适自”。例(2)(4)“当”“行”并不多见,时永乐、王景明在“当”下设“正要,恰巧”义项,正引例(2)[2]77;例(5)“遭”较为活跃,多与“偶”“适”等对文、连文使用;例(7)“遇”十分罕见,例(8)“偶”相对常见,且多以并列、附加方式复合使用。
复合或附加成词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值得一提的是单音节新词新义的产生。例(2)“当”、例(3)“行”,通过引申或假借获得“将,即”义,并由此进一步虚化表示恰幸语气。“不少语言中,时间上的将然与进行是相通的,如汉语的‘当’‘方’‘会’既表将然也表进行,若此,‘行’既然可以表示事情就要发生或行为当即实施,在语义上也就可能表示进行,而它一旦用以表示进行,语义上作用于一个时间点,转而在语气上也就可以表示‘恰恰,正好’了。”[3]85相对将然副词而言,含有“会合”义素的动词更是恰幸副词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先秦常见的“属”“方”“会”“正”“适”,还是《论衡》中特有的恰幸副词如“遭”“遇”“偶”等,尽管“会合”义素或隐或显、或具体或抽象,却都是经过对这一共同义素的提取、凸显才逐渐得以形成的。[4]36“遭”“遇”表“遭遇,遇到”,“会合”义不言而喻,至于“偶”,与“遇”音近义通,有了“遭遇,遇到”的动词义,再产生“恰巧,正好”义也就水到渠成了。
《论衡》集中出现了不少限于专人专书的恰幸副词,与文本内容、作者思想息息相关。“适偶论在王充哲学体系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论衡》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王充在语言表达与运用上,自然离不开特定的恰幸副词。他不仅积极地继承了先秦已有的旧词,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大量新词新义,使恰幸副词在《论衡》这一十分有限的空间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既不朝共时平面扩散,也不向历时平面流播的‘只此一书’、‘空前绝后’的局面。”[4]37、38
【阶、阶据、据见、就】
(12)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治期》)
(13)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书解》)
(14)女娲,人也。人虽长,无及天者。夫其补天之时,何登缘阶据而得治之?(《谈天》)
(15)问曰:“孔子妻公冶长者,何据见哉?”据年三十可妻邪?见其行贤可妻也?如据其年三十,不宜称在缧绁;如见其行贤,亦不宜称在缧绁。(《问孔》)
(16)何则?禄命、骨法,与才异也。由此言之,颜渊生未必为辅,其死未必有丧,孔子云“天丧予”,何据见哉?(《问孔》)
(17)夫言问天,则天为气,不能为兆;问地,则地耳远,不闻人言。信谓天地告报人者,何据见哉?(《卜筮》)
(18)其立姓则以本所生,置名则以信、义、像、假、类,字则展名取同义,不用口张翕、声外内。调宫商之义为五音术,何据见而用?(《诘术》)
(19)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论,又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是据见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审才能也。(《逢遇》)
(20)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虚实,非造始更为,无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对作》)
《论衡》中介引凭借、依据的介词丰富而独具特色,例(12)~(20)“阶”“阶据”“据见”“就”即其例。“阶”本指“台阶”,由体到用引申获得“依靠,凭借”义,有“因”“阶”连用例:“起于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论衡·恢国》)虚化为介词表示依据或凭借,相对而言十分罕见;例(14)“阶”“据”连文,在同期文献中更是绝无仅有。例(15)~(18)“据”“见”连用同样也只见于《论衡》。胡敕瑞引例(15)(17),指出“据见”为“根据”义,《汉语大词典》未收。[5]25从所引文例来看,“据见”与前置的疑问代词宾语“何”生成“何据见”,出现在“某一事实/观念+何据见”的表义框架中。“据”有“依仗,凭倚”义,由此虚化为依凭介词顺理成章且并不少见,那么,“何据见”是否可以分析为介词结构“何据”修饰谓语动词“见”而理解为“根据什么看见”呢?我们认为,由于前面的事实(“孔子妻公治长”、“孔子云‘天丧予’”)、观念(“天地告报人”、“调宫商之义为五音术”)是已然确定而不言自明的,“见”的“看见,看到”义无法落实;同时,“何”的疑问焦点也不是相关事实、观念,而是相关事实、观念发生或形成的依据,这样,例中“见”显然不宜处理为视觉动词。人们认知世界、获取信息主要通过视觉方式,“看见,看到”是作出判断、发表看法的基本依据,“见”作为一个典型的视觉动词,有可能产生依凭的介词用法。例(15)中“据”“见”连文、对文使用,不难看出二者在语义、功能上的相似性。例(19)(20)“就”用为介词,前者表示凭借,后者引进动作的对象或范围。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于,例(19)“就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中,“就”、“因”对文,介词宾语“遇”、动词宾语“之”不同指,“就遇”是“誉之”的依据或凭借;例(20)“就”使用三次,以“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为例,介词宾语“先师之说”、动词宾语“之”同指,“就”相当于“针对”,其宾语也就是谓语动词涉及的对象。“就”本动词“趋向,靠近”,抽象为“就着”义,由此虚化就可以介引凭借或依据、对象或范围了。
《论衡》一书,旨在“疾虚妄”,而要有力地批驳虚妄之说,自然少不了大量的理论事实,这样,凭借、依据类介词就有了用武之地。王充在继承“以”“用”“因”“缘”“案”“依”“随”之余,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借(藉)”“据”“阶”“就”以及“凭依”“阶据”“据见”等单双音词,其中“借”“据”“凭依”等为后世承用,而“阶”“就”“阶据”“据见”限于《论衡》一书,不妨视为王充的个性化言语现象。
二
句式方面, 我们统计、比较了判断句、被动句、疑问句、宾前句和处置句,也注意到了“谓+主+是也”、“为见V”、“……邪,而将……也/……邪,亡将……也”等为《论衡》独有的特殊句式。以下举例分析。
【谓+主+是也】
(21)贤之纯者,黄、老是也。(《自然》)
先秦无系词判断句中,有一种“谓+主+是也”的格式,其中“是”是代词谓语,复指上文所举事实,并认定主语即属于这种情况,相当于“如此,这样”。如:“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下》)例中“江淮河汉”是主语,“是”复指“水由地中行”。《论衡》中也有用例,如:“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逢遇》)这类判断句的谓语往往是一个谓词性短语或句子,描述某一类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而主语一般就是实施相应动作行为或具备相应性质状态的代表性的人或物。由于事物与行为、性状在范畴上的区别,主谓之间构不成逻辑上的等同或类属关系。
例(21)与无系词句“谓+主+是也”形同而实异。“贤之纯者”所称代的不是某一类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而是某一类人,“黄、老”与之构成类属关系,符合判断句表示类属的基本功能。这一句式可能来自于对先秦“谓+主+是也”的重析分析。由于谓语构成由谓词性结构、句子向名词性结构的转变,尤其主谓之间类属关系的建立,“谓+主+是也”由无系词句演变成了“是”字句,其中“是”也由指代词发展成了判断词。这是“是”字的一次质变,也是判断句的一种新发展。不过,可能是由于与先秦无系词句“谓+主+是也”形式相混,加之主语、谓语语序与一般“是”字句的不同,这类“是”字句的分布范围、使用频率相当有限,基本上可以视为王充的一种个人创造。
【为见V】
(22)起功之家,当为岁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咎乎?……今巳、酉之家,无过于岁月,子、寅起宅,空为见食,此则月岁冤无罪也。(《譋时》)
“为”字式尤其“为……所……”式是汉代的主流被动句式,东汉时期产生了各种衍生形式。《论衡》中偶或一见的“为N1所V1,N2所V2”式、“为见V”式即其例,其中“为见V”式为王充首创独用。
唐钰明指出,“之”“所”“见”性质相同,功能相当,三者的换用、复用生成了一系列“为”字被动式。[6]271、272“为N见V”式即是“为N所V”式中“所”替换为“见”所得。不过,该式先秦少见,东汉文献中也只在《孟子章句》出现1次,即:“伊尹为汤见贡于桀,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此者五。”(《孟子·告子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注)“为N见V”式的少见,直接决定了施动者“N”的省略式“为见V”的罕见。它们在东汉口语中可能并无运用,在译经、《太平经》等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宗教文献中了无踪迹,《论衡》一见,不妨算作个人用语。
【……邪,而将……也/……邪,亡将……也】
(23)所谓“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十邪?而将一有十名也?(《诘术》)
(24)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将匈奴敬畏精神在木也?(《乱龙》)
(25)然其为东郡都尉,岁恶盗贼不息,人民骚动,不能禁止。不知寿王不得治东郡之术邪?亡将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之治偶逢其时也?(《定贤》)
东汉文献中,选择问的构成要素丰富齐全,灵活的使用造就了多样的选择问句式。不过,从总体上说,各种格式频率偏低,大都一或两见,同时基本上限于《论衡》、译经等文献,从而呈现出文献分布集中、使用格式分散的基本特点。
秦汉时期,连词“而”可以连接词、词组、分句和句子,表示修饰限定以及并列、顺承、转折、递进、假设等各种关系,而“将”也兼有语气副词、选择连词的用法。例(23)“而将”,或是连词“而”与副词“将”的随机组合,东汉文献中仅此一见。
值得一提的是,“将”是一个揣测之词,也常用于选择问后一分句表示选择关系;同时,“亡(妄)”也可在选择问后一分句表示选择。“将”“亡”偶尔连用表示揣测语气,字作“将妄”:“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庄子·庚桑楚》)从理论上讲,“将”“亡(无)”连用表示选择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东汉文献中,“将无”多用来表示委婉语气,相当于“恐怕,该不是”,只见于译经,未见选择连词用法;同样地,“亡将”未见揣度副词用法,表示选择关系也只见于《论衡》,即例(24)(25)。可见,“亡将”“而将”在《论衡》中首次出现,与语气词“邪”“也”配合表示选择,上古未见,中古亦然,空前绝后,特色鲜明,应该是出自王充的“个人字典”。
三
以上我们离析了《论衡》中一些为王充所有的个人性的虚词、句法现象。如前所言,这些语法现象之所以具有个人性,是因为它们的使用限于《论衡》一书,既没有向同期文献扩散,也没有向后期文献流播。那么,对于这种“只此一家”的语言现象,鉴别、厘定的价值或意义何在?对汉语史研究又有什么影响呢?
在我们看来,个人性语言现象限于专人或专书,使用范围相当有限,出现频率往往也偏低,但相关的统计、比较和定性分析,不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读文本,也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推进汉语史研究。
首先,离析个人性语言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解读文本,促进古籍整理。以“遭”为例。据初步统计,“遭”表恰幸语气在《论衡》中凡25见,尽管在《论衡·奇怪》“遭吞薏苡、燕卵”的校释中,黄晖已明确指出“‘遭’犹偶适也,本书常语”,只是使用范围限于专人专书,加之黄晖也只提过一次,该意见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普遍接受,因此,“遭”的这一特殊用法也就少为人知。比如,《论衡·偶会》:“坏屋所压,崩崖所坠,非屋精崖气杀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适履。”蒋礼鸿认为:“‘遭居适履’义不可通,当作‘遭坠适厭’,‘居’为‘坠’之残脱,‘履’亦‘厭’之形讹。‘厭’义本为压,‘遭坠适厭’者,谓适遭崖之所坠,屋之所压耳。”[7]255根据“遭”的恰幸用法可以确定,“遭居适履”中“遭”“适”对文,都是“恰恰,刚好”的意思,整句意为“(命凶之人)恰恰住到坏屋里,刚好踩在崩崖上”。
其次,离析个人性语言现象,可以进一步证成具体的汉语事实发展演变的一些特点规律、动因机制等。个人性的言语现象,看似个性的创造和使用,却终究会打上语言共性的烙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共性。比如,通过分析秦汉时期使用范围广、出现频率高的“属”“方”“会”“正”“适”等,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恰幸副词虚化的语义基础——“会合,契合”义,尽管它们相对隐蔽。《论衡》中“遭”“遇”“偶”“邂逅”“际会”等,一来增加了聚合演变的典型成员,二来“会合”义相对显豁,无疑会进一步坐实“会合,契合→恰恰,刚好”这一演变模式。同样地,语境吸收是词义演变的原因之一,“必”“诚”等由强调副词到假设连词的演变,离不开所在的假设复句,而《论衡》中“实”的假设连词用法,自然也为“肯定断言→条件假设”的演化及其动因分析提供了支持。
其三,离析个人性语言现象,可以使我们对汉语发展演变的总体特点、规律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个人性的言语现象,是侧重就汉语史中某一特定时期而说的。一些在横向断面中表现出“个人性”的现象,一旦放到上溯下探的通史背景下,就可能由个人性切换为仿古性或新生性,而这一切换,有利于从宏观上蠡测汉语发展演变的一些特点、规律。比如,“恶”问事、“焉”“安所”问处所、“奚”“奚如”“恶”问方式情状,东汉时期仅见于《论衡》,似乎带有个人性。然而,从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演变来看,上述疑问代词在东汉已趋于消亡[8]323,它们仅见于《论衡》,既说明该书用语有古雅的一面,也说明一种语言现象在总体消亡后,也有可能残存于某人笔下。与此不同,“为N1所V1,N2所V2”是为适应同一受事主语承受不同施事的不同动作行为的表达需要而产生的,它在东汉仅见于《论衡》,个人性明显,不过由于后世有所沿用,也就只能视为当时的一种新兴被动句式。这又说明《论衡》行文的口语性,以及一种语言现象在产生之初,有可能就是某人的创造性使用。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既能认识到文献语料在用语行文上的复杂性,更能认识到语言的消亡、兴起,并非整齐划一的从有到无或从无到有,而是呈现出由面到点地消亡、由点到面地兴起的特点。这其中或亡或兴的“点”,就可能是个性化的现象。
最后,离析个人性语言现象,有利于分清汉语发展演变过程中性质、地位不同的语言现象,区别对待,从而把握汉语史研究的主体。比如,“阶”“阶据”在《论衡》中介引依据、凭借,用例可靠,理据可信,同时也与依凭类介词虚化、使用的总体情况一致,不过由于其使用囿于专书,对汉语依凭类介词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微,在依凭类介词的历史研究中也就无足轻重,“点”到即可。又如,仅见于《论衡》的“谓+主+是也”式“是”字判断句,尽管对于探讨“谓+主+是也”式判断句在先秦、两汉的继承和发展、尤其谓语所指由动作、性状到名物与“是”由代词到系词之间的关系不无益处,但着眼于判断句发展的整个历史,它的存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此类似,“为见V”式被动句反映了东汉时期“所”“见”替换、施动者“N”省略的语言事实,不过对于被动句演变过程、特点和因素等的研判,它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
四
语料是汉语研究的基础,汉语史研究需要真实可靠、纯粹典型的语料,这就离不开语料的整理和分析。就相对真实可靠的语料而言,纯粹典型的语料少之又少。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语料所反映的都不是一个共时的、静态的、同质的语言系统,其中不乏带有仿古、新兴、地域、语体、外来、个人等色彩的“异质”成分。对这些成分加以剥离、分析,是进行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的前提。语料分析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研究却远远跟不上要求。以上六种性质的语言现象,一方面揭示了语料的驳杂性,一方面也显露了语料剥离的艰巨性。目前汉语史领域对“六性”甄别、分析的情况,大致如下:仿古性、新生性素有传统,外来性成一时风尚,地域性、语体性渐受关注,个人性少人问津。
以上我们不揣鄙陋,通过对东汉八种文献中虚词、句法的统计、对比,立足《论衡》探讨了王充的个性化语法现象。从中不难看出,在语料的“六性”之中,个人性尽管并不显著,却也是普遍存在的异质成分。对个人性语料的鉴别、剥离,同样是汉语史研究不可替代的内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个人性的界定,往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的作品,与地域性、外来性、语体性等比较容易区分,而与仿古性、新生性容易混淆。如前所说,界定的标准、方法,当以共时比较为主,以历时比较为辅,二者必须兼顾,才可能离析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性成分,并由此客观、科学地评价它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