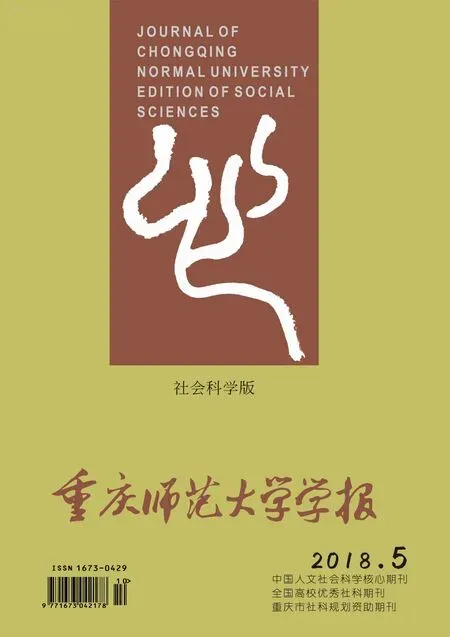家国命运的象征映射
——论抗战文学中的“女难民”书写
2018-03-29程亚丽
程 亚 丽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抗战文学中,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战火绵延中由飞机大炮倾泻炸弹造成的大量的废墟,古老中国物质文明遭受的巨大破坏,而是战争涂炭下平民的痛苦与不幸,普通百姓在战火蔓延中的无辜死难和由此受到的战争荼毒,所以对战时难民的描写与表现无疑构成抗战文学控诉战争最有力的题材。“发明民族主义的是印刷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语言本身。”[1]152考察抗战文学各种文体可以发现,在大量的对民族苦难的纪实性书写中对于女性战争苦难与境遇的真实表现又格外集中和繁密,从作者所表达的民族国家话语来分析,这些战时女难民形象其实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内涵与符号意义,这也由此构成抗战文学民族命运共同体战争动员别具意味的一种“形式”。
一、“女难民”:“战难”素描的聚焦对象
从“九一八”以后,难民的相关报道与文学描写就不绝于缕,有正义感的文学报刊,多十分关注“国难”带来的平民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命运,而其中的“女难民”俨然是作者有力控诉战争、呼唤和平的一个醒目符号,成为由战争而失去家园的普通民众——战争受难者的群体代表。
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学中就有表现战争女难民的书写,如舒群的短篇小说《难民》[2]138-152,最早将东北女难民的遭际呈现于国内读者视界。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九一八”以后,“我”从海上坐船逃到内地,于途中结识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难民的故事。因为没钱买票,混到船上的这一对母女,却被船上“护勇”查出来,“司帐”强令她们必须在离她们要去的目的地行程还有一半的中途提前下船,这让母亲感觉陷入绝境,因为举目无亲的她们下船就等于饿死。虽然有“我”的热心募捐照顾和仗义的承诺保护,但做母亲的还是因穷愁末路,撇下十八岁弱小可怜的孤女,在船上上吊自尽了。东北失陷,黑土地上的妇女遭了殃,不仅身体被摧残,逃亡路上亦尽是辛酸。
还有谢冰莹《两个逃亡的女性》[5]1-10写的自己从日本回到祖国,从汉口到上海坐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描写了难民在辗转迁徙旅程中的惨相:“狼狈的躺在船边的人,他们简直全是些难民,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烂的,男孩子们完全裸体,女孩子也只挂了一块破布,遮住某一部分,他们都低着头在打鼾,月亮照着他们枯瘦惨白的脸,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为生活受压迫的奴隶们。”沈紫曼女士的小说《逃难》[4]221-230则通过李婆婆一家的故事,表现了一幅“一二·八”淞沪战争中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景。李婆婆一家住在闸北交战区附近,因为舍不得丢掉家中辛苦积累下的财产,“结果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流弹飞来,儿子惨死;炸弹爆发,民房起火,有病的媳妇和辛苦积下的器具同归于尽。剩下相依为命的祖孙两个,从炮火中被救济会救出来,并且随着一大批难民被遣送回籍。”小说在描写战火给平民带来的灭顶灾难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存在的由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矛盾,火车上那一对无视难民境遇,丧失家国意识,只贪图个人享受的男女青年,让李婆婆万分感慨:“有钱的人,命是值钱的,人穷命也跟着贱了。”这种种对难民女性的书写显然旨在引起国民对同胞命运的同情,从而激发起热血男儿为保卫家乡、保护亲人奋身抗敌的血性。
有民族良知的作家无疑都会积极感应时代的苦痛,不断关注着逃亡到城市的难民生活状态,向社会各界发出救助、组织、教育难民的呼吁,逐步唤起国民的抗战救亡意识,这似乎已经成为1930年代主流报刊和新闻、文艺的一种公共义务与责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难民”题材更是大量涌现。骆宾基报告文学《大上海的一日》是一篇对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期间上海都市社会街景“一天”的历史铭写,在各种空间物理意象之间,最突出的是对于逃亡到上海的难民这个底层群体生存现状符号化的表现。有睡卧在露天的难民:“对面被挂着国际难民所红十字旗,隔在竹篱外的逃难乡民,早已打起寒噤,睁开怅惘的倦眼,环顾下面挤卧一堆的褴褛伙伴,习惯地又是一声短叹。呜——的一声,驶过一辆小型汽车,惊醒了另一些曲身蜷腿的难民,紧贴在主人身旁的丧家瘦狗仰了仰头。”也有正奔逃中的人头攒动拥来挤去的难民群:“从中山桥长长绕来的难民群,携老抱幼地拥挤着,行李卷靠着破铁锅,挑了两麻袋棉花的,弯着腰挤嚷,拉着破烂家具的黄包车夫吵骂。焦灼的火焰,燃沸每人的血流,然而还得默瞅着持棒巡捕的眼色,在左打右击中,从缠满铁丝网木桩口出出进进。”在大戏院门前,“蹲集坐聚的难民群,在纷纷互语着,形成一片杂音毕集的闹市。”更有典型的难民家庭:“老婆向啼哭孩子的大嘴里塞上软软乳头,蛮壮的丈夫,则扶持着躺在地下疾病丛生的爹爹,老妇在贪婪地吃大饼,小孩在玩弄桔子皮;相同的是:怅惆的眼光,千条万条交错成一片,七嘴八舌咒骂着命苦。愤恨解不了愤恨,手掌不止在搓。”这一幕幕难民的画面俨然是对抗战历史大都市社会局部的一种实录,准确地描画了战争中的难民群像,也使本文足以成为时代难民书写的经典,可谓有力声讨了日本侵略战争带给中国百姓的深重苦难。可贵的是,《大上海的一日》[6]178-180描绘的是一幕战争背景下的上海城市世相图,作家着意对难民群像加以细致的勾画点染,对贫富阶层分化的阶级现实进行精准的素描,对社会百态的实在面相加以清晰的勾勒,从而深入揭示出战争中上海一日所包涵的时代内容。正如鲁迅评价《八月的乡村》中援引爱伦堡的话所称:“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而在此散文中,无疑也展现了思想内涵对比鲜明的两幅画面:一边是旷日持久正在进行着的艰苦战争;一边是丑陋的社会现实生活,它们在文中组成丰富而密集的意象群,呈现出无比清楚的具有时代感的历史。有意味的是,作品也特意聚焦了都市妇女与难民妇女的生活,并将之加以形象对照:“竹筐里装满鱼肉的女仆走过,低首暗计塞到丈夫手里的那一角钱的报销”;“老婆向啼哭孩子的大嘴里塞上软软乳头”“老妇在贪婪地吃大饼”“一少女一老妇,战时加紧了交易。急拉着能借两顿米餐的顾客,朝人笑,朝人送着媚眼,老的也帮同拉衣,扯手”“白手绢塞着红唇的艳装少女,半靠倚了金边眼睛的男人”“金发妙女停下了,色彩鲜美的花摊的主人递给她一把鸡爪菊”,一边“抱着睡孩的失家妇人向她伸出乞求的脏手”。不同阶层女性意象与意象之间形成某种写意的对比,通过一种比较女性身体姿态的方式,揭示出社会生活的矛盾与复杂性。
丘东平描写“八一三”淞沪战争的“阵地特写”,《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难民W女士的一段经历》[7]264-269,是“我”对一路从大肆劫杀的日军陆战队枪口下“火线”中死里逃生的难民女性的见闻实录,“我”和表姊及其年老的姑母三人一起逃难,中间经历了各种艰难与不易,但重点揭露目睹的日军的侵略暴行。作家从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具体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无情:子弹横飞的战场,日军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对象的杀戮,无辜平民触手可及的死亡,随时被飞翔的子弹崩掉脑袋的各种真实战争画面。揭示战场的残酷情景:“我”奔逃中,“在猛烈的弹雨中已经失去了刚才走在我前头的两个女人的影子”,等“天亮了”“我发见自己的所在地是老靶子。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暗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描述女性视角下的战争体验,暴露日本士兵的暴虐和在“和平的市区”里杀害无辜中国平民的凶狠。作品还通过一位二十三岁的复旦女大学生郑文的遭遇,抨击了日本侵略带给知识女性的身体劫难。“年轻而貌美”的她,“对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很有研究”“有一种深沉、凛肃、聪慧的气质”;她生活幸福,“她有着甜蜜、宁静,不受波折的恋爱生活”,年轻的丈夫既英俊又有才干,性格“温厚和蔼”,从军官学校出来后做着成功的实业。但“我”眼见得“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陆战队员”,“手里的刺刀发出雪亮的闪光”,闯进平民区,“我清楚地听见”鬼子兵打破门,“带着狂暴的皮靴声冲进郑文的屋里去”,进而作者发出这样的设问:“郑文怎样呢?”女性遭受敌人性暴力的结果可想而知。这篇报告文学在描写逃难过程中的战斗场景、控诉战争暴力的同时,也讴歌了中国男子的血性与抵抗,在郑文遭遇到日军性暴力时,“我”发见:“中国人,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用了不可持劫的义勇,用了坚强的意志和日本疯狗决斗的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场景一:郑文的丈夫以一抵三,与日本人的拚死搏斗,“他们紧紧地扭绞在一起,那南方人的勇猛的战斗行为毫无遗憾地叫他们的劲敌尽管在他的身上发挥强大的威力”,最后“三个日本陆战队一同举起了他的残败的身体,从窗口摔下去”。男人的血性爆发出于保护妻子的本能行为中,虽然妻子无法幸免于难,但丈夫却在与敌搏斗中虽死犹荣。还有场景二:正在“脱危”的一家人,四十几岁的母亲与其“壮健”的四个儿子,在前面两个儿子被“一个黄色的日本陆军”用刺刀杀害后,第三个儿子“施行逆袭”,打倒了对方,但“他遭了从背后发出枪弹的暗袭”;那年纪最小的男子,“中学生”“他是那样的沉着,坚决,他的神圣的战斗任务全靠他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他用敌人的刺刀“向着那倒下还在挣扎的敌人的半腰里猛力地直刺”,但在一小队鬼子兵包围下,“我目睹着中学生在最后一瞬的苦斗中送了命”。而一瞬间失去了四个儿子的悲惨的母亲,“紧抱着中学生的尸体疯狂地向着我这边直奔而来”“她的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来像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她“象一只被袭去的狼似的”跳楼自杀了。由这种受难女性面部特写所呈现的,是战争带给平民的灾难与人命的无辜牺牲,是亲人离散,生离死别,子丧母疯的悲痛结果,还有严重威胁女性身体安全的侵略者的暴力,都在有形与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罪恶。
二、逃难中的“母性”呈现
抗战全面爆发后,到处战事频仍,战火延烧之下,有倾巢之虞的平民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扶老携雏逃离家乡,举家避难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战争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难民问题,有关战争难民的文学叙述也更加多了起来,如一篇报道“淞沪战争”中难民情况的照片“注解”所称:行走在街上的一家人,因“庐舍荡然,家人星散,仅余老翁弱媳和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共同走上茫然的征程”;群坐在一起的难民,“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老人或孩子,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刻划出颠连无告的苦痛”;第三张照片则是守着米桶端着空盆的难民,指出“有限的粮食,怎能接济无限度增加的难民。根本的办法,必须筹一笔较大的款项,将他们遣送到能够生产的区域去”[831]。但在难民群中,最为醒目的一群却是拖儿带女的妇女,她们因母性身份在战争中逃难的经历说来更加凄惨。曹白在《受难的人们》中描写的那个“在死神的黑影下面”得了“虎列拉”,在“戏院子”难民所里奄奄一息的病妇:“我弯下身去,摸一摸她的额骨,冰冷。再捏一捏她的手心,也冰冷。她闭着她的凹陷的眼睛,呻吟着,吃力地掀动着鼻翼;但她一双手脚却护定了她自己的一个最小的孩子,还有两个大的孩子在偎着她。恐怕就是这三个孩子也晓得他们的妈妈的病是如何的沉重了,不然,三张小脸上何以会挂满了泪的呢!”[9]33还描写了那个为了忧心日本飞机炸了在工厂做工的女儿而要赶快去察看的老妇,但与她一起在难民所里存身的还有自己的三个孩子,“那破绽了的席子上,四脚洛巴的睡着”,她于是想要把他们先托付于人,心理矛盾中形容充满悲苦:“她的白发默默地压在她的头脑上,那是人世的辛苦的标记,而她的皱脸浸在泪水里面了。”这篇“通讯”以一个难民服务人员的身份,讲述了难民所中“女难民”的普遍境遇,摭取了“受难母亲”的形象,通过身体叙述与对其生存处境的描写,表达憎恨战争期望和平的愿望。这些作品都在着重以战争中受难母亲的形象来打动人心,显然挪用了“母亲”能够召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价值,这是抗战文学叙事取材的普遍方式。
在舒群另一篇写于1937年7月的小说《婴儿》[3]23-26中,仍是以其惯常的表现方式描写同一题材,于许多乘船逃亡内地的东北难民中,却聚焦一位临产的妇女。没有医生、产婆能帮她接生,最后由一对看不下去的知识分子兄妹和叙述人“我”,一起帮助这个临产的妇人。
那个年青的妇人听从他开散着上身的衣服,赤裸着下体。让我抱着她的腰部,并不拒绝。好像绑赴怯场的小羊,任人刀杀。这时候,在她已经没了女人所惯守藏的秘密,在我们也失去了性别的感觉,只有他的妹妹脸上浸透着一层处女的红晕,让自己的手遮掩着脸颊,不敢扬起她的眼睛。
小说描写了年青的妇人在这种海上逃难、船只遇险中经历的“生产的苦难”,通过她的肢体语言,揭示了女难民由非常环境“生育”带给她的苦难,“也许是被风吹了,也许是受惊了,也许,……使她感受了更甚的痛苦:滚转着,不住地打着自己,她的手,突然捏住了自己的乳头,撕着,好像她要撕成一块一块的碎肉。”而“一切的船员与乘客都在集中抢险,都在注意自己如何逃脱,并没被她诱动”,就在这种情势下,她诞下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产后发热让她第二天就死去了,“我们从婴儿的手腕上,发现了已经透入皮肉里的几个字迹:东北好男儿 马革裹尸还母绝笔”。“生育”尽管代表着民族的延续,但对于逃难中的妇女而言却享受不到人们的祝福,妇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婴儿的新生,这一难民母亲形象显然构成了受难民族的象征,她最后的举动——将她对孩子的寄望刻写在孩子手腕上,由此让民族国家话语得到了转喻式表达。
丽莎的写实通讯《难民妇女》[10]13中所描述的“江浙来的”妇女逃难的情形。根据其中一个妇女的口述,“那苦况真是无法形容,特别是妇女”“一天七八十里,和男性一样走,脚小又拖儿带女,一个两个的已经要命,有的还带着五六个,背背抱抱,翻山,越岭,孩子哭,大人也一步一滴泪。”特别是“遇着荒村野外,自己整天没吃,孩子仍然要喂,自己的血,给孩子口口吞,母亲的心一下一下发疼。”逃难途中,“饥、寒,疲惫,有的倒毙,有的失掉”。在逃难的情况下,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父母将女孩丢掉,“一路上很多讨饭女孩”,因为“‘女人家’就是被丢的理由,就是不幸的渊源”。不仅如此,还有时不时的“突袭”中,“母亲受惊过度,顺产变为逆产,昏死几次”,生存在死亡线上的慌恐。报道总结道,“深觉在敌人侵略中,受痛最深,受害最惨的,还是妇女”。舒群报告文学《我走向了战场》记述了“八一三”淞沪第二次战争失利后上海形势转紧,他与几个东北流亡作家从上海到南京辗转迁移的过程,描述了一路上有关在战火中逃离家乡难民的见闻。列车上“夜色深沉”中失散的母子,“包裹行李丢满路边,被遗下的孩子,哭着,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同时,母亲已经喑哑了喉咙,仍在寻找自己的孩子。”[11]221在南京,战事临近,日本轰炸造成平民巨大伤亡:“我亲去看了一次仍在母亲怀抱中的一个死后的幼儿……我只看见她那连成珠串的泪水,只听见她那哭不成声的哭声,仰着脸,默无一言,仿佛不得不默认她的幼儿是一个无辜的殉难者,自己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作家强调:“日本几年来,几次地侵略中国,进攻中国,不知造成了多少她那样‘不幸’的母亲;如果有一个正确的统计,更不知要拖长多少数字。——也许惊动了一切像钢铁所铸成的人心。因此,我疑心日本军阀必是禽兽所生,全无骨肉之情!”作家对战争灾难下的妇女形象进行白描、速写,显然将其作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的平民苦难,以受难母亲的象征来抓取的具有“反战”意义的一个“符号”。
艾芜散文《难民哀话》[12]375-381中,叙述了全面抗战后战火延烧下带着两个孩子辗转一路逃难到桂林的年轻母亲的悲惨故事。随着武汉失守,战事紧急,长沙大火中,一家人全部财产化为乌有,在日军的夜袭中,丈夫又丢了性命,大点的男孩则被炸坏了一只脚,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面对如此不幸与灾难,女人因为缠过足走路很不方便,还要携子一路逃难,这个母亲却没有狠起心肠丢弃自己受伤的孩子,也没有把小的孩子送给别人收养,一直勉力坚持从衡阳逃到桂林。作品中写她,“为了把他两弟兄,弄暖和一点,我连一条裤子,都没穿的。”“她这么说的时候,还一面把她的光足杆,从旗袍岔口边上,露了一截”。她自称坚定一个念头,“就是做叫化讨口,都要把他弟兄养大”。在作者看来,这个母亲对孩子“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正是我们民族抗战坚定的基础与力量所在。“她们母子,在这苦难的世界上,在这日人迫害的天空下面,无论如何是要生活下去的。而且,无疑地能够生活下去的。”还有刘白羽的战争“速写”《疯人》,则描写郑州难民遭受日军轰炸的惨状,揭露日军造就的战争罪恶与灾难,并聚焦一个因遭受日军轰炸跟随丈夫坐火车逃离战火延烧的家乡的妇女,心里嘴里不断念叨着散失的儿子,一路嚷着要“回家”,以为失去了儿子的可怜的母亲。这类母亲群像身上映射出人类母性的光辉,却在战争的残酷阴影下越发凸显了。
三、战争死难下的民族反抗与坚韧
观察作家对“女难民”这一受难人群的各种书写,一般是将难民妇女的苦难叙述按照一个“逃难——遭难——男性反抗”的逻辑模式来叙述、组织并推进、演化的,旨在表达民族主义战争动员的抗战意识。
骆宾基写于同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阿毛》[13]86-88则生动描述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时难民逃离上海的悲惨情景。一批批原来流落到上海的难民现在又纷纷坐小木船离开上海。其中有青年农民阿毛,四天前“想从南车站走”,结果“活生生的妻子”却被炸死了,这时只能由自己抱持着幼儿“这个累赘”准备乘船逃回江西老家去,船上人很多,大家“蹲、坐、跪、立”“都在顾忌着自身的安全,盼望早一些平稳到家”。一个挨坐在阿毛身边有“金牙齿的”女人正与麻脸汉子攀谈,盘算着一起回家探亲的行程,因为这女人笑声“极像自己老婆的笑”,让阿毛“眼里又充满了泪水,默瞅着臂间的小孩”。谁知船刚一开出,就遭遇了日军军机轰炸,难民们纷纷跳水,“身子,胳膊,大腿,拢作了一团,在水里上下滚动。”而等阿毛凭着生的本能抓住一个破船板爬上了船,想起儿子还在水中,显然已救不及,“阿毛回头望了下漂散在水面的尸身和在水中窜动的人头,挪动两只脚板向前走。走到哪里去,他并没有想起,然而这时不但小行李卷已经离开他的脑子,连老婆孩子也无暇想起;他走,要活,要复仇,凭他九死一生后的一个光身!”这篇小说以阿毛为中心,人物形象十分鲜明,表现战乱下难民的普遍遭遇,控诉战争对平民尤其是对无辜妇女儿童的伤害,激励幸存的男人起来血性“复仇”。
万迪鹤小说《复仇的心》取自同一构思,难民王大有一家人逃难到河南,但在难民收容所妻子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自己想将挑篓里的半岁的孩子寄养给人家也不能办到,想报名当兵,军官也不让带着婴孩,等着回头去到放孩子的地方,却发现“这个还不到一周年的孩子,已经牺牲在敌方的枪弹之下了”[14]93。小说中如此写王大有的反应:“他没有哭泣,如像对着炸死的妻一样,他迟疑地站在一边看了一阵,伸手去把孩子抱了起来,就道旁挖了一个土洞,埋下他的孩子……埋了孩子,用手拍拍手上的灰土,默默地往前面走去……现在,占据他的心里的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复仇。”可见,抗战文艺描准了国人遭遇苦难的全部——失去的家园,死于横命的妻子,留下襁褓中的婴孩,战争将男人的一切夺走时,男性必会产生向死而生的勇气,就像作品中王大有所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当兵?我的家毁了,我的父亲母亲逃散了,我的妻炸死了,我应当复仇,我应该当兵去”。这儿其实是作家在借人物表达“抗战”意识,多数难民作品往往采取同样的构思方式,就是有意把男性置于生活的绝境,因为在父权-男权的体系中,妻子儿女是男人财产的主要部分,只有在失去家园与妻子儿女后,属于一个男人的全部财产才算丧失殆尽,这样他走向“抗日”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战争是无情的,特别是日寇轰炸下所造成的战争死难更是无差别的,但这种惨怖并没可能动摇中国人反抗的意志,反而让激烈的民族主义“复仇”情绪得到喷发。重庆大轰炸持续了8年,是世界战争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长期空袭,日军飞机成批次地无分别轰炸居民密集的城市,想要击垮移居“陪都”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但适得其反,更坚定了中国上下抗战到底的决心。但大轰炸造成了无数无辜平民的死难,就如女作家陆晶清,在她给欧洲友人写的信中所描述的“重庆大轰炸”的惨酷情景:
炸弹爆炸时我的耳膜都被震痛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最大最可怕的声音。在防空洞中,我和洞里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听到从飞机下抛掷的炸弹急雨一样的落下,爆炸声像巨雷一样的响……警报解除后,我随着虎口余生的大众出了防空洞,天!只看见三面火光,只听到一片哀号和哭。满街被难的人们扶老携幼哭诉着他们悲惨的遭遇,救护队用担架床不断的运送着鲜血直流的伤者。我木立在街头看烧红了半边天的火,看失掉了家的难民,看血迹模糊的伤亡同胞,辛辣的酸泪一直往肚里留!我怀疑字典里的“和平”,“人道”,是专为欺骗愚者而造的名辞。
……第二次更残毒的炸弹又来临了!那是四号傍晚,当各家正在准备晚餐时,大批日机又窜入重庆市,又是在我们住宅附近的市区掷下不能计数的炸弹和烧夷弹,立刻,房屋倒塌,四面大火,被难者的哭声震天,造成中外历史上未有过的惨劫! 那一夜,从四号黄昏直到五号天光,大火围着我们所在的地带燃烧,我们和成千万的人们都无食无水,且无路可走,惨淡的月光和血红的火光照映着遍地倒卧的伤者,无家可归的新的孤儿寡母,震惊过度失了常态的白发的老弱男女,他们的哭声是那样的悲哀,他们的呻吟是那样的凄惨,……我怀疑我已不在人间,那是地狱的景况,活的人间不应该有那样的惨状[15]110!
女作家让“大轰炸”下的生命死伤成为清晰可触的画面,寓居重庆的许多作家都亲历了“大轰炸”,也都纷纷书写了这种灾难体验。战难下的遍地死伤,孤儿寡母的抚尸悲哭,这种情景经作家的笔得以真实复原、再现,永远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创痛与难以磨灭的战争记忆,激起更多国人在战火下的抗争。当然,这随之而来的“复仇”决心绝不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报复,而是发自人类维护和平生活的抗争本能。蓬子为重庆大轰炸写的“时评”中就指出这样一个民族受难与复仇的关系。
敌人接连的烧和杀,曾经打击并动摇我们一丝一毫的抗战到底的铁石意志么!是的,我们的同胞中间,有数不清的人抱着母亲的血肉模糊的头颅痛哭,或者晕倒在丈夫的断肢残胫旁边,或者……但是,在一阵人性的激烈的痛苦中,我们并没有被恐怖所征服,并没有萎靡颓唐下来,并没有在自己的家屋的瓦砾场里,或自己的亲人的尸体前面,打过一个卑怯的寒噤!我们在哀伤中燃起炽红的怒火,要为自己的父母复仇,要为自己的儿女复仇,要为自己的丈夫妻子复仇,要为自己的兄弟姊妹复仇!复仇!复仇!忘记了复仇!才真是我们父母不孝的儿女!才真是我们民族忤逆的子孙[16]99!
韦君宜“自白”《牺牲者的自白》[19]56-58中,编者格外强调这是篇“真实”的心路记录,“自白”的是一个“智识分子”的青年女性在“恋人”被敌机炸死之后的心灵痛苦和爱国复仇情绪,显然这是一篇表达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铭文。“我感谢日本飞机,它教训了我,它告诉我,它到此地来不是打别人,正是打我,所毁灭的不属于别人,正属于我。它怕我还吝啬,就这一下子把我弄成了穷光蛋,再无懦怯打算,无法留恋,再也不用想任何最低限度的保留了。”以女性丧失亲人的痛苦体验来告知公众,表达强烈的复仇之心:“今天我相信自己能够杀人!我不害人,而人害我。现在,无论天底下曾经有过的那一种残酷行为,叫我做,我都可以毫不犹豫的动手将它加在我的敌人身上。仇恨呵!仇恨使弱者仁者忘了自己,仇恨使弱者变得比任何人更凶猛,使仁者变得比任何人都残酷,更忍心。——连命都不要了,那末,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吓唬我,可以使我顾惜的?”这种“自白”能获得战争中很多读者的精神共鸣,甚至民族主义激烈的情绪:“恨极的时候想过,我要坚决反对优待俘虏的办法。若是现在我手边有过日本俘虏,我必定用尖刀挑出他的眼睛割去他的耳鼻,剜出他的心肝,叫他也像我国被炸死的人一样。若是来的多,我必定来一个杀一个,个个都不用活着,叫他们也尝一尝,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究竟是个甚么滋味!”这是一个“复仇女神”形象,由“我的仇”到“中国的仇”“我们一百年来千万方里列祖列宗的深仇大恨了”,个人痛苦伸延到家国之痛。正如“编后记”所评价的,它与同期刊载的描写袜厂主人家破人亡、妻儿惨死的报告《血债》一样,都是“血腥的现实生活的记录”“决非靠幻想所能织成”的血泪之作。
诗人艾青在抗战中在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也非常善于借用女性形象符号来表达他的底层关怀,在他的诗歌《补衣妇》里,抒写了一个失去了家园,坐在路边依靠为人补衣艰难过活的难民妇女形象,这是继“大堰河”之后又一个母亲形象。如果说,《大堰河——我的保姆》表达的是一种素朴的阶级概念和对底层贫民的人道主义情感,那么《补衣妇》却淡化了阶级意识形态,而着意揭示战争背景下民族苦难的普遍现象。诗中的补衣妇是一个平民妇女,也是一个痛苦的母亲,她的丈夫不在场,是上战场了,还是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是诗歌未解之谜,但洗衣妇却显然要凭自己的双手挣饭吃,因为她有幼小的孩子要养活。诗歌通过无声的画面,静止的时间、单调的意象,揭示了这位难民妇女艰难生存的无望,由此强烈控诉了战争给平民妇女带来的无尽的灾难。
补衣妇坐在路旁/行人走过路/路扬起沙土/补衣妇头巾上是沙土/衣服上是沙土/她的孩子哭了/眼泪又被太阳晒干了/她不知道/只是无声地想着她的家/她的被炮火毁掉的家/无声地给人缝补/让孩子的眼/瞪着空了的篮子/补衣妇坐在路旁/路一直伸向无限/她给行路人补好袜子/行路人走上了路[17]11。
这位苦苦挣扎的战时女难民,被诗人视作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通过白描手法,诗歌将她以补衣为生,生存艰困的精神无望状态揭示出来。然而,战争能摧毁一切,却摧毁不了中国人抗战求生的精神意志,艾青抒写的难民诗不仅仅是控诉战争,他更注重揭示战争环境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生生不息的坚强意志,讴歌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再如他一九三九春写于桂林的《街》这首诗,所展现的正是那些战争中的难民向死而生的勇气:“被烽火所驱赶的人们”,尽管“女的怀着孕,男的病了,老人呛咳着/老妇在保育着婴孩”,男女老少“每个日子都在慌乱里过去”,但还是有“无数的人由卡车装送到这小城”“街上拥挤着难民,伤兵,失学的青年,耳边浮过各种不同的方言”,也因此一天天成就了一个“繁荣”的小城。然而,这儿仍无法得到和平,一天敌人飞机突然来轰炸,“给小城以痛苦的痉挛”“敌人的毒火毁灭了街,半个城市留下一片荒凉……”但就在废墟里,诗人却看见,“那曾和我住在同院子的少女”“她在另一条街上走过,那么愉快地向我召呼……——头发剪短了,绑了裹脚,她已经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了!”[18]31诗歌就这样借助一个象征性的少女形象,将前面战争苦难带来的灰暗一扫而光。
四、“女难民”的生产组织与斗争
在战时,随着战事的蔓延、扩散、相持,难民问题显已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他们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生存困境引起全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关注。由政府和民间主导的各种救济难民组织先后成立,除了募捐赈济,将难民组织起来自救生产也成为战时条件下当务之急。如何让他们自食其力,能在维持自己温饱的同时,服务于国家的抗战,这是政府和救济会首当考虑的:一般难民中的青年男性多被动员去服役当兵,难民女性则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培训后被组织参与抗战辅助性的工作,这成为一种战时需要。一篇《谈谈难民妇女问题》的时文里这样谈组织难民妇女对于抗战的重要性:“在这全面抗战的今日,全国一切的力量,将不分男女,阶层与党派的动员起来运用到抗战中去,特别是难民妇女们。”因为“她们的家乡已被敌人占领了,她们的财产已被敌人毁坏了,甚至于她们的家人儿女被敌人惨杀了,这客观的教训刺激了她们,假使能再给她们以训练,使他们正确深切地了解到她们所以陷入这般田地的原因,我相信她们抗战工作之热烈与努力,定会超过任何阶层的妇女”。在作了数字的大约统计后,该文作者指出组织难民妇女的意义,“全国难民总数中的难民妇女,其数量也着实可观,如以这部份的力量来参加到抗战中去,也不能不说是一支伟大的抗战力量。”“我们不能再让她们终日坐食无所事事,以消耗国家的资源”。作者指出教育难民妇女“也是整个抗战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今战争把她们集合在一起了,且终日坐食,没有半点工作可做,这正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机会,同时为了要提高她们的民族意识,使她们参加抗战工作,更需要教育的力量来起积极推动的作用”。那么,如何组织教育她们呢?作者提出教育难民妇女有三项内容:其一是提高妇女的民族意识;其二灌输一切战时常识,如防空、防毒;其三给以一切战时工作的技术训练,如救护、运输、侦察、生产等。“难民妇女的生产力是很伟大的,只要我们怎样很好的去运用”,作者提出六个具体措施:第一,开办难民妇女工厂,“为正在抗战中的国家生产必需的物品”;第二,筹设难民妇女生产合作社,发挥妇女善于缝纫刺绣针织的生产技能;第三,组织难民妇女洗衣队,为伤兵洗衣;第四,组织救护队,出发前方或留守后方医院进行救护工作;第五,组织战地服务队,开赴前线;第六,对过不惯流亡生活的难民妇女组织回乡服务队,给以教育,使其有组织的回到故乡去,到敌人后方参加抗战工作[20]8-9。
艾芜的《受难者》就真实表现了这一题材,女难民被抗战有力动员、组织,成为时代的积极力量。“尹嫂子”是一个难民妇女,她本来住在岛屿上,一家都靠丈夫打渔为生,但鬼子打来了,将丈夫和女儿抓走,听说女儿被鬼子轮奸,以为丈夫也被杀死了。“自己在火光枪声中逃走时,还跌死一个最幼的男孩”[21],然后一家五口人被一个镇子收容,孤儿寡母受到当地“收容所”与周边乡亲的照抚,但“这两桩惨事,她一提起眼睛就要流泪”。一次在与张二娘上山采菌子时,尹嫂子却发现她丈夫引着日本的兵船进来,要攻打这儿。担心鬼子来了大家要遭殃,二人想要回村报告,但张二娘脚受伤走不动,催促尹二嫂回去叫人来。但尹二嫂出于对丈夫的感情和全家生计的考虑,顾忌喊来“壮丁”会让丈夫有危险,然而想到镇里对她家的照顾,心里非常矛盾,“天哪!叫我怎么办呀!告诉呢,那就害了他,害了孩子,也害了我自己;不告呢,我就对不起她老人家,也对不起这里的好人家。”于是想有意瞒着,“日本鬼子打来,他们自然会同他打的,何必定要我来讲呢,……算了吧,听天由命好了”,然而回到镇里却听说,“壮丁”开走了,她担心镇里人的安危,为了使镇里的人免于她一家的遭遇,只有将鬼子已经从山后开上来的消息说出来。然而“敌人通通打退了,晚上附近各小镇市及村庄都燃起鞭炮,每个人都异常欢喜,张二娘赞她的义举是“活菩萨”,但“尹嫂子却倒在床上啜泣起来”,因为她丈夫给鬼子带路被打死了,虽然他罪有应得,“房子给鬼子烧了,女儿给鬼子坏了,不去报仇,倒反去帮鬼子的忙”,所以即使受到“长官”“真是顶呱呱的难民”的称赞和政府的奖赏,可是又怎能释解她失去丈夫的痛苦呢,“全家的担子她一个人可挑不起呀,没有爸爸他们一个个都会讨吃,变叫化子的。”小说通过心理活动描写塑造了尹嫂子这样一个善良而又普通的难民妇女形象,写了她被组织进抗日洪流的矛盾心理,揭示了日本鬼子毁了她的家,她虽爱丈夫,然而却不能不统一于“民族共同体”的觉悟过程,借助这一难民妇女形象,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对平民家庭生活的残酷破坏,揭示人性的软弱与善良,从而表达了民族国家话语,提出凝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
在全民抗战的方针下,难民固然是受救济的对象,却也被有机地组织起来,被有效动员服务于抗战建国的工作。在此过程中,难民妇女虽仍免除不了个人生活的苦痛,但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也进而获得了相关知识教育,习得了新的劳动技能,同时提高了民族自救意识,自觉参与民族解放的进程。如一篇散文这样描写难民收容所里的妇女的生活状态,尽管她们过的是“悲惨的生活”,是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一群”,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脂粉香”,只有汗水臭,“像肉块似的堆在一起”,还要“靠人家布施来生活”,但是,她们并不怨恨,“相反地,她们更坚决”,她们在“先生们的教育”下,了解到“这苦是谁赐给她们的:她们会永远的记住”“要清算总账,只要坚决抗战到底!”这个难民所里的妇女于是利用晚上不能睡的时间(因为臭虫),参加集体学习,了解时事,交流信息,学会了唱歌和演戏,“用戏剧和歌咏洗涤心中的郁热,而且得到不少生活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安慰。”“她们已有集体生活的意识了。中国胜利的曙光,在她们身上闪耀呐!”[22]10
由上所述可知,战时女难民在抗战各类纪实书写中的集中出现,既是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苦难的具像化身,其实也被作家有意建构成一个战时社会的象征符号,成为抗战文化表征战争与和平价值取向的有力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