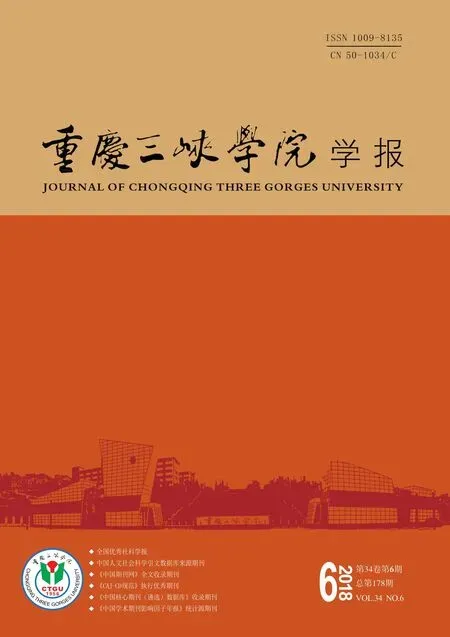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及其当代价值
2018-03-28戚文闯
戚文闯
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及其当代价值
戚文闯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黎庶昌被誉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出使西欧和日本期间,逐渐开创了文化外交的独特风格。黎庶昌文化外交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个由雏形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未走出国门前,深厚的家学渊源、理学大师曾国藩的言传身教等是此后黎庶昌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文化基础。出使西欧时期则是黎庶昌文化外交的雏形期,至使日期间终得以大放异彩。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对于当今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借鉴意义。
黎庶昌;曾国藩;《西洋杂志》;文化外交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沙滩人,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曾出访欧洲,历任驻英、德、法、西等国参赞,并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在驻外期间形成了独特的外交风格——文化外交。黎庶昌作为早期文化外交的提倡者和实践者,被誉为“文化外交第一人”[1],又被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称为“书生外交官”[2]。黎庶昌自始至终都秉持一个文人外交官的姿态,也正是这种文人气质,成就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与理念,这也是其所强调的“吾侪报国文为辅,邻境交欢德乃媒”[3]诗句的反映。其中,“文”与“德”的培养与积累,很大程度跟黎庶昌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这也对应了黎庶昌文化外交的缘起过程。
一、黎庶昌文化外交的缘起
黎庶昌文化外交的形成经历了由雏形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未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之前,黎庶昌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后又拜入理学大师曾国藩门下,这是此后黎庶昌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文化基础。
(一)深厚的家学渊源
黎氏一族在清朝遵义府的文教事业上可谓人才辈出,“上及他(黎庶昌)的祖辈黎安理,父辈有黎恂、黎恺,与其同辈的有黎兆勋、黎庶焘、黎庶蕃等人,子侄辈有黎尹聪、黎汝谦等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著作流传”[4]。自黎庶昌的祖父黎安理一代起,黎氏渐趋闻名,其后祖孙数代均在文学和学术上颇有建树,成绩卓著,推动了“沙滩文化”的形成,使遵义沙滩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区。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在张其昀等浙大史地系师生历经7年编成的《遵义新志》一书中,把近两千年的遵义历史分为从“夜郎期”直至民国的“新城期”九个时期,而第八期的“沙滩期”时间跨越清朝后期一百余年,从中可以看出沙滩文化在遵义地方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黎庶昌的祖父黎安理(1751—1819),字静圃,是“沙滩文化”的奠基人,其一生命运多舛,“为人严气正性,语言不妄发,举动必饬。终日坐必端、行必正”[5]73。29岁时中举,一直到58岁时“授永清教谕,迁山东长山知县,有治绩”[6]卷四四六《黎庶昌传》12480。其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同时将大半生放在从教上,培养了诸多人才。“受业于来知德高弟,得来氏传,故最精易学。”[5]68对子孙教育很严格,因其教导有方,其子黎恂、黎恺,外孙郑珍,均受影响,而成为黔中文学的代表,其言行事迹被子孙奉为楷模。黎庶昌少年丧父、生活艰辛,之所以能奋起,很大程度上是从祖父黎安理身上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
黎庶昌从小深受伯父黎恂的教导,而黎恂也是把沙滩文化推向辉煌阶段的关键人物。黎恂(1785—1863)字雪楼,是黎安理长子,幼年受父启蒙,成绩优异,“嘉庆甲戌(1814)进士。道光十七年(1837),署新平和县,政治平允,惠爱及民,历久而人愈思其德”[7]。黎恂是一位宋学家兼诗人,工诗和古文,后称病在家14载,一面潜心读书治学,一面开馆教授族人子弟,受教者众多。其后“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郑珍、莫有芝等都出其门下。黎庶昌6岁丧父,从小多受伯父黎恂的关照,也多次向伯父求教,深受教益。
黎庶昌的两位兄长黎庶焘、黎庶蕃和伯父黎恂的几位从兄也都喜爱文学,暇日聚首,互竞雄长,切磋诗艺,后来也各有诗集或词集传世。年岁稍长的黎兆勋和表兄郑珍,则是亦师亦友的首脑。少年的黎庶昌受二人熏陶,对诗和古文产生浓厚兴趣,但亲友中对黎庶昌影响最大的当数郑珍与莫友芝。在关于黎庶昌的多种传略中,包括清史稿在内,多谓郑珍、莫友芝曾授其课业,“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6]卷四四六《黎庶昌传》12481。郑、莫、黎三家比邻而居,衡宇相望。郑家的望山堂园林、莫家的青田山庐,与黎氏的沙滩村相距仅三五里之遥。三家也互结姻娅,互为师友。郑珍是黎恂的外侄兼女婿,莫友芝则是黎恂门生,而黎庶昌又是莫友芝妹夫。郑、莫既是黎庶昌的亲戚,并且为清季大儒,学术地位冠冕西南,故黎庶昌多向其请教,深受教益。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遵义人,受黎庶昌誉为“西南儒宗”[8]。其母是黎庶昌的三姑母。14岁来到遵义沙滩,从其舅黎恂就读,极受赞赏。其后“珍初受知于翕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6]卷四八二《郑珍传》13288。程恩泽是有名的汉学家,熟通六艺,善考据,是宋诗运动的提倡者,与阮元并为嘉庆、道光年间儒林之首。其后程恩泽调任湖南提学使时,特招郑珍入幕,授以汉学,“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于时”[6]卷四八二《郑珍传》13288。晚年郑珍隐居林泉,营建望山堂于子午山中,离沙滩颇近,黎庶昌闲暇之时,便前往望山堂向外兄求教,除受其诗法、古文外,还研读《说文解字》等。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近代章士钊将其与郑珍并称为“西南两大儒”[9]。莫友芝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莫犹人,系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莫友芝受其父教诲,“家世传业,通汇汉宋,工诗”[6]卷四八六《莫友芝传》13410。黎庶昌曾与莫友芝一同在曾国藩幕中,多向莫友芝问学请教。
综上可知,黎庶昌从小生活在书香门第,其父辈、兄长和师友都是黔中知名的文士,在儒学、文学上都很有造诣。在这种良好的家学环境熏陶之下,黎庶昌得以熟读经史,学贯今古,为其此后文化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主观条件。
(二)曾国藩的言传与提携
黎庶昌两次上书同治皇帝,对内政、外交、科举、财政等诸多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虽然未被皇帝采纳实行,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认为黎庶昌的上书颇有可用之处,便下令:“黎庶昌以边省诸生摅悃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方今延揽人才如恐不及,黎庶昌著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10]57-58自此,这位26岁的廪贡生便入驻湘军,并与曾国藩建立起深厚的师生之情。
曾国藩的学问(尤其是理学)、人品等在当时都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精研百世,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10]200。而其主导的湘军幕府中也可谓人才济济,其中的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等四人被时人称为“曾门四弟子”。曾国藩是“桐城派”的大儒,而此四人在文学诗词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文笔之中多带有“桐城派”的色彩。
1863年春,黎庶昌到达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大营,此时曾国藩幕府中已吸纳许多青年才俊,“太平军起,举国用兵,一时将帅,各开幕府招致奇才瑰异之士,以救时匡国,于是幕府中往往有名臣大将出焉。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11]4。曾国藩对黎庶昌以礼相待,并积极栽培,悉心教导,而且其对黎庶昌的评价甚高:“尝谓庶昌生长边隅,意气迈往,行交坚确,锲而不舍、可成一家言。”[11]49
曾国藩很注重提拔幕府中的后学之士,黎庶昌的官职升迁也多为曾国藩一手提拔。1863年12月28日(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朝廷举荐黎庶昌:“委用知县黎庶昌,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尽先补用,先换顶戴。”[12]奏稿八95其后在1867年1月8日(同治五年十二月三日),曾国藩上奏朝廷嘉奖幕府人员:“直隶州用江苏委用知县黎庶昌,内阁中书吴汝纶、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具王定安……该员等身先士卒,会克坚城。”[12]奏稿九2681868年,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上奏朝廷时,对黎庶昌的个人品行做出评价:“臣查黎庶昌自到营以来,先后六年,未尝去臣左右。北征以后,追随臣幕,与之朝夕晤对,察看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暂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12]奏稿十226并对他的官职差遣提出建议,受到清廷采纳。1870年夏黎庶昌出任吴江知县,随后又转任青浦。
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来看,1863年至1871年的8年之间,关于黎庶昌的记事有43处。如:(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天气阴雨,愁闷殊甚。至幕府与黎莼斋久谈。”[13]1081(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习字一纸,围棋二局,添写彭雪琴信二叶、黎莼斋信二叶,阅《祀天门》十一叶。”[13]1186(同治十年正月初五日)“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数件。黎莼斋自吴江县来,久谈。”[13]1345(同治十年六月十四日)“夜,换作《黎子元墓志铭》,黎莼斋之父也,作二百余字。三更睡。”[13]1379(同治十年九月廿四日)“酉刻,核批稿各簿。夜,李勉亭、黎莼斋来久坐。”[13]1405等。曾国藩的日记中多次提及与黎庶昌“久谈”,从中也能看出两人关系紧密。
黎庶昌追随曾国藩长达6年,其学问、德行以及为官处世的态度深受曾国藩影响。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金陵之时,黎庶昌如丧考妣。黎庶昌所撰《曾国藩年谱》中,对曾国藩之于晚清政局作了很高的评价:“自道光中叶以还,天地千戈,庙堂咨儆,二十有余年,人才之进退,寇乱之始末,洵时事得失之林,龟鉴所在。而我公所以树声建绩,光辅中兴者,或筹议稍迂,而成功甚奇;或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或任人立事,为众听所骇怪,而徐服其精;或为国忘躯,受万口之诋訾,而所全实大。”[14]对于黎庶昌而言,他与曾国藩之间已形成一种师生加父子般的深厚情谊,其文学、革新思想以及文化外交思想等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去世前数月,身染重病,仍手不释卷,“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15]。曾国藩这种对学问孜孜追求的精神,也是此后黎庶昌编印《古逸丛书》的重要缘由之一。黎庶昌曾撰写祭文感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与教诲,“始吾读书识字,尝欲抗志夫先哲,而如幽乏烛无,以辨学术之歧。自遇公而始有师,以为世不复见孔子,见公则亦庶几”[15]。
综上所述,黎庶昌文化外交的形成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黎庶昌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家学渊源的深厚,使得黎庶昌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深受郑珍、莫有芝等“西南大儒”的教诲,也入曾国藩幕府,受曾氏言传身教,列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同时在未出国门之前,受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儒家“华夷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国家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但走出国门后,面对中西文化差异,黎庶昌在游历西方的过程中,深入考察西方各国经济文化、政教民俗等方面的实况,促使其文化外交渐趋形成。
二、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活动
走出国门之后,黎庶昌以参赞身份游历考察西方诸国,了解所在国的风土民情、社会生活,记录成文字,终成《西洋杂志》一书和其他数篇游记,以实际行动阐述其文化外交。其中,出使西欧时期是黎庶昌文化外交的雏形期,为此后文化外交在日本的成功开展奠定基础。
(一)出使西欧的游历——雏形期
光绪二年(1876),清廷以郭嵩焘为驻英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刘锡鸿为副使,黎庶昌为参赞及其他译员、随从人员赴英,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遣驻外使节。光绪三年(1877)十月,黎庶昌又随驻英副使刘锡鸿前往柏林,改任驻德使馆参赞;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又奉调赴巴黎,任驻法使馆参赞;光绪六年(1880),又改任驻西班牙参赞,在马德里居住一年多,直到光绪七年(1881)七月,回国就任出使日本大臣时为止[16]。短短五六年里,黎庶昌几乎游历了西欧各国。同时秉持“经世致用”的明确目的和对世界人文地理的浓厚兴趣,著成《西洋杂志》一书,收录了其旅欧期间所写的各类杂记、游记、地理志等,涉及西欧各国政治外交、地理风俗、教育文化、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
1.西欧的社会生活。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恰如一幅描绘19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生活的风俗画。这是其文化外交中所关注的,深入体察驻在国的文化风俗,以便融入其中。举凡英国之婚姻立约,巴黎之街道水沟、油画院、歌剧院、各国钱币、巴黎灯会、赛船、英法赛马、西班牙斗牛、溜冰、马戏、耶稣复生会等等,都描绘得生趣盎然,栩栩如生。如黎庶昌在《斗牛之戏》除了细致入微地描述西班牙斗牛场景外,还从客观冷静的叙述中,透出自己的感悟:“斗牛之戏,惟日斯巴尼亚有之,为国俗一大端……此事西洋各邦,无不讥其残忍;然成为国俗,终不能革。并属地古巴,亦有此风。观其房式,正与罗马斗兽处废址如一。闻罗马古时,以罪人与各种猛兽徒搏,此只用牛,则习俗由来已久矣。”[17]113-114
2.西欧的政治、经济。黎庶昌在出使西欧期间,对西方政治体制、工业生产等方面也有深入的观察。《西洋杂志》卷三中分别介绍英国选兵之法、德国议政院、法国议政院、巴黎阅兵、英君主阅视兵船等西方政治制度。通过亲自到各国议院、议会旁听,让黎庶昌看到一种迥异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议会民主政体。如对德国上下议政院开会的差异作了细致描述:“戌寅(1878),正月初旬两点钟,德国开会堂于宫中,余疑其盛典与英同也。及往观之,则仪文繁简迥异。院绅来集者约五十人,排列庭中央,北向。次相和福曼、各部大臣十余人,南向……宰相毕司马克立于台边,亦持洋纸向众宣诵。”[17]54-55
黎庶昌在《日国更换宰相》一篇中介绍了日斯巴尼亚(西班牙)议会。“日国宰相干那瓦司,保党也;其前任宰相刚波司,公党也。”他认为,“公”“保”两党之争在西欧诸国十分普遍和激烈,与中国的党祸是大不相同的,“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17]47。《与李勉林观察书》一篇中考察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并针对时局提出“中国诚能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从,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内修战备以御外侮,扩充商贾以利财源,此非不足大有为于时也”[17]47的外交建议。在《西洋杂志》卷四则分别介绍乌里治制炮厂、阿母司汤制炮厂、赛勿尔磁器局、巴黎电气灯局、葛美尔制钢铁厂、蝉生玻璃厂等西方工业生产。其他还有几篇介绍英法德俄等国货币、西方的交通资讯、泰晤士报馆、伦敦电报局、邮局等西欧工业的发展情况。
3.地理考察。《西洋杂志》从一名旅游者的角度对西欧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工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直接观察,在外交官的出国游记中可谓别具一格。黎庶昌不仅考察西欧各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深入探索西欧各国的地理,知己知彼,尤其关注与中俄相关的西北边疆地理,以求服务于外交事务,在边界问题交涉中占据主动。
《西洋杂志》一书中也收录数篇地理游记,其中《西洋游记》七篇,详细记述黎庶昌游历西欧各国时见闻。这七篇游记对沿途所经城镇、风光名胜、居民人数、工厂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在《欧洲地形考略》一篇中介绍欧洲各国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地形概貌,“欧罗卜(即欧罗巴)分十五大区。在北四区:日盎格勒待尔(即英),三岛总名为格郎得布乃丹叶,都城为郎得尔(即伦敦)……在中六区:日佛郎司(即法国),都城为巴黎……在南五区:日波尔堆加尔(即葡萄牙。堆,地迂切,后仿此),都城为利司奔”[17]125-126。同时对各国行政区划,每国所辖主要城市均有涉及。并简明扼要地介绍欧洲地形,附近的各个海湾、海峡、岛屿、半岛山脉、河流、湖泊和火山等,可谓是当时很好的一本普及欧洲地理知识的读物。
自从《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便借通商、游历之名深入中国内地考察,并绘制详细的地图;而当时的晚清士大夫却对此少有关注、茫然不知。中俄边界绵延二万余里,沙俄也早有吞并新疆、蒙古之意。黎庶昌为了摸清中俄西北边境地理,在上曾纪泽的多封信里,多次表示愿意奔赴中俄边界考察:“庶昌久蓄此议,徒以非其时,非其人,不能有所建白。今幸值侯爷奉命订约,兼使俄都,故敢力陈斯议。倘蒙商之总理衙门,奏明办理,庶昌不惜躯命,乞充一路之任,以上报国家,为奔走臣,亦以明文正公知人之美。”[17]188为此,黎庶昌便广泛寻求关于中俄西北边界地理考察资料,并将所获之书翻译成汉文。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汇编为《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地路程考略》二篇。此二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详细记载了蒙俄边境的地形、气候、植被、交通、物产以及军事设施等,是黎庶昌专门从一位英商所作的游记中译出的。黎庶昌认为:“俄虽与国为邻,而行事谲诈,欧洲之人,无不心畏而恶之,此殆未可深恃者也。”[17]186目的就是为弄清中俄双方的边境地理情况,以利于巩固边防或便于处理边界争端事宜。黎庶昌将其邮寄给了驻俄公使曾纪泽,以便于他在中俄伊犁问题谈判中有所用,同时请曾汇送总理衙门以备察核,意在希望朝廷能派他亲自考察中俄西北边界,以实际行动践行其文化外交的理念。
(二)使日期间的文化外交——成熟期
游历西方时期虽是黎庶昌文化外交的雏形期,但其文化外交并没有在西方有大的开展,原因有二:一是中西文化在本质上差异巨大;二是限于语言障碍,“庶昌不习洋文,不能自读”[17]191。而在出任驻日公使后,黎庶昌的文化外交终得以在日本大放异彩。
在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期间,公使馆人员与日本官僚文士的交往一般规模较小,多为私人交游或小型的宴席集会上互赠诗篇。在日本人源辉声编撰的《大河内文书》中记录了首届驻日使团与日本文士在东京向岛聚会赏樱饮酒赋诗的场景。1878年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贵族源辉声邀请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驻日使团人员和一些日本文士等人,一同到东京隅田川畔的向岛赏花饮酒。席间中日两国人士观樱赋诗,彼此吟对唱和不断,场面极为热烈,此被中国官员称为“海外看花第一遭”[18]。
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使日时期,中日两国官僚、文士交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黎庶昌“驻日期间,以文章辅外交,与日朝野士大夫之醇于汉学者相接纳,文酒酬酢”[19]。定期举行诗歌唱和活动,而且接连编辑多本宴会诗集,结为《黎星使宴集合编》《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等,为后人认识在此期间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官僚、文士举行多次宴饮诗会,并坦诚倾谈、热情接待,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日本喜欢汉学的朝野官僚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文章和德行也都十分仰慕,欣然将自己所作诗文集请黎庶昌赐序、审定,并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以我学士大夫略涉文墨者,以不知黎公为耻”[20]183。黎庶昌与不少日本人结成莫逆之交,如:黎庶昌与日本著名汉学家藤野海南结下深厚友谊。在藤野海南死后,黎庶昌为其撰写《墓志铭》,并抚养其遗孤——藤野真子;后黎庶昌夫人赵氏死后,藤野真子又为赵夫人撰写《墓就铭》,一时传为中日文化交流之佳话。同时,黎庶昌也从中获取一些极为可贵的外交情报,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于好”[6]卷四四六《黎庶昌传》12481。日本将要出兵朝鲜的情报就是黎庶昌在与宫岛诚一郎交谈中获得的,“庶昌心异其言,使人侦知其事,密电驰报”[21]。从而破坏了日本出兵占领朝鲜的图谋。两度使日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极为成熟而富有成效。
三、黎庶昌文化外交的评价
对于黎庶昌而言,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对本国以及驻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同时保持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去游历西方与日本。在游历过程中,他以文人特有的眼光考察驻在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便较全面掌握驻在国的文化,并将其与外交事务相结合,以期达到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最终圆满地完成外交任务。
(一)在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能在日本大放异彩,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启国门,正如李鸿章所言:“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22]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转变,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形势、地理人文,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使自己对外部的世界大势由无知变为有知,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黎庶昌正是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走出国门,为文化外交的展开创造客观条件。
其次,就黎庶昌个人修养而言,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师从数人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积累,也是桐城派散文家的重要代表。同时秉持“经世致用”之志,眼光开阔,富有远见卓识,以自己的学术文化成就和坦诚态度赢得驻在国朝野人士的赞赏,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推动了黎庶昌外交事务的开展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使团随员孙点曾言:“终公两任之中,两国之交,亦竟无微嫌小衅睚眦于其间。固由调燮之有方,使令之得人,而区区杯酒往还,其所以合上下之欢心,集朝野之名誉者,此亦其明验乎!”[20]362-363这些都是黎庶昌文化外交大放异彩的主观条件。
最后,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虽然在欧洲游历时已初见雏形,但在日本却表现得极为成熟而富有成效。其根源在于中西文化之间差异较大,而中日之间文化渊源深厚,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文化差异,才导致黎庶昌只能从浅层的表面事物入手,以求抓住其本质,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选择在尊重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继而再了解西方文化。《西洋杂志》一书也是按此思路进行的,详细记载西欧各国社会风土民情,但短期之内难于与上层建立密切关系。而日本与西方则大有不同,“日东与我共处亚洲,唇齿之谊,益以同文。故其交契,笃于各邦”[20]362。故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在日本开花结果,大放异彩,“遵义星使,以敦笃之才,任上使之重,先后奉命驻东六年。上自王公贵人,下逮布衣草莽,公见私觏,温乎可亲”[20]362。加之,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力学习西方,甚至提出“脱亚入欧”之论,但当时日本学术文化界慕华之遗风余温尚存,这都促成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在日本富有成效地运用。
当然,尽管黎庶昌通过文化外交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也赢得不少日本朝野文士对中日唇齿相依、共图富强的良好愿景的认知,但在他围绕琉球、朝鲜问题与日交涉时,坚持与妥协又是并存的,其中既有力图扶大厦之将倾的坚韧,也有各种无奈和无力。19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虽有剑拔弩张之时,但始终没有爆发正面冲突——战争,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以黎庶昌为首的驻日使团人员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与贡献。妥协的一面体现更多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在内有清王朝面临外部列强侵略,统治者却腐败无能,无实质作为,大厦将倾;外有日本逐渐走上一条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步步紧逼。在如此的内外大背景之下,从事对日外交的黎庶昌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也就显得无奈和无力。
(二)当代价值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也是文化交流的历史。当今世界深受全球化的影响,而全球化让文化因素在外交事务中影响力日益凸显,文化已经悄然成为各大国争夺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力武器。美国、欧洲、日韩等国都逐步制定文化海外发展战略,作为文化外交先行者的美国占据主动。通常讲的美国三片:薯片、大片、芯片,即从个体上抓住人心、功能上输出文化的成功样板。欧洲的德法、亚洲的日韩等国紧随其后,甚至是冷战后逐渐复兴的俄罗斯,也都在开展文化外交,全球已然迈入“文化外交”时代。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东海划界等海洋权益问题上的争端加剧。同时,南海问题也由于美国和日本的介入而日渐突出。黎庶昌文化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于处理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层面若辅以文化外交,应能收到更大成效。当今世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已经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因此,国家应当利用好文化外交这一具有“和平性”或柔性特点的外交形式,在和平自主的基础上加强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增进国家间的政治互信,进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动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也可以说是对“文化外交”的极好诠释。通过充分利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情结,可以增进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为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营造更为有力的外部环境。
[1] 李文希.清末“文化外交”第一人[J].北京观察,2014(3):78-79.
[2] 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M].北京:中华书局,2003:60.
[3] 黎庶昌.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M].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17.
[4] 朱良津.古黔墨韵[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210.
[5] 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一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6]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新纂云南通志:第183卷[M].江燕,文明元,王珏,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09.
[8] 郑珍.巢经巢文集校注[M].黄万机,黄江玲,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1.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第30辑(郑莫黎专辑)[M].遵义:遵义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7:66.
[10]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7.
[11]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3]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1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255.
[15] 管佩韦.我国之前辈外交家——黎庶昌别录[J].读书通讯,1947(137):9-11.
[16]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376.
[17] 黎庶昌.西洋杂志[M].王继红,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8]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7.
[19] 黎庶昌.古逸丛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1.
[20] 黎庶昌.黎星使宴集合编[M].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1] 冯楠.贵州通志(人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82.
[22] 梁启超.李鸿章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90.
On Li Shuchang’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QI Wenchuang
Li Shuchang was honored as“the first person to open his eyes to the world in Guizhou”. During his trip to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he gradually created a unique sty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diplomacy is not accomplished overnight, but a process from embryonic form to gradual maturity. Before he went abroad, he had a profound family background. The words and deeds of Zeng Guofan, a master of neo-confucianism, were the important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Li’s cultural diplomacy. The Western Europe period is the embryonic period of Li Shuchang’s cultural diplomacy and finally achieved its maturity in his Japan diplomatic period. His cultural diplomacy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handling of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Li Shuchang; Zeng Guofan;; Cultural diplomacy
戚文闯(1989—),男,河南开封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K252
A
1009-8135(2018)06-0112-08
(责任编辑: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