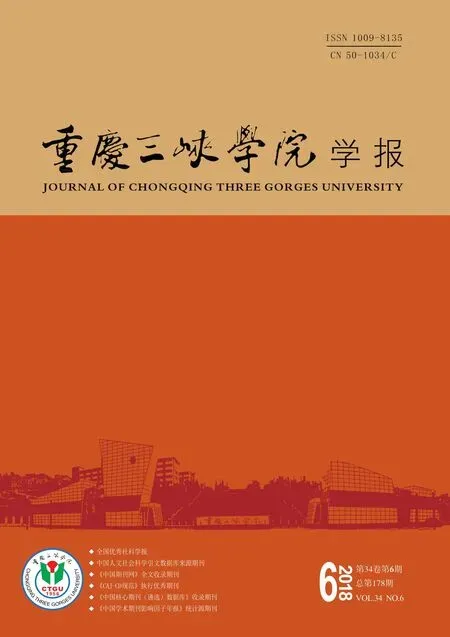《别让我走》的叙事学研究
2018-03-28马珍萍
马珍萍 黄 莹
《别让我走》的叙事学研究
马珍萍 黄 莹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江西南昌 330100)
《别让我走》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内部和外部的叙述聚焦模式,赋予了小说厚重的伦理意义,完美地深化了主题,形象地刻画出人物性格。以里蒙·凯南的叙事聚焦层面理论为基础,可以清晰地探究该小说的叙述聚焦、叙事技巧所赋予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叙述聚焦;叙述技巧
《别让我走》发表于2005年。作者石黑一雄运用含蓄幽深的手法绘制出一个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澜涌动的故事。小说文风素朴典雅,却力透纸背,让读者低回不已。小说中相互交织的现实和追忆创造出一个虚空飘渺的迷离世界,往昔如雨线般丝丝缠绕着女主人公凯茜的心绪。当细碎的记忆汹涌袭来,历经悲欢离合的凯茜用成人的眼光洞悉过往的懵懂、冲动、错过和悔悟时,才觉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纯真、梦想、友情和爱情,内心深处早已伤痕累累。萧瑟的流光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唯有回忆和伤痛填补着她的心灵缺口。
叙述聚焦指描述事件时的观察角度。里蒙·凯南提出聚焦有三个层面:感知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本文将以里蒙·凯南的叙事聚焦理论为基础,从这三个层面探究该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感知层面
里蒙·凯南提出聚焦中的感知层面(视觉、听觉、嗅觉等)涉及聚焦者的感官方面,由空间和时间确定。从空间的角度,聚焦者的外部位置与内部位置转换成空间概念,成了鸟瞰式视域与有限观察者这一形式,包括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1]139-141。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女主人公凯茜·H,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个为叙述自我,即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为经验自我,即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2]。小说中,叙述者“我”经常放弃自己目前(叙述自我)的观察角度,而采用正在经历事件时(经验自我)的观察角度。这样产生了故事外的叙述者和故事内的聚焦人物,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不再统一于叙述者。在该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凯茜在工作场所中通过回忆,叙述自己以往悲欢离合的人生经历,故而工作场所是该小说的话语空间;作为叙事内容的人或事主要发生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村舍、诺福克和康复中心等地方,构成了该小说的“故事空间”。
视角作为重要的叙述技巧和叙述话语的一部分,必然涉及到如何观察和描写“故事空间”的角度问题,对揭示主旨和构建“故事空间”有重要作用。黑尔舍姆学校是人物叙述者凯茜·H一生无法抹去的印记,小说第一次对黑尔舍姆学校的描述如下:
环绕主楼后边的小径是我的最爱之一。它可以带你去所有隐蔽的犄角旮旯和扩建的地方;你得挤过灌木丛,你得猫着腰经过两扇爬着常春藤的拱门底下,再穿过一扇生锈的铁门。而且一路上你可以一扇一扇的窗户向里面窥视。[3]41
在这段描写中,故事外的叙述者“我”暂时放弃自己目前的观察角度,转用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观察角度。“经验自我”描述了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坐落在如诗如画的英格兰乡村的深处,学校里有视野开阔的主楼和体育馆,以及穿过田野的弯曲小道。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凯茜特别喜欢穿行主楼后边的小径,这条幽静宜人的小径也是她愉悦而又闲逸的心灵之路。所有这些细微的描述都反映了女主人公凯茜·H对黑尔舍姆学校的深深眷恋。她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阶段——童年。学校里充满了欢乐、祥和、诡异、惶恐而又神秘的氛围,这里既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也是孩子们成长的伊甸园。当“成年后的我”回忆起在那里的童年生活,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我第一次明白,真正明白,汤米、露丝、我,我们其他所有的人,是多么幸运”[3]5。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局限性,读者仅能看到聚焦人物视野之内的事物[4]104。聚焦人物此时正就读于凯茜寄宿学校,学校的布局和环境可以通过聚焦人物的眼光来描述,但由于聚焦是通过一个故事人物的位置完成,不能进行同时或全景的聚焦。因此,学校之外的世界无法描写出来,除非聚焦人物走出学校并且体验学校之外的环境。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凯茜从未离开过学校,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那时候,对黑尔舍姆之外正等待着我们的世界,我所知不多。”[3]97
凯茜短暂的一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童年时期在黑尔舍姆度过,青少年时期在村舍,成年时期在医院和康复中心工作。自从青少年时期离开学校以后,凯茜就永远离开了黑尔舍姆。当有谣言盛传说“黑尔舍姆这些日子已经成了一家饭店、一所学校,或是已经成了废墟”[3]263,成年后的凯茜开车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尝试去找到它,我真的没有兴趣看到它,不管它现在什么样了”[3]263。但不论凯茜穿梭于何地,她都能发掘出黑尔舍姆的影子。凯茜和伙伴们刚来村舍时,“我们期望那里是一个大龄学生版的黑尔舍姆”[3]106。实际上,“村舍是一个多年前破产的农场的残存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外围的建筑,实际上都快要倒塌了”[3]106。残破不堪的村舍怎么能和如诗如画的黑尔舍姆媲美呢?人物叙述者凯茜描述村舍环境时,均在强调来自黑尔舍姆学校的克隆人与破败的村舍在寓意上的互为映衬关系,隐射出凯茜和伙伴们无忧无虑的黄金岁月将一去不复返,他们的命运也犹如村舍外围的建筑“都快要倒塌了”[3]106。
成年后的凯茜尽心尽力地做着护理员的工作,唯有开车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暇时刻,凯茜多次提及在开车的时候,经常出现梦幻看到了黑尔舍姆,例如:
我如今在乡间驾车时,仍然会看到让我回想起黑尔舍姆的东西。我可能从薄雾笼罩的田野的一角通过,或当我从山谷的一边开车下去,远远地看到一幢大房子的一部分……我就会想:“也许就是这儿!我找到它了!这儿确实就是黑尔舍姆!”[3]6
当我开车外出时,我会突然认为自己看到了它的一部分。我看到远处的一个体育馆,就确信那是我们的体育馆。或者看到地平上一棵模糊不清的大橡树边上有一排白杨树,一瞬间我就深信我正在从另一边向南操场驶去。[3]263
采用人物视角展现的空间,既是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同时又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投射[4]134。从这两处的描述中,可以得知人物叙述者凯茜在开车的时候,思绪很快转向到想象的空间,开启“白日梦”的模式。人物叙述者以“白日梦”的形式切换到主人公凯茜的心理空间,这些缥缈而又虚幻的心理画面展现出主人公丰富的主观世界,并且映照出主人公的内心秘密。此时凯茜将面临她的第一次身体器官捐献,意味着她在豆蔻年华中即将逐步走向死亡。此时的凯茜失去了同学、好友、爱人和黑尔舍姆学校,人世间值得留恋和牵挂的人和事也逐渐逝去。成年后的她内心深处饱经创伤,唯有梦回童年时期生活过的黑尔舍姆学校,才能抽离出残酷而又丑陋的现实世界,回归到童年时体验到的圆整感、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对于主人公凯茜而言,黑尔舍姆学校就是她生命起航的地方,友情和爱情凝聚的地方,这里是她的家,是她的心灵港湾。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主人公凯茜对黑尔舍姆学校的这种眷恋和不舍。有一个来自黑尔舍姆学校的女孩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逃离了黑尔舍姆,由于种种原因死在他方,“可是她的鬼魂总是在林子里游荡,盯着黑尔舍姆,渴望着能够允许回来”[3]46。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凯茜而言,黑尔舍姆学校有着“家”的意象,这种原初感受完全是构建在一种渴望受庇护和寻求归属感的秘密心理反应上。
任何叙事作品都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5]人物叙述者凯茜正是通过叙事把抽象和不可捉摸的时间变得形象具体,并且通过这种形式找回已然逝去的光阴。里蒙·凯南提出从时间的角度,如果是一个人物对他的过去进行聚焦,外部聚焦者可以支配故事的所有时间范畴(过去、现在和将来)[1]141。例如:
As it was, an opportunity did come along for her, about a month after the Midge episode, the time I lost my favorite tape……Even so, it’s one of my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s. Maybe come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I’m no longer a career, I’ll be able to listen to it more often.
此处采用了总结性的回顾性叙述。第一人称叙述者凯茜用目前的眼光观察往事,观察者“现在的我”处于往事之外,因此这是一种外视角。外部聚焦就是逆时的[1]141,无论在第一人称还是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事视角均不囿于故事范畴[2]。在这段描述中,有着非常鲜明的时间性:“As it was, an opportunity did come along for her, about a month after the Midge episode, the time I lost my favourite tape” 运用了过去时;“Even so, it’s one of my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s” 运用了一般现在时;“Maybe come the end of the year, when I’m no longer a carer, I’ll be able to listen to it more often” 运用了将来时。此处充分表明人物的意识在特定的空间内,打破了自然时间的规律,以心理时间为基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石黑一雄在此处成功地运用了时间蒙太奇的叙事技巧,以此揭示人物的意识活动,展现出叙述者的跳跃性思维。此外,时间蒙太奇不但可以在一个特定和受限制的空间内把叙述者凯茜各阶段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现出来,而且还能把叙述者凯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历和感知穿插、交织和重叠,从而映照出人物意识的流动性、立体感、多元化和延展性。
里蒙·凯南提出内部聚焦者只限于支配人物的“现在”[1]141。小说中,当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用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往事,那么人物聚焦者“我”则处于故事之内,从而产生内部聚焦。在时间上,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在进行叙事时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局,故意佯装不知“我”的逆时感知,耐着性子掩藏秘密,闪烁其词地讲述往昔易逝的流光。如此一来不仅造成悬念,而且可以缩短叙述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二、心理层面
里蒙·凯南认为心理层面涉及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由聚焦者对于被聚焦者的认知作用和情感作用构成。从认知角度看,外部和内部聚焦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不受局限认知的和受限制的认识之间的对立[1]142-144。从情感角度看,外部/内部的对立,可以转换为客观(中立的,不介入的)聚焦与主观(受感染的,介入的)聚焦的对立形式。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包含叙述自我(外部聚焦)和经验自我(内部聚焦)两种观察角度。小说的人物塑造通过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的对立表现出来。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者凯茜回忆了她人生当中三个重要阶段。
“过去的岁月中,我一次又一次试着把黑尔舍姆抛在脑后,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不应该总是回头看。”[3]5“叙述创伤事件时会再度经历创伤事件时潜藏的张力与冲突”[6],追忆往昔的悲欢离合必然会揭开凯茜心中的伤疤。在人物叙述者凯茜的叙事进程调度中,读者看不到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恢弘气势的场面,更多的是凯茜的悲情和无奈。叙述者凯茜通过外部聚焦的角度把黑尔舍姆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十三岁之前的黄金岁月和十三岁到十六岁的阴暗岁月。凯茜通过内部聚焦的角度叙述了在黑尔舍姆学校度过的童年生活。因为喜欢杰拉尔丁小姐,幼年时期的她和小伙伴们甚至创建过秘密护卫队来保护这位监护人。“学校的园丁和送货人和你开玩笑,和你开心地大笑,还叫你甜心”的时候[3]33,年龄尚小的孩子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特殊身份。此时的孩子们拥有着最纯洁和最通透的心灵,认为自己和黑尔舍姆学校的监护人、园丁以及送货人都是一样的正常人,可以亲密地靠近,也可以默默地守卫。黑尔舍姆的孩子们大约在八岁的时候想先躲在某处等夫人出现,然后大家向她一拥而上,以此来论证夫人是否真的害怕这些孩子们,夫人看到这些孩子们后,“突然僵住……似乎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3]32,夫人害怕这些孩子们就像“害怕蜘蛛一样”[3]32。这时候孩子们从这样一个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时候,“这会是一个让你心底发寒的时刻”[3]33,这也会促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一刻”[3]33。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孩子们知道自己和监护人是不一样的,随着成长,逐渐认清了自己是谁和自己的使命。
有一次监护人露西小姐正在作一次关于抽烟的讲话,突然玛奇问她是否曾经抽过烟,她承认抽过烟,接着说道:“你们是特别的,所以要保持身体良好的状态,这对你们每个人远远比对我来得重要。”[3]63当时只有9岁或10岁的孩子们听后只是保持沉默,他们不敢多问“为什么监护人可以吸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抽烟?为什么身体健康对我们非常重要……”孩子们对吸烟有害的认知并不是很深刻,只是隐约知道这与他们的未来有关。监护人总是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们不敢向监护人更深地打探那些未知的领域,因为一旦靠近那个领域,监护人总是表现得很尴尬,这是黑尔舍姆的孩子们非常痛恨的地方。
孩子们和露西小姐在体育馆里躲避大雨,当听到孩子们在谈论梦想时,露西小姐打断孩子们并且明确告知孩子们必须明白自己是谁,不可以拥有梦想,长大成人后就要捐献器官。那时候孩子们有十五岁了,听了露西小姐的讲话并不感到惊讶,有些孩子认为露西小姐有可能一时丧失了理智;或是其他监护人让她这么说的;或是因为孩子们太吵训斥他们。“那又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了”[3]74,这就是孩子们的态度。实际上,当他们大约在6、7岁的时候“就被告知有没有真正被告知”,为了延长人类的寿命,克隆人长大成人后就要开始捐献身体器官。监护人总是刻意选择时机告知孩子们的宿命安排,孩子因太小没有辨别能力只有机械地全盘接受信息,以至于今后听到更多关于身体捐献器官的话题时,他们不会感到意外和惊讶。这些可怜的克隆人正值纯真烂漫的时候,就被直面社会阴暗和污秽的一面,就被无情地折断了梦想的羽翼,就被告知一生已经规划好了——长大成人后就要开始捐献身体器官直至死亡。未来迎接他们的只有日益临近的黑暗岁月,这无疑给这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植入了创伤的种子,随着他们逐渐认清现实的残酷,心灵深处的创伤只会与日俱增。
公开讨论身体器官捐献是禁忌,可是当孩子们到了13岁后,可以拿捐献开各种玩笑,例如:“当捐献的时刻到来时,你就在自己身上裂开一点儿,一个腰子什么的就会溜出来,你就可以把它给人了……你拉开扣子取出自己的肝,把它扔到什么人的盘子里。”[3]79黑色幽默是在绝望条件下做出喜剧式的反应,此处作者运用了黑色幽默的叙述技巧,反映了在伦理道德腐化的病态社会里,这群无依无靠的克隆孩子们在绝望条件下做出的喜剧式反应,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们就是存在于荒诞世界的替罪羊,非比寻常的宿命感像绞肉机一样使他们的身心支离破碎。这些不知生于何方却知死于何处的克隆孩子们除了能在绝望中插科打诨缓解身心的苦痛,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和选择权。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病态、疯癫和荒诞的无情世界,把这群本该朝气蓬勃的孩子们逼迫得抑郁寡欢、精神接近崩溃。
凯茜通过内部聚焦的角度叙述了村舍的生活。孩子们满了十六岁以后就离开黑尔舍姆,其中有七个人和凯茜生活在村舍。村舍是一个破败的农场,管理员是位性情乖张,名叫凯弗兹的老头,不爱与孩子们说话,“一边四处走动,一边厌恶地摇头叹气;当你上前向他问好,他竟会瞪着眼看你,好像你疯了”[3]106,天冷的时候,孩子们央求他多留一些煤气罐,“但是他会阴着脸摇头”[3]107。黑尔舍姆的孩子们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冰冷和无法融入,“我们总是一起走动,并且似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尴尬地站在农舍外面,不知道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做”[3]109。管理员凯弗兹对待村舍的克隆人种种生活需求都是熟视无睹和置若罔闻,这体现出作为正常人类的他与克隆人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也反映了他厌恶克隆人并且缺乏怜悯心。这也意味着黑尔舍姆的孩子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地方,以后就要学会独自面对惨淡的人生。叙述自我(外部聚焦)对经验自我(内部聚焦)有着潜在的评价判断。成年后的凯茜通过外部聚焦,重新理解那段岁月,在孤立无援的陌生世界,黑尔舍姆的孩子们生存在社会边缘,备受排挤和歧视,缺乏安全感,只有相互靠近才能取暖。
村舍里流传着“可能的原型”等各种说法:当你找到原型,“你就能一瞥自己的未来”;“原型是一个不相干的事物,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一个技术的必要成分”[3]128。叙述者凯茜为了对自我有个更清晰的了解,甚至去翻看杂志试图查找自己“可能的原型”。当寻找原型失败后,凯茜的好友露丝绝望地说道:“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3]152对于原型的各种看法反映出克隆人对“我是谁”的苦苦追寻。克隆人都知道自己是原型和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原型是他们对人类世界的唯一念想,他们只是想找到与自己紧密关联的原型,幻想着有原型一样的未来,幻想着通过原型来更好地洞察自我。然而在冷酷无情的世界里,克隆人只是被边缘化的社会异类,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梦想的权利,没有知晓确切身份的权利,他们只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商品。“我是谁?”“我的原型是什么?”“我能有梦想吗?”克隆人心中充满了种种疑问,他们不敢问村舍管理员,不敢问社会上的正常人类,更不敢大张旗鼓地去探索清楚,最后只能认命,只能默默把疑惑留在心底,暗自把伤痛隐藏在心田。
凯茜和其他克隆人伙伴们在黑尔舍姆和村舍的生活都有着不如意的地方,但是真正让人身心备受煎熬和摧残的却是长大成人后所面临的巨大生死考验。离开村舍后,所有的克隆人都要从事看护的工作。“看护”一词看似平常,其实暗藏玄机,掀开这个词语的面纱我们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人类通过委婉语的使用,故意掩盖社会污秽和阴暗的一面。在小说里,看护员指的是还未开始捐献身体器官的克隆人,看护员先照顾那些已经开始捐献的克隆人,当收到捐献器官的通知书后就意味着看护工作结束。叙述者凯茜当了十二年的看护,多次亲临现场目睹捐献身体器官的凄凉场景,但是这样的叙述却不多。叙述者凯茜通过内部聚焦的角度详细追忆了令人心碎的一次经历。凯茜的好友露丝在完成第二次捐献后,凯茜在露丝临终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守护:“那是捐献者在令人恐怖的挣扎中有时候会有的一瞬间清醒”[3]216,体现凯茜经常面临这样生离死别的场面。看护员在工作中亲眼目睹一个又一个克隆人在灿烂的年华里不停地捐献器官直至死亡,无疑是噩梦般恐怖的情景。最惨淡的人生也不过如此,这真是一份让人心底发寒的工作。若干年后当凯茜回想起她与好友露丝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此情此景让读者痛彻心扉,但凯茜却没有像常人那般嚎啕大哭、捶胸顿足、怨天尤人。面对好友的离世,她理性得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为什么呢?因为凯茜是位优秀的看护员。叙述者凯茜通过外部聚焦的角度概括了看护工作的优良表现。
看护员需要来回奔波各地,穿梭于各家康复中心和医院,有时候还需要日夜兼程地同时照顾三四个捐献者。凯茜没有时间去哀悼好友的离世,怜惜自己可悲的命运,还有许多捐献者等着她照看。凯茜不是冷漠无情,她有着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她确实看到了露丝的痛苦,看到了她的挣扎,看到了她的恐惧和不安,看到了她对自己放心不下,看到了她不想这么年轻就这样黯然离开这个世界……但凯茜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无法逆转克隆人宿命的安排,无法控诉这个无情无义的社会为何要剥夺人的生存权,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露丝一步一步被死神带走。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化悲痛为力量,竭尽所能做好看护工作,尽可能为露丝以及其他捐选者给予生前最温暖的人性关怀。
童年时期的凯茜因为稚气未脱,隐忧中散发着纯真可爱;青少年时期的凯茜备尝无助感和失落感,抹杀了向往的梦想和人间温情;成年后的凯茜发现了许多埋藏已久的秘密,也看清楚了克隆人是被世界遗弃的异物,没有权利追问自己的身份,没有权利憧憬美好的未来,更没有权利逃离宿命的安排,只有默默履行宿命直至死亡。叙述者凯茜通过外部和内部聚焦之间的对立,层层揭露了她的心路历程。读者通过追寻人物叙述者凯茜的成长印记:懵懂无知的孩童、彷徨无措的青少年以及痛彻心扉的成年时期,可以感知到她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内心饱受创伤的历程,并为她和克隆人的悲剧命运感到无比的凄凉。
三、意识形态层面
里蒙·凯南提出:“意识形态层面常被称为文本的规范,是由一个以观念形式看待世界的一般体系构成,这个一般体系是评价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依据。一个人物,可以通过他对世界的看法或他在世界上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同样,叙述者——聚焦者的意识形态规范可以通过给予故事的倾向暗示出来,但也可以直接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意识形态除了在聚焦中发挥作用之外,还在故事(人物)以及叙述中起作用[1]147-148。在文学作品中,叙述技巧和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叙事本身也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
作为最常见的叙事形式,叙述视角并不仅仅囿于形式技巧,本身还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叙述视角和叙事声音是小说修辞的一部分,它们通过进入人物内心和调解叙述者与人物的叙事距离,控制着读者看待事情的立场以及对人物的同情,且读者通常并不曾注意控制自己的立场和同情的那些修辞手段[7]。石黑一雄通过叙述视角的运用,使读者对女主人公凯茜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小说将凯茜作为视角人物,从而有效拉近了读者与凯茜的距离。通过凯茜的内部聚焦让读者清楚地透过事件发现她的种种缺点,例如缺乏安全感、惺惺作态、自我封闭以及自卑而又清高等等。但这并不影响读者找到她高尚的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凯茜处于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她总是努力适应新环境,力争做到更好。在黑尔舍姆学校,她认真上课,积极汲取文化知识的养分。例如,在上陶泥课的时候,凯茜认真做着东西,旁边的同学阿曼达·C看后惊叫道:“凯茜,那个真的、真的很棒!这么棒!我敢说会被选进画廊!”[3]29作品能够被选进画廊,那是对黑尔舍姆学生最高的赞誉,由此可见凯茜的陶泥做得非常好。在童年时期,黑尔舍姆学校流传着各式各样有关校外耸人听闻的流言,使学生对外界产生了惶恐不安的心理阴影。事实上,凯茜离开黑尔舍姆学校后,来到残垣断壁的村落开始新的生活。经历了开始的恐惧和迷惑后,凯茜积极地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并且“一年之内我不仅会养成独自长时间散步的习惯,而且还会开始学开车”[3]108。当她长大成人后,离开村舍成为了看护员。看护员要面对工作中的挫败感、自我的孤独感以及身心俱损的疲惫感,一旦应对不妥就会劳心劳肺和忧愁苦闷。面对工作中的艰辛和不易,凯茜学会了忍受和灵活应对各种困难和压力。“我努力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我也设法做到了必要的时候让自己的话受到重视。当事情糟糕的时候……至少我觉得我已经尽心尽力而为,并且将事情合理的处理了。”[3]190
面对易逝的爱情、残酷的宿命和生离死别的时候,凯茜表现出超凡的淡定和从容的意志力,以及百折不挠和自我奉献的意识形态。几经坎坷和曲折后,凯茜和汤米终于能在一起。然而他们的爱情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汤米完成第三次身体器官捐赠后,身体每况愈下,生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听闻相爱的克隆人情侣可以申请推迟捐献,凯茜和汤米主动找到黑尔舍姆学校的监护长埃米丽小姐和夫人寻求帮助,但是结果却令人万念俱灰。在回去路途中,汤米因为一时无法承受失望的结果,“他狂怒着,喊叫着,挥舞着拳头,踢着腿脚……”[3]252面对爱人的悲痛欲绝,凯茜只是默默地拥抱着汤米,“我伸手抓住了他挥舞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他企图把我甩开,但我仍然抱着他,直到他不再喊叫,而我也能感到他已经不再挣扎。然后我意识到他的双臂也正抱着我。于是我们这样一起站着,站在那片野地里,站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彼此相拥……我们好像就这么彼此依偎着,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不被卷入黑夜的办法”[3]252。
事实上,凯茜和汤米早在青春期就彼此暗生情愫,露丝的插足导致凯茜和汤米错过了彼此。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汤米在三次身体器官被无情摘除后,依然坚持画画,期盼通过自己的作品证明自己和凯茜是真心相爱,以此来申请捐献从而延长与爱人相守的时间。与爱人相守是汤米一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梦想,但无情的事实击碎了他的爱情梦想,这无疑是给他提前判了死刑,他的生命也因此失去了一切光彩。凯茜非常清楚申请捐献一旦失败,汤米即将身亡命殒,他们的爱情也会转瞬即逝,但她依然没有失去理智,没有与爱人一起抱头痛哭,没有咒骂命运的不公。虽然凯茜心里有恨、有冤、有怨,但是她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因为她明白,无论他们如何逃避,他们逃避不了责任、道义以及良心的谴责,他们做不到违抗宿命的安排。她必须在汤米面前坚强起来,绝对不能感情用事和精神崩溃,因为她清楚汤米既是她的挚爱也是她看护的对象。虽然她无法和汤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她必须在汤米一息尚存的情况下,分秒必争地与汤米紧紧相爱;在汤米身心俱损的情况下,她是汤米唯一的温暖来源、生命的动力和存在的意义,凯茜必须要顽强并且成为汤米的精神支柱。只有这样,凯茜才能稳定好汤米的心神,让他不惧不悔地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步,让他们的爱情没有遗憾。
小说最后,凯茜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好友,失去了爱人,失去了黑尔舍姆,但是她没有万念俱灰,因为她还有看护的工作,如果没有工作了,她还有论文要完成,还有一些收藏品可以用来追忆往昔的岁月,甚至还可以到诺福克去“寻找”失去的人和事……不论身处何种绝境,凯茜总能绝处逢生,总能找到精神慰藉的来源。为什么艰难险阻打不倒她,为什么风雨雷电击不垮她呢?究其根本是凯茜的童年经历在潜意识里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凯茜自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黑尔舍姆学校,养育在人道和有教养的环境中。黑尔舍姆学校开设了一系列的课程,例如:地理课、体育课、美术课、诗歌课、陶艺课、英文课、生理课、文化概况课以及音乐鉴赏课等等。另外学校还开展了丰富的课外活动,例如:拍卖会和交易会。学生们都有从拍卖会和交易会获得的收藏品,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对自己的收藏品十分怀念”[3]36。学生们甚至“会在子虚乌有中制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独自前往的地方”[3]67。这些形式多样的教学课程和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生活,扩展了他们的见识,增长了他们的人文知识,塑造了他们的灵魂。为了让克隆人学生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今后的惨淡人生,监护人早早就告知学生们长大后就会离开学校,接受培训后从事一段时间的看护工作,一旦工作终止后就会被安排身体器官的捐献。如果想要过体面生活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学生们必须时刻认清楚自己的宿命安排。因此学生们哪怕离开了学校,他们不会忘记黑尔舍姆,不会忘记监护人的教导,不会忘记所学的人文知识。令读者感动的是,哪怕凯茜和同伴们在村落彷徨无措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探讨。“我会想起我的那堆平装书,书页被弄得皱皱巴巴,好像是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会想起每天清晨,我在黑谷仓楼上的房间里醒过来,听见外边学生争论有关诗歌和哲学的声音,或是在漫长的冬季里,我们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随意地讨论卡夫卡和毕加索。”[3]109“我们不知何故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在村舍过得好不好——你适应得多好——不知道为何竟是反映在你看了多少本书。”[3]112在孤立无援和四面楚歌的时候,这些人文知识的阅读和探讨在克隆人学生们的心里点亮了温暖的火把,让他们有超凡的勇气和胆识应对今后的风霜雪雨。当凯茜失去了友情和爱情的时候,她想到黑尔舍姆学校布置的最后一项作业——论文。“今天当我想起我的论文,我所做的是仔细思考其中的某个细节:我或许会想到我能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旦等我不再做看护员而有了时间,我要回头再写它一遍。”[3]106友情和爱情的失去意味着凯西失去了人间的一切真情,她的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巨大的虚空感灌注于她的头脑,论文的写作无疑是她的另一种重要的精神慰藉方式。
叙述视角为读者提供观看的角度、态度和立场。通过控制读者的立场使得读者不仅能够同情,而且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一致[8]。通过人物叙述者的视角,读者发现黑尔舍姆学校与克隆人之间有着既矛盾对立又唇齿相依的关系。黑尔舍姆的克隆人一生都在惶恐、迷茫、不安、追寻和服从中度过,“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去往何方?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画好画?为什么要写好诗歌?为什么要有创造力?为什么不能拥有梦想?为什么夫人要带走优秀的作品?为什么要有黑尔舍姆学校的存在?为什么黑尔舍姆学校会倒闭?为什么克隆人要捐献身体器官?为什么人类残忍地对待克隆人?”他们自己无法找出答案,黑尔舍姆学校的克隆人所有的无措和茫然都需要学校监护人来指导、安排、布局和揭晓答案。事实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治愈不治之症的方法。“人们宁可相信这些器官是无中生有而来的,或者最多也就是相信它们是在什么真空里培育出来的。”[3]241人们根本不会把克隆人看作正常意义上的人类。创建黑尔舍姆“实际上是在尝试一件不可能的事情”[3]242,监护人几经博弈和战斗,艰辛地在黑暗的世界里创造出一方小小的象牙塔。他们给克隆人孩子们提供庇护所,精心呵护着孩子们在人道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培养孩子们从小就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尊严地面对宿命安排。虽然黑尔舍姆的监护人们都对克隆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无法改变克隆人的宿命安排。学校的监护长埃米莉小姐在开晨会的时候,有时候会如梦似幻地说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令我们颓丧的可能是什么呢……可是我不会屈服的!哦!不会!黑尔舍姆也不会!”[3]108从黑尔舍姆创立之初到运行管理中,监护长埃米莉小姐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为了给克隆人提供庇护,埃米莉小姐和其他克隆人保护者们挣脱外界的质疑和排挤创办了黑尔舍姆学校;为了保护更多的克隆人和唤醒人类的良知,埃米莉小姐和其他克隆人保护者们在国内组织大型的活动来展览克隆人孩子们的优秀艺术作品,并且大声疾呼“瞧那件作品!你们怎么胆敢声称这些孩子们不如健全的人类”;为了让黑尔舍姆学校更长久地运转下去,埃米莉小姐和其他克隆人保护者们必须说服赞助人援助这些无依无靠的克隆人孩子们。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克隆人保护者们的力量过于薄弱,黑尔舍姆学校最终不得不关闭。“风向已经大为改变,再也没人愿意被人看见在支持我们,而我们小小的运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扫地出门了……在整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再也找不到黑尔舍姆这样的地方。”[3]242-243而今,人类大肆地掠夺克隆人的身体器官,无视克隆人的悲剧命运。克隆人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他们只被视为身体器官的提供者而存在,再也没有人把克隆人当作正常人类看待。目睹着血淋淋的现实,埃米莉小姐和其他克隆人保护者们痛心疾首却又爱莫能助。
小说结尾写道:“我只是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车上,朝不管哪个我该去的地方疾驰而去。”[3]264作者打破传统小说的固有创造形式,没有给出固定结局,而是将多种可能性结局组合并置起来。End 意味着一个终端,一种目的的实现,一个问题的解决;它意味着一种释然。数尾并存,悬念依在[9]179。叙事者所站的角度背后,是由实际意义上的作者所决定的。而对于视点的选择则隐含作者希望由小说传达给读者的某种意义价值[10]。读者从凯茜的角度阐释此处的结尾,意味着凯茜在失去了世间重要的牵挂和羁绊时,没有精神崩溃。“我只是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车上”,意味着回归理智后,凯茜还要继续履行宿命安排。读者不难猜测凯茜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器官捐献者,因为她非常清楚身体器官对于无数“不治之症的患者”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凯茜短促的一生,生时平凡无奇,死时无声无息,但她的生命因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焕发出伟大的人性光辉。然而该小说并不是以最后一句话的结束而结束,即便凯茜最后要面临捐献直至死亡,也无法扭转冷酷无情的现状:再也不会有黑尔舍姆这样的学校;克隆人的悲惨命运不会就此终结;利益熏心的人类不会停止对身体器官的掠夺;科学家们违背伦理和道德的研发也不会就此停止,未来人类也有可能会被取而代之……小说塑造的整个世界俨然就是一个动荡不安、荒诞、可笑又可悲的世界。小说中丰富的伦理意蕴不仅体现在文本内部的道德讽喻上,还表现为构建于个体创伤之上的集体创伤。即便如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哪怕是身处绝境都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念,他们本着道义和责任,力所能及地为这个世界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这种高贵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无疑令读者感动而又钦佩。
四、结 语
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别让我走》打破了线性和因果叙述结构,时序交错和空间漂浮不定。小说中的故事没有清晰的开头,没有精彩的情节,也没有确切的结局,整个文本呈现出松散性、碎片化和随意性。为了构建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文学世界,石黑一雄在小说里运用了丰富的叙述技巧,例如:拼贴、时间蒙太奇、黑色幽默、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隐喻、时空错位、抹除等。文本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召唤“读者对文本的参与创作是最佳的阅读方式,而且也只有积极的、创造性的阅读才能给人带来快乐”[11]。作为叙述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角的选择是叙事话语中重要的叙事策略,是文本中连接技术和意识形态、文学形式和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12]。作者选用什么视角必定有其不同的审美思想作指导,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9]166。石黑一雄在小说里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内部聚焦和第一称外部聚焦的叙述视角,赋予了文本厚重的伦理意义,完美地深化了主题意义,形象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和性格。通过揭示小说中克隆人的悲惨命运,石黑一雄对当今肆意主宰文明发展的跋扈当权者,提出了最为深沉的批判和抨击。面临冷酷的现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却表现出了一种殊死的勇气。石黑一雄通过对叙事聚焦的灵活运用,使该小说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M].赖干坚,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139-148.
[2] 申丹.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在视角上的差异[J].外国文学评论,1996 (2):14-23.
[3]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3-263.
[4]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龙迪勇.叙事学研究之五梦:时间与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2(8):22-35.
[6] VIKROY L.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M].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2002:29.
[7] 李丹.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0(2):37-41.
[8]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
[9] 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52.
[11] 尚必武,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确定性管窥[J].求索,2006(2):170-174.
[12] 李海英.视角与意识形态——辛格短篇小说叙事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A Narratological Study of
MA Zhenping HUANG Ying
Kazuo Ishiguro’s novelrepresents his innovation on narrative techniques. Ethical Significance, thematic mea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are vividly presented in the novel through first-person external focalization and first-person internal foc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immon-Kenan’s focalization, the paper, in the ligh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tends to analyze how narrative focalization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endow the novel with the permanent artistic charm.
Kazuo Ishiguro;; narrative focalization; narrative techniques
马珍萍(1968—),女,江西南昌人,硕士,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黄 莹(1983—),女,江西南昌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高校外国语言教学研究专项课题”(14WX305)。
I106.4
A
1009-8135(2018)06-0072-10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