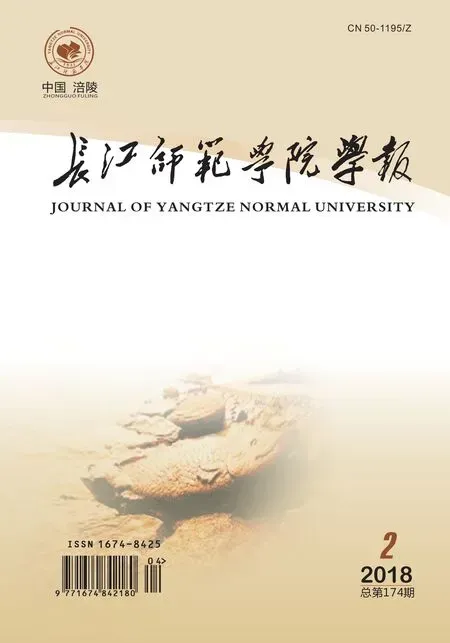巴渝地域视角下聂华苓的小说创作
2018-03-28徐璐
徐 璐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一、抗战时期聂华苓的巴渝经历
华文作家聂华苓一生漂泊迁徙,跨越了大陆、台湾、美国3个地理空间。“在20世纪特有的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不论个体的越界行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表示对以往生活的一定否弃,对人类寻求幸福、自由的权力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1]虽然去国已久,聂华苓却始终未割舍自己对故土的眷恋,在其创作中不断书写过往的人生经历甚至衍生出“想象的乡愁”。原因之一是童年经验对作家的人生影响非常深刻,“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2]。因此,聂华苓作品中的童年经验与“乡愁”可以说是“正本清源”,但却因作家不断漂泊的经历难以具体定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多变的政治形势,致使大部分现代作家处在不停的迁徙之中,那聂华苓的乡愁究竟该归于何处?根据她的自传《三生影像》可以确认,聂华苓在抗战时期的流寓空间,总体而言是溯长江而上,穿三峡,由荆入渝。1938年8月,聂华苓从武汉坐轮船至宜昌,再从宜昌到古镇三斗坪(今属湖北宜昌)避难。1939年,聂华苓先就读于湖北恩施屯堡的湖北联合中学,后进入地处重庆长寿的国立第十二中学。1944年,聂华苓进入战时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直至1946年暑假随中央大学复校南京。可以说,抗战时期,聂华苓在巴渝地区近八年的人生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佛大学的布伊尔曾提出,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借助“地缘感”而实现的。“地域”具有“地理性、社会性与地缘性”,融合地方的“自然元素、社会关系和内涵意义”;“地缘感”则是“个体对地方的亲身体验”[3],尤其是个体在识别、感受所在地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意义基础上对该地产生的心理认同。因此,作家在特定地域中的身心体验与情感认同直接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表现对象、叙述方式与审美价值观。聂华苓作为跨越复杂时空的作家,没有像她的小说《桑青与桃红》中的主人公在经历漂泊生活后,异化为内心无根的精神分裂者,这应该归功于深沉在个体意识底层的稳定强烈的地域文化心态。
从这个意义之上,可以初步推断,巴蜀地域文化在聂华苓内在精神空间刻下了深刻烙印。而聂华苓后来的文学创作皆有重要章节取材于抗战期间在巴渝区域不断迁徙、避难求学的生命体验,并开掘了三峡书写和重庆抗战书写两大小说题材,使这两大题材空间在自己的小说叙事中重复书写,衍生成为独特的巴渝抗战时空架构。
二、聂华苓小说中的三峡书写
1938年8月,作为抗战重镇的武汉陷入日军包围,身居武汉的聂华苓随母亲一行9人突破重围,到鄂西古镇三斗坪(今湖北宜昌)避难。当时的聂华苓年仅13岁,对自己乘坐的木船险些在三峡天险“鬼门关”遇难的经历印象深刻。1976年,聂华苓创作了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在中国名为“桑青”、在美国移民局官员面前自称是“桃红”的华人知识女性。作者透过主人公的视角和记忆的碎片,运用超现实的中国古代神话、诗歌和身为“桑青”的日记、自认“桃红”的书信,以及报纸的新闻片段和地图,将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再现了这位女性知识分子1945到1970年间在大陆、台湾和美国3地迁徙、流亡、挣扎逃离各种压迫的人生经历。《桑青与桃红》共4部分,第一部分为“桑青日记1945年7月27日-8月10日”,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桑青从南京离家出走后,沿长江搭乘木船流亡重庆,在三峡的瞿塘峡遇险的经历,作家沿着桑青的流亡线索,展开了对长江三峡风貌的深情描绘:峡江激流、江中各处险滩;在江上奔波生活的船夫、纤夫;嵌在江坝峭壁上的古镇,沟通两岸往来的谷上吊桥与石板街、茶馆、担担面馆,一系列的自然景象和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颇具三峡特色的地域风情。
桑青和朋友“老史”在瞿塘峡的起点黛溪古镇等待木船,作家通过桑青的外来人视角介绍这里沿岸险峻陡峭的环境,黛溪古镇像“一条细细的小链子,挂在很高的山岩上。没有河坝,人一下船就上梯子。就着山岩凿成的梯子,很窄”[4]18。黛溪镇之下是“新崩滩”,桑青搭乘的木船在新崩滩上被撞坏,作者借镇上担担面馆老板娘的闲话展示整个三峡的激流险滩:“新崩滩还不算险呀!再上去还有黄龙滩、鬼门关、百牢关、龙脊滩、虎须滩、黑石滩和滟滪滩。有的是枯水滩;有的是洪水滩。枯水滩逢枯水险;洪水滩逢涨水险。逃过了枯水滩,就逃不过洪水滩;逃过了洪水滩,就逃不过枯水滩……”[4]23
果然,桑青和老史等一行人过了虎须滩,“滟滪冒石,黑石下井”,船只还是搁浅在黄龙滩上,这还不是最险恶的情形,作者在此通过一幕失事惨剧表现了峡江中的急流,木船落入江中的漩涡,“船上的人叫着,女人孩子哭着。船转的很快很快,象个小陀螺一样,有一根无形的鞭子抽着它得得转。漩涡四周冒着白沫。白沫溅起来了,翻起来了……那条船就象西瓜摔在石头上一样裂开了,把船上的人全抖到水里去了。又一阵大浪翻起来了。大浪过去了,水里的人不见了。”[4]56-57主人公“桑青”过三峡不断遇险的经历无疑是聂华苓取材于自己在三峡“鬼门关”的亲身体验,将自己的童年经验重现于小说文本之中,是作家生命精神、情感的移植重现。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抗战正是中华民族的“三峡”式历险。支撑民族击溃外敌侵略的主要力量正来自中国的民间大地,就像三峡上古老的航船依靠纤夫集体的原始气力,终将抵抗滔天巨浪、激流险滩,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江河中不断行进下去。聂华苓在小说中重复书写自己的三峡历险经历,是因为这从中得悟不屈精神的生命体验,已经成为聂华苓终生的精神财富,使她获得了应对人生各种灾难、变故的精神基底。
千百年来,在峡江之上为求生存,纤夫渐渐成为三峡一道古老而不可忽视的风景,一代又一代的纤夫高喊着“川江号子”与险滩急流勇敢搏斗,纤夫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七月派”作家阿垅就曾在1941年创作现代诗歌《纤夫》,提炼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与抗争精神——血泊中的中华民族犹如纤夫牵引的那条“衰弱而又懒惰/沉湎又笨重”的大木船,但纤夫们那“严肃的”“坚定的”“沉默的”着的脚步不畏艰险,凝成“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民族苦难中的艰难奋进。
在《失去的金铃子》里,聂华苓也细致描绘了三峡纤夫的民俗风情:“在下游,十几个纤夫半裸着身子在陡峭的崖壁上匍伏着前进,身子越弯越低,几乎碰着地面。河里的木船象一把小小的钝刀,吃力地切破白浪,向上驶来。船过了滩,纤夫们有的在崖石上呆望着那条已经过滩的木船;有的跑下河里洗澡,一面捧起水喝;有的站在崖石下,两手叉腰破口大骂,裤子吊在肚子底下。一场多么庄严而美丽的挣扎啊!”[5]此处,作家通过主人公“苓子”的视角,聚焦了背负纤绳匍伏在悬岸峭壁之上挣扎前行的纤夫和切浪划波艰难上行的木船——半裸的纤夫、紧贴崖壁、匍匐前进、江水解渴,呈现的是赤裸裸的生命;如钝刀的木船,劈波斩浪、挣扎前进,象征着坚韧的生命力。这里,一方面,作家向读者展现了三峡纤夫生活的艰辛、危险、困苦;另一方面,作家感动于纤夫渺小个体却勇于挑战天险的坚韧勇敢,感知到个体迸发出的原始力量,由此窥见了一种贯穿于历史与现实中的、于艰难中不断跋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聂华苓小说中“三峡纤夫”描绘和阿垅的诗作《纤夫》都是从虚实相生的角度,以古老的纤夫形象指涉更为深广的抗战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失去的金铃子》创作于1960年的台湾,时值作家供职的《自由中国》杂志停刊,雷震、殷海光等同仁被捕入狱,聂华苓在苦闷困顿中将目光投向儿时在三斗坪生活的经历,基于一点昔年记忆以冲淡现实的严酷。在《苓子是我吗?》中,聂华苓回忆了《失去的金铃子》的创作背景:“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候我才十三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6]
三斗坪最初带给作为外来者的“苓子”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奔腾咆哮的长江、状如刀切的万丈崖壁、峭壁上的一线栈,当地特有的抬人的滑杆与兜子、始终萦绕“苓子”耳畔喳喳鸣叫的金铃子……这些富有浓郁三峡气息的风物,构成了一幅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情画卷。不同于外部世界,相对闭塞的三斗坪没有战争、死亡的威胁,取而代之是泥土、阳光的芳香。但随着苓子对三斗坪民间百姓生活的观察、体验不断加深,才逐渐意识到三斗坪及周边的三峡乡村依然笼罩在陈腐颓败的封建传统思想之下,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受到族权、父权压迫的女性形象:玉兰为赖家儿子守一辈子活寡;美貌的巧姨年轻守寡,她与医生杨尹之互生爱慕,却遭到亲朋的合围,最后放弃反抗,认罪出家;丫丫和郑连长相爱,但其家人贪图财产,逼她嫁给哮喘病人,但丫丫最终逃婚私奔……聂华苓通过以上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批判了三峡乡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风俗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这足以说明聂华苓对三峡的民风民俗有着深入的体验、了解。
三、聂华苓的重庆抗战题材书写
1940年夏,聂华苓被分配到长寿栀子湾的国立第十二中学。1944年夏,进入战时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随后转入外文系,直到1946年暑假,聂华苓随中央大学复校南京。总体来说,聂华苓在重庆生活了6年时间。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曾指出,文学景观提供了作家观照世界的方式,作家不同时期的生存体验和文学创作反映出人与空间和流动性的关系,赋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空间以恒久意义,显示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文化的景观[7]。从聂华苓晚年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她对自己在重庆度过的战时大学时光怀有深深的眷恋:“国立中央大学一年级在嘉陵江畔的柏溪,自成一体。校本部在对岸的沙坪坝,遥遥相对……那一群新大学生,突然跨进一个自由无羁、生动活泼的世界,读书、救国、恋爱,春风吹野火也挡不住。”[8]
半个世纪后,在小说《千山外,水长流》的创作中,聂华苓将主人公柳凤莲和金炎都“安排”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他们每天在松林坡走上、走下、去上课、去自习。松林坡上的校舍、小路、教室、图书馆以及松林坡边上的嘉陵江,这都是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由此,重庆战时的大学校园景象甚至于一些微小的细节一一浮现,清晰得让人感觉仿佛近在眼前。而在当时国难当头、战事仍频的时局之下,国家经济惨淡,“官方报告的1940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92 441 020元。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9]471。由于通货膨胀恶化,南迁的大学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9]473。聂华苓通过中央大学学生柳凤莲的“抗战日记”透露当时学生的饥饿贫苦的生活:“我们已经在饥饿线上挣扎好几年了。我们的学校生活只是个‘抢’字:在饭厅‘抢’饭吃,在图书馆‘抢’参考书,在阅览室‘抢’坐位——挨近昏黄灯光的坐位。”[10]122而大学生们抢的饭其实就是战时常见的“八宝饭”。
尽管学习生活艰难贫苦至此,那一代学生仍继承了五四青年的责任感和蓬勃朝气。青年学生以学习知识为主,中央大学的学子亦是勤奋治学。学校设备差,图书馆没有足够的位置和饮水设备,学生就把课桌搬到茶馆,在茶馆里用功看书。与此同时,学生们如饥似渴汲取着来自外界的文化信息,尤其喜爱观看话剧演出。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剧演最多,影响很大,称得上是话剧中心。虽然重庆经常受到日寇飞机轰炸,但秋冬两季日日云雾弥天,便于演戏。聂华苓自述:“我在中央大学,从沙坪坝到重庆,有车坐车,没车步行,决不错过重庆上演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家》《蜕变》……”,“我们在学校也演戏……譬如曹禺先生的《原野》和《北京人》。那时候的戏剧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11]。从观看重庆的话剧演出中,聂华苓受益良多,特别是在《桑青与桃红》中许多场景设置颇具戏剧特点。
但这些青年学子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胸怀家国,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投笔从戎者众多。《千山外,水长流》中,柳凤莲的抗战日记记述了当时大学校园内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历史情境:“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随时可能窜到重庆……可把重庆苦闷的年轻人打醒了,纷纷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去和盟军一起打日本人……一伙伙男同学穿着灰布棉军装,一脸慨然就义的神情,走出校门。”[10]122小说中,中央大学学生金炎考取译员训练班,在重庆接受英语训练后,到远征军当译员。
小说《桑青与桃红》的第一部分是聂华苓抗战书写最为重要的篇章。聂华苓不仅设置主人公“桑青”和其他4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亲历日军的轰炸,还通过不同角色的经历侧面展现日军在南京等地犯下令人发指的奸淫虐杀罪行,以及在重庆进行大轰炸造成的灾难。“老先生”讲述自己曾亲历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他在山坡下的防空洞里躲了七天七夜,实在受不住出来透气,却遇上日军又一批轰炸,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周遭已是一片草草堆起的坟茔,大轰炸过后的重庆“冒着几根很粗很粗的黑色烟柱子,影子映在嘉陵江里,成了顶天立地的黑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是灰色的,好象整个重庆的灰尘都掀起来了”[4]52。当“老先生”从坟里救起一个被轰炸吓到神经错乱的女人,她满口疯话,脑海里只剩下几年前在南京大屠杀中险被侵略者侮辱的惨痛记忆,甚至忘记了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不仅“老先生”亲身经历重庆大轰炸,与桑青结伴同行的“老史”告诉众人自己的家庭住址是重庆大隧道,因为她的父亲死于1941年日本疲劳轰炸下制造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当时因窒息遇难的有一万多人。“流亡学生”的母亲则死于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轰炸。
聂华苓揭开了日寇侵略下中国大地生灵涂炭的惨状,中华民族在日本残酷入侵下己是满目疮痍、尸横遍野。这些令人激愤、心痛的噩梦般的场景描绘无疑带有强烈的反侵略性质,同时也在促使读者重新叩问、反思历史:为何已经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中国仍然会遭遇如此沉重的灾难?在小说中,聂华苓试图通过老少两代人的对话与分歧给出自己焦灼痛苦的思考与解释——现代中国仍未摆脱某些颓败腐坏的封建思想的桎梏,因而无法适应整个世界的现代性潮流。《桑青与桃红》中的流亡学生父亲,身为现代官员,举止西化,却有一妻六妾;在众人扶箕预测是否能脱离瞿塘峡的险滩困局时,老先生唤来的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以及诸葛亮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聂华苓借老先生之口明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分天下的困局:“重庆国民党,延安共产党,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咱们这船人到重庆去,也是因为忧国忧民,要为国家做点事情。现在咱们偏偏困在八阵图不远的滩上。”[4]48“老先生”这个角色,显然是作者特意安排的以知识分子视角来分析国运时局、反思故国历史,在他眼中,要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的一船人是被“困在历史里呀!白帝城,八阵图……这四面八方全是天下英雄奇才留下来的古迹呀!你们知道铁锁关吗?铁锁关有拦江锁七条,长两百多丈,历代帝王流寇就用那些铁索横断江口,锁住巴蜀。长江流了几千年了,这些东西还在这儿!咱们这个国家太老太老了!”[4]49聂华苓借人物之口传递出知识分子对古老中国传统和历史的思考喟叹——在理性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某些衰老陈腐的民族传统已成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阻碍,但情感上,他们又满怀对昔日辉煌历史的留恋。而青年一代的流亡学生则表现出疏离传统,渴求新生的心态:“现在不是陶醉在我们几千年历史的时候呀!我们要从这个滩上逃生呀!”[4]49藉此,聂华苓试图打破的是“老先生”们沉醉于家国历史的甜蜜岑寂。
桑青等人在瞿塘峡险滩上的困境,可视为国族讽寓的场景呈现,指向的是在战时救亡图存的整个中国民族面临真实“困境”。面对困境,聂华苓浓墨重彩,着意刻划了中国民间微小却坚韧的原始生命力,其中蕴藏着的乐观知命精神,这体现在一船人被困瞿塘峡险滩各自表现出的个性特征和集体表现的民间狂欢化生趣。值得注意的是,聂华苓塑造了怀抱婴儿寻夫的“桃花女”,这个来自中国民间的普通青年母亲形象。“桃花女”是童养媳,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她拥有一种温柔坚韧的母性特质,不仅能在渺茫的寻夫途中安娴地抚育婴孩——这个婴孩可以看作是民间抚育着的民族未来的希望。而且身处瞿塘峡的绝境中,“桃花女”并未如知识分子身份的“老先生”一般怀古叹今,也不像青年一代的流亡学生那样时时陷入恐慌焦躁之中,她以自己乐观豁达的心态影响着同一条船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桃花女听闻在重庆念书的丈夫在学校另结新欢,千里寻夫却有自己的主见:“见了面,他好,一辈子的夫妻!他不好,他走他的阳关大道,我过我的独木小桥!”[4]43“桃花女”的千里寻夫不再是千古以来悲凉无助的怨妇曲,她乐天达观的坚韧心性来自中国的民间和大地。后来,聂华苓曾在《浪子的悲歌》中谈到:“桃花女和船老板是生活在中国泥土上和大江上的人,他们那一股新鲜的原始生命力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维持他们在历史上一场场浩劫中活过来了。”[12]
四、结语
聂华苓漂泊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她的文化视域和创作空间必然更为宽广。综观聂华苓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中,三峡风物民俗与重庆的抗战书写已成为她笔下最为重要的两个题材。实际上,两个题材根本上相通的,无论是对三峡历险的描绘、三峡纤夫的刻画,还是战时重庆的灾难性书写,贯穿其中的都有坚韧、乐观的巴渝精神。抗战时期的巴渝生存体验让青年聂华苓收获了不屈向上的民族精神,这成为她终生的财富,使她获得了日后应对人生各种灾难、变故的精神基底。因此,聂华苓不断将自己抗战时期在巴渝地区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审美经验,透过对自身经历的多重书写,化私人记忆为小说技艺,重塑国族历史的存在与形式,也抚慰了自己在漂泊中失根、藉由书写不断寻根的游子之心。
参考文献:
[1]张德明.流浪的缪斯:20世纪流亡文学初探[J].外国文学评论,2002(2):53-61.
[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3]Buell,Laurence.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M].Cambridge:Harvard UP,2001.
[4]聂华苓.桑青与桃红[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5]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4.
[6]李恺玲,谌宗恕.聂华苓研究专集[M]//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7]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聂华苓.三生影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16.
[9]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0]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1]聂华苓.三生三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84.
[12]庄明萱,等.台湾作家创作谈[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