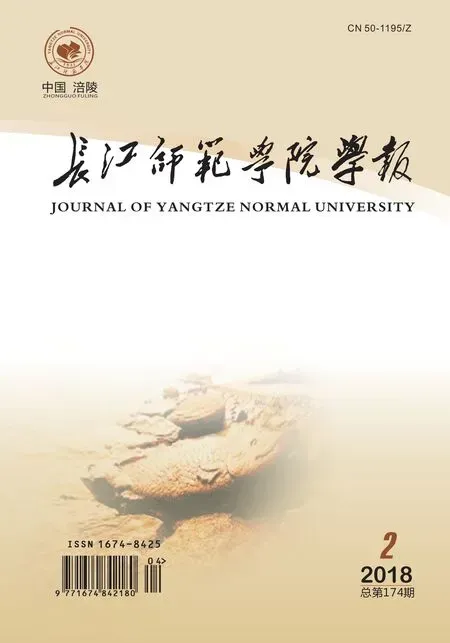孤独的映衬与共谋的反讽
——论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
2018-03-28陈志华
陈志华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作为20世纪一种特有的文学观念,不可靠叙述已经广泛渗透到整个文学活动当中。不独作家的创作观念、文本表征展示出不可靠叙述蔚为大观的局面,读者阅读也深受不可靠叙述观念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会对不可靠叙述产生浓厚的情趣,钟情于天真叙述、白痴叙述等不可靠叙述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可靠叙述所引发的独特的艺术效果,而反讽效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作为西方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反讽(irony)在我国有“讽刺”“滑稽”“讥讽”“暗讽”等多种译法,可见这一概念内涵之丰富,时下似乎已基本统译为“反讽”。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修辞方法,反讽自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在很长一段时期作为微观修辞的技巧被人们运用于文本修辞的狭义研究中,比如,新批评派就在修辞层面讨论反讽。随着对反讽理论探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反讽能形成复杂的审美意味和丰富的主题意蕴,决非简单的修辞技巧。反讽已经超越出了微观修辞技巧的层面,日益被当作一种评价作品的标准和美学尺度,人们正倾向于将它视为一种超技巧的范畴来看。米克在分析了F.施莱格尔、海涅等人的观点以后,指出:反讽“也许在于获得全面而和谐的见解,即在于标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或价值观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在于传达比直接陈述更广博、更丰富的意蕴,在于避免过分的简单化、过强的说教性,在于说明人们学会了以展示其潜在破坏性的对立面的方式,而获致某种见解的正确方法”[1]。这显然是在效果层面谈论反讽。
由于反讽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反讽形式的多样性、反讽发展的未定性,对反讽这一概念的界定,就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般将它理解为表里不一,尤指字面意思与深层真意的不一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反讽效果一般就表现为,作者将自己的态度或实施的真相暗含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述中,我们只能透过表象,领会其深在的含义,其情形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确实比直接宣白更有力量、更具意味。我们将从不可靠叙述的角度切入,分析此种文学观念所导引的叙述策略会引发怎样的反讽效果。
二、审美与伦理:不可靠叙述反讽效果的双重审视
“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我将这类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2]158布斯这一经典界定对不可靠叙述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不可靠叙述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对于其效果的探讨也便成为备受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那么不可靠叙述会生成何种独特的效果?作为“不可靠叙述”概念的提出者,布斯对其效果进行过较为充分的探讨,主要从审美效果和伦理效果两方面进行阐述。
审美效果,是指具体文本因其潜在的艺术价值、美学质素在阅读中所生成的效果。因而,探讨艺术效果,有别于对文本的道德、认知、教育等效果的分析,而是基于艺术本性,从审美的角度去考察效果。艺术的效果或效应,是实用批评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实用批评看来,作品的目的就在于对读者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审美的、道德的、情感的还是认知的。实用批评倾向于以是否成功地达到上述目的来判断作品的价值。我们暂不评述其整体理论构架的得失,就其强调艺术作品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之间的血肉联系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布斯接着以《喧哗与骚动》中“杰生的叙述”为例,指出,“尽管根据小说中叙述的事件,我们理解杰生邪恶的道德世界的思路,在许多方面已经清晰,但实质上,它的形成还在于我们自己与作者之间达成的隐蔽而带有嘲讽性质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形成并不需要作者任何直接介入性的提示、指引。不可靠叙述者富于幽默的、或不光彩的、或滑稽可笑的、或不正当的冲动等行为举止,将会使文本整体呈现作者寄寓其中的反讽意味。“当我们与错误从未被直接指出、很少令人同情的主人公进行交流时,也发现我们的反讽快感增强了。”[2]306正是在这种秘密的交流中,读者与作者所共享的价值规范与叙述者所秉持的价值规范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形成对于叙述者的反讽。相反,任何对于叙述者的评论将会大大降低文本的反讽意味。布斯也意识到,有缺陷的叙述者并非都是文本的反讽指向所在。布斯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样本,展示了不可靠叙述反讽效果的另一类型:通过有缺陷的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将讽刺的笔触伸向站在叙述者对立面的其他人物及相应的社会情境。对于“声称要自然而然地变邪恶”的叙述者哈克,作者“沉默地”表示着对他的美德的赞扬。哈克的不可靠叙述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其所处社会的罪恶,正是因为受了当时种族歧视思想的毒害,哈克才会把自己帮助黑奴吉姆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文本强烈的反讽意味由此生成。
作为不可靠叙述的命名者,布斯充分肯定了它在生发独特的艺术效果方面的出色表现,但不可靠叙述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让布斯忧心忡忡。不可靠叙述不仅造成叙事文本情节上的含混,蓄意混淆读者对小说基本真实的认识,而且使读者在阅读、接受文本时产生极大的困惑。相对可靠叙述清晰而确定的伦理表达,不可靠叙述文本中的伦理关系显得复杂而多样,含混而朦胧。不可靠叙述使得从作者、文本到读者的整个文学活动呈现出丰富的伦理交流场域。这种复杂而生动的伦理交流关系,丰富了文本的艺术效果和读者的审美感受,也对读者的伦理判断构成极大的挑战。因而,对于不可靠叙述伦理效果的考察就成为布斯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兴奋点。即便在对艺术效果的分析中,布斯也时常隐约提到,不可靠叙述者可能对读者产生的伦理观念上的误导。在“非人格化叙述的道德与技巧”一章中,布斯干脆把全部的重心都转向他极为关注的道德问题。“非人格化叙述已经引发了许多道德困难,以至于我们无法将道德问题视为与技巧无关的东西而束之高阁”,原因在于,“内心观察甚至可以为最邪恶的人物赢得同情”[2]378。而不可靠叙述恰是最能展现内心观察生动性的一种叙述方式,试想,当一位不可靠叙述者占据着话语权,不断向读者展示他内心世界的冲突、困惑时,读者如何能不受其影响?当这位不可靠叙述者又是一位懂得修辞艺术的自觉叙述者时,其感染力岂不更为强烈?尽管我们不能要求文学为生活提供道德指引,然而,当某些作品确实以不可靠叙述等出色的技巧,挑战了社会的道德底线,甚至可能引发类似的道德实践行为,我们还能无视叙事的道德安全问题吗?对于不可靠叙述反讽效果的探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入,我们主要依据上述对不可靠叙述审美与伦理这双重观照,以文本的反讽指向为划分标准,区分了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会情境的反讽和指向叙述者的反讽这两种反讽效果类型。
三、孤独的映衬者:人性探索与社会批判
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会情境的反讽,即隐含作者通过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对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和社会情境进行反讽。换句话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成为隐含作者对文本中人物和社会情境进行反讽的方式。如此,不可靠叙述者往往秉持着与所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成为文本世界中一个孤独的个体或孤独小群体中的一员,以不可靠叙述者坎坷的生活历程折射出其所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诸种问题,实现对于人性的深度探索和社会问题的严肃批判。从存在认知缺陷的人物视角进行叙述,是达成此类反讽效果最常用的手段。在具体文本实践中常常分为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直接采用儿童、白痴等有缺陷的人物进行叙述,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的叙述)、莫言的《檀香刑》(赵小甲的叙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海明威的《我的老爸》等等。这类叙述者往往能对事件的表象作出较为客观的描述,却无法形成正确的判断,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构成对成人、常人所处世界的强烈反讽。由于儿童单纯天真的本性,依靠他们的生命直觉认识世界,更能接近世界的原初形态,也就是说,不够世故的孩子承担叙述者的角色,反而能因童心未染尘俗从而对事件的报道更加可靠。隐含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儿童或者白痴的叙述,见出处于对立面的虚构世界的丑恶、荒诞,从而生发出强烈的反讽意味。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以白痴班吉为叙述者。之所以通过白痴讲述家族历史,那是因为“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3]。福克纳这一解释很好地表达了白痴叙述者班吉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胶着状态。“只知其然”表明班吉的叙述尽管由于意识流的手法,特别是多层次的闪回而显得极为混乱,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却能传递出可靠的叙事信息。“不能知其所以然”则见出了班吉在感知、评价轴上的不可靠性,无法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作出可靠而稳妥的反应。这样,白痴班吉就成为一面镜子,周围的人在他面前展现出或善或恶的人性本相,白痴眼中毫无意义的所见事物经过白痴眼光的聚焦与客观呈现,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空间画面与意义组合。凯蒂在《喧哗与骚动》中反复被提到,在杰生、昆丁的叙述中,凯蒂是一位充满欲望、自甘堕落的女性。那么,班吉眼中的凯蒂呢?班吉的智力缺陷使他不会产生任何修辞性的叙述行为,他只是凭着自身的感受,仔细地记录了凯蒂对他的关爱,也记录了以下场景:接吻之后用香皂洗嘴、查理面前她的兴奋、从婚礼上跑开,等等。杰生和昆丁的叙述,由于各自的原因,有意识地放大了凯蒂的缺点,忽略其性格中美好的一面。班吉的叙述无疑有效地颠覆了杰生、昆丁对凯蒂形象的过度歪曲,但同时又传达出凯蒂的堕落。尽管他无法对周围的事件形成正确的判断,然而,隐含作者正是借班吉的眼光,表达对以杰生、昆丁为代表的没落的康普生家族的反讽。更深一步看,康普生家族的败落实际上是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这样,隐含作者的反讽指向就扩大到了当时整个社会情境,既讽刺了南方旧制度的破败,也包含有对杰生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儿童视角运用的典型文本。叙述者少年哈克讲述了帮助黑奴吉姆逃亡的故事。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哈克叙述的不可靠性。哈克正是因为受了种族歧视的传统思想的毒害,才会觉得自己帮助一个黑奴逃脱他的主人,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后要下地狱的。哈克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混乱反映了美国当时种族歧视的深重影响,因而,文本的反讽意味指向国王和公爵等人物及文本所呈现的当时美国的社会情境。作者对哈克美德的赞扬,就是对哈克所处的社会情境的反讽,尤其是对于美国种族歧视制度的反讽和憎恶。
另一种是儿童、白痴等有缺陷的人物并不作为叙述者,而只是从他们的视角进行叙述,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等等。这类文本从儿童、白痴的眼光进行限知叙事,好比一面“镜子”,能客观反射事物的原貌和人物的外在行为,即能对事件作出较为可靠的报道。借助于有缺陷的认知视角,作家实现的是对这些有缺陷人物所处的虚构世界的客观冷峻的呈示,批判和反讽的意味也就隐匿在叙事之中。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中叙述者少年霍尔顿的叙述带着明显的孩子气,鲜明呈现出青春期少年成熟与幼稚混杂的心理特征,如:“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像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像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不对,可并不完全对。我压根儿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这段不可靠叙述突出的表现为他对自己成长的矛盾看法:他一会儿觉得自己的行为举止还像十二三岁,对于别人让他老成些的说法颇为恼火;一会儿,他又认为自己的举动显得成熟得多,进而埋怨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在小说的其他段落,当别人认为他的年龄小时,他居然一次一次扒拉出自己的白头发以证明自己的成熟,而此时却又说白头发从小就有,言下之意,白发与年龄的成长毫无关系。叙述的不可靠性就在少年霍尔顿颇显幼稚的叙述声音中清晰的呈现出来。整个文本充满着这种青春期少年所特有的叙述声音,真实地展现了处于人生转折点的少年成长的迷茫和彷徨,也体现出他对于社会上那些中产阶级之间种种无趣规矩的讨厌以及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厌恶。
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知道什么》描绘的是多层通奸的故事,叙述这一切的任务完全是通过孩子“梅西”的所见所闻来完成的。梅西既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同时对这一切又毫不理解。“如今她看得出妈妈这次婚姻很美满,她也总算有望开开心了——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惟一的心愿是巴望好事,有朝一日能尽情地玩耍嬉戏。”梅西观察得很准确,可靠地展现出她周围发生的事件。然而,以孩子的认知力,梅西显然无法对事件作出可靠的判断。实际上,梅西的母亲伊达只是在赶赴社交聚会途中顺便进来看看她。尽管大人们只顾寻欢作乐,把她禁闭在枯燥无味的学堂里,梅西对妈妈依然深信不疑,满怀希望期待着“有朝一日尽情玩耍嬉戏”。然而,读者对此并不抱幻想,深知孩子这小小的心愿是无法实现的。孩子的信赖与大人们的自私、虚伪形成鲜明对比,叙述的不可靠性恰恰表现出隐含作者对于伊达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强烈反讽。
四、遭讽的叙述者:作者与读者的共谋
指向叙述者的反讽是指文本的不可靠叙述体现出隐含作者对于叙述者的反讽。将叙述者作为反讽的对象是不可靠叙述中最为常见的反讽表现方式。从文学发展史看,反讽在可靠叙述文本中早已出现,比如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都是极富反讽意味的文本。可靠叙述文本中的反讽从来都是指向虚构世界中的人物或者社会情境,并不构成对叙述者的反讽。换言之,叙述者与作者(隐含作者)一样,只是反讽意味的发出者,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在传统的可靠叙述中,叙述者几乎都是作者理想化人格的具现,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基本是同一的,占据着美德、智慧或学识的制高点。这种叙述权威性的树立,使读者对于叙述者深信不疑,总是依据叙述者的认知、判断去感受、理解故事,阅读的结果往往是达成与叙述者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不可能成为反讽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故事中的人物才会成为反讽的对象。
在不可靠叙述文本中,叙述者不再拥有这种特权。相反,不可靠叙述者往往都是文本的反讽指向所在,比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杰生的偏执和残忍、亨利·詹姆斯《说谎者》中莱昂的虚伪等等。布斯从交流形式出发分析反讽效果。“反讽部分地总是一种既包容而又排斥的技巧,那些被包容在内的,又刚好具有理解反讽的必备知识的人,只能从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感受中获得小部分的快感。在我们参与其中的反讽中,叙述者自己就是嘲讽的对象。作者与读者背着叙述者秘密地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发现叙述者是有缺陷的。”[2]300也就是说,不可靠叙述者的缺陷使得读者与作者在共享与叙述者相异的价值规范时,形成文本的反讽效果。在此,尽管布斯没有进一步阐发,但他还是意识到了不可靠叙述反讽效果的独特之处:叙述者已无力承担反讽效果的发出者。叙述者的缺陷既可能是自身成为反讽指向的原因,也可能是读者藉此读解出对其他人物或社会情境反讽意味的路径。在可靠叙述中,叙述者所处的优越位置使其只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反讽的发出者,从来不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尽管不可靠叙述者未必都成为被反讽的对象(比如天真叙述中,反讽多是指向与儿童处于对立面的人物或社会情境),然而,不可靠叙述者显然已不再成为反讽的发出者。20世纪以来,许多作家不满于叙述者的权威性,不断消解其叙述的可靠性。作为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全知叙述”遭到了作家普遍的厌弃,作家放弃了说教者的角色,消失在作品中,也即昆德拉所说的作家放弃了“公共人”的角色。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述等各种限知叙述形式纷纷涌现。限知叙述往往是叙述者作为旁观者或者亲历者对于故事的讲述,里蒙·凯南曾将叙述者亲身卷入事件列为不可靠叙述的主要根源[4],叙述者的可靠性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质疑。而且,根据布斯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那些最缄默的叙述者,一旦把自己以‘我’来提及时……他也就被戏剧化了……在此类作品中,叙述者与创造他的隐含作者常常根本不同”[2]152。一般而言,限知叙述多为同故事叙述,往往加深了叙述者的戏剧化程度。戏剧化的叙述者往往和他所讲述的其他人物一样活灵活现,读者可以根据对其品质的判断来判定他所讲述的事是否可信。因此,无论采用何种叙述人称,叙述者的可靠性都越来越容易受到质疑。这些叙述者往往秉持与隐含作者截然相反的价值规范,从而被置于反讽的境地。既然是不可靠叙述文本,叙述话语的不一致必然会造成叙事信息的含混不清,文本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含混特质;由于叙述的不可靠,也必然会出现叙述者与作者(隐含作者)之间在事实/事件、知识/感知、价值/判断等轴线上的不一致,作者(隐含作者)对于叙述者的否定也经常带有善意的或恶意的、强的或弱的反讽意味。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加剧了文本的反讽意味。可靠叙述文本中的叙述者接近于作者(隐含作者)的趣味、判断、伦理观念,其叙述总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导向性,读者往往只要紧随叙述者就能获得对虚构世界的认知和判断。由于有叙述者的引导,尽管这种引导总是以间接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文本的反讽效果比较容易被读者所识别和领会。而在不可靠叙述文本中,作者(隐含作者)只能在叙述者身后与读者交流,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经常会干扰读者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这种无声的交流显然对读者更具挑战性。也就是说,不可靠叙述者对于读者推断力的要求,显然比可靠叙述者所要求的更为强烈。可见,这种基于不可靠叙述所产生的反讽效果显然更为复杂。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有助于作者含蓄有力地体现自己的修辞目的。当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越隐蔽,读者最终对于整个文本反讽意味的体会也会越强烈。
指向叙述者的反讽是指文本的不可靠叙述体现出隐含作者对于叙述者的反讽。将叙述者作为反讽的对象是不可靠叙述中最为常见的反讽表现方式。根据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展露程度,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指向叙述者的反讽类型:显在型反讽和隐在型反讽。
显在型反讽,一般指隐含作者直接传达出对于不可靠叙述者的反讽意味。这一反讽类型有着清晰的文本标识,读者很容易与隐含作者产生“共谋”关系,从而读解出对于叙述者的反讽意味。这类叙述者一般有以下特征:叙述者被赋予“偏执狂”“恶棍”“罪犯”等非常态型人格特征;叙述语调或激烈、偏执,或无知、愚昧;叙述内容清晰地展现出迥异于隐含作者和读者的价值取向。由此,读者一进入文本,就会自觉对其叙述可靠性产生警惕,体会出隐含作者对这类叙述者的反讽指向。《喧哗与骚动》中杰生的叙述就是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福克纳说过,“对我来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依我看,从我的想象里产生出来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恶的一个”[5]3。小昆丁是杰生的妹妹凯蒂寄养在母亲家中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和杰生的残酷让小昆丁得不到任何温情,由于小昆丁不服从杰生的命令,杰生居然拿出皮带抽她,老仆人迪尔西不畏惧杰生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影响,勇敢地保护小昆丁,杰生叙述如下:“她抱住了我的胳膊。这时,皮带让我抽出来了,我一使劲把她甩了开去。她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桌子上。她太老了,除了还能艰难地走动走动,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反正厨房里需要有个人把年轻人吃剩的东西消灭掉”[5]201。对于为康普生家族忠心耿耿服务了一生的迪尔西,杰生居然“一使劲把她甩了开去”。年迈的迪尔西成天为康普生家族劳作,他却说“除了还能艰难地走动走动,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杰生自私、残酷和阴冷的本性在这段叙述语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隐含作者在杰生的自我表白与辩解寄寓了强烈的反讽意味。显在型反讽多为不可靠的同故事叙述者。叙述者常常由于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错误而成为反讽对象。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伊恩·麦克尤万的《他们到了死了》、马丁·埃米斯的《金钱》、朱利安·巴恩斯德《好好商量》等文本都属于这一类型。
隐在型反讽,则是指隐含作者隐蔽地展示出对于不可靠叙述者的反讽意味。与显在型反讽的清晰、直白不同,隐在型反讽的辨识对于读者的文本理解能力要求更高,读者需要在细致的文本阅读中才能体会出来对这类叙述者的反讽意味。这类不可靠的同故事叙述者常具有以下共性:一般呈现出常态型人格特征,有的甚至从表面上表现出诚实、真挚、理性等优秀的个人品质;叙述语调通常比较理性、和缓;叙述内容体现出高超的修辞艺术,“超越了各种旁观者与叙述代言人之间的区别,是意识到自己是作家的自觉叙述者”[2]155,叙述态度真诚,甚至表现出自我忏悔的倾向,让读者稍不留意就为其叙述所迷惑,而认同其所传达的为隐含作者所否定的价值立场。亨利·詹姆斯的《阿斯彭文稿》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叙述者是故事的主人公,一位美国评论家,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为获得大诗人阿斯彭的文稿而费尽心机,最后却功败垂成的故事。与杰生不同,叙述者一直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具有绅士风度、非常文雅,对诗人阿斯彭充满敬意的追随者。表面上看来,如他所叙述的,“我一直尽可能亲切和蔼”,这位叙述者确实尽可能地展现出他的绅士风度。他对于阿斯彭老情人的慷慨大方、对于蒂娜示好,甚至带其出去游玩……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因其不可告人的企图而采取的手段:慷慨大方是为了接近文稿创造条件;对蒂娜示好是为了利用她的痴情得到文稿,甚至将自己不择手段获取文稿的行为美化为对于诗人阿斯彭的热爱所致,叙述者对于其卑劣意图的掩盖都昭然若揭。尽管叙述者一直占据着话语中心,不断为自己辩护,甚至,偶尔也会对自己利用蒂娜感情的行为进行反省,表现出一定的自审意识,“我有气无力地想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误,无意之中,但终究是令人遗憾地愚弄了人家的情感。然而,我并没给她任何理由——很明显,我并没有”[6],但获取文稿的狂热追求使叙述者的道德感发生偏差,从这段反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具有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的色彩,这种自我辩解的叙述行为贯穿文本始终,读解出作者对这位叙述者的反讽需要对整个文本叙述的不可靠性仔细加以甄别。
五、结语
隐在型反讽不仅包括难以辨识不可靠性的同故事叙述者,而且还包括全知叙述者。全知型叙述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叙述模式。全知叙述者如上帝般盘踞在文本上空,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进行叙述,既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将故事娓娓道来,又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心理,传达人物丰富的情感体验。对于文本的这种全面掌控能力很容易树立全知叙述者的权威性。全知叙述者在文本中有两种表现方式:戏剧化和非戏剧化。非戏剧化是指全知叙述者不诉诸于任何人称讲述故事,而戏剧化则是指全知叙述者通过“我”或“我们”使自身在文本中显形,直接对故事置评。一般而言,无论是否被戏剧化,全知型叙述者都是比较可靠的。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等都属于可靠叙述之列。而在有些文本中,无论是否被戏剧化,全知叙述者也会出现不可靠的情况,而且其不可靠性往往比较隐蔽。在全知叙述者将自己或多或少地“个性化”或人物化时,全知叙述者的可靠性就会削弱。也就是说,叙述者在讽刺、挖苦人物的时候,自己也成为了隐含作者的反讽对象,从而形成了双重反讽:叙述者对于人物的反讽,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反讽。
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主要表现为指向叙述者的反讽和指向文本中人物和社会情境的反讽。这两种反讽效果在文本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实际上,很多文本都呈现出反讽双重指向性。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效果强化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丰富了反讽的审美效果,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对于文本积极、主动的思考,呼唤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
参考文献:
[1]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35.
[2]BOOTH W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3]福克纳.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谈创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62.
[4]SHLOMITH R K.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M].Florence,KY,USA:Routledge,1983:100.
[5]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译本序[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M].主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