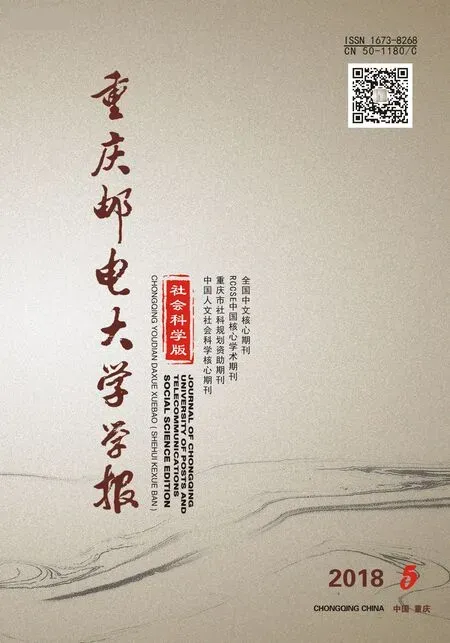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2018-03-23张荣杰
张荣杰
(内蒙古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孤悬关外,忍辱负重,承担着关内外邮政汇兑、邮件传递和中外邮件运转之重任。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相关成果较多,兹不赘述。学界对事变后东北邮政亦有一些相关研究,如杨斌收集整理了九一八事变后邮政总局处理东北邮务经过的一些史料[1];丁三青论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2];张荣杰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工入关经过作了初步述论[3];《中国邮政》曾对东北沦陷时期邮政撤退作过简要介绍[4];孙玉玲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劫夺东北邮电权益进行了剖析[5]。此外,杨天石[6]、左双文[7]、段智峰[8]以及台湾地区一些学者如沈云龙[9]、刘承汉[10]、张翊[11]等均在其研究中涉及到了事变后东北的通邮问题。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主要侧重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的封锁与通邮经过的描述上,却较少涉及国民政府对事变后中华邮政的处置与应对。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应对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被迫封邮后日伪对东北邮政的侵犯
东北邮区局所众多,业务发达,还承担着欧亚大陆国际邮件转运的重任,有中华邮政生命线之称。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并未劫夺东北邮政。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邮政不仅能增强民众交流,还能活跃各地间经贸往来;二是日伪尚未做好劫收东北邮政的准备。因此,中华邮政得以在日军铁蹄下运行达十个月之久。虽如此,日伪却不断侵犯邮政业务,挤压中华邮政生存空间,通过严密监控邮政、迫害邮工、侵占邮产、干扰邮务、阻断邮路、威逼利诱邮政员工等粗暴手段,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东北邮权。日伪对东北邮政的侵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取邮务情报
为攫夺东北邮务,日伪设法窃取东北邮务运行情报,甚至凭借武力强行夺取邮务情报。例如,1931年9月20日,日本关东军紫芝大尉率卫兵闯入辽宁邮务局,抢夺邮务长巴立地的邮务密码本;同日,日本驻营口领事馆职员岩赖,到营口邮局盘问邮票及票款用途。四平街日本客邮局长也到当地邮局调查中华邮政运营状况。此外,日军还深入公主岭、兆南、凤城、昌八等地调查邮务运行状况[12]392。1932年5月6日,日本宪兵闯入安东邮局,抢夺该局邮用英文密电码[12]394。邮局部分日籍邮员背叛中华邮政,名为雇员,实为间谍,伺机窃取邮务情报,如辽宁邮局日籍邮员田中勘吾利用职务便利,窃取邮务情报[10]294。日方凭借武力抢夺邮务密码,强行调查邮务,实为刺探邮政情报,为其夺取东北邮政做准备。
(二)利诱胁迫邮政员工
邮政无物,唯人为实。邮务运行全赖人力。为使邮局员工留局为其效力,日伪对高级雇员利诱,而对中下级邮工则采取恐吓、胁迫、殴打等手段,强迫邮工就范。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授权辽宁邮局局长巴立地维持东北邮务,行使邮务交涉权[1]。日籍邮员田中勘吾趁机利诱巴立地为日伪服务,并承诺用现金支付其在华退休金[12]393。巴氏不为利诱,日伪随即改变策略,威胁恐吓巴立地。宪兵以巴立地不遵守停送新闻纸命令为由,将其拘押14天[12]394-396。沈阳日本客邮局长贿赂沈阳南满车站邮务支局长马德荫,诱其将邮务运行情况秘告日方[12]393。此外,日本宪兵宣称逮捕副邮务长刘耀庭及其他高级邮员,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强行搜查安东邮局长住宅[13]。日伪恐吓威胁中下级员工,手段极其粗暴。沈阳被占后,多名邮员惨遭拘押殴打,甚至被迫填写愿为伪满洲国“服务表”[14]。日伪企图采取利诱、威胁、恐吓等手段胁迫员工留局,以充实“伪满”邮政班底。
(三)以邮检为由控制邮务
巴立地以其意大利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竭力维持东北邮务正常运行[15],但日伪却以邮检为由,肆意扣留拆毁邮件,仅长春、吉林两邮区,五个月内被扣邮件高达九千余件(见表1)。通信自由不受非法检查是国际社会普遍准则。经巴立地与日伪多次磋商,先后达成《检查邮件临时办事规则》和《检查邮件规则》。邮件检查规则制定后,虽不能确保邮件安全无虞,但总算有规可循,被扣邮件有所减少。需要指出的是,日伪以法规形式加强了邮务控制。通过强行向邮局分派监察员和视察员,以管理和监督邮务[14]。至此,独立运行的中华邮政体系被打破,日伪逐步管控了东北邮务。
资料来源:《东北邮权问题》,《全国邮务职工总会半月刊》1932年第2期
(四)封锁邮路,孤立东北邮政
日伪凭借武力封堵东北邮路,割裂东北邮政与关内的联系,孤立东北邮政。对孤悬关外的东北邮政而言,此举是日伪对东北邮政的致命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日军侵占锦州后,禁止普通邮件和挂号信出入关口,仅允许快递信件出入。陆路被封后,关内寄往东北的邮件,仅能靠海路运往大连,再交由日本客邮局转寄。大连日本客邮局则成了关内外邮件赖以维继的枢纽站。不久,大连日本客邮局封锁海路,除国际邮件和快递邮件外,不再转发其他邮件。陆路和海路被日伪封锁后,北平邮局试图用汽车将邮件运往承德,再向朝阳和开鲁转发。因路途不靖,无法保证邮件安全,只得作罢。河北邮政局被迫将挂号信件装入快递邮袋,以图早日转发[16]。后经上海邮务长乍配林多次斡旋,“伪满交通总局”才勉强准许每日发轻班邮件100袋,但须由大连汽船株式会社承运[17]。重班邮件(书籍及印刷品)和包裹因日方阻扰依然无法运递[18]。日伪封锁东北邮路,扼住了关内外通邮的咽喉,以此迫使中华邮政放弃东北邮务。
(五)谋划夺取东北邮务
日伪对东北邮政觊觎已久,之所以未敢贸然攫夺,是因为其未做好准备。日伪一方面试图利用武力逐步控制邮务;另一方面,着手罗织邮务人员,拼凑伪满邮政班底,为伺机全面攫取东北邮务做准备。1932年4月,日伪派员接受吉黑和辽宁邮务遭拒[19],日伪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加紧劫夺东北邮务步伐。同年6月,日本递信省派监察官藤原保明充当“伪满”邮务总办,同时从日本递信省选派20余名管理人员奔赴东北,分掌伪满通信机关。此外,日伪搜罗往昔东北邮员,以充实“伪满”邮务班底。人事安排逐渐到位后,日伪筹划在东京印制邮票,为攫夺邮务做最后准备。为此,交通次长陈孚木和邮政总长黄乃枢紧急商议,由外交部对日交涉,交通部筹划抵制办法[20]。正当中方对日伪交涉之际,日伪突然宣布自1932年7月1日起东北邮政改用大同年号,张贴日版邮票。此宣言无异于下了“逐客令”。中华邮政封锁东北邮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邮政封锁在国际上是一种制裁或报复手段,用以孤立敌对国家和地区,交通部和邮政总局遂商定封锁东北邮政[21]。1932年6月29日,国民政府致电万国邮联,必要时将封锁“东北各邮局”[22]。与此同时,日伪也加速了劫夺东北邮务进程。1932年7月10日,伪满邮政司长藤原称发行邮票为既定政策,不可更改。藤原以挑衅的口吻声称,接管东北邮务后发还邮局全部现金及未用邮票,并对邮局动产与不动产开具收据[9]。伪满交通部长明令巴立地赴长春商议接管邮政,巴立地严词拒绝,辞职归国以示抗议。同年7月15日,日伪索要吉黑邮局员工名单,遭拒后又以考察公务为由刺探邮务。东北邮务紧张局势,深受国际社会关注。日伪宣称中华邮政已与伪满洲国达成妥协,混淆国际视听[14]。中华邮政在舆论上陷于被动,已无退路可言。
在此情形下,邮政总局积极准备封邮,下令东北各邮局将所存邮票、邮政储金档案、重要文件、贵重物品等运往天津。1932年7月23日,交通部致电国际邮联,暂停东北邮务,所有寄往欧美邮件改由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海路运递,敦请各会员国寄往中国邮件亦同样办理,并下令全国各地邮局自7月24日起,停止收寄来自东三省信件、汇票、包裹等业务[23]。东北封邮是在日伪紧逼、邮权无法维护情况下,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与其说是主动封邮,不如说是为保全颜面而被迫封邮。
二、封邮下的“通邮”
东北封邮后,关内外民众通邮无法遏制,关内外邮路“藕断丝连”,仍有各种渠道保持联络。国际邮路以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维持“通邮”。在封邮令下,关内外通邮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势。
(一)伪满区域照常通邮
在东北日伪占领区,因租借地和日本“客邮”的存在,各地封邮政策不尽相同,封邮区域也不断调整。1932年7月25日,邮政总局变更进出口邮件政策。其中,进口邮件除由南满铁路区域寄发者外,由大连或其他邮路转来,如有以下情形,一律科罚欠资:贴伪满洲国邮票;贴日本普通邮票;贴中华民国邮票,盖伪满邮戳。对于来自南满铁路的邮件,除发自关东租借地不计外,如贴有日本邮票均照常征收一倍国内资费。对于贴有“未曾涂销”之中华邮票之邮件,或发自关东租借地贴有日本邮票之邮件,均按“付足邮资之邮件办理”[24]。对于出口邮件,则按如下规定办理:(1)运赴俄国及亚洲邮件,改由海参崴海轮邮递;(2)寄往朝鲜邮件改由大连由日本邮便局转递;(3)寄往欧洲邮件,由苏伊士运河转递[25]。可见,虽东北封邮处于半封锁状态,但南满铁路区域邮件不在封锁之列,其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1932年8月2日,邮政总局再次变更封锁范围,决定对南满铁路区域开放,照常收寄,该线路经由大连到南满后,再由当地日本邮便局所投递[26]。但对于南满铁路区域发来的邮件,如贴有日本邮票,虽经大连邮局用日戳销毁,仍以邮资未付作“科罚欠资”处理[27]。而对于外国寄来转往东三省各处的邮件,不论平信、挂号、保险,均加“service suspended to sender”戳记后,退回原寄局处理[28]。同年8月6日,邮政总局局长黄乃枢电令河北邮区邮务长科登称山海关邮局停收东三省邮件。同年8月9日,邮政总局再次下令,山海关局只接收由邮联国成员发往中国各地邮局的邮袋,但接收时不出具任何收据[29]。邮务总局此举旨在对南满铁路区域日本“客邮”的遏制,表示对“伪满”不予承认,不发生任何实质性接触。
然而,封邮政策在日军武力面前无异于一纸空文。例如,山海关邮局拒绝接收伪满邮袋,引发日伪不满。1932年8月10日,山海关邮局局长遭日本宪兵队拘禁殴打,被迫签署如下条件:(1)接收邮联国发来邮件(给收据);(2)接收日本宪兵队、守备队及居留民邮件(即满洲国之邮件);(3)接收山海关当地邮件。河北邮区邮务长科登致函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抗议日军破坏邮政的暴行,要求日军不得干涉邮务[30]。日军对此抗议置之不理,仍强迫山海关局接受伪满邮件。慑于日军武力,河北邮务长被迫接受,将伪满邮件暂存邮局而不投递转递[31]。可见,在日伪武力胁迫下,伪满寄往关内的邮件照旧运递,东北封邮也逐渐流于空谈。
(二)国民政府控制区绕道通邮
东北封邮后,国民政府仍控制部分区域,为维持该地区与关内通邮,中华邮政总局与苏联邮局商订大黑河邮局与海兰泡交换邮件办法,取道苏联海参崴邮局中转。国府管辖的大黑河、瑷珲、奇克特、乌云、金山镇、漠河六个邮局,除汇票及包裹业务停办外,其他业务照办。上述邮局除寄往黑龙江沿岸及苏联外,其余的由大黑河邮局直封上海,邮袋标明“取道海参崴交由该处直封上海轮船带运”。大黑河邮局升为管理局[32]。凡关内寄往各该局邮件,均先寄往上海邮局,再由上海邮局汇封总袋后寄往大黑河,邮袋标明“大黑河中华邮局收由海参崴及海兰泡转”[33]。对于仍属国府管辖的吉林绥芬河、东宁、抚远等邮局,依据中苏邮政当局签署的绥芬河邮件互换办法进行。绥芬河邮局将邮件直封上海邮局,邮袋标明“取道海参崴交由该处直封上海轮船带运”,其他各地寄往绥芬河等处邮件,均先寄上海,由上海邮局汇封总袋,标明“经由海参崴寄交绥芬河中华邮局”。绥芬河邮局升为吉林东部各局管理处,供给邮票[34]。萝北仍属国府管辖,寄往萝北邮件正常收寄,与寄往黑龙江沿岸邮件一同办理[35]。为便于管理,沿黑龙江七处邮局划归河北区管辖,绥芬河区域十八处邮局拨归上海管辖[36]。后因战事不利,1932年12月20日,黑龙江沿岸大黑河等八处邮局暂停业务[37],次年1月9日,绥芬河等邮局停止收寄邮件[38]。至此,东北邮区沦陷,大小局所悉数被日伪所侵夺。
(三)关内日侨自办邮务
东北封邮后,关内日侨唯恐与关外断邮,擅自设立邮局,公然对抗国民政府。1932年7月25日,上海日侨商联会委员长与日本驻上海领事商议筹设临时邮局以对抗封邮令,决定自8月1日起,开办临时邮局,由大连汽船会社和日本邮船上海分公司承运邮件。日侨筹设临时邮局破坏中国邮权,交通部严令上海邮局调查取证,以便转请外交部向日方抗议[39]。1932年7月26日,大连汽船社在上海黄浦码头设邮箱,派员收寄东北和西伯利亚邮件[40]。随着寄往东北邮件的增多,日侨商议由民团行政委员会、各路商联会合组邮政委员会管理临时邮局[41]。东北寄沪邮件,由日侨小学童子军递送[42]。另外,青岛日侨也擅设邮局,对抗东北封邮[43];平津日侨亦设置临时邮局,由日方带往东北[44]。对于平、津、沪、青等地日侨违法设立邮递,侵犯邮权的粗暴行径,外交部多次抗议[45]。1934年,日侨在平津设立国际观光局以走私东北邮件,北平每日向天津偷运东北邮件700余件,再由日本商船运往大连[46]。虽经中方严正交涉不再公开收寄,但国际观光局仍暗中收递日侨邮件[47]。上述事件表明,各地日侨走私邮件屡禁不绝,中华邮政应对各地邮件走私乏力,这显现出日方对中国政府的无视。
(四)欧美邮件“借道”通行
东北邮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便捷通道。封邮后,寻觅通往欧美的便捷邮路成为交通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欧美邮件改经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海路递送后,较原路多耗时八九天。为缩短时间,邮政总局与法属西贡至马赛间航空公司商议,运欧邮件经由上海运至海防,再由火车运至西贡,用飞机载至马赛,再转达欧洲各国[48]。该线路虽耗时较海路短,但因多次运转,故支出也有所增加。不少客户追求快捷,仍将邮件向日方投递,走西伯利亚邮路。交通部长朱家骅希望开通西北航线,由飞机从上海运往塔城,再由火车运往欧洲各国。交通部为开辟欧洲邮路所作努力均不理想,以至于国际邮件走私禁而不绝。在沪、汉、青、津等地,走私者以极低价格收揽寄欧邮件,至大连集中后,由日伪邮局经南满铁路转运至欧洲[49]。可见,追求快捷是国际客户违抗封邮政策、依赖走私的重要原因。
欧洲寄华邮件同样深受影响。旅居东北的英法侨民与关内通邮深感不便,英法等国希望能尽快妥善解决通邮不便问题[50]。事实上,欧美各国出于便捷考虑,来往邮件仍由“伪满洲国”运递。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最早破坏封邮政策,借助“伪满”邮路运输邮件。日伪趁机要求英国缴付“万国邮政公约所规定之转递资费”,诱使英国承认其地位。经国联顾问委员会商议,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前提下,国联通过了国际邮件经过“伪满洲国”的办法,以便各国与“伪满洲国”发生邮务关系时做必要的技术处理[51]。此后,欧美邮件便可顺理成章地“借道”运递。
(五)关内外民众通邮
封邮政策对关外寄往关内邮件的影响较小。伪满洲国成立后,关外邮件交由日本设立的“客邮”转递[52]。据《华盛顿条约》规定,大连及南满铁道附属区日本客邮照常寄递[53]。始料未及的是,南满铁道区域的日本客邮,竟趁封邮之际大肆扩充邮件收揽区域,交通部只得变更封邮区域,恢复南满铁路附属地邮务以示抵抗[54]。南满铁路区以外寄往关内邮件亦有两种方式变通:一是用两个信皮封装,内皮写明收信人地址,外皮写旅大租借地或大连熟悉人地址,先贴“满洲国”邮票寄出,内皮再贴日本邮票寄出关外。二是由日本观光局或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转寄,外皮贴日本邮票,书写“寄交大连日本邮便局”或其他日本客邮局所,再由日本客邮转寄。至于外国邮件,亦由日本邮局代为转寄,所有关外汇兑业务,同样由日本邮局受理,关内寄往关外的信件也如此。东北封邮不仅造成了民众通邮手续繁琐和负担加重的后果,而且徒给日本邮局增加收入。
(六)邮件走私屡禁不止
封邮后,邮件走私难以遏制。交通部下令严防邮件走私,并敦请海关等部门协助[55],但仍防不胜防。例如,北平邮局发现,走私者以东三省同乡名义将寄回原籍信件装入大信袋运往山海关转寄出关[56];上海俄文报纸宣称可代寄“伪满洲国”信件;在海关查获案件中,有俄人私带邮件180件的记录[57],也有走私者将邮件通过日本轮船运递“伪满洲国”[58]。关内外走私邮件报道不绝于耳,国际邮件走私亦层出不穷。上海外侨协会致电万国邮联,要求恢复西伯利亚邮路,甚至私下鼓动恢复“客邮”。各国侨民为邮件便捷起见,多私运至大连或日本转寄,对交通部更迭邮路通告置之不理。而各国对于贴用伪满邮票之邮件,亦接受递送。由此来看,伪满与欧洲各国通邮,反较关内便捷。香港邮局刊登“取道西伯利亚邮件仍可寄递”公告,不言而喻,仍由日本邮局居间转递。而欧洲各国寄华邮件,因遵循万国邮联所规定之“选用便捷路线之权”,多数仍经西伯利亚邮路[10]353。可见,东北封邮令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欧洲各国看来,更是一纸空文。
三、汇通转递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和平沈铁路的通车,关内外邮路已到了不通自通的地步。封邮不仅未达到孤立“伪满”的效果,而且反使自己受限、百姓受累,更未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封邮政策对政府而言犹如鸡肋,关内外通邮已是时间问题,正如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所言:“邮政问题,迟早终须谈及。”[9]因各方歧见,1934年11月7日,国防会议最终议决,以不承认“伪满”为前提,由中方商人设置商办通信机关,交换邮件及业务往来文件。国民政府与日方历时4个月的艰难谈判,最终达成通邮备忘录[注]该协议只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涉及政治,不签名用印,以备忘录形式供以后参考。(参见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1934年12月14日,邮政总局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关于关内与关外通邮办法的记录》《关内外通邮办法谅解事项的记录》《处理出进山海关、古北口邮政汇兑暂行办法》[注]具体条款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558页)。不过,因遵守“不成文规定”,双方均未签字用印,中方在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下,决定由民间机构承担关内外通邮职责。
(一)汇通转递局的设置
1934年12月20日,退休邮员黄子固向邮政总局呈文:“愿与邮局订立合同,在山海关和古北口设置转递机关,承转关内外信件、包裹、汇款。”黄子固称,此举可使关内外同胞“时同消息”,又与“伪满无直接关系”,与“政府大计亦无抵触”的“两全之策”[59]。可以说,汇通转递局的设立,既承担了关内外通邮之重责,又避免了国民政府与伪满直接接触,保全了国民政府的颜面。1935年1月1日,黄子固与河北邮务长签订合同,由汇通转递局承转进出山海关及古北口的邮件、包裹、汇票,受河北邮政管理局指挥监督[60]。
作为自负盈亏的商办机构,汇通转递局办公经费除私人垫资外,还从邮汇中按百抽一,充作办公费,另收取邮件转送佣金。汇通转递局与邮政管理局签署合同时规定,如有盈亏,与邮务管理局方面无关[61]。为保证汇通转递局正常运转,免于赔累,转递局雇员的薪资、房租、电费以及其他办公经费均由天津邮局报销。如遇汇兑繁忙,可临时雇人或向天津邮局借用人员,费用实报实销。此外,转递局所需家具及办公用品,亦由天津邮局提供[60]。不难看出,汇通转递局在人员薪资、办公经费、办公用品等方面无不依赖天津邮局,受其指挥监督;虽称民间性质,但难掩其浓厚的官办色彩。
(二)汇通转递业务的开办
1935年1月10日,汇通转递局正式运行。寄往东北的平信、挂号、快递邮件(保险邮件、代收货价之挂号邮件、平快及双明信片等除外),以及寄往欧美取道西伯利亚的邮件均可收寄。1935年2月1日起,开办东北与关内包裹(保险包裹除外)和汇兑业务。汇通转递业务以中方不承认“伪满”为前提,运行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1.邮件所用邮章,重要地名用英文,小地名用中文,日期用公历。不准用日伪地名,如“满洲国”“满洲”“新京”等字样,否则退还原寄件人。
2.寄往东北邮件,邮资照旧;寄往欧美,取道西伯利亚的邮件,邮资同样照旧收取。南满铁道沿线及其附属地邮件,由日本“客邮”代收,须贴用中国邮票方能寄往关内,伪满洲国邮票及特种邮票不能适用[62]。南满铁道附属地以外邮件,如寄往关内须使用特种邮票;如贴用其他邮票则无效,由转递机关负责赔偿,不再向收信人征收欠资。
3.因业务关系,往来文书均须经交换局交转答复。除交换局外,不得与关外邮局往来文书[63]。
关于汇兑业务,双方汇款月底结算,互不发生关系,由汇通转递局负责办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伪满洲国“货币价低于我方钞洋”,平津邮局与汇通转递局商议,凡收到关外汇款后,以转递局加盖邮戳日期为凭,按市折价,其相差数目“由汇通转递局与伪满洲国邮局清算,或按票额作实”[64]。因而在制定折合率时,需要根据市场汇率变化,予以增减,以免有“亏蚀之虞”[65]。
(三)汇通转递局的命运
1935年,汇通转递局开通业务当天,寄往东北邮件15 800余件,入关邮件26 000余件;次日,出关邮件37 500余件,入关26 300余件;第三日,出关37 400余件,入关21 000余件[66]。细微的邮件运转量与昔日中华邮政最大邮区的地位极不相称。由此不难发现,“地下邮路”分流了巨量邮件,导致汇通转递局业务不温不火,并未出现井喷之势。
汇通转递局的设置,虽表面上在执行封锁邮政政策,但实际上意味着国民政府对封锁东北邮政的取消。东北“通邮”被斥为汪精卫与黄郛的卖国行为,山海关汇通转递局被爱国志士投掷炸弹,所幸无人员伤亡[67]。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1938年8月15日,伪邮政总局在北京成立。至此,东北及华北沦陷区皆被日伪控制,汇通转递局已无存在必要。1941年8月21日,处于夹缝中的汇通转递局结束历史使命[68]。
四、从封邮到通邮的原因
(一)日军武力胁迫
长城抗战最终以中方妥协签署《塘沽协定》而暂告结束,中日双方就停战善后处理达成一致,但关内外交易、交通、通信等遗留问题仍须由双方谈判解决。1934年6月,平沈铁路通车方案公布,日军进而提出通邮谈判。其实通邮仅为简单技术问题,日军的真实目的是诱使承认伪满洲国地位。从当时局势来看,日军威逼平津,通邮谈判为形势所迫。而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为方针,避免与日军冲突[7]。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致电黄郛与何应钦,提出谈判底线,“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签字,不换文为最要”。而坐镇北平、身处险境的黄郛则主张利用国联通过该原则为出发点,只求邮票上无“满洲国”三字,其余不妨让步。因其担心通邮不能妥善解决,则此后北方多事,更无法应付[11]411。交通部长朱家骅致电谈判代表:“国势以政府之安定为救国之唯一要图。”[10]332可见,国民政府与日方举行通邮谈判,仍秉承庐山会议精神,息事宁人,暂维和平,避免军事冲突。由此看来,通邮谈判受日军武力胁迫,绝非出于邮政业务需要[10]310,该观点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二)日本“客邮”异常发达
对东北封邮,意在孤立伪满,不料事与愿违,反而造成日本在东北“客邮”的异常繁荣。日俄战争时,日本趁机在南满铁道附属地设置邮便局所,邮政业务日渐发达。华盛顿会议后,因日本百般阻扰,其在南满铁路区域设置的“客邮”暂定维持现状,邮务正常运转[69]。封邮后,东北寄往关内的邮件,日本邮局照收后再转送大连,由大连转送到关内,再由中国邮局正常投递。据统计,1935年,满铁附属地日本邮局所接受及投递邮件各约为13 000万件,其数量接近当时伪满全境邮局处理邮件数量[70]。封邮后,日本在东北设置的“客邮”便成为民众所依赖的邮政机关,这刺激了日本“客邮”业务量的大幅增长。日本在东北的“客邮”不仅增加了邮便局所,而且大幅扩张邮路,使得业务量暴涨。
据调查,当时仅大连日本邮便局,每天收寄信件不下2万封,以每封信收取3分邮票计,每日邮票额达600元以上。日本在华“客邮”除东北外,遍及十余省,大小邮便局所共达187处,各类信箱、信柜、信筒总计344个[71]。若将其他各地日本邮便居所业务合计在内,国民政府仅邮资损失一项,不在少数。
(三)中华邮政巨额损失
东北封邮导致中华邮政出现亏损。封邮前,东三省每年寄往各省邮件约7 800万件,各省寄往东北的邮件也大致相等[72]。就邮政经济而言,东北邮政为中华邮政最大邮区,东北邮务局所共有2 685处,占全国1/16,邮路85 200余里,占全国1/10,邮政员工计3 600余人,占全国1/12,产业共值2 325 000余元,占全国1/8,有“中华邮政之生命线”之称[73]。关外每年向内地汇款达1 500万元左右,封邮后,汇款多经中、交等银行代汇,仅贴水每年损失就达50多万元[74]。东北邮政业务,每年平均收入约为440万元,扣除东北3 200余名邮政员工薪资外,尚有240万收入。此外,还有3 000余名东北邮工需要入关安置[75]。据交通部统计,东北邮政停办后,政府每年约损失440万元[76]。邮政总局局长黄乃枢苦于无法弥补巨额损失,曾四次递交辞呈[77]。
(四)封邮失效
封邮之前,邮界资深人员就曾质疑封邮效果,认为封邮很难收效。国民政府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最终酿成骑虎难下之势。如巴立地曾致函邮政总局,预言“封邮难收实效,且亦不易获得各国之合作”,建议“暂维现状,以待政治变化”。国民政府并未采纳,反而怀疑巴氏受日伪诱惑[注]国民政府并未采纳,反而怀疑巴氏受日伪诱惑。交通部致电邮政总局:“亟应由贵局发电该邮务长,唤起主义,免堕奸谋”。(参见张翊:《中华邮政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398页)。外交部顾问赛道亦诘问外交部长,政府对于东北并未有任何封锁之举,何以独有邮政封锁?且此举并不伤及日本,反使应与友好之人民受其害[11]398。果不出所料,东北封邮不仅无效,而且反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国民政府采取的“封邮”政策,显然未能顾及关内外民众的通邮需求。封邮试图切断关内外民众的一切联系,而日伪却利用各种方式保持关内外通邮。在华北及各地的东北人,或因思乡心切,或需汇款接济家人等,不得不将信件等交由日方邮寄。东北邮政封锁后不久,国民政府便将南满铁道区域开放,无形中使东北近半邮务放开,致使其封锁效果大打折扣。无怪乎时人批评东北封邮,“效率几等于零”[78]。1934年,长城抗战结束,关内外已“暂行通邮”,中日双方均在古北口设立邮局,邮件到古北口后,可相互转递[79]。所以,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封锁东北邮政,并未取得真正效果。1934年7月,平沈路通车后,邮政列车传递邮件,关内外邮政已处于“似通非通之畸形状态中”,据估算,每日到山海关邮件约3万件,东北邮政已到“不通自通”的地步[80]。
1934年5月18日,国联开会讨论“邮件通过满洲国”问题,议决通过“凡邮联会员国与东北暂通邮件之往来”方案。根据方案,各会员国与“满洲国”邮政机关发生关系时,仅视为维持邮政技术而发生的关系,绝非国与国之关系,亦不适用于世界邮政公约[81]。此后,欧美邮件便名正言顺地借道“伪满”,不用再绕道。该项决议得到了国联各会员国的普遍支持[82],国民政府幻想通过东北封邮孤立伪满,不料却遭到国际社会的无情抛弃。
五、结 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忍辱负重竭力维持邮务,深受外界好评,英国总领事表示“应向邮局脱帽致敬”[11]350。面对日伪逼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示对“伪满洲国”强行夺取东北邮权的报复,力图在国际上孤立伪满。可以说,封邮是在内外交迫、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民众要求对日绝交抵抗、国联干涉无效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被迫应对方针。封邮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众要求,是对以往不抵抗政策的否定。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封锁东北邮政以博得国际社会同情,但却事与愿违,各邮联会员国出于自身利益,毫不顾及国民政府封邮政策,纷纷“借道”伪满。
封邮无效,被巴立地言中。时人对封锁东北邮政的批评,讥之为“掩耳盗铃”[83]。封邮未能在国际上孤立伪满,反而让伪满与国际邮联会员国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邮件的来往比关内还便捷。从邮政经济上看,封邮使得中华邮政收入锐减,负担加重,出现亏损;从关内外联系来看,封邮造成关内外通讯不便,令民众苦不堪言。封邮还造成邮件走私屡禁不止的后果,给邮政管理带来极大困难。上述难题均是由国民政府封邮令造成的,这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国民政府的封邮令,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无疑是对封邮政策的巨大嘲讽。
封邮未能孤立伪满,反而隔离了关内外民众。维持关内外民众通邮,是国民政府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国民政府希望借国联讨论国际邮件转运之机,一并解决关内外通邮问题;希望通邮令出自国联,而不是中日谈判,如此则保全国民政府颜面。不料,国民政府再次失算,再度被弃,最终在日军胁迫下,历经艰难谈判,达成通邮协议。就谈判结果而言,国民政府坚守不承认伪满底线,目的基本达到,而日军借通邮以谋取“满洲国”合法化,机关算尽,但仍未得逞。这样,国民政府既能在国际上保全颜面,又能在国内获得民众支持,维护政府威信。从国民政府封邮与通邮的痛苦抉择来看,均是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封邮与通邮反映了国民政府进退维谷、军事上不能争斗、外交上不能屈服的窘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