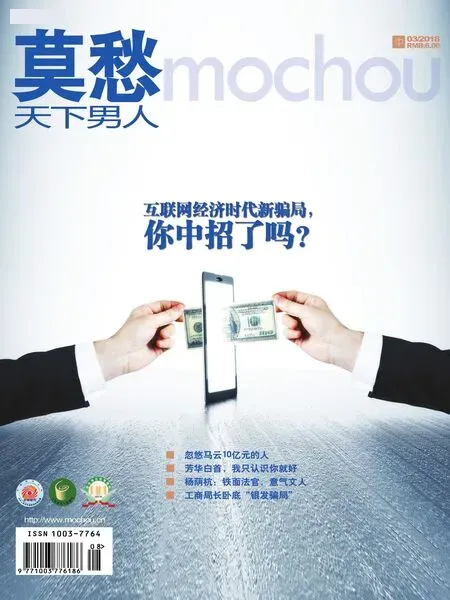丰子恺:一颗童心,快乐做人
2018-03-21强江海
文/强江海
丰子恺,中国现代漫画家、散文家、教育家、翻译家,他养育的七个子女,每一位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说,外祖父一直以来最重视的并不是孩子取得多大的成绩,而是孩子是否快乐。一个人只有对生活感到快乐,才会对未来产生无限期待。
不愿孩子成为小大人
丰子恺出生于浙江桐乡石门镇,家里从事染坊生意,五六岁时,他便开始用颜料到处涂涂画画。丰子恺9岁时,父亲死于肺病,全家人的重担便都落在了母亲身上。转入私塾上学的丰子恺,课间拿出自己描画的《芥子园画谱》给同学看,大家都夸他画得好。老师发现他的才能后,便让他给学校画一幅放大的彩色孔子像。小小的丰子恺有些紧张地接了活,后在姐姐的帮助下完成了这幅画。他笔下的孔子像很有几分庄严肃穆的圣人气象,此后便有了“小画家”的称号。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丰子恺结识了此生对他最为重要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从两位老师那里,丰子恺学会了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毕业后,他跟同学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亲任图画老师。这一年,他和徐力民结婚成家。
徐力民怀上第二个孩子时,丰子恺赴日本学习绘画和英语。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新作,这种简洁明了但立意悠远的绘画风格,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漫画”这种新事物。
1932年,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丰子恺被迫从上海回到老家。他用多年积攒的稿费在家乡建了一座房,取名“缘缘堂”,在这里潜心创作。此时,他身边已经有了六名子女:丰陈宝、丰宛音、丰宁欣(丰子恺大姐丰满之女,一直跟随丰子恺长大)、丰华瞻、丰元草、丰一吟,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3岁。孩子虽多,但丰子恺从来没觉得闹腾,只要有空他就会陪孩子们一起玩,甚至和他们一起“开发”新游戏。
丰子恺专门辟出一间房作为图书屋,每天晚上领着孩子们看书,孩子们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看得起劲,丰子恺会把一些名人或名著,以故事的形式说给孩子们听。谁表现好,谁就可以得到一颗糖,或者跟丰子恺玩一个游戏,图书屋里常常传出孩子们的笑声。
一次,家门口来了卖小鸡的商贩,走一路吆喝一路:“卖小鸡仔喽!卖小鸡仔喽!”年幼的丰元草听到后,拉着爸爸的衣袖说:“我要买小鸡。”说完就往门外跑。没一会,几个孩子都挑好小鸡,就等丰子恺来付款了。见孩子们都迫切想卖,商贩坐地起价。追着孩子们而来的丰子恺想要还价,便故意对孩子们说:“待会还有人来卖,我们买下一家,这家太贵了。”他想拉着孩子走,以此让商贩降价。谁知道,孩子们根本不配合,全都大哭起来。商贩不肯降价,挑起担子昂然前行。丰子恺安慰孩子们:“你们大家说要买要买,那人便不肯让价了。一会儿再来买吧,但下次……”他说不下去了。他在《做父亲》一文中反思自己: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


漂泊十年快乐同伴
1937年,丰子恺编成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这一年,抗战全面爆发,丰子恺只能带着全家逃难。临行前,全家人检点行李,发现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只有数十元现款。这时,六个孩子齐声说道:“我们有。”说完,他们把每年生日父亲送的红纸包统统打开,竟然有四百多元,解决了全家人的燃眉之急。这件事让丰子恺颇为感慨,他说:“只有珍惜眼前的一切,不管是钱、人或者事,才能得到福报。”
全家人先是躲到了江西萍乡,借住在朋友家。很快老家传来消息,缘缘堂被炸毁,这让丰子恺伤心了很久。看着几个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受尽苦累,丰子恺特别心疼。为了驱散战争带来的恐惧,丰子恺尽全力在贫困中给孩子创造出惊喜。离开萍乡后,他们又辗转去了湘潭、长沙。
1938年春,丰子恺来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当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丰子恺兴奋不已,画了一棵大树,并题上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丰子恺曾对好友宋云彬、傅彬然说:“我虽没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可以使民众加深对暴寇的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离开武汉后,全家人又去了桂林、遵义等地。眼见孩子们大了,却没有固定的学校可读书,丰子恺十分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教孩子诗词、写作。除了命题作文之外,他还采用给孩子讲故事,然后让他们凭记忆写下来的办法,锻炼孩子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
一次,丰子恺竟然让孩子们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孩子们听后哈哈大笑。丰子恺解释道:“麻将本身无罪,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它。至于我们要写的说明书,是因为写说明书和写作文不同,要写得一看就懂,并能应用。”
在丰子恺的安排下,逃难生活虽然苦,但从未少了生活的乐趣。丰家孩子面对苦难从容不迫的个性,便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和七名子女“约法六章”
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丰子恺大喜,当即创作了《卅四年八月十日之夜》,抒发对胜利的喜悦之情。
在外漂泊了约十年后,丰子恺携全家人再次回到上海。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不过总算有了临时的家。
1947年,丰子恺刚好50岁,此时,儿女们均已长大。丰子恺与子女们“约法六章”:
年逾五十,齿落发白,家无恒产,人无恒寿,自今日起,与诸约法如下:
一、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大学毕业后,子女各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
二、大学毕业后倘能考取官费留学或近于官费之自费留学父母仍供给其不足之费用,至返日为止。
三、子女婚嫁,一切自主自理,父母无代谋之义务。
四、子女独立之后,生活有余而供养父母,或父母生活有余供给子女,皆属友谊性质,绝非义务。
五、子女独立之后,以与父母分居为原则。双方同意而同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六、父母双亡后,倘有遗产,除父母遗嘱指定者外,由子女分受得。
这种不靠父母,自力更生的家风,深深影响了家每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几年后,丰子恺用蓄购买了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一幢三层小楼。由于二楼屋内的阳台上,通过天窗可从不同角度看日日落,丰子恺为其取名“日月楼”。
这段安稳的时光是丰子恺创作的鼎盛期,他译了俄文《猎人笔记》、日文《源氏物语》,写下了《缘堂随笔》和《续笔》等文章,出版了《丰子恺画集》和《子恺儿童画》,并完成了《护身画集》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随着孙辈们的降临,丰子恺成为爷爷和外公。在小辈们的象中,他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日月楼”。据宋雪君回忆,那时一寒暑假,他就和兄弟姐妹去外公家小住,因为外公家地方大,有不完的零食。其中,最吸引孩子的就是外公喜欢带他们去书店,子们选什么他都会付款。那段时间,宋雪君几乎把所有好看的人书都看了,大多是外公给他买的。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七个孩子未放松过在学术上的追求,他们始终记着父亲教给他们的“人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这句箴言。
如今,丰子恺的后代人丁兴旺,分布于全国各地,还有的在国、日本发展,不乏在各自岗位做出令人瞩目业绩者。
2006年,丰子恺的骨灰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回浙江桐乡门镇,一代大家风雨漂泊几十年,终于叶落归根。
宋雪君说,他依然能梦到小时候在外公家的情形,外公在房画画,他们在外屋玩耍,有时候球滚到了书房里,外公会笑着他们捡起来,那慈祥和蔼的样子,至今难忘。(作者声明:本文谢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