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钱锺书交往解读
2018-03-21北塔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茅盾与钱锺书,一个是革命作家,一个是非革命作家,基本上没有交集和来往,关于两人的各种传记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对方的名字。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都是文坛名家,而且都住在北京,不仅见过面,而且还有一点点文字上的交往。钱锺书曾给茅盾写过一封信,为一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牵线搭桥。

茅盾

钱锺书
钱锺书这封信内容如下:
盾翁大师道座:

即请
近安
晚 钱锺书敬上
七月十五日
仅过5天,茅盾就回信如下:
锺书先生左右:
七月十五日大札及时钟雯信敬悉,因事迟复为歉。时钟雯能译《桃花扇》,想必于中国诗词甚有修养,不胜钦佩。她拟于今年九月间访北京时与弟相见,甚为欢迎。请先生转函为致鄙忱为荷!
忆有《宋诗选注》,似出先生手笔。近来有何著?幸逢明时,想必精神畅快。弟老病纠缠,常与药炉为伍,乏善可陈。
匆上 即候
暑安
弟 沈雁冰上
七月二十日
两人这次通信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为何通信?
其实,钱锺书投书的原因,简单之极:转信附言而已。他要转的是时钟雯女士给茅盾的一封信。
那么,时钟雯女士为何不直接给茅盾写信,而要由钱锺书转达?
原来在此之前,时钟雯并不认识茅盾。但按理说,她可以向钱锺书打听茅盾的收信地址,自己直接投书。笔者认为,她也许是出于以下顾虑,没有这么做。
(一)当时(1979年)中美之间交通很慢,一封信在邮路上可能要走半个月。时钟雯托钱锺书转给茅盾的信写于1979年6月30日,钱锺书在7月15日才收到。如果等钱锺书帮她打听好了茅盾的地址,再写信告诉她,她再给茅盾写信,估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信才能抵达茅盾处,而她9月份就要来北京,留给她准备的时间并不宽裕。
(二)直接给像茅盾这样的大人物投书,在礼仪上似乎有所不妥,所以要经过钱锺书转一下,相当于请钱锺书介绍认识,比较妥贴。时钟雯请钱锺书转了那封信之后,还没等收到钱锺书的回信,她又直接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大概是寄到茅盾的单位(即文化部),因为茅盾在回信中才给了时钟雯所谓的“北京寓址”。可惜,那封信没有被收入《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是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选的,收录了茅盾与时钟雯的通信共三封(其中时钟雯给茅盾的有两封),由上海文汇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先排的是时钟雯6月30日给茅盾的信,紧接着就是茅盾7月21日给时钟雯的一封回信。按照这样的编排,读者乍一看,会以为这就是茅盾针对时钟雯托钱锺书所转信函的回信。其实,中间时钟雯还给茅盾另写了一封信,那应该是在她给钱锺书的信发出之后不久,她直接给茅盾写了一封信。茅盾在给她的回信中说:“日前从钱锺书先生转来大函……顷又得大函。”两封信的写作相隔时间很短。
笔者之所以推测时钟雯6月30日的信不是直接寄给茅盾的,是因为1970年代末从美国到中国的邮件一般来说也不至于需要20天。茅盾收到时信的日期是7月20日左右,而钱锺书是15日左右收到的。半个月比20天的邮路时间更合理一些。
另一个更加内在的理由是:时钟雯委托钱锺书转的信没有单独封起来,因此钱锺书读了并知晓其中的内容。时钟雯在这封信中说钱锺书是茅盾的老友,引起了钱锺书的不悦,以至于他在给茅盾的推荐信上毫不客气地说:“渠所谓老友云云,乃后生辈无知。”如果钱锺书没有读到这封信,他何至于发这种针对性的言论?
那么,时钟雯是如何认识钱锺书的呢?
据《访美观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记载,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对美国进行了为期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访美代表团一行共10人,到访了华盛顿、纽约、匹兹堡、纽黑文、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火奴鲁鲁等十余地的政府机关、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钱锺书的行程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旧金山北湾)和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是他重点访问的学府,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帕罗奥多市(Palo Alto)境内,临近旧金山。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人把斯坦福大学译为“史丹佛大学”,但不是孔庆茂在《钱锺书传》中所说的加州大学分校。
时钟雯何许人也?在《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一书中,关于时钟雯的介绍,编者只给出了一条极为简单的注解:“时钟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戏剧家。”
这条注解有三个问题:(一)编者没有仔细核查时钟雯的出生年份,只打了个问号了事。笔者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时钟雯生于1922年10月8日,2014年7月6日卒于脑动脉瘤,享年92岁。
(二)美国有三所华盛顿大学,分别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1821年建校时名为哥伦比亚学院,1904年更为现名;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WUSTL),1853 年建校;位于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W),1861 年建校。书中注解只说“华盛顿大学”,读者不知指的到底是哪一所,容易引起混淆。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Drama: Yuan Tsa-Chu
),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于1976年1月,中文版于1991年1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这个角度而言,她是戏剧学家或者是学者,但她自己并没有创作过戏剧作品,因此不能说是戏剧家。在与茅盾的通信中,她没有提到戏剧,甚至对茅盾夸奖她翻译《桃花扇》都没有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条注解的信息只是来自钱锺书给茅盾的信,钱锺书写信可以简单,所以只说“华盛顿大学”。但编者既然要添加注解,不能只是照搬钱锺书信中有关内容,而是应该做点功课,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至少做到不要误解误传(把戏剧学家说成戏剧家)。

时钟雯非等闲之辈。她是安徽人,从小随父母移居上海,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后留学美国,1955年获得杜克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后至哈佛大学东亚系做博士后研究,曾任斯坦福大学中文助教,1965年转到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任副教授,期间(1971-1972)又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从1972年到1993年,一直以教授身份执掌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长达二十多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简称GWU或者GW,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比邻美国国务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距白宫只有几个街区。钱锺书他们曾在华盛顿逗留访问,可能跟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时钟雯女士有所交流。因此,时钟雯在给茅盾的信中说:“今年四月间在华盛顿又见到您的老友钱锺书先生。”
由以上种种线索可知,钱锺书之所以要主动给茅盾写信,是因为受时钟雯之托引荐她。
二、时钟雯为何要找茅盾?
在钱锺书给茅盾的信中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说时钟雯“于公仰望,不啻泰山北斗”。她确实是把茅盾认作文学界的泰山。同年10月9日她在北京饭店给茅盾写信说:“无疑的您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文学家。”
时钟雯在6月30日给茅盾的信中先说她来中国见到了巴金,又在美国见到了钱锺书,然后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您领教……今年九月间我再度回国很想有机会能见到您。”
茅盾于7月21日(给钱锺书回信后第二天)就回信给时钟雯说“不胜欢迎”。
不过,时钟雯拜访茅盾,可不是简单的见面闲聊,而是有备而来。她是来做专题访谈的,不仅录音,而且还要摄像。她在10月9日的信中说:“我从美国特地请来了一位专业电影摄影师。”
原来她是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纪录片。
在给茅盾拍摄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人手不够,她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茅盾是首任部长)派出的一位陪同人员帮助录音,结果那位陪同人员不会使用洋机器,错按了按钮,茅盾的很多谈话内容没能录上,导致整个访谈没法用。时钟雯特别着急,在10月9日写给茅盾的信中说:“这部片子如没有您,就大为逊色。”并恳求茅盾另外安排半个小时,重新接受他们的采访。她在信中还附了将要提问的问题。
我们没有看到茅盾对时钟雯的这封信的回信,但从结果来看,茅盾同意了她的返工请求,并配合了她的工作。
据说,时钟雯的纪录片最后做得相当成功,她也因此而闻名一时。她这部纪录片的题目叫《从寂静中归来:中国现代作家》。这部片子曾经在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公共电视台是美国唯一一家既不收费又不在节目当中插播广告的电视台,创建于1969年,目前在美国全国各地有三百多家分台,一般位于大学校园或社区,在学界影响很大。
三、称呼问题。
时钟雯比钱锺书小12岁,钱锺书比茅盾又小14岁。从学术传承的代际划分来看,正好各相差一代。
钱锺书对时钟雯似乎不太客气,在给茅盾的信中称呼她为“后生辈”,还说她“无知”。而钱锺书对茅盾却恭敬有加。他对前辈文人(比如同光体领袖陈衍)喜欢用“丈”来称呼,表示敬意;他称茅盾为“翁”(比“丈”敬重的程度更高),而且还用上了他极少用在当代中国人物(尤其是文学界人物)身上的“大师”一词。众所周知,钱锺书在臧否不少现当代中国作家尤其是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时候,往往流露出不屑的口吻。比如,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台湾作家水晶曾问过他对鲁迅的看法,他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短气’(Short 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 -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此事被水晶记入《侍钱“抛书”——两晤钱锺书先生》一文(罗思编:《写在钱锺书边上》,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这番话中,钱锺书对鲁迅先褒后贬。为什么说“气短”是一个贬义的文学价值概念呢?他在一篇论文中曾写过这样的话:“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谴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short-winded style)……”然而,对于鲁迅的战友茅盾,在短短一封信中,钱锺书三次用“晚”(相当于“晚辈”)来称呼自己,表现了极大的谦逊。当时他自己也已年近古稀,而且德高望重,在别人眼里,早就是“翁”,是“大师”,是“泰山北斗”了。时钟雯可能是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对茅盾的称呼非常简单:“先进作家沈雁冰先生”,甚至简单到直呼“茅盾先生”。“先进作家”相当于“前辈作家”,时钟雯在同一封信中还用“先进作家巴金先生”“先进的老作家”等称呼,没用“泰山北斗”这样的敬词。钱锺书却不吝用了,说明他对茅盾还是相当尊崇。

中国文人之间的称谓有个传统至今留存:在文字交往时,无论辈分相同还是相差(哪怕很大),前辈为了表示自己谦逊为人、奖掖后人,往往喜欢以“兄”称呼晚辈,以“弟”称呼自己。如,钱锺书称陈衍为“丈”,陈衍呼钱锺书为“世兄”(见《石语》)。茅盾在给钱锺书的回信中两处称自己为“弟”。时钟雯比茅盾小26岁之多,但茅盾第一次给她写信时居然称她为“钟雯大姊”,似乎她比茅盾还要年长似的。要知道,当时茅盾已83岁高龄。茅盾这么称呼钱锺书,是循了老例。
钱锺书在信中对茅盾还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称呼,即“记室”。这是古代的官职名,东汉始置,诸王、三公及大将军都设记室令史,掌章表书记文檄。茅盾是前任文化部长,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钱锺书用这个词称呼茅盾,本意可能是表达茅盾乃最高层信得过的文坛领袖。但这个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贬低了茅盾的地位和形象。要知道,记室只是书记官,在地方或部门(由诸王、三公及大将军把持)都没有什么高位,无法跟茅盾这位全国性的文化执牛耳者相比,茅盾当时在中国文化界所处的位子显然比所谓的“记室”高多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前面钱锺书对茅盾的那些尊称?他对茅盾到底是何种评价?
夏志清曾说:“钱锺书的书信是不能发表的,他骂人太多,凡是不喜欢的他都骂,这怎么能发表呢?”(见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但钱锺书对收信人却也有“捧”的时候——过分揄扬对方,以至于作家韩石山总结说:“钱锺书在私人信件里的称赞不可当真。”
钱锺书此时称茅盾为“泰山北斗”,但是后来对茅盾之“不拘小节”,还曾有过微词。
1985年4月6日,香港《广角镜》杂志151期刊登秦德君的文章《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愿以本文,引起健在者的追忆与补充》(为了扩大文章在内地的影响,此文12年后经过重新整理修改刊登于《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4期,署名是“秦德君口述、刘淮整理”,题目则一如其旧;此时距离茅盾去世已经16年),文章披露了作者与茅盾的一段感情纠葛。《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开篇就是“偶遇秦德君”:“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知道她……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他们坐在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对于这段感情,茅盾在其晚年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只字未提。钱锺书曾动笔给《广角镜》杂志的时任主编李国强写信说:“前日睹贵刊《一段情》之文,与内人皆叹为石破天惊,而更叹兄之有偷天妙手、泼天大胆。正思写信,尊函适至,知果惹恼招怒,然此亦早在意中。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钱锺书在信中似有指责茅盾刻意回避并掩饰自己的婚外恋问题之意。

林非、刘再复著《鲁迅传》
钱锺书于信中所提的“三年前”应该指的是“四年前”,即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40周年,当时为了纪念而出版了一部《鲁迅传》,是钱锺书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林非和刘再复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林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写过一系列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至今,已出版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专著。1981年,林非还被提名为纪念委员会委员,参加主持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中的学术讨论会,后来又曾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刘再复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1981年出版了学术论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201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还推出了他单独撰著的《鲁迅传》。林非和刘再复在《鲁迅传》中确实“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乔丽华撰写了《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2009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
四、两处存疑
(一)钱锺书与茅盾1978年何时何地因何见面?

(二)时钟雯真的翻译过《桃花扇》吗?
钱锺书给茅盾的信中推介时钟雯,说她是“以译《桃花扇》得名者”。这一点引起茅盾很大的兴趣,并且对时钟雯油然产生敬意和好感。他在给钱锺书的回信中说:“时钟雯能译《桃花扇》,想必于中国诗词甚有修养,不胜钦佩。”在7月21日给时钟雯的回信中又突出说:“您译《桃花扇》,真不简单,想见对中国诗词素有研究,无任钦佩。能否见惠一册,如果方便的话。”笔者查了多处关于时钟雯的资料,都没有找到她翻译《桃花扇》的信息。1972年,她完成博士论文“Injustice to Tou O: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ou O Yüan
”(《对窦娥的不公平 :〈窦娥冤〉的研究与翻译》),论文中附录了她翻译的《窦娥冤》。《窦娥冤》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时钟雯的学术兴趣基本都在元杂剧上,她一生的学术代表作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而《桃花扇》是清初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而写就的一部传奇剧,不在时钟雯的学术兴趣范围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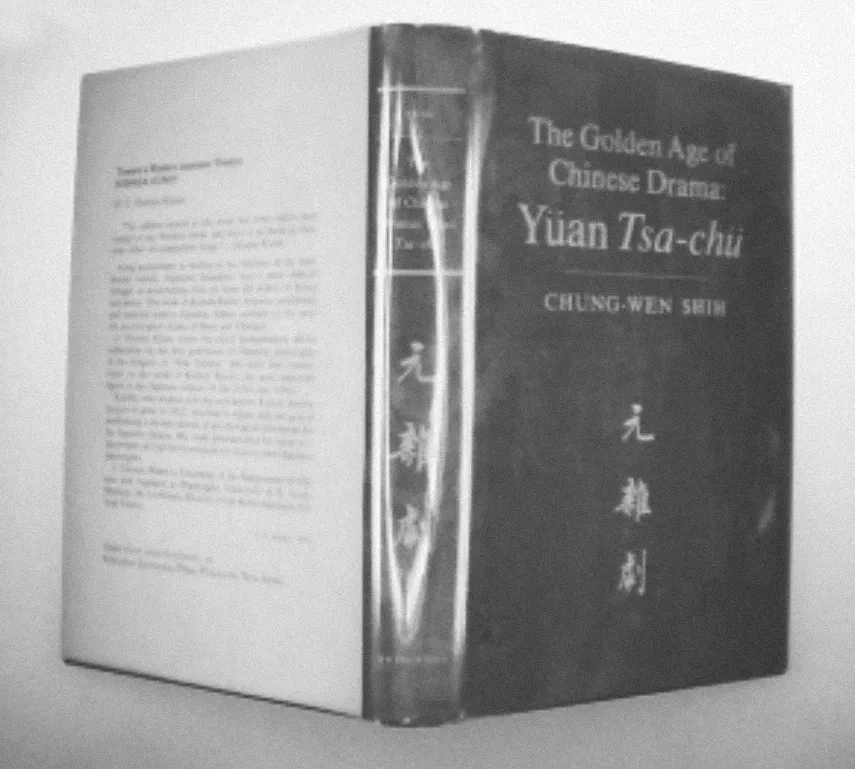
时钟雯著《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
笔者大胆假设:钱锺书把《窦娥冤》错记成了《桃花扇》。其间可能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原因:时钟雯是在跟钱锺书见面时口头上匆匆说了一下书名,而且是用上海话说的。在我们吴方言里,窦娥冤的发音(Deu Eoyo)和桃花扇的发音(Dao Huoso)相当接近。钱锺书可能在匆忙间因为这谐音而导致了误记。当然,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于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