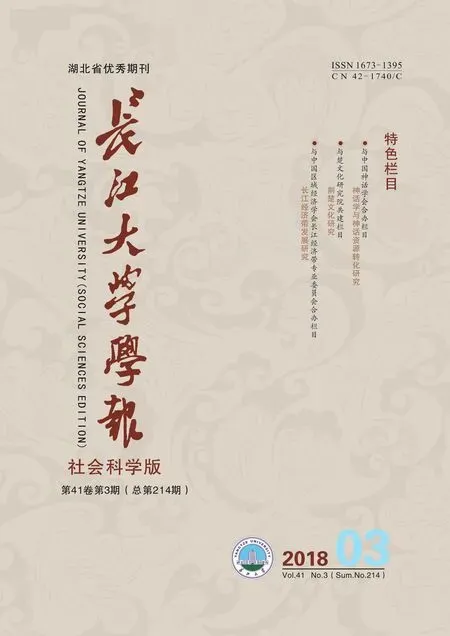“替死鬼”故事类型研究
2018-03-20徐金龙许秋伊
徐金龙 许秋伊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在鬼故事中,“替死鬼”是一个常见的故事类型。该故事的核心情节就是死亡的人会寻找能够代替自己的替身,借此机会复活为人或者前往地府。这类故事的雏形出现于魏晋干宝的《搜神记》,在同一时期的《甄异录》《幽明录》里也有类似的故事;唐代的《广异记》《冥报记》中,该类型的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宋代《夷坚志》记录了3个与此相关的故事,南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出现了更为完整的故事;到明代,“替死鬼”成了笔记小说中的常见情节之一,如陆延枝所著的《说听》卷二《周八尺》,张泓《滇南忆旧录》所记载的《成公祠》,曾衍东在《小豆棚》中所记载的《折腰土地》等;如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收录类似故事有16篇。
“替死鬼”故事在中国故事类型研究中记载较少,与此相关的是“渔夫与水鬼”这一故事类型。钟敬文先生将之概括为:“渔夫得水鬼相助,生活顺利。某一日,水鬼向他告别,谓将得替转生为人。渔翁破坏了他的计划(或者水鬼自己未实行自己的计划),他仍然不能离去。不久之后,水鬼得升土地或者城隍,向渔夫告别。他们此后或许还会再见面,或许永不见面。”[1](P343)值得注意的是水鬼与渔夫告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找到了替代者。与此同时,艾伯华也提出了“渔夫与淹死鬼”这一故事类型。主要内容为:“一个渔夫和一个淹死鬼结下了友谊。鬼希望能寻找到一个替身,渔夫阻止了他,鬼放弃了这个意图。鬼做了城隍,渔夫去看望他并找他讨教。”[2](P218)在这两种记载中,“鬼找到了替代者”是关键情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于“替死鬼”这一故事类型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将重点分析“替死鬼”故事的两个亚型,梳理该故事类型的演变过程兼及国外流传的同类型故事异文,探讨该类故事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
一、“替死鬼”故事的两个亚型
“替死鬼”故事分为两个亚型,分别是“抓替死鬼”型和“鬼惑人”型。这两个故事亚型一起构成了“替死鬼”这一故事类型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互相影响。
“抓替死鬼”型故事按照被替代者身份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首先是“人和人之间的死亡转移”型。本类型可以概括为:鬼奉命来到人间取某人的性命,因为某件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主意,自己选择或者是由当死的另外一个人提供线索,将与当死之人名字相同或者长相相同的人的性命带走,而应该死的那位得以保全。这一故事类型的代表性文本有:《甄异录》所记载的“张罔”条,《搜神记》所记载的“施续”条、“贾偶”条,《冥报记》所记载的“马嘉运”条,《广异记》所记载的“章仇兼琼”条,《太平广记》所记载的“李简”条等。试看《搜神记》“施续”条:
吴兴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一黑衣白袷客来,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门生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按着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3](P288)
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情节是,鬼从某个地方来到了人世,担负着取人性命的任务,却将本该死亡之人遭受的苦难转移到了另外一人的身上。该情节与现实生活中的转移巫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弗雷泽在《金枝》里提出了交感巫术理论。这一理论包括相似律和触染律。从巫术理论来说,转移巫术是交感巫术中的顺势巫术,在实行的过程中,又需要通过触染的方式来完成。弗雷泽认为,“总之,社会和思想水平发展较低的民族一般都理解并运用找替身受罪的原则。”[4](P764)他们所转嫁灾祸的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一种动物或一个物体;有的人将自己的灾祸转移到用泥做的偶像上;有的人将自己的灾祸转移到树木或者灌木上。在中国,同样不乏类似的记录。《尚书·金縢》记载,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贵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其大意是周公愿意为鬼神祈求,将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史记·封禅书》也提到“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情形,如中药渣被认为是一种疾病的转移媒体,病家通常把中药渣倒在路上,希望随着药渣的被踩踏而将病痛带向远方。在这个亚型中,被替代者与替代者唯一的联系就是死亡转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联系,唯一类似的部分可能是名字,也可能是出生日期等。
其次是“鬼和人之间的死亡转移”型。故事情节概括为:鬼在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等待可以代替自己的人出现,在该人死亡之后,鬼获得了复活为人或者前往地府的机会。早在清代,蒲松龄便借王六郎之口对这个类型加以诠释:
询其姓字,曰:“姓王,无字;相见可呼王六郎。”遂别。明日,许货鱼,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与欢饮。饮数杯,辄为许驱鱼。……语甚凄楚。惊问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两人,言之或勿讶耶?今将别,无妨明告:我实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于此矣。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人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酹奠耳。明日业,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5](P29)
王六郎直接点出了他留在人世间的目的:“当有代者,将往投生”。这一亚型代表型篇目有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王六郎》、湖北省流传的故事《鬼友》、广东省流传的故事《老虎鬼找替身》等。不过,以这一情节为中心独立成篇的比较少,反而在“渔夫与水鬼”型故事里出现得比较多。
“鬼惑人”型一般会与“恶鬼”故事联系在一起,并且穿插于不同的故事类型之中。故事情节概括为:人来到了某地,迷迷糊糊被人叫出去或者去参加某种集会,最终发现参加的是鬼的集会,而叫自己出去的人则是鬼所化身的,人会遇到危险(被人所救或及时醒悟)。如《夷坚志》丙志卷三所记载的“黄花怅鬼”条;《夷坚志》丙志卷11所记载的“华严井鬼”条;《夷坚志》丁志卷11所记载的“沈仲坠崖”条。且看“沈仲坠崖”条:
予叔父家养羊数百头。放诸山上。多为狼所食。尝遣表侄沈仲迹寻之。值夜未毕事。方独行。忽逢家所使刘行者在前。戏呼其姓名。仲虽怒,而暗中喜得侣。即相应答。刘曰:此路甚险恶,宜随我来。乃踵以前,才数十步,遂坠落崖中。臂几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识其声,急张灯携梯掖之以上,扶还家。左臂穿穴透骨,犹能道所见。而刘行盖未尝出,始知鬼也。[6](P632)
沈仲与鬼素不相识,却被鬼伪装成自己认识的人引诱,最终才行数十步,遂坠落崖中,可谓十分不幸。当下流传的“替死鬼”故事经常会把这个类型与“鬼和人之间的死亡转移”型联系起来,增强故事的离奇性,如黑龙江地区流传的《淹死鬼抓替身》《铁匠与吊死鬼》、广东地区流传的《老虎鬼找替身》等。
二、“替死鬼”故事的演变过程
转移巫术在原始社会的盛行是“替死鬼”故事得以形成和流行的社会文化基础。从时间上来说,转移巫术从远古时期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从地域上来说,弗雷泽在《金枝》里所记载的该巫术流传范围从苏门答腊岛到印度南部,从欧洲地区到新西兰。[4](P765)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如今搜集到的“替死鬼”故事,从时间上来说,早在魏晋时期便有同类型的故事产生;从地域上来说,该故事在全国16个省皆有分布,社会影响广泛。
在早期,“替死鬼”故事一般是“人和人之间的死亡转移”型,而在后期变成了“鬼和人之间的死亡转移”型,故事情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
(一)由人变鬼的被替代者
在早期的“替死鬼”故事中,被替代者和替代者都是人。而到了后期,被替代者由人变成了鬼。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死亡观念的变化有关。
魏晋以前,中国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者不可复生。后汉少帝刘辨曾经作诗:“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他对于死亡的想象尚停留于人死后会去往幽玄。孔融曾经写过《临终诗》,末句为“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他认为死亡便是一切的结束。这些作品关于灵魂和死后世界的看法都不甚明确。
佛教的出现,事实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死亡观念。佛教对于生死的理解与中国本土的区别很大。早期,一些民族流传着灵魂不灭的思想。如满族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将会变成雄鹰;而在蒙古人的传说里,人的灵魂像一只蜜蜂,在人睡觉的时候,进入人的鼻孔。直到佛教出现之后,灵魂不灭的观念才进入传统的思想道德体系之中。[7]佛教提出了三世的观念,即前世、现世和来世,扩大了中国人对于死后空间的想象,为死后人的灵魂将归何处提供了新的答案。这一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敦煌文书《佛说要行拾身经》题记里说:“清信弟子史苟仁,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前死后亡写。开元十七年六月十五号记。”所谓七世父母,指的是以轮回为基础,在本世之前的过世的代代父母。[8]这一文书的出现,体现了佛教出现之后中国人对于灵魂观念全新的理解。
在“替死鬼”这一故事类型中,《冥报记》中的“马嘉运”条在继承前朝“替死鬼”故事传统的同时,又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马嘉运被人带到死后的世界,见到了东海王。东海王听说马嘉运的文名,希望能把他留在冥界当文书官。马嘉运推脱了此事,同时推荐了绵州一位叫陈子良的人。这位名叫陈子良的人在一天中突然去世,旋即苏醒,自言前往冥间遇到了东海公。与此同时,另一位叫陈子良的人却去世了。[9](P68)相较于之前的故事,“马嘉运”条增加了人去往冥间又死而复生的情节。这一情节中蕴含的灵魂不灭、死而复生的思想,正是佛教的产物。而陈子良逃脱死亡的方式与之前的“替死鬼”故事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用名字相似之人的性命取代了自己。“马嘉运”故事可以说是“替死鬼”故事情节变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到了宋代,“替死鬼”故事中的被替代者从人变成了鬼,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替死鬼”故事模式。南宋《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中的“黄裳与水鬼”条中,水鬼直接说:“吾在此十纪,来日当去,惟候淮南二急脚来替。”[10]故事中的转移巫术内核完全披上了佛教的外衣。鬼魂将死亡转移到他人的身上,让自己获得复生或者投胎。这本质上就是原始的转移巫术。跟以往的故事相比,鬼魂成为故事里的被转移者,被替代者的范围得以扩大。跟“马嘉运”故事相比,这个故事增加了灵魂可以在人世间长期存在的思想,也补充了灵魂的离去(无论是复生还是转世)是需要满足某种特殊条件(在唐代,这个条件一般会是是否信仰佛教,是否积累善业)的理念。而这两条来源都是佛教。当该佛教思想与转移巫术发生联系之后,取他人性命也可以成为需要完成的条件之一。在两种社会思潮的联合作用下,“替死鬼”故事最终演变成现今所看到的版本。
(二)消失的巫师
在早期的“替死鬼”故事中,鬼扮演的角色实际上类似于人世间的巫师,而它的身份则跟神较为类似。事实上,在鬼产生之初,鬼与神的区别是模糊的,甚至在某些民族鬼和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如拉祜族的传说,有“天公鬼”“地母鬼”“风鬼”等类似于汉族传说中的神的存在。[11](P5)与此同时,人变成连接神和鬼的中介也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这些思想的存在缩小了鬼与神之间的距离。
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想象人死后到达的世界。那时,人们称死者归去的世界为“黄泉”“幽都”。大约在西汉时期,民间形成了“泰山治鬼”的说法。[12](P7~23)所谓“泰山治鬼”,指的是人死后将会前往泰山,由泰山府君管理。在魏晋时期的一些著作中,人们所设想的泰山府君管理下的冥界具有某些特点:阳间和冥界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泰山府君的地府和人间的官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现实世界中的死者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在冥界获取官职。鬼与神在此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13]这一时期的鬼所扮演的巫师角色,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巫师及其责任的一种反映呢?
而佛教出现之后,鬼和神的区别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并最终深入到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中。在唐代《冥报记》等记载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与魏晋时期的故事相比,唐代鬼魂进入冥界有了条件限制。一般表现为信佛者和不信佛者在冥界会有不同的待遇;有罪者暂时不能进入冥界,要在人间以服苦役的方式进行赎罪等。如《冥报拾遗》中的“李信”条,李信的母亲因为瞒着自己的丈夫将米给了女儿,变成了一匹马,凭着力气偿还自己的债务。《法苑珠林》中的“赵太”条,故事中的小女孩想盗窃父母的钱来买脂粉,在目标没有实现之前就死去了。她不得不因为自己的罪名而变成一头青羊,以此来偿还父母给她的性命。而鬼是否可以在冥界获取一定的地位,也与它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是否满足一定条件有关。这一现象的出现,事实上标志着鬼和神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替死鬼”故事里,鬼基于自身与神类似的特点而获得了扮演巫师的机会。但是,随着鬼与神距离的扩大,该说法最终湮灭在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三)不断复杂化的转移过程
总体上来说,“替死鬼”故事类型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其中在“转移死亡”这一重要情节之中,转移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复杂化。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魏晋时期的“转移死亡”条件限制比较少,仅仅对于替代者自身有所限制,多半为姓名或年龄相似之人。而到了故事发展的后期,在转移过程之中多了对于被替代者身份的说明,出现了“意外死亡”的暴死鬼;对于替代者,从早期的姓名、年龄、地域等条件增加了其人的出现时间、地点;转移结局也由被替代者存活变成了离去、转世、成仙等。大体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特点。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被转移者身份的增加,源于在社会上一直存在的人类对于“暴死者”的恐惧。在先秦时期,“恶鬼”便已经出现,被称为“厉”。这些恶鬼常年在人间作祟为害。而这些被畏惧的恶鬼,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那些意外事故死亡者所变的鬼魂。实际上,仰韶文化时期就存在着对于“凶死”者的恐惧,如成人二次葬的瓷棺葬等,就被一些研究者解释为是“凶死”的一种葬俗。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凶死”之人的灵魂也是凶恶的,他的灵魂不能跟本族人埋在一起,某些情况下,对于整个人类群体都是采取一种加害态度,甚至于毫无关系的人也可能成为该鬼魂的牺牲品。这一恐惧最终与在民间流传的“替死鬼”故事有了交集,于是,该故事中的被替代者也会在某些时候被形容为意外而死的恶鬼。
佛教则为故事中的被替代者提供了多种结局。首先,佛教的出现,让民众开始觉得人的灵魂去处与其生前行为有关。其次,佛教关于地下世界的想象深入民心,它将传统的黄泉、幽冥等去处扩大为六道,即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基于此,在“替死鬼”故事中,被替代者有的直接复活(《打渔郎娶妻》),有的投胎做人(《抲鱼佬与河水鬼》),有的将往投生(《王六郎》)。这些故事都有佛教观念的影子。
民间故事的观念思想有时并不是单一的,民间流传的城隍信仰同样对“替死鬼”故事产生了影响。在明清以来的“替死鬼”故事中,城隍信仰频繁出现,结局通常是“鬼”直接升为城隍,或者是被任命到城隍庙去做官。城隍信仰是我国的民间信仰之一。最早的城隍就是城墙,从唐代开始,城隍从自然神变成了人神,从城池化身之神变成了人死后可以成为的人神。明代将城隍信仰列入整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城隍庙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公共场所。政治措施的实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城隍信仰在“替死鬼”故事中大量出现,如《城隍遭贬》中的鬼变成了城隍神,《抓替身》中的鬼也成为了城隍,还有《鬼友报仇》中的鬼最后成为了城中庙里的神仙。这一信仰的存在使得“替死鬼”故事情节更加生动,引人入胜。[14](P69)
三、“替死鬼”故事与民间禁忌
禁忌是民俗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宗教色彩,又在日常生活中被完全地世俗化,它们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有的禁忌比较细微,但是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如正月里不能剪头发;筷子不能直立摆放在饭碗上;在过年期间不能说“死”字等。禁忌实际上是一种否定性的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民俗信仰。因违反禁忌而带来的处罚是不可逆的,否则,禁忌的威慑力会被削弱。从社会层面来说,禁忌的存在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某些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持,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积极的影响。[15](P291)
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与民间故事互相构建。民间故事诠释了禁忌意义之所在,禁忌则为民间故事提供了主题。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替死鬼”故事为某些地区日常生活禁忌提供了具体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这些地区特有的生活秩序。
在水边长大的人,应该都听说过“水鬼”故事。至于“水鬼”的来源,通常是很久以前在该地溺亡的人,固守于水中,待某一年无辜者来到这片水域的时候,或用渔网,或用水草,觑得一个不设防的拖下水去,换得一个前往地府或者直接托生的机会。湖北荆州也流传着相似的故事。该市宝塔湾一直流传着“水鬼”会拉人下水的传说。宝塔湾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水里冤魂极多,若是下水,则会被鬼魂抓住腿不能动弹,最终死于非命。宝塔湾水文条件非常复杂。河水表面平缓,实则暗流涌动。岸边的堤坝看似洁净,实则水下密布青苔。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不要下河游泳”成为一种禁忌。而在宝塔湾流传的“水鬼”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诠释了该禁忌产生的原因,扩大了该禁忌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影响。
这类故事就是以替代者为视角诠释“替死鬼”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收录了一则相似故事。大意是“水鬼”米云桂在水中待了3年,希望抓到替身换取自己离去,最终他抓了恶霸阎斌,将此人推到水里淹死,换来了自己的远走高飞。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河里的“水鬼”在特定的地点将无辜者拉进水中的故事,只不过换了一个叙述人罢了。与此相似的故事在中国各地均有流传,对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
四、国外流传的替死鬼故事异文
转移巫术在世界上流传的范围甚广,基于转移巫术而产生的“替死鬼”故事所涉及的地域也不止中国这一个国家。
《日本灵异记》(全名为《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民间故事集。它成书于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期,由奈良药师寺僧人景戒编撰。《日本灵异记》共收录116则故事,内容全都是志怪故事,被视为日本怪奇小说的源头。在这116则故事中,包括两个与“替死鬼”故事相似的故事,其大概内容为:某个村子的衣女将要被鬼取走性命。鬼直接说:“我受如飨,故报汝恩,若有同姓同名人?”在此,本当去世的衣女指出,“同国垂郡有同姓衣女”,最终鬼带走了同姓衣女的性命。[16]这个故事与《甄异录》中所记载的“张罔”条在情节上极为相似。除此之外,《日本灵异记》还记载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用邻村同年人的死亡代替了自己。虽然景戒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日本灵异记》是在中国佛教经典《冥报记》和《般若验记》的启发和影响下编撰而成,但是他所编撰的“替死鬼”故事则更接近魏晋时期的产物。这其中是否有着日本本土故事的身影,尚待进一步研究讨论。
与此同时,“替死鬼”故事也出现在泰国和韩国的电影中。2014年的泰国电影《化身》中,女主角艾米痛失自己的亲生女儿,打算把小女孩茉柏领回家当自己的孩子照顾。但是,死去的孩子希望将茉柏当做替身,从而实现复活。这个故事情节与“替死鬼”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韩国电影《女高怪谈:死亡教室》中,死去的学生真珠一直在死去的地方徘徊,并在电影的最后让罪魁祸首死去。该电影的情节与“替死鬼”故事中的“鬼惑人”型有着相似之处。网络文学中的“替死鬼”故事更是不胜枚举。该故事类型直到今天仍然充满魅力和活力,对文学创作和民间生活都有着深刻影响。
五、结语
鬼文化是中国社会一项颇有影响力的民俗文化。围绕着死后的世界,人们产生了种种联想和思索,并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诞生了鬼文化。“替死鬼”故事只是庞大的鬼文化中的冰山一角,通过梳理该类故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思想是如何进入到民间文学的视野中的,并对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恶鬼恐惧、城隍信仰,还是佛教观念,这些思想都在民间故事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替死鬼”故事并不只是简单的鬼故事,在它的诸多篇章中,隐藏着极为严肃的宿命观念和道德主题。灾祸转移的原因仅仅是姓名相同,被替死鬼带走的原因是此人做尽坏事。无论在世如何,在死亡面前人人殊途同归。面对茫茫而不可知的未来,或许这些故事能给尘世间苦难的人们带来一点理想的希望与微弱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M].王燕生,周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英)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5]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江新建.论佛教对中国人生死观的影响[J].求索,1995(2).
[8]赵青山.佛教与敦煌信众死亡观的嬗变——以隋唐宋初敦煌写经题记为中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9]李时人,何满子.全唐五代小说(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顾希佳.“渔夫水鬼”型故事的类型解析[J].思想战线,2002(2).
[11]徐华龙.中国鬼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2]余英时.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A].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韦凤娟.从“地府”到“地狱”——论魏晋南北朝鬼话中冥界观念的演变[J].文学遗产,2007(1).
[14]郑土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M].上海:三联书店,1994.
[15]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故事和传说中的禁忌主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6]杜佩娟.《日本灵异记》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志怪故事比较[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