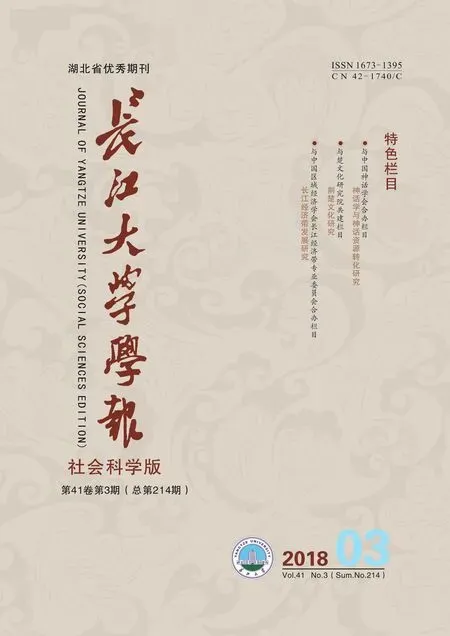神话“鲧禹治水”的历史解读
2018-03-20黄文著
黄文著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于什么是神话以及神话的性质,曾做过这样的说明:“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又说,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P113)。马克思对神话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和认识神话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理解神话,我们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做出如下三点解读:神话故事沉淀着历史的内容,神话是对历史的一种变形的反映,这种变形反映是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一、关于“鲧禹治水”的记载
“鲧禹治水”的神话,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虽零零星星,但也有迹可循。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山海经·海内经》中的记载,是鲧禹治水整个故事的提纲,文字虽然简洁,但大体故事的轮廓却已经具备了,事情的起因、发展、结局是清楚的,现在流行的“鲧禹治水”的神话读本都采用这个版本。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
舜之时,共工振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篇》)
以上记载是传说中尧舜时代洪水泛滥的情景,是《山海经》中“洪水滔天”四个字的具体化。至于洪水是怎样泛滥起来的,《淮南子》里说是由于共工“振洪水”。
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经·海内经》)
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国语·晋语八》)
鲧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
这三段文字具体补充了鲧窃息壤、被杀以及“鲧复生禹”的内容。
《孟子·滕文公上下》《淮南子·本经篇》《国语·晋语八》《越绝书·外传记地》《荀子·成相篇》《楚辞》《尸子辑本》《太平广记》《吕氏春秋》《汉书》《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对鲧,特别是对禹的治水过程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里不一一录叙。
以上这些丰富的典籍记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鲧禹治水”绝不仅仅是一个神话故事可以囊括的,其中一定与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而禹因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市南),当地仍存禹庙、禹陵、禹祠等。这些遗迹对于“鲧禹治水”的历史事实是可资佐证的。
中国神话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神话这条线与历史这条线互相平行而又纠缠在一起,神话可以转化为历史,历史也可以转化为神话,即所谓的神下地和人上天的问题。[2](P10)关于历史转化为神话,高尔基说:“古代‘著名的’人物,乃是制造神的原料。”[2](P10)鲧和禹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古代著名人物,他们与尧、舜一样,是原始社会时期著名的部落首领,因治水建立了功劳,受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因而被神化了。
二、历史的解读:一个治水的历史事实
(一)关于“洪水滔天”
中国古文献所记载的文明史,是从尧舜禹时期治理洪水开始的。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的起源也与洪水的故事有关。例如希伯来著名的《旧约·创世纪》记载,其民族开始于“诺亚方舟”的故事;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追述其历史,也是从“大洪水”开始。[3](P66)
根据近代气象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在距今8000~3000年之间,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转暖,气温上升,冰雪融化,河水泛滥。这时期,中国的黄河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洪水滔滔,水患成灾。[3](P66)中国神话中最早记载的水灾就反映在神话“女娲补天”里,其时间大概在距今6000年前。
大概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黄河处在频繁改道的时期,到了尧舜禹的时候,黄河由南线入海改道为北线入海,当时的水患非常严重,这在周秦的文献里多有记载。这就是“鲧禹治水”神话里所说的“洪水滔天”。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类,在同一时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洪水,这是这个神话故事产生的自然背景。上文所引古代典籍对当时水患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明。
(二)关于“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当时中国的政治结构,是由舜建立起的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一个松散的国家,“鲧禹治水”里的帝就是舜,鲧与祝融是两个部落的首领,在舜领导的国家中任职。“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位,为人臣。”[4](P21)这一时期也正是龙族形成的时期,面对严峻的水患,原来各自为政的部落,联合在了一起,共同面对灾害,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华夏民族形成了,龙的传人产生了。而“龙”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符号,也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图腾。
从黄帝以来,由于水患的原因,为了获取生存的空间,中华大地上两河流域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华北平原聚集,因此,当时黄河两岸居住着大量的人口。这一局面的出现,使得鲧的治水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治水用疏而不用堵,这是常识。鲧用堵而不用疏,肯定有他的难处。用堵的办法,是人进水退,也就是以人的意志来改变水的意志,这是基于可行性的判断,也就是有可能堵得住。而用疏的办法,是水进人退,也就是水的意志改变人的意志,这是基于不可行性的判断,也就是不可能堵住。
这两个办法都有风险。堵有堵不住的风险,如果堵不住,人的生命和财产将面临巨大的损失;疏有疏的困难,大量人口往哪里迁,如何安置,部落之间如何协调,等等,代价也大。所以,鲧虽然勤奋工作,但还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4](P21),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这种两难具体反映在治水方法的选择上,上层出现了分歧。舜是主张疏的,“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从神话的角度看,是帝将息壤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舜帝是不主张用“水来土掩”的堵的办法的。至少他还在犹豫,没有最后下决心。“不待帝命”这一句,表明鲧与帝舜在如何治水上产生了分歧。《国语·晋语八》中,对鲧与帝舜的治水的分歧也有说明:“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於羽渊。”
而鲧作为一线的治水官员,他既要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鲧并非不知道治水要用疏,而不能用堵。但疏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要把那么多的部族和人口迁徙到别的地方,这个工作其实不好做。加上水情紧急,需要他临机处置,一个“窃”字表明是他临机做出的决定,而“不待”则说水情紧急,没有时间反馈信息、通报水情了。但是洪水太大,没有堵住,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治水失败,既得罪了舜帝,也获罪于天下,杀之必然,《史记》里讲:“天下以舜之诛为是。”[4](P21)
(三)关于“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杀鲧是问责,治水失败,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个责不能由舜来承担,那就只能是鲧。对于其他的部族和受灾的人而言,杀鲧是必然的,可是对鲧的部族和鲧本人而言,则是委屈的。如此巨大的洪水,已经超出了当时人类的应对能力,无论鲧如何努力,恐怕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鲧的悲剧是天定的。“鲧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死后尸身三年不腐,这种文字的叙述,表达的是强烈的愤怒。流了汗还要流血,付出了辛苦,还要付出生命,鲧部落的不满,可想而知。所以帝舜玩了个政治平衡术,杀鲧的同时又启用鲧的儿子禹,这就把两边都安抚了。
禹治水用疏的办法,这个办法既符合舜的意志,因为舜是主张疏的,也符合自然的意志,因为这时再用疏的办法,就没有什么阻碍了,反正都淹没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禹因势利导,治水成功,但禹的成功是建立在鲧失败的基础上的。没有鲧就没有禹,这就是“鲧复生禹”。“复”即“腹”字。禹是从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是神话的表述方式,当然不可信。但可以说明的是,禹的事业是建立在鲧的基础上的,鲧当然不是禹的母亲,但鲧的失败是禹的成功之母。禹既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也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最终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
关于禹的治水,后面的神话有许多记载,这里不一一赘述。以上从历史的角度,还原了“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神话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三、诗性的历史
神话自然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沉淀着历史的内容,它变形地反映着历史。但是原始人类为何要以这种浪漫的文学形式来表现书写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原始“诗性文化”。
“诗性文化”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创立的一个范畴。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谈论“诗性文化”,他认为原始文化就是诗性文化。在维柯看来,原始人类之所以要以神话的方式来记事,来书写历史,与原始人类处于“诗性文化”阶段有关。
第一,原始文化是一种以艺术(广义)为载体的全息性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形态,除了原始艺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文化形态,原始艺术的范畴几乎就相当于原始文化的概念。原始艺术承担着全面的社会功能——传递信息、教育氏族成员、组织生产和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等。总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切交流、沟通和联系均在诗性的、艺术的形式和氛围中展开。[5](P68~70)比如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还处在诗性阶段,歌舞是他们认识、理解世界的全部方式。又如《诗经》现在是文学的形式,可是在当时却是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诗歌的功能,这说明《诗经》是原始诗性文化的遗存。
第二,原始文化是以原始型的审美思维、诗性思维为基础的文化。先民以一种“以己度人”的方式来理解一切,解释一切,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都以一种诗性的方式,也即感性的、拟人的方式展开。[5](P71)原始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对世界的探索是从零开始的,没有可资借鉴、参照的坐标体系与知识体系,一切都得从自身开始,于是自己的经验便是一切认知的起点,是认识事物的参照系。“……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6](P250)他们“从实际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出第二自然”[7](P564),即把自己的经验投射到外物上,把自己和外物联系起来了。太阳的东升西落,就如同人从东走到西一样,于是有“东隅”“桑榆”之说,天下大雨,就如同东西破了兜不住一样,于是有了“补天”之说;“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腹生禹”也一样,都是从自身经验中产生的认识。
他们将宇宙人情化,把物我一体化,世界是“我”的世界,宇宙是“我”的宇宙,一切都从自我的维度来解释,这便是一种诗性的、审美的思维。我们所知道的《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等,都是这样的,而且年代越是久远,这种特性越是突出。
第三,原始文化是一种浑一性的文化。在原始文化阶段,不仅诗、歌、舞等艺术形式浑然为一,而且,它还是载负着原始文化全部内容的全息的浑一性。也就是说,在原始文化阶段,文化是无法分门别类的,诗是历史,诗性化的神话也是历史。“在具有神话思维的原始人中,这种虚幻的神界故事却是绝对真实的。”神话故事在古希腊的定义中就是“真实的叙述”。[8]
原始人类的诗性文化特性与他们的思维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停留在对事物形象思维的阶段,这是由他们的认识水平决定的。理智类概念的确立与普适性知识的形成,这是后来的事,在中国大概到了西周时期才得以最终确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说明,孔子已经认识到了神话的非理性特征。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黄帝四面”时,孔子解释为“黄帝派四个人去管理四方”,这就不是神话的解读,而是历史的解读了。
四、传承方式
神话是诗性的历史,而诗性的历史又与原始时代的传承方式有关。
人类传承文化与知识的方式到今天大致有四种:一是遗传传承;二是大脑传承,也叫口头传承;三是文字传承;四是电脑传承。这四种传承方式的特点与作用各不相同,分别形成了四种文本,即遗传文本、大脑文本、文字文本和电脑文本。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如何传承文化知识、记住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口头传承,除了大脑文本,原始人类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口头传承是对后天学习、实践得来的知识的继承,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记忆,而且要一代又一代人反复进行,才能流传。最生动、最鲜活的内容,也最容易记住,而体现生动、鲜活内容的艺术形式也就成了最好的书写方式,神话、诗歌当然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几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它们最早的历史书写无一例外地不是诗歌,就是神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与口头传承的特点有关。
口头传承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时空性,即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由人们共同来完成,否则就无法传播,也无法理解;第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口耳相传;第三是言传身教。因此原始的文化知识的传承必须在原生语境进行,离开了原生语境,传授与理解都无法完成。传授与理解的双方必须在一种氛围中进行,双方必须投入情感与生命,用心去教与学,因而双方必须具有一种诗性的精神。例如,我国彝族的文化传承,他们古代书写的传统中从来没有散文体的作品,所有涉及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宗教、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技艺等的学科,几乎都是以诗歌的形式书写的。在方式上,也是以声教、示范、表演、辩论、故事等为主,而且伴随着身体动作、手势、唱腔等,洋溢着艺术的精神。传授的过程也是在一定情境中进行的,如宗教仪式、祭祀活动、族群集会等。[9]
因此,原始的歌谣、神话、传说,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咏唱、讲述才有意义;神话只有在庄严的祭祀典礼上伴随着请神、送神的仪式而由祭司颂说才有意义;传说只有在祭祖仪式上,伴随着祭祖活动,由家族中的长老讲述才有意义;歌谣也往往是在春飨秋尝的祭祀中,由人们载歌载舞才有意义。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不断地重复与演示,历史与文化就被保留下来了。[10]
可以理解的是,“鲧禹治水”以及其他神话,应该是后来在祭祀活动中,我们的先民对于历史场景的回忆,是后人对于祭祀表演的一种记载,而非真实场景的记录。这种晚出的文字记录,蒙上了历史神秘的面纱,在记载历史实景的背后,也体现着先民的情感、认知与批判。“洪水滔天”是实录,也是面对自然巨大压力的艰难承重;“窃”既是鲧面对洪水的无奈之感,也有对鲧的贬斥之意;“息壤”既是治水的实际办法,也有对这一办法的无限憧憬;“鲧复生禹”既有对鲧治水功过的评价,也包含着对鲧因公而死的无限同情。这些充满着张力的文字之间,回响着我们的先民内心的激荡之声。
文字传承有巨大的优点,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传之久远。但是文字传承也有缺憾,就是它不能记载原生语境的具体性。由于文字的传承是脱离原生语境的,文化的传授与理解不需要共同参与与具体感受,因此文字所记载的内容一年两年还好说,十年八年就在变,一百年就可能与当时的情形截然不同,一千年以后,就更加不知所云。脱离了原生的语境,脱离了与之共生的仪式与制度,神话就会变得莫名其妙。所以在春秋时代,神话已经是绝学了。这个困难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发生,屈原在《天问》中说:“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古人对于神话的理解尚且如此,今人就更加困难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袁珂.中国神话选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王利器.史记注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5]顾祖钊.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8]杨文虎.神话思维的发生[J].文艺争鸣,1990(6).
[9]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J].读书,2003(10).
[10]刘宗迪.文字原是一张皮[J].读书,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