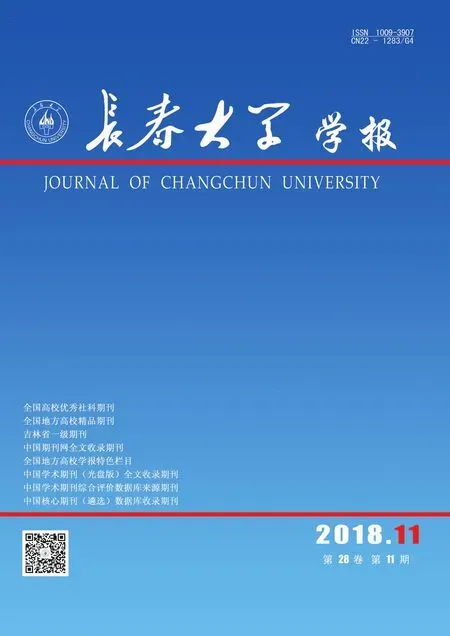奥斯汀小说中的庄园改建与审美
2018-03-20姚颖
姚 颖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乡村庄园既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权力媒介,也是奥斯汀时代英格兰乡村审美的集中体现,浓缩了摄政王统治时期的建筑与景观设计所注重的“投入”、“幻想”和“隐蔽”。18 世纪末,庄园主们需要的是富于浪漫色彩的景象——湖泊、林荫道、一片广袤之地或是一片灌木丛,在这漂亮的邸园里骑马散步,喝茶会客。简·奥斯汀将自己长期生活的乡村景色和亲友们住宅的设计、改建精确地描绘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尼克森(Nigel Nicolson)这样想象:“悠闲的旅行让简·奥斯汀可以四下张望乡村和集市广场……她观察窗外掠过的城镇与乡村的房屋,将它们添置进自己脑子中对建筑风格的储备中。”[1]《理智与情感》中的诺兰庄园、巴顿庄园和米德尔顿庄园,《傲慢与偏见》中的彭伯利庄园和内斯菲尔德庄园,以及令人神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都有自己的美妙景致”[2]132,也正是奥斯汀世界中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伊丽莎白·班内特、法妮·普莱斯甚至家境富足的爱玛都在爱上男主人公之前先爱上了他们的庄园。起先,拒绝达西求婚的伊丽莎白在参观了豪华气派的彭伯利庄园之后,怦然心动,觉得:“在彭伯利当个主妇也真够美气的!”[2]195当后来她接受了达西的求婚,姐姐简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达西时,她也老实承认:“应该从我最初看到他彭伯利的美丽庭园算起。”[2]339《曼斯菲尔德庄园》更是以庄园为题,说明曼斯菲尔德庄园本身确实不逊色于小说中任何一位人物。当读者随着离开庄园3个月的法妮回到曼斯菲尔德郊野的时候,在看见“时髦的、优雅的、环境优美的大宅本身”之前,“触目皆是翠绿的草地和种植园,林木虽然尚未浓叶蔽枝,但却秀色可餐”[3]383。
聚焦奥斯汀笔下以改建的庄园为代表的乡村新景观,得以了解这个时期的景观审美折射出的英国乡村经济、文化和审美等方面的变革,并剖析奥斯汀对这些改变的真实态度。
1 “世外桃源”的新审美形式
摄政王时期,庭园设计成为新的潮流,很多画家、诗人、戏剧设计家纷纷转行,包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威廉·肯特(WilliamKent)、“能人”布朗(CapabilityBrown)和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Repton)。他们着力将乡村庄园改建成宛如坐落自然之中的世外桃源,周围不再是泾渭分明、死板的花坛和小径,使庄园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与大自然无缝统一,并在环境改造中有意融入希腊、罗马和英伦等元素,讲究风雅。
达西先生拥有的彭伯利庄园就是完美的例子。“这是一间匀匀称称的大屋子,布置得十分雅致”,“位于山谷对面,陡斜的大路蜿蜒通到谷中。这是一座巍峨美观的石头建筑,屹立在一片高地上,背靠着一道树林葱茏的山岗。屋前,一条小溪水势越来越大,颇有几分天然情趣,毫无人工雕琢之痕迹。两岸点缀的既不呆板,又不做作……它那天然美姿丝毫没有受到庸俗趣味的玷污”[2]195;从庄园里往外看,“窗户外面是一片空地,屋后树木葱茏,岗峦叠嶂,居间的草场上种满了美丽的橡树和西班牙栗树,令人极为赏心悦目”,远处绮丽的景色随着房间窗口的不同而变换姿态,“不管走到哪个窗口,总有秀色可餐”[2]210。
在这样的景致中,地主与佃农之间历史悠久的联系被抹除,圈围公田、农村普遍资本主义化的现实掩盖在与自然融合的面纱之下,这是经济生产改良中一种对自然的科学理解的审美形式[4]。
2 景观审美下的庄园改建
为了跟随这样的潮流,也为了使庄园背后的经济现实得到升华,改建庄园成为当时英国乡村的新风尚。雷普顿本人在《景观园艺理论与实践考》(ObservationsontheTheoryandPracticeofLandscapeGardening,1803)中声称,至少设计了200个这样的庄园,还提到了艾德稠普(Adlestrop)的工作。当时这个工程由庄园主交给奥斯汀的舅舅托马斯教士监工。托马斯在继承了丽石庄园后,随即再次聘请雷普顿在1807年到1809年间进行更大规模的类似改建。此时的奥斯汀正在着手《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创作。这显然给了奥斯汀灵感,她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了4个庄园的改建,还直接提到了雷普顿对庄园的改建。
拉什沃思先生首次出场是去邻郡看望一位朋友归来,就提到这位朋友请雷普顿先生改建了康普顿庭园:“真是完美极啦!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哪个庭园变化如此之大。……如今,通往庭园的路可是乡间最讲究的一条路了”[3]45-46。亨利·克劳福特21岁就改造过自己的庄园埃弗灵厄姆,格兰特太太认为它“可以与英国的任何庄园比美”[3]53。克劳福特给埃蒙德提改建桑顿莱西的意见时说:
……房子的正门和主要房间必须处在风景优美的一面,……你那条路应该修在那里——让它穿过花园现在坐落的地方。在现在的房子背后修一个新花园,向东南方向倾斜——这就构成了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观。……现在这座花园以及将来新修花园外边的那些草地,从我站的地方向东北面延伸,也就是通向穿村而过的那条主要道路,当然要统统连成一片。这些草地在树木的点缀下,显得十分漂亮……[3]208
很明显,这建议是以艾德稠普的改建为模板:雷普顿建议托马斯移走了一条路,将大屋前后倒了个,将牧师住所附近与大屋的土地融为完整的景观花园,将小溪拓宽为大屋后面的人工湖,这样整个景观的视野不会被田地里劳作的景象所破坏。
对庄园改建的问题,书中人物的分歧愈发明显。索瑟顿庄园“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建造的,是一座高大周正的砖砌建筑——厚实而壮观,有许多舒适的房间”,但是“地点选的不太好,盖在庄园地势最低的地方”[3]49。拉什沃思在看过康普顿后,觉得自己的庄园“俨然是一座阴森可怖的旧监狱”[3]46,打算请“雷普顿或他这行的随便哪个人”把它装扮得富有现代气息。拉什沃思的平庸愚蠢更突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冲动,他没有主见,只是盲目跟随潮流而已。伯伦特小姐也认为“这座庄园非得改造不可”,“这里的风景还不错的,这片树林挺漂亮的,不过大宅的位置很糟糕”,“由于地势不好,从哪个房间都看不到多少景色”,她觉得这里的优点是“教堂离大宅不是很近”,因为“教堂的钟声搅得人实在心烦”[3]72-74。虚荣的伯伦特小姐只关心自己的福祉,对教堂的态度也充分说明这位未来的庄园女主人没有责任心与道德心。与他们不同,范妮更欣赏索瑟顿的历史感,古老的房子让她肃然起敬。当拉什沃思说要砍掉林荫大道,法妮引用考珀(William Cowper)的诗句委婉地表达不满:“你倒下的阴路大树啊,我又一次为你们无辜的命运悲伤。”[3]49对于谁应该负责主持改建,玛丽·克劳福特“把亲自参加改造看做最讨厌不过的事情”,“希望乡下样样东西应有尽有,什么灌木丛啦,花园啦,还有不计其数的粗木椅。不过,建造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用我操心”[3]50。埃德蒙则认为,“假如我有一座庄园要更新的话,我就不会听任改建师一手包办。我宁愿改得不那么华丽,也要自己做主,一步一步的改进。我宁愿自己做错了,也不愿让改建师给我改错了”[3]48。
然而,小说内外改建庄园的潮流都已势不可挡。数据显示,在占地超过3000英亩的353所大宅中,虽然各自开始重建的时间不一,但是在1810年-1880年之间,超六成的庄园改建工程进入白热化阶段[5]。这些数据还只包括了规模较大的完全重建,不包括对外墙等的改建,也不包括像奥斯汀家和她的亲戚们所居住的小型屋舍的改建。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在奥斯汀的小说中为什么这么多房子被冠以“现代”。奥斯汀死后,她哥哥爱德华的儿子,即威廉·奈特(WilliamKnight),于1823年将奥斯汀父亲的牧师居所连同向东延伸的路边村舍一起拆除。1826年,他在对面的山上修建了壮观的别墅大宅,遥望重新整治的土地,远离逐渐没落的教区教堂[6]。
3 反讽到批判:奥斯汀的审美观
当时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驱赶了教区居民,而时兴的景观审美进一步导致了庄园与教区教民的割裂。这种景观审美将教堂与大宅分隔,从大宅的窗户望去看不到人民劳作的田野,遮蔽了令人不悦但又必需的功用。这种审美后的主导价值观是认为“摒弃劳动不仅是体面的,而且是保持身份、礼俗的一个必要条件”[7]。奥斯汀在其小说中是以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呈现这种景观审美的。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亨利的这些建议是在“投机”纸牌游戏中提出的,他教授范妮这个游戏的秘诀就是“要贪得无厌,要心狠手辣”[3]206,也暗示了他此时提的庄园改建意见轻率、狠辣的态度。被遮蔽的田间劳作为庄园的主人提供经济利益,而劳动者的精神幸福应该是牧师的职责所在。牧师“所担负的责任,对人类来说,不管是从个人来考虑还是从整体来考虑,不管是从眼前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负责维护宗教和道德,并因此也维护受宗教和道德影响而产生的言行规范”[3]81。有趣的是,疯狂支持庄园改建的托马斯舅舅的妻子玛丽·利,坚持牧师与教区的传统观念,坚决反对雷普顿式改建,致使艾德稠普的改建工作直到1797年她去世以后才得以进行。就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奥斯汀表达了和玛丽相同的观点:
一个好的牧师所以能在他的教区和邻近一带起到有益的作用,并不仅仅因为他讲道讲得好,还因为他的教区和邻近一带范围有限,人们能了解他的个人品德,看得到他的日常行为。[3]81
然而,对土地的贪欲还是驱赶了艾德稠普大部分的教区居民,割裂了庄园、教堂、教区与村民的联系,景观与建筑改良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割裂。
奥斯汀在作品中不止一次用反讽手法批判当时庄园改建的潮流。乡绅阶级像《诺桑觉寺》中的蒂尔尼兄妹那样,“带着绘画行家的眼光,观赏着乡间的景色”,用一些莫名奇妙的术语判断哪里可以做出画来[8]。这种装模作样的附庸风雅被《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如此讽刺:
“我对风景一窍不通,要是谈的太具体了,我的无知和缺乏审美力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反感。本来是险峻的山岭,我却称之为陡峭的山岭;本来是崎岖不平的地面,我却称之为奇形怪状的地面;在柔和的雾霭中,有些远景本来只是有些隐约不清,我却一概视而不见。”
玛丽安也认为,“赞赏风景成了仅仅是讲些行话。人人都装作和第一个给风景优美下定义的人一样,无论是感受起来还是描绘起来,都情趣盎然,雅致不凡”[9]。《爱玛》中的哈特菲尔德的庭园造型虽然优美,但因为与枫园太过相像,被埃尔顿太太大加赞赏,颇为讽刺:
“这房间从形状到大小,跟枫园的那间晨室一模一样……这楼梯多么相像,放在房里的同一位置。……跟枫园像极啦!不仅房子像……那庭园也像极了。……自己有宽庭大院的人,总是喜欢类似的庭园。”[10]269-270
《爱玛》的当维尔寺更符合奥斯汀的审美理念。当维尔寺“又大又气派,位置适宜,富有特色”,“那儿还有一排排、一行行茂密的树木,既没有因为赶时髦而破坏掉,也没有因为挥霍无度而糟蹋掉”,与哈特菲尔德比“式样截然不同”[10]357。这里不像诺桑觉寺那样摩登,有现代化的设施和众多的温室,格局也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审美。奈特利先生“想把通往兰厄姆的那条小路往右移一移,不从家用草场经过”,但“要是改道后给海伯里的人带来不便”[10]106,他就不改了。当维尔寺“不大讲究视野”[10]357,但是让爱玛骄傲的正是其主人不追赶时髦,别具一格,是“从血统到意识都纯正无瑕的地道绅士世家”[10]357。“两旁都是欧椴树”的一条路“宽而短”,“并不通向什么地方”,“顶头只看到一道立着高柱的矮石墙”。这样的格局显然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庄园审美,但是“这路本身却是迷人的,周围的景色美不胜收”[10]359。不同于改良派雷普顿,奈特利信奉理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所说的“不大讲究的风景是英国自由的表达”[11]107,“这儿景色宜人——真令人赏心悦目。英国的青葱草木,英国的农林园艺,英国的宜人景色,在灿烂的阳光的辉映下,毫无令人抑郁之感。”[10]359奈特利先生是奥斯汀小说中唯一一位从事生产粮食的地主。在英国乡村的巨大变化中,地主如果想要保有财富,必须要投身到新科学中。农业家阿瑟·杨发现绅士们开始自己打理农场,学习“耕种”和“农村经济学”[11]107。奈特利便是这样的现代绅士。他不会用农用马匹去拉绅士小姐们出游的四轮马车,他和佃农一起阅读农业报告,“向哈丽特介绍农作物种类方面的知识”[10]327,话题总是围绕实际的农业问题。
4 结语
聚焦奥斯汀笔下以改建庄园为代表的乡村新景观,将其作品重新置于历史语境中,折射出英国乡村经济、政治和价值审美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也彰显了奥斯汀对这些改变的真实态度:庄园主不应该割舍自然美,割裂与历史的联系,完全割裂与田野农民的联系,将他们和自己的责任遮蔽在这如画一般的人造美景之外;完全放手让设计师从美学而不是实际的角度将庄园改建成世外桃源,更是脱离实际、不负责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