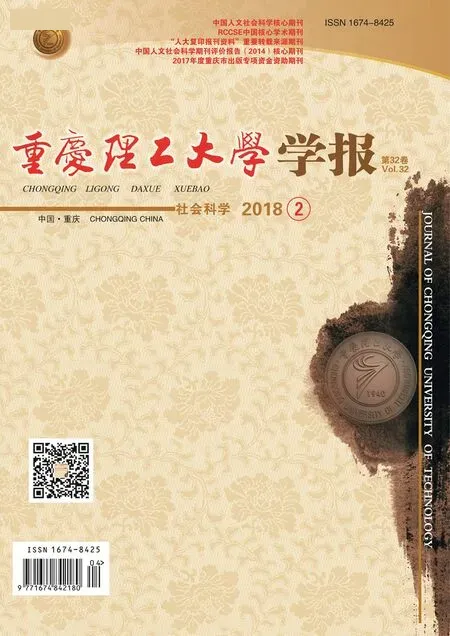公共理性的理论抱负及其现实局限
2018-03-19刘富胜
刘富胜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公共理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讨论颇多的话题。有学者认为,“公共理性”的提出,既克服了“现代性的危机”,又保留了“理性主义”的精华[1]。还有学者认为,公共理性意味着平等、参与和宽容,对促进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然而,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前提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反思,对“谁之公共理性”“重叠共识何以可能”等基础性问题并没有进行充分追问。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恰恰关系着公共理性的理论抱负能否得以实现。
一、公共理性的理论抱负
人们通常认为,“理性”是与“感性”相对的认识论范畴[3]。实际上,理性作为认识论范畴是相对较晚的事情。理性最初就是一个本体论概念。从词源来讲,理性的希腊语为λγοç(逻各斯);拉丁文为ratio(根据、原因)。理性的原始意义就是万事万物都是有其理路、有其根据。古希腊哲学探讨万物的“始基”,是人类从神话走向理性的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寻找事物真正的根据。他们从“水”“气”“火”“原子”等形下之器开始,逐渐追寻“数”“存在”“理念”等形上之道。巴门尼德区分了“存在”与“非存在”,对存在的认识是真理,而对非存在的认识就只能是意见。柏拉图区分了“理念”与“现象”,在他看来,现象只是理念的影子,现象是不真实的存在。人的灵魂受制于肉体的欲望,只能认识到现象,无法认识到真理。现象是多,本体是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只有真理才能够得到人们的共同认同。真理得到共同认同的基础就在于它符合了本体世界的“逻各斯”。
从笛卡尔开始,人们开始从主体出发寻找事物的“根据”。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思”是“在”的原因和根据,没有“思”就无法谈论“在”或者“不在”。康德更是提出,我们在对外界世界进行判断之前,应该首先清理一下我们认识能力的地基。康德要为认识建立一座“法庭”,以防止一切没有根据的“僭越”[4]5。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的认识能力严格限制在现象领域,在他看来,所谓知识是先天知识范畴作用于后天感性杂多的结果。人的知性范畴只能运用于现象之上;一旦把知性范畴运用于本体上,就会造成“二律背反”。因此,人只能为现象界“立法”,本体界是人类认识能力无法穿透的迷雾。黑格尔则认为,“二律背反”不是理性的僭越,它恰恰反映了思维的本性。黑格尔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出发,强调“本体即主体”。本体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主体是概念矛盾的自我燃烧。康德和黑格尔都强调主体性,但是他们对主体性的依赖并不相同。康德把主体分为认知主体和实践主体,认知主体能够获得客观必然性的知识;实践主体则可以成就自由意志的德性。黑格尔则强调认知主体与实践主体的合一,主体既可以获得客观知识也可以依据客观知识而获得行动自由。在康德看来,客观知识无法保证行动的善;而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客观知识的主观自由恰恰可能成为恶。黑格尔由此从道德走向了伦理,从个体走向了国家。
如果说在本体论哲学那里,理性是事物内在之理,理性本来就是公共的,那么到了认识论哲学这里,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内在于“主体性”之中。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主体既是“自由自觉的存在”,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尼采认为理性就是人与外界打交道的工具,而且还是一种卑劣的工具,是弱者战胜强者的工具。弗洛伊德更是从人的潜意识出发,认为主体是“本我”“自我”“超我”的存在,理性构成了对本我的压抑,同时也导向了超越自我的升华。主体并不纯粹,“主体性”并不是“公共性”的保证,从认识论出发难以找到“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路径。
现当代政治哲学家们另辟蹊径,通过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把“主体性”的自由和“公共性”的规则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理性的根据来源于主体,因此理性要体现为人的自由;理性的作用是达成一致,因此理性要能够确保社会规则得到承认。用密尔的话来讲就是,“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生活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5]81。在密尔这里,理性是行动的依据,而非认知的依据。在“私人领域”里面,没有是非对错,只有行为选择,个人在私人领域内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私人领域不存在任何标准。但是在“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公共规则。公共规则的理性来源于“用”,即只有它才能确保人们的自由。传统社会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不明,要么是公共权力私人化,个人随意制定公共生活的规则;要么是私人生活公共化,公共权力随意侵犯私人生活。
如果说在密尔看来,公共规则因其具有维护个人权利之用而成为“理性”;那么在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共善”[6]225。所谓“公共善”,就是它不仅对个体合理,而且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也是最优的选择。公共理性并不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从社会的长治久安出发。它考虑到个体自由平等权利的维护,更考虑到个体发展的机会平等,以及对不利者的制度安排。罗尔斯认为人们只要从“无知之幕”出发,屏蔽了个体在未来制度安排中的身份地位,就会一直选择他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应该说,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依然建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的基础上,他把理性分为“公共理性”和“非公共理性”,认为公共理性就是“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6]10。从形式上讲,罗尔斯所谈的公共理性就是公共生活需要的理性,它具有超验性,但这也是哈贝马斯批评罗尔斯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桎梏的原因;从内容上讲,罗尔斯所谈的公共理性是有明确指向的,是内在地包含着“正义原则”的理性,其本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宪法论证。
公共理性的提出是要说明,在非强制的背景下,任何“完备性学说”都注定难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只有能够得到各种“完备性学说”共同支持的原则才能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理性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重叠共识”。罗尔斯所讲的“重叠共识”只不过是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公共走廊”的现代翻版,幻想它能够得到所有理论从“自己的理由或依自身的优势”的支持。但正如认知理性难以自我澄明,总是面临着“主体性何以走向主体间性”的反思一样,公共理性也同样如此,总是存在着“重叠共识何以可能”的追问。
二、公共理性的内在悖谬
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与他人“共在”是人不可逃脱的命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反思的焦点问题。现当代政治哲学家们倡导公共理性,就是要让人们从公共生活出发,避免个体理性对人的束缚,为合理的公共生活奠定基础。问题在于,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就如硬币的两面,始终纠缠在一起。个体理性存在的问题,公共理性也难以克服。
公共理性并不“公共”。个体理性是指从个体视角、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出发的合理性。传统哲学家强调“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个体要么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炼、要么通过“辩证法”的思维研习,否则难以通达客观普遍的真理。现当代哲学家则认为,个体理性是“合理的局限性”,个体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在思维中带有个体印记。他们承认个体理性存在,同时认为人应该超越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否“公共”,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个体印记,而在于它的出发点是个体的还是公共的。在密尔那里,公共理性首先要维护的是个体利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分开之后,私人领域是绝对的,公共领域是相对的,公共领域是为个体利益服务的。公共领域需要规则和秩序,只是因为没有公共领域的规则和秩序,个体利益就无法实现。个体需要是公共规则的前提,公共规则是个体需要的保障。罗尔斯提出了“正义优先于善”,他说的“正义”就是个体权利,每个人的权利是自由平等的,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体的自由平等权。也就是说,尽管罗尔斯主张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善”的问题,就是由社会发展不平等导致的差别问题,但是差别原则永远要服从于自由平等原则,不能侵犯到个体利益。公共理性在形式上谈的是公共领域的事情,但在内容和实质上维护的是不受侵犯的个体利益。
公共理性也不“理性”。理性就是根据和原因;公共理性就是公共生活的根据和原因。在传统哲学家看来,公共生活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要么是神意的安排,要么是人性的内在需求。现当代政治哲学家都反对传统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预设,在他们看来,公共生活是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是说,公共生活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既然公共生活没有根据,那么公共生活的规则从哪里来呢?现当代哲学家不得不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预设,要么讲述“自然状态”的故事,要么讲述“无知之幕”的设计。“自然状态”是说人类最初生活在没有规则之中,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于是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纷争。纷争不能使人们得到利益,而且使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实现,于是人们开始妥协。社会规则就是人们相互妥协的产物。“自然状态”能够阐述为什么会有规则,但是它无法阐述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则。“无知之幕”是说人们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如果知道了自己在规则未来运行中所处的位置,就会让规则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只要屏蔽了这些信息,任何人制定规则都会做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公平正义的规则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无知之幕”,试图解释规则的合理性,但是它无法说明“如果人什么也不知道,他又怎能制定规则”的问题。
公共理性难以为合理的社会秩序“奠基”。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只要人们足够“公共理性”,就一定会选择“此种社会秩序”而非“彼种社会秩序”。现当代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公共理性是“重叠共识”的基础,“重叠共识”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要人们从公共领域出发,从“公共善”出发,就“一定”会产生思想上的某种交集。事实上,不同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相互一致的,有大同小异的,也有截然对立的。
公共理性对“重叠共识”的承诺难以实现,就在于现当代哲学家们总是从理性出发来看待社会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存在来审视人的理性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密尔反映了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的诉求,而罗尔斯则反映了发达富裕时期资产阶级的向往。公共理性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如果忽略了其阶级性的内容,就很容易被它的理性外表所迷惑。
三、公共理性的现实局限
从理论上讲,公共理性的提出就是对公共生活的否定,公共生活成为了“无根的生活”。公共领域既无自身价值也无自身的规则,其存在仅仅是维护私人领域的绝对自治。从实践上讲,公共理性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片面地提倡公共理性只能导致对现实苦难的漠视和对个体自由的践踏。
公共理性立足建构而非超越,将成为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辩护力量。公共理性要为公共生活制定规则,但是它并不追问公共生活自身的合理性。在现当代政治哲学家看来,只要人们足够“理性”,就会认同他们所提出的规则。他们所设想的理性是没有前提的抽象理性,是与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理性,即无论现实生活的境遇如何,人们都会拥有共同的理性。马克思认为:“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525公共理性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理性,它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反思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而是远离社会生活,并要求人们服从现实生活。公共理性所提倡的规则,是维护私人领域自治的规则,是追求“形式平等”的规则。在公共理性主义者看来,只要个体拥有私人领域的自治,而且这种自治的权利在形式上是平等的,理性的任务就完成了;任何超越“形式平等”的向往和追求都被视为是一种“僭越”。哈耶克、弗里德曼、波普尔等人还一再地警告人们,追求“实质平等”是理性的自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公共理性立足划界而非解放,将成为个体自由的压制力量。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表面上看是权利划分,实质上是责任划分。公共领域是个体自由的边界,个体只能在私人领域内拥有自由,在公共领域要服从规则。私人领域不是公共理性的对象,只是个体理性表演的舞台。公共理性放弃了“私人领域”,就意味着私人领域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个体负责。应该说,现实生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现实中的某种生活只是社会的“个别现象”“偶然现象”时,个体性因素就成为现实生活的主要原因,个体就应该为自己的现实境遇负主要责任;但是当现实中的某种生活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和“必然结果”时,个体就没有理由再为这种境遇承担主要责任,社会就需要进行制度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困难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公共理性对私人生活领域的放弃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就是“自由”;对无产阶级而言就是无可奈何的“苦难”。抽象资本对具体劳动的宰制从形式上看依然是“平等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达成了劳动力买卖的“契约”。公共理性主义者要工人屏蔽自己的地位和信息,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资本家;但现实上只有具体的个体,没有抽象的任何人。现实生活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一旦成为“恒定不变”的合理,就会对个体自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工人只有将劳动力出卖给“这个”或者“那个”资本家的自由,而没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宏大”,而且“具体”,是避免公共理性误导的“解毒剂”。历史唯物主义被不少现当代哲学家视为是“宏大叙事”,它所强调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让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8]141。他们不仅夸大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的要求,而且忽视了“宏大叙事”对社会的拯救。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坚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和螺旋式地上升,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它应该被超越而且能够被超越。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 主张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解放的前提,“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9]。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公共领域内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选择。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不仅不能带给人们自由,而且会加速人们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决定了人们“公共领域”平等的形式化、“私人领域”自由的虚幻化。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对立状态,人们在思维方式上才能真正地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才会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才会达成社会合理秩序的“重叠共识”。
总的来说,公共理性不是没有前提的绝对理性。它从抽象人出发,通过“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分的教条,维护着“形式平等”但“实质不平等”的现实。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现实生活的对立是人们思想分歧的根源,现实生活的和解才是理性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根本保证。
[1] 韩璞庚,陈平.罗尔斯“公共理性”及其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07(5):54-58.
[2] 钱弘道,王梦宇.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18-32.
[3] 张昌盛.从现象学的先验感性论到生命主体间性[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2):18-22.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 詹晓非.从马恩书信看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依据[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4):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