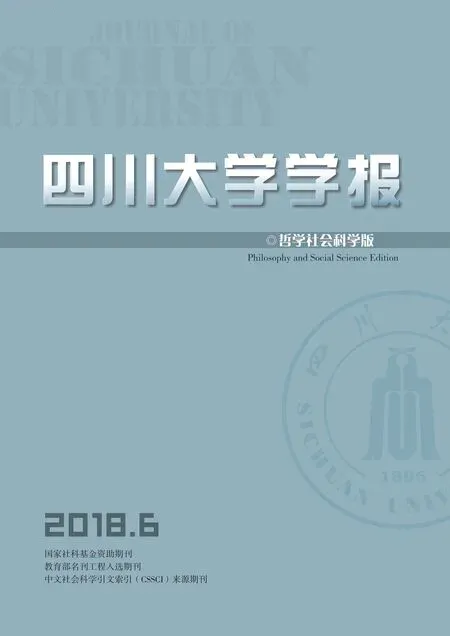资本、现代性与社会建构
——基于夏威夷王国历史的考察
2018-03-17王华
王 华
资本负载着一种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和促使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强制性客观力量,它的出现成为现代性的真正根源。自近代以来,随着其运动和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资本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空间,“釜底抽薪式地消解着依靠剩余劳动支撑的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同时也在建构着不断扩张的新的社会生产系统,并进而衍生出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现代性也在此过程中生成”。*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64-65页。资本的确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它把生活世界的一切纳入其运转体系之中,并将之打造成为各种具有现代性的事物,这就是资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夏威夷近代社会的发展即是如此。资本的巨大张力,首先直接促成了夏威夷物质生产体系的改变,建构现代经济结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分工结构、市场结构)的过程得以开始。紧接着,它也在其他所有的社会结构领域激发出深刻的变革:消解传统的等级关系、族群关系、友邻关系,总之是人与人之间一切原有的社会伦理关系,并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将之重构。于是政治、社会、宗教以及人本身,都开始接受和呈现新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启蒙理性作为资本的产物同时也是合作者,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4页。在资本的社会建构作用下,现代性终于从夏威夷社会的内部全面萌生。*不论是作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独立国家或地区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国内外学术界对夏威夷王国历史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早在20世纪30—60年代,就出现了分别以哈罗德·布莱德利的《夏威夷的美国边疆》和拉尔夫·凯肯德尔的三卷本《夏威夷王国史》为代表的一批通史和专题论著。70年代以后,受到后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转向的影响,夏威夷社会变迁问题开始得到更多关注,在分散而具体的一些主题上(经济、文化、疾病、女权等)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例如马歇尔·萨林斯、O·A·布什尼尔·鲍林·杜金斯佳等。但这些研究一则更趋个案性,二则其理论方法往往只适用于对特定领域甚至问题的阐释,因此在对夏威夷近代社会变迁这一长时段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和宏观结构演替的揭示方面缺少足够的解释性。正是在试图对夏威夷近代社会转型的宏观结构性变化进行解释的思考中,笔者重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资本和现代性对这一问题的可释性和合理性。此处所涉之“现代性”,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将对“现代性”的关注置于其制度性维度,即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概念所界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以及作为表状和具象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深层趋势、持久进程和特征。亦与吉登斯作为现代化后果的“现代性”较为接近,即涉及人、事物、社会等呈现的性质或状态,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转型。国内学者对资本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郑杭生、刘敬东、孙正聿、高宣扬等的文章都对笔者理解资本和现代性问题产生了影响,其中从鲁品越、骆祖望和刘同舫的文章中受益最大,在此谨致谢意。关于资本究竟如何影响夏威夷经济形态的变化,促成现代性在社会生产系统领域生成的内容,尽管构成本文所述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但因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资本与传统社会现代性的培育——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历史佐证》中专题论及,故此不再赘述,仅将重点置于资本力量影响下现代社会结构在夏威夷的初步衍生和发展,特此说明。本文立足于夏威夷近代社会变迁的史实,力图通过对其在宗教与思想观念、政治与社会、国家与主权三个领域所发生演变的逻辑梳理,围绕“人”这一能动性主体,揭示夏威夷王国如何在资本这一社会变迁原动力的作用下,逐步滋生成长出“现代性”,初步完成近代社会结构的再建构。
一、宗教、理性与现代性
宗教是夏威夷社会结构演变和现代性萌生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多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1819年禁忌体系的废弃视作打破传统束缚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但在笔者看来,“破”只不过是宗教信仰领域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它的确对此后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条件作用,但说它是最关键的就未免言过其实,与现代性就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如果没有新的“立”的发生,这种“破”也许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局部的改变,甚至还可能出现传统的回流。这一担心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主要是因为资本力量业已给当时的夏威夷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根源性改变,再加上与之直接相适应的基督教的传入和迅速发展,促成了结构性变革的发生。
1778年库克造访之后,欧洲文明要素(商品、贸易和观念)的渗入逐渐在夏威夷宗教领域产生影响,在对物的观念发生改变的同时,夏威夷人对自然神和神力的坚定信仰也被动摇了,传统信仰体系、宗教生活方式都在悄然变异,对信仰体系的怀疑、对禁忌体系的不满和破坏不断发生。卡梅哈梅哈一世借助君权强化传统信仰的努力也无法再改变什么,最终在1819年,长期的累积终于得到爆发,新登基的利霍利霍国王公开废弃禁忌体系。*王华:《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1-124页。这场借由废除禁忌抛弃传统信仰的行动是从夏威夷社会内部发生的,在绝对君主权力出现暂时性真空的时候,由高等禁忌女酋长发动,以国王谕令的形式完成,原因是她们早已不满于禁忌体系把女性限制在远低于男性的不平等地位。该事件的形式其实再简单不过,在卡梅哈梅哈一世去世后的哀悼仪式期间,他的两个妻子奇奥普奥拉尼和卡阿胡马努就公然打破禁忌与男酋长同桌进食。她们还宣布说:“就我和我的人而言,我们想从禁忌中解放。……丈夫与妻子必须在同一个炉灶中烹煮食物,在同一个食具里吃饭。我们也要吃猪肉、香蕉和椰子,要像白人那样生活。”*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历史之岛》,刘永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半年之后的11月,新王宣布废除饮食禁忌,公开与女酋长同桌进食,随后又下令拆毁所有神庙和偶像,并剥夺了祭司宣布禁忌和提供牺牲的权力。*Ralph S. Kuykendall & A. Grove Day, Hawaii: A History, from Polynesian Kingdom to American Stat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48, p.225.由是,禁忌体系从夏威夷社会内部崩溃,而“整个禁忌体系崩溃的同时,传统宗教也垮掉了”。*William R. Castle, Jr., Hawaii: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7, p.38.
禁忌体系的废弃打破了束缚着夏威夷人的传统精神枷锁,为一场新的宗教和思想革命提供了机会。就在1819年下半年,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夏威夷传教。1820年初,来自美国的第一批新教传教士也抵达群岛,并很快为传教事业打开局面。与禁忌系统的废弃始自女酋长(这类似一场“女权革命”)一样,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夏威夷站稳脚跟并广泛传播,也跟女酋长们的支持密不可分,它其实是前者的自然延伸。与其说是信仰真空状态下的宗教渴望,不如说是这全新的基督教文明展现出的更趋平等化的两性关系,对高等级女性酋长如奇奥普奥拉尼和卡阿胡马努形成了莫大的吸引力,她们很快接受基督教并给予坚定支持。奇奥普奥拉尼最早推动了新教传教事业,她在1823年临去世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最高禁忌女酋长成为了夏威夷第一个皈依者”。*Juri Mykkanen, Inventing Politics, 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47.其后,卡阿胡马努继续推进新教传教事业,使之繁荣,并将基督教信仰与王国的统治相结合。1825年,卡阿胡马努入教。1830年起,卡阿胡马努利用自己摄政的身份,动用国家权力强行在夏威夷推行基督教,禁绝巫术和其他宗教。正是在她的政策下,夏威夷传统宗教体系彻底崩溃。[注]Samuel M. Kamakau, Ruling Chiefs of Hawaii, revised edition, Honolulu: Kamehameha Schools Press, 1992, pp.298-299, 307-308, 321-322.1832年卡阿胡马努去世,卡梅哈梅哈三世的姐姐基纳乌成为新摄政,继续其前任对新教的支持政策。与此同时,她也将卡阿胡马努于1829年开始的禁绝天主教措施推行到极致,从而引发了30年代末新教与天主教的大冲突。1839年基纳乌去世,在法国的军事要挟和战争威胁下,夏威夷实行宗教宽容,给予了天主教与新教同等的地位。夏威夷上层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支持政策,加之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导致群岛迅速基督教化。自1823年出现第一个新教皈依者,十年后夏威夷的新教信徒已经达到577人,还有几百个天主教徒。[注]Trevor Lummis, Pacific Paradises: The Discovery of Tahiti and Hawaii, Strou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2005, p.172.1837—1843年,夏威夷更经历了其基督教传播史上的所谓“大觉醒”时代,6年间有约2.7万名夏威夷人皈依基督教,占到当时夏威夷总人口的近21%。[注]Belle Marvel B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waii: How American Missionaries Gave a Christian Nation to the Worl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8, pp.89, 117.殆至1846年,基督教更正式成为了夏威夷王国的国教。
毋庸置疑,夏威夷的基督教化本身就是其现代性的一个直接表现。从传统宗教过渡到基督教,决不是从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那么简单。正如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夏威夷式的传统宗教具有强烈的巫术和原始的意味,他们因此宁愿视之为“崇拜”或“巫术”,而拒绝使用“宗教”这个称谓。即便在当今的学术界,这种观点也不是小众的存在。基督教则被认为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宗教,在经历了始自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已经与资本主义实现了基因的整合,改革后的基督教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获得并体现了现代性。传入夏威夷的正是改革了的新的基督教,这种外来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力量一旦植根到夏威夷社会本身,成为它的固定组成部分,其中的现代性也就必然转化为这个社会的一种内在要素。所以,如果我们认定基督教本身属于现代性的范畴,那么当然就可以说,由于基督教化的发生,夏威夷在信仰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造,在世俗的物的观念嬗变的基础上,夏威夷人又在精神层面发生“异化”。更何况,基督教本身所蕴含的启蒙理性要素,还进而直接促成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原则在夏威夷的确立。
基督教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异,反过来推动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并影响生产结构的改变。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的发展正是“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的伟大历史过程。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例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它一方面更多地促使了获取私有财产的能力的释放,另一方面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道德,即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伦理:只要资产阶级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他们还会获得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劳动成为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由此对这种资源劳动的利用也合法化,即把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一种天职;劳动者也将因为禁欲主义而变得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韦伯认为,“这一切,很明显,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力的影响”。[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79、117、119-120、138-140页。基督新教是夏威夷基督教化进程的主力,群岛的基督教化主要由美国的新教传教团促成,1843年之前的皈依者中,大约4/5以上都是新教教徒。新教信众还占据了夏威夷统治阶级的绝大部分,而天主教的影响力更多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鉴于19世纪中叶之前夏威夷社会变革的力量主体存在于统治阶层的现实,我们就可以想见新教对夏威夷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了。当然,宗教的影响很难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进行准确的评估,我们只能结合这一时期不同社会结构领域的变化事实作出这样一个大致的推断。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宗教的辅助性作用下,资本力量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在诉诸于人的“异化”意义上,对社会伦理关系、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进行了“理性化”的改造。
传教士带给夏威夷的绝不只有基督教信仰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作为殖民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在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与资本力量一起,建构出一幅夏威夷社会的新面貌。传教士为夏威夷人带来了“文化的革命”,他们为夏威夷创造了可供书写和阅读的文字,并把西式教育引进这个群岛。1822年起,传教士创立并改进完善了字母表,以此为基础将当地人的语言转变成了可书写的文字,通过印刷和普遍发行,从本地成年人开始进行普及性扫盲。与此同时,他们在夏威夷各处设立学校,亲任或从母国引进教师,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培养当地教师和学生,推广夏威夷语和英语,教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组织翻译圣经。[注]Kuykendall & Day, Hawaii, p.45; Kamakau, Ruling Chiefs of Hawaii, pp.248-249.正是在此基础上,夏威夷王国在19世纪30—50年代发展起了较为系统的现代学校教育。传教士们将扫盲、宗教开蒙跟西式思想科技文化教育相结合,推动了夏威夷的“文明开化”,在文化思想领域培育出了现代性要素。1840年前后夏威夷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正是这一教育和文化发展的结果表现之一。他们还为夏威夷引进了自由报刊这种“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从1834年第一份本地语报纸《夏威夷名人》由美国传教团在毛伊岛创刊始,在十年里,各国传教团共创办4份本地语报纸,在当地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注]Helen Geracimos Chapin, “Newspapers of Hawai‘i 1834 to 1903: From He Liona to the Pacific Cable,”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18, 1984, p.51; Noenoe K. Silva, “Early Hawaiian Newspapers and Kanaka Maoli Intellectual History, 1834-1855,”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42, 2008, pp.105-134.文字的发明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必然会深刻影响其所在人类社会的凝聚性结构演变。就其对夏威夷的文化影响而言,随着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传教士们推动着夏威夷人展开了“文化的再生产”。不仅新文化被引进和传播,传统历史和文化也被解释性再造。书写文字的强大力量在于,一旦它被创造出来,并且与启蒙文化有机结合,那么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就在经筛选改造后被神话化和边缘化,沦为遥远的秘索斯记忆。“神”和不变的神话时间结构从现实中退隐了,而“人”终于被真正“发现”,并开启了其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由此,历史和传统就在不经意间被新文化改头换面,它不再是那个通过长久的民族记忆固定下来的流传有绪的现实之源。当经历过传统时期的一代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纷纷弃世,鲜活地留存在他们头脑中的交往记忆也随之消逝,文化记忆得以发生。变革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不得不主要从文字的记录中认识本民族的过去,而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已经全然是“被阐释和再造的历史”,已经是基于现实的需要而反溯式再构建起来的民族文化记忆,一种以启蒙理性为基本内核的民族文化记忆。[注]关于“文化记忆”的形成条件及其在形成过程中必然基于现实合理性去选择和遗忘的理论理解,可参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传教士所播种和培植的启蒙理性的胚芽,根本性地改变了夏威夷人本身,如果说资本首先通过商品、贸易、产业等现代经济要素让人“拜物化”,那么外来的“宗教性”和“启蒙理性”又进而将他们从精神和思想上“异化”。欧美文明用一场表面温和的剧烈社会文化变革,改造了这个传统社会的精神和世俗基因。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在夏威夷人的头脑中断裂了。在白人到来之前,夏威夷人在循环往复的时间中固化历史。而在基督教化和“文化革命”之后,这一时间意识被彻底改变了。“历史”变成了“传统”,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取代了原有的循环往复的时间观。“传统”被重新塑造成不具合理性的和落后的,而合理性和进步则只属于新文化主导的“现代”。这一文化的“重塑”,只不过是夏威夷人对自身连续性的虚构和合理性的切割式接续。
二、政治、社会与现代性
在完成夏威夷大岛的统一之后,卡梅哈梅哈一世以传统的部落制结构和传统宗教为依托,逐步创建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尽管这是在大量保留传统残余基础上的非纯粹形态,封建的大致形式和很多方面仍属部落制的实质并存,却仍算得是夏威夷政治飞跃式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并且为此后近半个世纪“封建制”的填补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毕竟,政治进程的发展不可能跳脱循序渐进的合理形态,一蹴而就地实现。其实在夏威夷(乃至其他很多因殖民运动而快速改变传统面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形式先入而内容后补的错位式政治发展是一种经常的情况,往往先有对外部世界政治形态的主动模仿借鉴,搭建起一个相类似的形式架构,实质性内容的改变只能在随后逐渐发生。[注]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政治体制的建构,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历史,他的两个入了夏威夷籍的英国顾问约翰·扬和伊萨克·戴维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资本力量在群岛的发展,夏威夷传统的权力观念和结构遭到冲击,以物质财富衡量等级地位的倾向发生,财富取代神明成为现实世界的权力来源和保证。1820年代起,酋长阶层逐渐演变成“拥有土地的贵族”,[注]W. D. Westervelt, “The Passing of Kamehameha I,”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Honolulu: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1923, p.30.并不再满足于绝对君权的权力结构。在利霍利霍统治时期,阿利伊酋长集团的势力上升,逐渐将国王置于其控制下,导致王权的收缩和绝对君主制的衰落。1825年,夏威夷确立摄政制度,并由阿利伊成员组成范围广泛的酋长会议,接手国内外事务的议决权和部分立法权,摄政与酋长会议间的共谋关系使之初具一院制议会的雏形,国王事实上变成单纯的行政首脑,政治分权制度初步形成。1837年摄政制度被废除以后,国王和酋长会议继续保留,原属摄政的权力转移给酋长会议,从而使得酋长会议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立法和决策机构。[注]W. S. W. Ruschenberger,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n Embassy to Muscat and Siam in 1835, 1836, and 1837, Phila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 1838, pp.458-459.
如果说上述的这些变化还只是发生在上层权力分配上,完全没有涉及平民阶层,其显著的欧洲“封建制”特性还与“现代性”相去甚远,并且在变革的主动性力量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力量的干涉和指导,那么1839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就具有了新的转折性意义。1820年代之后以开智为目的的西式文化教育在夏威夷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夏威夷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启蒙理性之光”开始照耀他们,向往欧美政治和自由平等、呼吁改变夏威夷政治现状的呼声甚嚣尘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欧美教育“启蒙”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酋长,在30年代后期进入了夏威夷政治的中心。不仅如此,得益于传教士的传教和教育的逐渐普及化,即便在普通夏威夷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赞同革新的思想。一场政治大变革就在他们的呼吁和推动下发生了,《183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成为其开端。该法案是一份对西方类似的权利法案的模仿之作,因此充斥着欧美现代政治色彩。法案提出一切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并对平民的权利予以详细界定和保护。就其意义而言,它无疑称得上“自夏威夷二十年前废弃旧宗教和禁忌体制后最重要的法律,也是夏威夷所推行过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注]W. F. Frear, “Hawaiian Statute Law,”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Honolulu: Hawaiian Gazette Company Ltd., 1906, pp.35-36.紧接着,王国又制定颁布了《1840年宪法》,除再次申明权利法案对人权的规定和保护外,进而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出两项重要规定:一是创设两院制议会作为立法机构,在贵族院(原酋长会议)之外设立经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众议院议员每年从平民中选举产生,任何法律未经贵族院和众议院多数同意不得通过。二是在各岛分设法院和由总督任命法官,并创设王国高等法院,从而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1840年宪法》引进了欧美的三权分立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而使夏威夷步入了宪法政治的时代。1852年,又一部经过修订的新宪法颁布,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注]Robert C. Lydecker, compiled, Roster Legislatures of Hawaii, 1841-1918, Honolulu: The Hawaiian Gazette Co., Ltd., 1918, pp.12-15, 36-48.由此,具有典型西方近代政治特征的政治体制在夏威夷确立,夏威夷在政治发展上首先完成了近代化改造。
现代性特征也在其他重要的社会领域表现出来。人口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残酷的“殖民现代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一些“殖民化和现代化”最彻底的非欧地区(如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该“现代化”是以人口的替代式改造为基础特征的:原住民人口大幅削减,而殖民者和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最终,后者整体性取代前者,构成文明的新持有者。这就像是地质学里化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交替置换作用,经过对最基础的社会构成细胞的替代,这个社会肌体也就在其本质意义上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我们姑且称之为近代殖民扩张中的“替代式”文明演变。19世纪初以来,夏威夷人口结构总体呈现急剧变化的态势:本地居民人数急剧减少,外来居民人数迅速增加。据保守的估计,1778年时夏威夷共有本地人口约30万,1819年减至约14.5万,其中仅1805—1819年间人口绝对值就减少约12万,1823年减至134750人,1836年降至102579人,1853年更锐减至71019人,此后这一剧减趋势一直延续,以每4至6年8%~17.3%的速度递减。迄至1900年,纯正的夏威夷人已不足2.9万人,较之1778年减少了90.5%。[注]A. Marqu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Is the Hawaiian a Doomed Race?”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1, No.1, 1892, pp.257-258; Romanzo Adams,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A Study of the Mutually Conditioned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Amalgam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7, p.8; Robert C. Schmitt, “New Estimates of the Pre-censal Population of Hawaii,”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80, No.2, 1971, p.241.造成夏威夷人口剧减的主因不是杀戮或者出生率的下降,而是外国人带来的“文明的礼物”——病菌,如天花、麻疹、麻风、霍乱以及花柳病等。诚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说,“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积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注]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13页。1804年、1848—1849年、1853年的三场瘟疫大流行,成为原住民数量阶段性大衰减的罪魁祸首,这是可以从人口统计数据上得到验证的历史事实。1804年爆发的“蹲病”(可能是霍乱),造成至少0.5~1.5万本地人死亡,甚至有人认为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注]Schmitt, “New Estimates of the Pre-censal Population of Hawaii,”p.240; Urey Lisiansky,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4,5,& 6, London: John Booth, Longman, 1814, pp.111-112, 133; Robert C. Schmitt, “Catastrophic Mortality in Hawaii,”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3, 1969, p.67; Ralph S. 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 p.49.1848—1849年的麻疹、百日咳、痢疾和流感的混合发作,持续半年之久,导致至少1万人死亡,占到当时人口总量的约十分之一,因此也被视为群岛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灾难之一”。[注]Robert C. Schmitt & Eleanor C. Nordyke, “Death in Hawai‘i: The Epidemics of 1848-1849,”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35, 2001, p.1.1853年3-4月,天花侵袭瓦胡岛,使得瓦胡岛总人口减少了约30%,火奴鲁鲁部分城区的死亡率甚至达到了40%。[注]Scott G. Kenney, “Mormons and the Smallpox Epidemic of 1853,”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31, 1997, pp.9, 13.瓦胡岛社会陷入了恐慌和混乱,“一度导致种植园劳工缺乏,在需要人手的时候雇不到人”,[注]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1, p.328.其直接影响就是推动了50年代始外国契约劳工的输入。病菌作为欧美人强有力的隐性征服工具,为殖民者对夏威夷的征服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岛上外国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1795年,夏威夷只有大概5个白人居民,1810年已增加到“相当的数量”。[注]Archibald Campbell,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from 1806 to 1812, NewYork: Broderick and Ritter, 1819, p.166; Harold Whitman Bradley, 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Hawaii: The Pioneers, 1789-18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36.1832年,王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群岛共有非夏威夷人约400人,占总人口的0.3%。[注]Robert C. Schmitt, “A Brief Statistical History of Hawaii,”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37, 2003, p.50.1850年有了确切的外国人统计数字:1572人,三年后又略增为2119人,占到总人口的2.9%。进入60年代,由于契约劳工的引进,外来移民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878年夏威夷外国居民数突破1万,1890年更达到49278人,比当年本地人口还多出了8656人。到1900年,非夏威夷人人口数为115747人,是当时夏威夷人数量的4.03倍,人口的种族结构彻底改变。[注]Marqu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Is the Hawaiian a Doomed Race?” p.257; Adams,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p.8; Schmitt, “New Estimates of the Pre-censal Population of Hawaii,” p.241.夏威夷人口结构的变化,能够很好地揭示出夏威夷逐步殖民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夏威夷近代社会变革在人种意义上的条件基础。这种置换式人口构成的变化,是夏威夷最终发生彻底性殖民化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夏威夷原住民数量的剧减和非夏威夷裔人口数量的激增,必然导致社会发展支撑性力量的改变,发展和变革的主动权在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中逐渐转移,非夏威夷人特别是处在结构上层的欧美白人,最终主导了这场社会转型。
如果说将人口结构的改变直接视为一种现代性特征尚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因为人口结构改变而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化就明显具有现代性意味了。夏威夷原住民人口的急剧衰减,外来移民的逐渐增多,以及夏威夷社会从卡梅哈梅哈一世时期开始的一些改变,都直接导致了夏威夷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从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时期开始,夏威夷社会在完全的夏威夷原住民人口结构状态下的阿利伊(酋长)、卡胡纳(祭司)、玛卡阿伊纳纳(平民)和帕帕考瓦(奴隶)四阶层(阶级)部族式结构,逐渐演变调整成君主、阿利伊、卡胡纳、玛卡阿伊纳纳和帕帕考瓦五层格局,体现出了某些封建君主制社会结构的特征。1820年代以后直至30年代末,社会阶级进而发展成君主、阿利伊、“豪佬”(Haole,外国人,包括传教士)、玛卡阿伊纳纳、帕帕考瓦五层结构。40年代以后,夏威夷王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帕帕考瓦逐渐消失,玛卡阿伊纳纳则相应地被赋予了现代政治的身份属性,成了“私人自由公民”。[注]Richard H. Harfst, “Cause or Condition: Explanations of the Hawaiian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81, No.4, 1972, p.444.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夏威夷定居,外来移民与原住民人口形成彼消此长的趋势。外国人口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增加社会阶级的复杂性:50年代之前的白人移民主要是传教士、外国商人、政客、种植园主等,他们在本地权贵和平民之外形成一个新的阶层——“豪佬”,在地位和影响力上既受到本地权贵的一定约束,又在很大程度上居于他们之上。“豪佬”阶层在扩大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其内部的等级分化:欧美白人是上层(包括传教士、各国领事及代理、白人政府官员及其他归化的白人、未入籍欧美人),亚裔、非裔等其他人种是下层,更接近于普通夏威夷人(玛卡阿伊纳纳)。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下,欧美白人对夏威夷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初步奠定了夏威夷20年后逐渐白人化和殖民化的基础。这样,到19世纪中叶,夏威夷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这样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格局:国王、阿利伊、上层豪佬、下层豪佬、玛卡阿伊纳纳。而权贵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初步分立也已经出现,前者由国王、阿利伊和上层豪佬组成,正显露出一点向资产阶级过渡的迹象;后者由下层豪佬和玛卡阿伊纳纳组成,其中正分离和形成雇佣无产者。50年代以后大量进入的亚裔契约劳工,则迅速充实扩大了下层豪佬和无产者的队伍,构成了以后夏威夷无产阶级的主体。待到1890年代,当夏威夷人口结构发生颠覆性改变,外来人口超过原住民人口,并且上层豪佬(特别是美国人)完全把控了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时,夏威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王国,它已经在社会阶层(阶级)结构上完成了“质变”。阶级结构的变化首先属于社会生产结构的内容,其次它还与社会伦理关系相关,传统的田园诗般的关系伴随着这此消彼长的变化,渐趋转化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基督教世界的一夫一妻观念和家庭生活观念也被传教士和西方人灌输给了当地人,迅速改造了他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发了一场婚姻生活的变革。根据传教士们的早期描述,传统的夏威夷社会盛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并在“最高等级酋长”阶层中部分存在血缘通婚的事实。因此,摩尔根在有限的材料基础上,不恰当地将其婚姻形态归纳为伙婚制的“普那路亚”婚,从而造成了学界长久以来对夏威夷传统婚制的误解。[注]王华:《夏威夷婚姻形态及其近代演变研究——兼论摩尔根的“普那路亚”婚》,杨鹏飞、李积顺主编:《近代历史与当今世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1-481页。尽管如此,夏威夷传统社会形态下婚姻生活的“落后性”还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家庭制度的基础,……当然也是影响社会条件、文明和民众幸福的极其重要的关系”,婚姻形态的改造自然也成了夏威夷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重要内容。基督教传教士将其视作“将夏威夷社会从混乱带入秩序”的力量,是其“上升为一个民族和有道德的基督教国家的重要步骤”。[注]Sheldon Dibble, A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Honolulu: Thomas G. Thrum, 1909, p.211.为此,从美国传教士们来到群岛上开始,他们就在“震惊”于这里婚姻形态的混乱之余,开始着手推进其改变,逐步用基督教的婚姻观和道德观直接影响和改变夏威夷人的婚姻观念,并用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专偶婚)改造夏威夷人的婚姻形态。1822年,群岛上出现第一场基督教婚姻。1823年,酋长阶层中开始接受一夫一妻制,并迅速成为一种风尚在新派的统治层中被追捧。传教士们则将基督教婚姻观念作为布道的内容,在夏威夷平民中广泛传播。有了王室和酋长们的引领以及传教士们布道的影响,平民们很快开始比较普遍地接纳基督教式婚姻。基督教婚姻立法则在根本上普及和稳固了新式婚姻。1825年,摄政卡阿胡马努颁布第一个“禁忌”婚姻法令。1829年,王国政府进而颁布首个成文婚姻法,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宣布在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注]Kauikeaouli, Laws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Oahu: Mission Press, 1835, sec.6; Kuykendall & Day, Hawaii, p.46; Kamakau, Ruling Chiefs of Hawaii, pp.298-299, 340.基督教式婚姻立法确实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在夏威夷的稳固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促成了夏威夷人在观念上彻底转向基督教婚姻观。到1850年代中期,不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夏威夷的婚姻形态都不再是传统的样子了,整个王国已经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只有在很个别的非常荒僻偏远的角落,在农耕者和渔猎者中多少保留着一些古代婚俗的遗迹。借助于婚姻形态的改变,上帝的原则赋予了人以自然的权利和理性的法则,使之进入到合乎“文明”的新阶段,迈出平衡人际身份的第一步。
生活世界的货币化也必然在“过程中展示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形成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对照”。[注]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第68页。火奴鲁鲁(檀香山)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扩张带给夏威夷的一个物质结果和表现。火奴鲁鲁并非夏威夷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资本力量的产物。19世纪前20年,因为跨太平洋贸易的繁荣,外国商人选择了拥有天然良港的火奴鲁鲁作为远航中转站和贸易集散地。1819年时,它已经发展为外国商人汇聚、贸易最繁荣的港口,初具市镇的规模。1821年以后,夏威夷政府将首都迁至此处,由此促成它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崛起。商业的兴起、人口的快速聚居、教育的集中化发展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是此后一段时间火奴鲁鲁城市发展的主要内容。到1834年,这里已经“像一个英国二等海港”。[注]Frederick D. Bennett, Narrative of a Whaling Voyage Round the Globe, Vol.1,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0, p.208.进入40年代,市政管理机制也在火奴鲁鲁建立,不仅较为完善的治安体系和法律体系已经出现,成规模的市容改造也启动并初见成效,并先后修建起了6个码头和几个修船厂。50年代,政府又专门斥资疏浚和扩修港口。[注]王华:《檀香山: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城市兴起》,《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98-102页。一系列的措施,使得火奴鲁鲁具有了现代港口城市的雏形,并在1854年夏威夷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被正式称作“市”。[注]W. D. Alexander, “Early Improvements in Honolulu Harbor,” Fifteenth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1907, p.19.火奴鲁鲁的城市发展,为资本对夏威夷传统社会的改造提供了清晰的注脚,它是“资本扩张过程最为壮观的宏大物质表现,而生活世界货币化在此过程中展示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形成了现代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最鲜明的对照”。[注]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第68页。
三、国家和主权:现代性的悖论
如果说在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发展中,夏威夷经历的是从“我们的”(公共的)到“我的”(私人的)的转变,那么在国家的建构发展上,它则经历了从“我们的”(区域的、泛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到“我的”(夏威夷的、国家的)、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化历程。资本力量促成的自我建构的内因和殖民关系结构带来的“他者”建构的外因,共同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国家作为一个客观的形态,“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为了应对社会的矛盾对立而从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1810年,卡梅哈梅哈一世最终统一夏威夷群岛,建立卡梅哈梅哈王朝,这是国家在夏威夷的真正诞生。这个具有“封建制”色彩的岛国,已经完全符合国家所必须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统一的新王国按照地区而非氏族组织划分和组织国民。通过条块化分割土地和跨地域封地,卡梅哈梅哈一世切断了酋长阶层与原属氏族和土地之间的联系,并因此剥夺了氏族势力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注]W. D. Westervelt, “Kamehameha's Method of Government,”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Honolulu: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Press, 1922, pp.24-26.原有的世袭大酋长也被要求离开封地,与国王共居,从而确立起所谓的“虚主制”。[注]Stephenie Seto Levin, “The Overthrow of the Kapu System in Hawaii,”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77, No.4, 1968, p.420.其次,设立了公共权力。卡梅哈梅哈一世一定程度上借鉴英国的政治模式,进行政府管理,在作为国家最高首脑的国王之下,分设首相和议事会。首相掌行政、司法和商务,并兼任大司库和首席顾问。议事会“库希纳—努伊”类似长老院,主要由五名大酋长组成,早年主要负责战时行政事务和民众福祉,并享有大事议决权,甚至可以否定国王的决定,后来衰落成一个咨议机构。[注]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1, p.53.在地方上,卡梅哈梅哈一世则从忠诚的酋长甚至平民中选派了四名总督,专职负责四个行政大区的行政管理和征税。总督之下再分设次等属官,如征税官等。[注]Albert Pierce Taylor, Under Hawaiian Skies, Honolulu: The Advertiser Publishing Company, 1922, p.119; Kamakau, Ruling Chiefs of Hawaii, p.175.卡梅哈梅哈一世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在20—30年代经历过不断的发展变化,摄政制度也一度被添入其中。而与此同时,对绝对君权的抵制和削弱也伴随着这个发展历程。阿利伊阶层的上升和君主日益行政化,最终在启蒙理性的集中作用下,导致夏威夷在1840年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这样的变迁速度,在世界范围的国家历史发展中都是很少见的,资本的社会改造和建构力量之大、势头之凶猛,不能不让人感叹。
夏威夷国家形态的快速发展演变,却并不会直接伴随国家意识的相应提升,这一意识只有在“主权”(sovereignty)观念出现以后才可能产生。作为太平洋岛屿世界的一个部分,传统的夏威夷并不存在国家主权意识,实际上整个波利尼西亚都是一个具有宗教和文化同质性和统一性的“泛社会”,夏威夷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传统的夏威夷在国家观念上是完全开放式的。传统意识作用在人身上,往往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早期的夏威夷王国没能也不能摆脱这一观念框架的束缚。从1810到1820年代,夏威夷先后发生过几次对外关系事件,包括卡梅哈梅哈一世向英国寻求帮助和保护的“领土让渡”事件和抵抗俄国人意图挑拨考爱岛独立的事件,从中能明显看到统治者对主权概念的无知和主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注]Rhoda E. A. Hackler, “Alliance or Cession? Missing Letter from Kamehameha I to King George III of England Casts Light on 1794 Agreement,”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20, 1986, pp.7-11; W. D. Westervelt, “Kamehameha's Cession of the Island of Hawaii to Great Britain in 1794,” 22nd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Honolulu: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1914, p.21; Hiram Bingham, A Residence of Twenty-one Year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Hartford: Hezekiah Huntington, 1849, p.208.然而进入30年代以后,经历过多次与外国人和外国政府的接触和摩擦,加之本地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程度的提高和通过学习带来的自我意识觉醒,夏威夷统治者慢慢产生了朦胧的主权国家意识。他们在西方国家对夏威夷殖民权力的争夺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定位,不仅放弃了泛波利尼西亚社会的观念,而且还渐趋把夏威夷视同为与英、法、美等国家一样的平行甚至平等国家。在君主立宪政体建立以后,夏威夷开始独立开展对列强的外交,并在1845年立法组建外交部。经过一番努力,夏威夷先是获得了列强对其独立地位的认可,继而通过“宣誓效忠法”,试图借此保障王国政治不被外国人操纵。[注]W. F. Frear, “Hawaiian Statute Law,” 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 Honolulu: Hawaiian Gazette Company, Ltd., 1906, p.45; 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1, pp.230-238.1845—1852年,夏威夷又与列强各自谈判签订了比较平等的条约,替代了此前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与列强之间确立起一种更加平等的外交关系。至此,夏威夷的独立主权国家意识方才确立。当然,无论是国家的事实建构还是意识建构,夏威夷还只是停留在主权的层面,距离启蒙理性影响下的更成熟的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生成,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我们并未看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夏威夷产生的明显迹象,此后的历史发展也没有再给它以足够的时间和机会,19世纪末列强在太平洋的殖民扩张把所有的可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但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抹煞现代性已经在夏威夷国家建构方面初步发生这一事实。
然而在另一方面,夏威夷的国家建构从一开始就被近代殖民体系结构牢牢捆缚,太多殖民化色彩渗入其中,使得它不可能生成完全自主的国家建构。不论夏威夷在国家意识的成长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效,它在列强眼中始终是一个典型的“他者”。即便是承认其独立并给予相对的平等外交地位,也不过是因为殖民吞并的条件还不成熟,列强间的殖民矛盾未能获得解决,从而给它留下了喘息的空间。更何况人口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剧烈改变,更是从人种基础上埋下了文明“失落”的结构性诱因:一个原本已初步具有了“自我革新”意义的主权国家,终将在这一“置换式”的人种演替过程中彻底异质化。所以夏威夷国家始终是一个病态的肌体,这也成为夏威夷最终沦为美国领土扩张的果实,并被美国文明吞噬的深层原因。
当我们回顾1854年之前夏威夷社会的整体演进过程就会发现,殖民势力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无孔不入地进入并渐趋控制了它的每一个社会领域。资本力量改变了夏威夷的社会经济结构,外国人变成各种新兴产业的主人并深入到传统产业领域,实际操纵了它的经济命脉。白人从最初作为顾问进入夏威夷政府,到后来深层把控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完成了对夏威夷政治的占领,让所谓“宣誓效忠”的规定也最终沦为一纸空文。宗教领域的基督教化、文化教育领域的西化,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夏威夷人精神和思想的主宰。更何况还有“豪佬”这个新阶层的上升,人口构成上本地人种的急速减少和外来人口的迅猛增加,这种替代性的变化是殖民扩张形态中最彻底的一种类型,其最终的变化结果不再是或快或慢的演变,而是消灭!1854年,夏威夷还是完全“独立”的,但已经在事实上被西方的殖民势力全面操控,“白色化”出现在各个社会领域,它业已沦为殖民体系中的“他者”和附属。
四、结 语
近代以来的非西方社会,基本都经历了被资本入侵和征服的历史,并在不同程度上遭遇破坏和重建。通过渗透和蔓延,资本力量异化改造了“人”这一社会基础细胞和核心生产力,从而一步步瓦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并要在这个废墟上自觉地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资本的本质决定了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必然具有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在殖民条件下的非西方社会的成长,最初必然始于一种外来的植入,但仍需成长于本土的自发乃至自觉,即由外来转而成为内生。社会原本就是由人这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构成的,任何结构性的变迁都不应该是纯粹客观化机械化的结果,而是人这一主体性要素的变化在结构意义上的自然呈现。资本改造了人,人促成了社会的变迁。因此,夏威夷王国近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滋生和成长,本质上发自于人的“现代化”。1778—1854年间的夏威夷,经历了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结构的初步“现代化”。然而殖民主义在开始了这个进程的同时,也在阻碍着它的完成,并奠定下瓦解它的基础。作为资本世界扩张的目标,非西方社会并不被允许发展成为与西方一样的现代社会和国家,而只要它容纳进资本的殖民体系结构,成为边缘和附属,为中心提供发展的支撑。一旦该结构确立,非西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现代化演进反而会成为体系的破坏因素,必然遭到扼杀,区别只在于扼杀的形式。
“文明的商业”找到了夏威夷这个新市场,却并没有在此遭遇如在中国和印度一样的需求缺失和对传统服饰的偏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74页。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极其匮乏的社会,其整个社会体系几乎不具备对资本力量的任何有效抵抗。资本于是找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摧枯拉朽一般瓦解了旧的等级制秩序,催生出启蒙理性,推动夏威夷在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几乎就是一种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历程,从传统的部落社会到封建性社会,再到初步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全新社会形态,中间仅仅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是这一看上去令人兴奋的社会演进道路却让人感到无比沉重,殖民主义的魔影紧紧地攫住了它,它的社会演进道路注定没有美好的结果,终将无望地夭折。因此,夏威夷近代以来的社会演进道路绝不是一个寻求自主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可以参照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