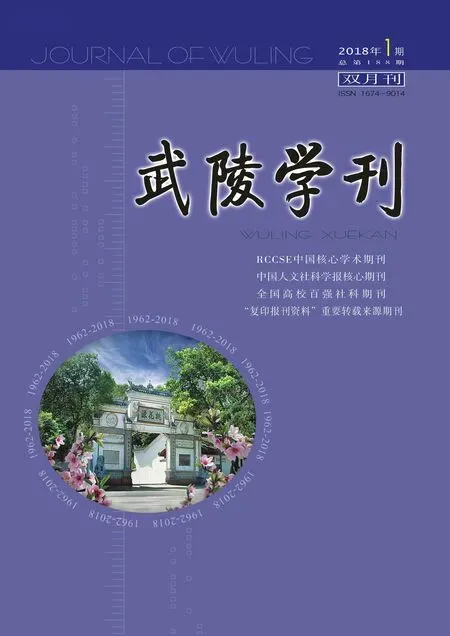明代的平民讲会及其对个体人格建构的影响
——以泰州学派为例
2018-03-08宋文慧
宋文慧
(四川美术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重庆 401331)
明朝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包蕴宏富、色彩斑斓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历经艰难跋涉,终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征兆。这些征兆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伴随手工业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新型雇佣关系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等。与之相应,社会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平民讲会的兴起恰恰就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讲会即讲学之聚会,其兴起与北宋理学家们的私人讲学活动有直接关系,然而两宋的讲学活动还只是知识分子之间切磋学问、砥砺道德的一种聚会,至明中叶王阳明倡起“良知之教”,将普通百姓纳为教化对象,讲会已超出一般师生相聚讲学的范畴,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民间自组织性文化活动,在个体人格建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泰州学派的平民讲会运动
明代讲会运动的兴起与阳明学的兴盛不无关系。就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而论,所有重要的讲会活动几乎都与王门学者有关。这一时期的讲会不仅逐渐淡化传统讲学以繁琐的章句训诂与抽象的哲学议论为主的学院派作风,更加凸显劝善规过的道德教化内容,而且其规模与数量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以面向的对象来论,这一时期的讲会运动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仅限于知识分子间以讲学研讨为主的聚会,如邹守益号召举行的青原会;另一种则是面向平民阶层、以传播阳明的良知之学以及教化风俗为主要目的的讲会,后者尤以泰州学派为盛。
泰州学派的平民讲会运动既是儒家学者对“以斯道觉斯民”的社会责任的承当,也是对阳明讲学理念的继承与践行。在讲学方面,王阳明不仅十分尊崇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而且十分重视讲学的灵活变通。他曾教育自己的弟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132。依据历史上的记载,王阳明一生的讲学活动虽然以面向士人阶层为主,但是他的教育理念却极大影响了泰州学派的讲学实践。
(一)淮南三王的讲会活动
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王艮在拜师阳明三年后,其蓬勃的救世激情再也无法抑制,他对阳明说道:“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者乎?”[2]70于是,他向阳明请辞,自制一蒲轮车,上面挂着一幅标语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2]71王艮一路讲学至京师,却受到了阳明在京弟子的反对。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王艮的做法太过张扬,并纷纷劝其南返。王阳明也写信给王艮的父亲守庵公劝其停止在京师的讲学活动,王艮无奈之下只好返回会稽。但是这一事件却奠定了泰州学派“入山林”“启发愚蒙”的讲学宗旨。
在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在家乡泰州一带开门授徒,面向社会各阶层进行讲学。在王艮的观念中,儒者最重要的事功之业就在于讲学,“经世之业,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2]18。所以在王艮的影响下,泰州学派的成员无不重视讲学。王襞作为王艮衣钵的传承者,终生以讲学为业,在临终时对门人更是“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3]。邓豁渠拜访王襞时,观其讲会之情形,赞叹道:“是会也,四众俱集,虽衙门书手,街上卖钱、卖酒、脚子之徒,皆与席听讲,乡之耆旧率子弟雅观云集,王心斋之风犹存如此。”[4]王栋同样兢兢业业地从事讲学活动,他不仅主持书院讲会,还在太平乡“集布衣为会”。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在江西南丰县兴起讲会,使“四方信从益众”。又隆庆二年(1568),创水东会,并作《会学十规》。他的讲学实践与其秉持的以“匹夫之贱”移风易俗的理念不无关系。王栋认为:“圣人经世之功,不以时位为轻重。今虽匹夫之贱,不得行道济时,但各随地位为之,亦自随分而成功业。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5]所以在泰州学者看来,他们并不以卑贱之身行讲学之事为耻,其讲学活动更不看重出身,并认为如此做法才是“圣贤经世家法”,才是“天地生物之心。”
(二)颜均、罗汝芳的讲会活动
嘉靖十九年(1540),颜均于江西南昌同仁祠举行讲会,揭“急救心火榜文”。罗汝芳就在这次讲会中拜于颜均门下,开启了泰州学派在江西地区的传教之旅。与泰州学派的其他人相比较,颜均的讲学活动具有明显的宗教神秘色彩,这一点从他与其母在家乡举行的“萃和会”的组织形式中即可看出。在这个乡会组织中,颜均的母亲实际上承担了类似圣母的角色,所以“萃和会”在举行三个月后便因其母亲的逝世而不得不解散。另一个重要的例证则是颜均、罗汝芳于泰州心斋祠举行的讲会。颜均在其《自传》中提及这次讲会:“秋尽放棹,携近溪同止安丰场心师祠。先聚祠,会半月,洞发师传教自得《大学》《中庸》之止至,上格冥苍,垂悬大中之象,在北辰圆圈内,甚显明,甚奇异。铎同近溪众友跪告曰:‘上苍果喜铎悟通大中学庸之肫灵,乞即大开云蔽,以快铎多斐之恳启。’刚告毕,即从中开作大圈围,围外云霭不开,恰如皎月照应。铎等总睹渝两时,庆乐无涯,叩头起谢师灵。是夜洞讲辚辚彻鸡鸣,出看天象,竟泯没矣。嗣是,翕徕百千余众,欣欣信达,大中学庸,合发显比,大半有志欲随铎成造。”[6]颜均与罗汝芳诸人在讲学时天空出现异象,于是颜均率领众人跪告上苍,望其以“大开云蔽”的方式验证自己所学,最后竟得到了上天的回应。颜均以此为凭借最终为自己赢得了教化权威,使人“欣欣信达”,纷纷追随他学习。这种近似于宗教传教的方式,无疑在整个儒学领域内都显得十分特殊,然而却恰恰符合颜均思想的整体气质。正如前文所述,颜均对于孝悌等儒家伦理规范的解释就经常运用“因果报应”的逻辑。总体来论,颜均在儒学造诣上并无特殊之处,他之所以获得罗汝芳及其他弟子的真诚信仰与其宗教人格发挥的感化力量密不可分[7]。
据杨起元的《罗近溪先生墓志铭》记载,泰州学派在江西地区的另一代表人物罗汝芳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开始举行讲会,当时讲会的地点为滕王阁。次年他在参加会试时又与同志大会于灵济宫。又次年在家乡“建从姑山房,以待讲学之士”。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乡会组织举办的讲会活动。嘉靖二十九年(1550),罗汝芳回乡“立义仓、创义馆、建宗祠、置醮田、修各祖先墓,讲里仁会于临田寺”[8]。“里仁会”属于当时乡会组织的一种,同时兼具讲会的功能。至于讲会的场所临田寺则早在嘉靖初年(1522)就已经由罗汝芳的父亲重修作为讲习之地。里仁讲会的实践为罗汝芳借由地方组织开展讲学活动提供了经验。在此后几十年间,罗汝芳常以乡约组织为基本单位组织讲会。与王畿等王门弟子以理论研讨为主的精英讲会不同,罗汝芳参加与组织的讲会形式更加多样化,并且由平民大众参与的讲会要远远多于知识分子间的聚会,这就造就了他在讲学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特点。
总而言之,泰州学派的讲会运动,突破了书院讲学的种种局限。首先,它没有场所的限制,书院、寺庙、道馆甚至打谷场都可作为讲学之地。泰州学派的韩贞就经常于“秋成农隙”在打谷场面向一村之人进行讲学。其次,没有等级的划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乡野村夫都是讲学的对象。泰州门下较有名的弟子就有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再次,没有形式的局限,诸如“童子捧茶”“穿衣吃饭”等日常行为都是讲学的重要素材。这样灵活的讲会形式对阳明良知之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面向平民阶层的良知之教
泰州学派的讲学与面向读书人的讲学活动不同,它主要以日用指点为方法,致力于良知在实际生活中的落实,又因为它是随顺人之情性的,故而无论是教与学,都有“无边快乐”。具体来讲,其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日用指点为法
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以世俗大众为教化对象,是对儒学经典教育的一种纠偏。儒家经典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孔子教育弟子,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而其中尤以礼、诗、乐为重,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之说。荀子也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至汉以后,官方更设“明经科”作为取仕之法,如此一来,儒学就沦为了家法师传的训诂之学。宋代以后,虽然四书代替五经成为儒学教育的必修书目,然而这种专门面向知识阶层的教法,实际上将无缘读书之人挡在了儒学的大门外。而朱子提倡的格物之教,同样以读书明理为主。这种经典教育的严重弊端造成了知识的文本化,对儒学学习的繁复化。王阳明为了纠正儒学固化的弊端,将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重新定位为道德本性即良知的弘扬,这就为道德教化方式的简易化提供了契机,而泰州学派试图通过“日用指点”的方式使人醒悟良知,更是对阳明简易教法的总结。他们以“童仆往来”“童子捧茶”这些形象生动的生活实例作为启发教育的素材,简单明了、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尤其是罗汝芳特别强调当下指点,其结果是“虽素不识字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9]。
(二)以良知实落为要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试图通过构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道德理想之境来引导人向善。然而,在阳明提出良知学之前,这一理想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因为阳明将朱子“学以至圣”的目标转换为对人自身所具有的圣人性(良知)的弘扬,人人皆可成圣的理想才具有了现实的社会含义。泰州学派所从事的讲学活动,其目的就是让人相信良知本有,当下即是,将之扩充开来就可以达到圣人之境。并且,与王畿、罗洪先等其他王门后学从本体、工夫的角度探讨良知不同,泰州学者对良知的阐发方式显然已经有了通俗化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阳明良知之教的基本精神不是逞口舌之争,而是将良知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引导百姓日常行为的思想、理念与信仰。例如罗汝芳就以“爱亲敬长”来阐释良知,认为只有从“爱亲敬长”这种人伦日用的情感出发,才能使人感受到良知的切实存在,这是落实功夫、修养的门径。
(三)以自然快乐为宗
“自然”与“乐”在泰州学派的思想中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自然”就是反对“持功太严”,而“乐”则是“自然”所达至的效果,同时又是为学的目的与最终境界。所以,讲学就要随顺人的习性,不刻意,不强迫,“不屑凑泊”,“不依畔岸”,根据人的当下行为进行指点,使人能够现下醒悟,并将醒悟的良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而不必去做那些戒慎恐惧、克念忍欲的工夫。为此,王艮提出:“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2]5而这种“不费些子力气”,又有“无边快乐”的学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显然更加亲切可行。
三、讲会对个体人格建构的影响
与家族、乡约等民间组织相比,讲会突破了血缘与地缘的限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等交往的平台。在这种平等的社会交往中,个体摆脱家庭的羁绊与束缚,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具体来讲,讲会对个体人格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意识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流动性较差,世代繁衍而成的古村落将人的足迹圈定在彼此熟悉的乡土社会,因此人们最主要的交往活动就是家庭与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关系为例,其中君臣、父子、夫妇、长幼都以后者对前者的敬顺、服从为要求,而后者的主体性与自我价值则受到了极大压抑。此外,在这些关系中,又特别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义务,所以每个人出生以后就像一个负债者,要用尽一生的努力为家族、国家做贡献,而自身的利益却无从保障。这种伦理关系中的不平等,权利与义务关系中的不对等,极易造成个体自主意识与独立性的缺失。
但是讲会组织将个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形成由独立个体组成的新社群。在这一种新社群中,成员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并且以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进行交往。一时间“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10]共会听学,彼此间只以学问相切磋,而不管彼此的身份如何。讲会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是人主动参与建立,而非先天赋予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意识得以显现。
(二)促进人的个性的多元发展
明代讲会的兴盛与阳明后学的提倡密不可分,而阳明本人的教育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对人的个性多元化的尊重,他曾对弟子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者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1]118意思是说,圣人教人往往根据学生的资质、能力因材施教,而不是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每一个学生,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每一个学生。泰州学派的平民讲会以面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为特点,并且尊重不同人的职业属性,它并不以经典、圣人行迹去约束受教对象,而是使其遵从自己的良知本心,由良知本心判断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这对于促进人的主体性与个性的多元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讲会的兴盛,为文人士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
大量文人士子沉积在民间社会是明朝后期显著的特征之一。一方面,学校教育的兴盛与文化的相对普及大大增加了知识人的数量,但是科举名额却并没有随着知识人数量的增长而增加,由此造成了大量被科举淘汰的知识人沉积在民间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朝政的黑暗与政治的腐朽也造成了士人生存境遇的恶化,士人越来越感到已经无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济世理想。所以,如何在入仕为官之外寻求一种新的实现救世济民之理想的途径,成为困扰士人的重要问题。讲会的兴盛则极大扩展了明代士人的生存空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像泰州学派的成员大部分未入仕为官,却能够凭借讲学为自己赢得社会声望,得到世人尊重。在这种既能够自我实现,又能够成风化俗的社会活动中,儒家的“成己成人”之道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所以说,讲会的兴盛对于士人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挺立个体人格,树立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M]//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王襞.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M]//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11.
[4]邓豁渠.南询录[M]//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82.
[5]王栋.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M]//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86.
[6]黄宣民,点校.颜均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6.
[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96.
[8]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M]//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920-921.
[9]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762.
[10]张建业,张岱.焚书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