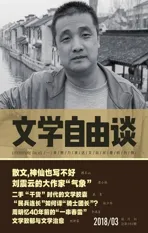一个人和一个“小国”的伟大文学
2018-03-07董兆林
董兆林
1991年深秋,当横跨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从北京向着一个陌生的国度疾驰的时候,谁能想到,这趟列车上的一位懵懂青年,若干年后会和令人尊敬的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著名作家凯尔泰斯亲如家人。他就是后来凯尔泰斯系列作品的中文翻译者,被称为“匈牙利文学代言人”的余泽民。
当他历经旅途的疲惫,坐了十天十夜的火车,拖着几十公斤重的行李踏上匈牙利布达佩斯东火车站的站台时,车站灌满阳光异常高大的拱形棚顶,在余泽民眼中如宫殿般雄伟,周围来来往往肤色各异的人们让他倍感新鲜,只是这异域风情的新奇还未来得及领略,赤手空拳、闯荡天涯的游侠般豪情,还未来得及抒发,顷刻就被眼前无情的现实击碎:他投奔的大学好友三个月前去了奥地利。举目无亲,余泽民被同学的朋友孤零零地丢在南疆的一座小城。在这座距离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边境都很近的名叫塞格德的边城里,他在一家位于一幢居民楼八层的中医诊所工作了仅半年,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意外,这让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挫。诊所倒闭,失业,失恋,失掉居留身份,几乎一夜之间,余泽民的生活陷入绝境。孤独、寂寞、贫寒、饥饿,对现实的恐惧,对未来的彷徨,都让他绝望到几近抑郁。余泽民出国的时候正值东欧剧变,匈牙利对中国人免签,但因为大量中国人的涌入,匈牙利政府又在1992年初对华恢复签证,随后进入了移民局排华最为严重的时期。无奈,一些人铤而走险偷渡到了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余泽民很少出门,而迫不得已外出就怕遇见警察,即使坐在屋里,邻居的脚步声重了些,也会让他产生一丝惊惧。一连几个月,他和家人、朋友失去了联系,租住的房间几乎成为自己的囚室,甚至连吃饭穿衣都要靠朋友们接济。1992年最凄惶的那个冬季,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绝望无助,就如同在幽暗的枯井中等待遥不可及的黎明。
还是当地朋友亲人般的帮助,让余泽民逐渐走出人生的低谷。与他合租住房的室友,是三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他们帮他寻找各种工作以糊口,办讲座,教中文,到俱乐部打工……到了假期,他们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泽民流落街头,就轮流将他接到乡下自己或朋友家中。在靠近罗马尼亚的农庄小镇马科,余泽民感受着来自匈牙利乡村生活的淳朴和温暖,那颗孤寂的心也渐渐冰释。在乡下,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每天辛勤打工劳作,帮家里干各种农活挣零花钱攒房租,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候就是晚饭后父母给他们发“工资”,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带着家里的狗,在乡间的土路上嬉戏奔跑,或和同伴去打猎。当夜幕降临,在蒂萨河畔,林中的篝火映红了他们青春的脸庞,晚风,星辰,虫鸣,溪水,田园的诗意暂时告别了生活的坎坷,积蓄着可以享受一生的情愫。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他而言弥足珍贵,就像尘封的老酒,秘藏在百宝箱里,舍不得品尝,后来在他的长篇小说《纸鱼缸》中多少可以品味出当时的那种情感。
初抵匈牙利的余泽民,面对听说难懂的匈牙利语时简直一筹莫展。那时东欧解体不久,苏联军队刚刚撤离匈牙利,而匈牙利人的外语主要是俄语、德语,很少有人说英语。为了生存的需要,尽快学会匈语成为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如果将匈牙利语比作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并不为过。匈牙利语的形成比较复杂,其虽在欧洲但并非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属于乌拉尔语系之一的芬兰-乌戈尔语族,这个语族主要只有匈语、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公元9世纪,现代匈牙利人的先辈、源自东方游牧民族的马扎尔人,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湾一带,一路西进,劫掠欧洲。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和其他民族的交往,匈牙利语中有关畜牧方面的词汇来自古突厥语;在和斯拉夫人学习农耕技术时,斯拉夫语中的农业词汇融入其中;在和波斯人做生意时,波斯语的一些词汇又被吸收进来;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语中又有了日耳曼语系的元素。匈牙利语中没有前置词,表示从属关系是由格的形式来体现。匈牙利语的时态、语态、主语表达都体现在词尾的变格上,比如一个动词会有十几或几十种变格,不同的词还有不同的变格方式,一个由几个字母拼写的短词,如果加上各种后置词尾,可能会长达几十个字母。可以说,即使你学会了一个单词的原型,在生活上也有可能用不上。余泽民最初的阅读是从电视周报开始的,一段简短的电影简介,常常要让他连查带问地琢磨半天。
两年之后,1993年的早春时节,余泽民在朋友家中结识了小说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朋友介绍说拉斯洛是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从后来看,这件事对余泽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拉斯洛刚刚从中国出访回来,本来就对东方这个神秘国度产生浓厚兴趣,如今邂逅了泽民,对他来说是个意外惊喜。他们一见如故,拉斯洛还请余泽民到自己位于乔班卡山乡的石头屋家中住了两星期,后来他们有了多次交往。1998年初夏,拉斯洛又一次出访中国,这一次余泽民应邀陪同。他们在中国旅行游历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访了近十座城市,和不同的出版机构见面洽谈,参加各种关于创作的座谈会、读者见面会等等。在中国的采风结束后,耳濡目染让余泽民对拉斯洛的作品充满了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此时,恰好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出版,朋友送了他一本,他得以一探究竟。只是没有想到,书中的文字宛如天书,让他读起来叫苦不迭,几乎每个字都要翻词典。余泽民索性靠着一本《匈英词典》,既作为弄明白小说内容,也作为匈牙利语的自学练习,硬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其中一篇六七千字的《茹兹的陷阱》译成中文。多年后,在《小说界》为他开辟的栏目“外国新小说家”中,《茹兹的陷阱》成为他译作的首选作品。只是当时余泽民不知道,拉斯洛的作品是匈牙利文学中最让人难读的一类,那些如岩浆般涌动的长长的句子,常常让他抓狂,但也让他感到一股炽烈在心中翻腾。过后再看,这样的翻译是对作品的深度阅读,对余泽民来说也是一种语言的训练,只是当时他没有意识到,从此以后自己会和翻译结下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更不会想到,他本人会成为拉斯洛作品的译者。2015年,拉斯洛荣获了国际布克奖,余泽民翻译的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不久前也在译林出版社出版。
翻译让他上了瘾,匈语的水平也日渐长进。之后的三年里,余泽民陆续翻译了匈牙利不同作家的几十篇作品,直到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到来。
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了整个匈牙利。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寂寂无闻的凯尔泰斯是谁,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竟然获得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誉。当时,在布达佩斯的书店里,有一位叫“凯尔泰斯·阿库什”的作家的小说被抢购一空,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弄错了。也许是因为凯尔泰斯沉重的文字有些晦涩难懂,也许是因为他所选择的题材“不合时宜”,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不那么“通俗”“流行”,总之,他所有的作品印数都不太高。当时中国国内也是一头雾水,相关的一些出版机构也在四处打探凯尔泰斯何许人也。作家出版社捷足先登,率先弄清原委,就在凯尔泰斯获奖后两周,与余泽民取得了联系。他们不仅委托他帮助联系版权事宜,而且还把翻译作品的重任交付给他。现在看来,作家出版社的举措非常明智,也充满着智慧。天时地利,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非余泽民莫属,而且在岁月流淌写作功力不经意的打磨中,他也为此做好了准备。
几经打探,余泽民找到了凯尔泰斯位于布达佩斯二区一幢普通的五层楼房里的家,可是听邻居们讲,这位和蔼可亲的作家以往也是深居简出,更何况眼下据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德国柏林,已经很少回这里了。也是无巧不成书,此时,余泽民担任布达佩斯的一份华文周报《联合商报》的主编,报社办公室的房东太太是凯尔泰斯作品匈文版出版社社长莫尔察尼先生的岳母。真可谓柳暗花明!于是通过这层关系,余泽民找到了拥有作家版权的德国出版社。两个月后,作家出版社顺利地购买了凯尔泰斯《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命运无常》的中文版权。在接下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国王大街一间24平方米的小屋内,余泽民开始了几乎黑白颠倒 “暗无天日”的一种生活。
他知道,翻译凯尔泰斯对自己是一次极大的挑战,诺奖获得者为世人瞩目,翻译其作品容不得有丝毫闪失,责任重大,稍有不慎,那将是对原作极大的伤害;更况且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工作,也是不能有丝毫懈怠。余泽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对待这次机遇,自忖唯有用完美才能诠释两年后的亮相。他开始着手翻译《英国旗》,不料《英国旗》的第一句,就是占用整页篇幅复句套复句的一个长长的句子,为此他整整译了两天。从此以后,余泽民几乎衣不解带,夙兴夜寐,如古代将士般“兵不卸甲,马不离鞍”,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埋头在键盘前不停地敲字,连吃饭、洗澡都成了奢侈的享受,不愿占用太多的时间。随着翻译的进行,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处于发现一个未知世界的惊喜之中。当面对身体的疲惫、劳累、困顿时,凯尔泰斯那些深邃、富含哲理,抑或令人不解、读来时常感到窒息沉重的富有肌理的语言,更让他有一种冥思苦想后释然的解脱和兴奋。作品中那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让他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彻悟,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他和凯尔泰斯孤独的伟大,有了某种神祇的契合。
凯尔泰斯·伊姆莱1929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他被关进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后被转移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被盟军解救。1948年,他返回布达佩斯并做了一名报社记者,1953年成为自由撰稿人,开始了翻译和写作生涯。这期间,凯尔泰斯翻译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依德等德国哲学家的大量著作,从中获益,他的写作也深受影响。从1975年费尽周折才得以出版的长篇小说《命运无常》开始,反思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便成为他所有作品的主题。
对于少年凯尔泰斯来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暴行,那种恐怖、绝望、黑暗的记忆挥之不去,那种如梦魇般的伤痛烙印难以弥合,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凯尔泰斯说:“每当我构思一部作品时,都会想到奥斯维辛。”他也因此被誉为“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无论《命运无常》中那个在纳粹集中营里屈辱求生的少年克维什,还是在《英国旗》中,随着主人公经历的一场心灵磨难,抑或《船夫日记》《另一个人》中关于哲学、文学思考的沉思录,他都在从容地面对苦难和痛楚,以冷静、平和的心态,以最真实的笔触,书写记录着集中营里的悲惨经历。凯尔泰斯凭借着孤独的个体记忆,表现那些感人至深的悲怆,同时也承载着对历史的反思。苦难是悲惨的,揭开伤疤是令人痛苦的,敢于面对曾经噩梦般的劫难,是一位坚强者的姿态,也是一位真正作家的智慧。凯尔泰斯不仅仅是在控诉纳粹法西斯的罪恶,不仅仅是在控诉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邪恶,而是将纳粹法西斯的大屠杀置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层面来思考,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反思历史,反思人类的堕落和沉沦。反人性的战争,失去自由的禁锢,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强暴的专政,无休止的迫害,思想的黯淡,人性的扭曲,无不因为人类堕落的因子在起作用。凯尔泰斯把自己最深刻的思考都融入了作品之中。
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对凯尔泰斯作品更广泛深入的解读,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深入,余泽民和这位伟大作家那种穿透纸背的心灵沟通,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融合,都让他感到漂泊在外的温暖,消解着孤独带来的寂寞。2007年8月,余泽民前往柏林拜访凯尔泰斯,给他带去《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和《命运无常》的中译本。他们的见面平静温馨,就像多年未见的家人一般。凯尔泰斯和蔼的微笑,宽厚长者的谈吐,都让余泽民感动。他不禁想起第一次给凯尔泰斯打电话时的情景,当他毕恭毕敬地称呼“凯尔泰斯先生”时,凯尔泰斯马上打断他说“就叫我伊姆莱”。在匈牙利能够直呼其名,那是代表了一份亲近,这让余泽民初次和他接触就有了一份莫名的感动。此时一杯咖啡之后,是一瓶葡萄酒,他们的话题也越聊越多,从翻译谈到文学作品,从欧洲文学谈到各自的创作,从匈牙利局势谈到中国的发展,甚至对美食也聊得津津乐道。原本计划一小时的晤面,他们整整聊了近四个小时。凯尔泰斯夫妇邀请他共进午餐。当他们在凯宾斯基酒店楼下的咖啡馆外分别时,凯尔泰斯再一次和余泽民拥抱,他以父亲般的慈爱说道:“翻译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亲人。”闻听此言,伏在凯尔泰斯肩头的余泽民禁不住流下感动、幸福的眼泪。
翻译凯尔泰斯和匈牙利及其他东欧作家的作品,让余泽民的文学感受有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以其闪烁的睿智思想,丰富的人文情怀,对历史的冷峻开掘,以及表现出的质朴的文学精神,开启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文学表现的新的视角。这一点特别让他获益,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写作。这种影响凸显在余泽民不少的小说、散文创作中,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纸鱼缸》。
这个本科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1989年毕业后却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的研究生,在匈牙利当过医生、大学讲师、导游、插图画家、果农、家教、编剧、演员、记者、编辑,最终成为翻译家、作家……曾经的北京小伙儿,步入中年,给我们带来了他独特的阅历,深邃的思索,直抵心灵的写作和蔚为大观的译作,他以一己之力将匈牙利文学的璀璨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看到了匈牙利文学的伟岸。
2017年4月,在第二十四届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上,余泽民荣获匈牙利文化贡献奖,这是对他多年来为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匈中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的肯定。正如授奖辞所说:“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匈牙利当代文学通过他得以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这份殊荣实至名归,这是对他那艰难又美好、感伤而难忘、困惑迷惘且蓄势待发、浴火磨难实则脱胎换骨的往昔岁月的褒奖。正如余泽民自己所说,他在匈牙利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这个国家虽小,文学却很伟大。
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信身在异国他乡的余泽民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