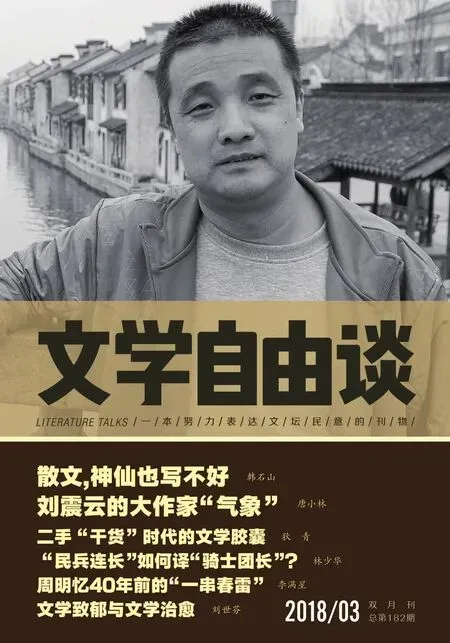屈原、心灵鸡汤与心理学的“毒药”
2018-03-07张大为
张大为
心理学在今天似乎具有某种奇特的重要性。如果说每天以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涌来的“心灵鸡汤”会让你嗤之以鼻的话,那么,2016年年初,当两位学界人物选择以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诀别时,那些“心理学专家”们的表演则让人很不舒服。由此想到屈原,推想肯定会有心理专家分析屈原的“心理问题”。那年端午节当天,果然就看到“屈原是否有心理问题”的公众号文章——这次终于说到了屈原。尽管文章加了各种限制条件和补充说明,但最终其扭扭捏捏的基本结论无法回避:中国人顶礼膜拜、深情怀念了两千多年的屈原,是一个心理病人。
一个过分推崇和依赖心理学的时代,总让人想到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末人”)世界。尼采的“最后的人”形象,蒸发掉了长短不齐的人性化内涵与生存价值重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就是一种整齐而纯净、“健康”而“幸福”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人:
大地在他的眼里变小了,最后的人使一切都变小了,他在大地上蹦蹦跳跳。他的族类不会灭绝,犹如跳蚤……
间或吃一点毒药,这制造了安逸的梦。但毒药过多又造成安逸的死。
没有一个牧人的一群羊!人人需求同一,人人也都一样:谁若感觉不同,就自觉进入疯人院。
“从前,整个世界都疯了”——他们中最优雅的人如是说,并眨巴着眼。
人们在白天有自己的小快乐,在黑夜也有小快乐:但他们崇尚健康。
“我们已发明了幸福”——最后的人说,并眨巴着眼。
在今天的各种媒体当中,人们都不难看到各路“心理专家”以掌握世界终极真理的姿态眨巴眼睛的“优雅”。那么,心理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门学问?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神力?19世纪末,欧美一系列“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促使心理学从哲学对于人的“灵魂”研究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个体心理经验构成的基础之上,它大体是以面对一台静止的机械装置的实验与实证态度,形式化、抽象化、技术化地对于个体心理机制进行探究的学问。心理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心理学不仅研究人,也研究动物。心理学因此是一个从下往上、从低往高看的思路:用心理来理解人的灵魂,用个体心理视野来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与思想天空,用技术调适来取代生命价值抉择。总而言之,对于人来说,用尼采的刻薄术语来讲,心理学就是用“畜群”来理解人。
在“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和“情感问题专家”们看来,人类唯一的问题,就是个体心理层面上发生的“机械故障”。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宏大精神命题和观念主题,都可以看作是个体心理的产物,无论什么样的形而上的灵魂冲突和价值焦虑,都可以通过形而下的、技术性的调适来解决。就此而言,心理学无法解决哲学所致力的真理、道德、正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不是心理构成与心理结果,也不是个体心理经验所能解释的;它同样不考虑社会历史层面的宏大的精神价值现象,因为它无法理解伟大与渺小的问题;它无法理解文学当中悲天恸地与忧愁烦恼的灵魂,因为它无法解释情感的形而上意义和价值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专家”仍然没有将屈原送进疯人院,而仅仅将屈原当成心理病人,这应该已经是很客气的做法了。
此种“心理学”的思路,打个不很精确的比方,就像是认为电视节目是电视机的电子元器件本身的“产物”一样,如果电视节目出了问题,是因为电子元器件出了问题,通过修理小工的敲敲打打,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今天很多人的生活似乎离不开的“心灵鸡汤”,就主要彰显了这种“心理学”的逻辑。“心灵鸡汤”可以说就是修理小工的哲学,小工的视野就是电视机后盖里的视野,按照他的哲学,这个世界完美得就像是电视机后盖里的线路板与电子器件。他永远不会知道电视屏幕当中正在上演的剧情,也理解不了光电物理世界之外的逻辑。在他看来唯一不完美的问题在于:这里有的地方会发热,有的地方会发光,有的地方会有噪音。在小工看来,这都是可以“修理”一下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修理”来让你“改变自我”的问题。因此,从修理小工的哲学出发,通过“心灵鸡汤”来指导别人的人生,似乎是一种无法遏制的人性欲望:你为什么要发热?你为什么要发光?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
“心灵鸡汤”包含了一种文化程度不高或者与文字接触不多的人们对文字本身“神力”的迷信与崇拜,比如,他们觉得靠一篇粗浅的“鸡汤文”就能让人把人生“活明白”。但这不是主要的。“心灵鸡汤”的基本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完美,没有什么不正确、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一切的问题都源自于你自己,要接受这一切,并且“改变”自己,而这种“改变”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与调适。当视野里剩下静悄悄、冷冰冰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的有序排列时,世界在修理小工的眼里变得完美起来……这种论调好像有点佛教教义的味道,但佛教有着 “普渡众生”的宏大誓愿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毅担当,而这里只有“适应环境以求混得出人头地”的鄙俚诉求,以及获得精神胜利式的心理平衡乃至“快乐”的荒诞逻辑。因为回避了精神价值内容与心灵修养的实质性内涵,所以“心灵鸡汤”的说教,就只能是一些抽象的、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抽象并不是智慧与高明。黑格尔早就说过,抽象思维其实是骂大街的老太婆的思维方式,而智慧在于具体地思维。所以人们可以看到,真正智慧的人、卓越的人、聪明的人、成功的人,其实很少会以“心灵鸡汤”那样的方式、那样的口吻,来指导别人教训别人,因为他知道问题的“具体”的复杂性,与每个人、每件事的“具体”的艰难之处。
但正因此,“心灵鸡汤”痛恨与众不同者。从而,在“心灵鸡汤”指导人生、要求你“改变”的训教背后,对于你“总是与大家不一样”的切齿之声依稀可闻。“与众不同”不管是卓越不凡还是离经叛道,都让“心灵鸡汤”对于“生活”的理解与认知发生困难,使它的“普遍”有效性与适用性发生困难。而在这背后,是其好不容易建立或重新建立起来的生活信念、价值信念的崩塌——这种信念原本能够让一部分人群感受到一种与“大多数人”在一起的安全感,一种抽象“平等”的幸福感,以及处于“低处”的可靠性:从这个视野看来,什么样的人生都有可以指摘的地方,而这样的指摘本身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幸福”来源。就此而言,“心灵鸡汤”其实更像是底层生存者将饱经挫折之余的某种激愤的逆向思维,顿悟为“正能量”“真智慧”的状况,而“心灵鸡汤”的文字,更像是粗通文墨者急欲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憨直拙笨。然而,当乞丐嘲笑皇帝没有晒太阳的余暇、心理专家指摘屈原的“心理疾患”时,在“心灵鸡汤”枯干支离的文字当中,我们隐然听到了生活在“公平”“安稳”的踏实幸福感当中的人群,大众狂欢节式的胜利的欢乐与欣慰。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心理学的学理基础,当然不至于建立在如此偏狭、浅薄的前提之上,而又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真理所在。心理学自有它存在的意义,而心理学的价值诉求与价值表达,在特定的历史情形下,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许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视野当中,当有的学者说当时看到“文艺心理学”这个概念就激动不已时,或者当有的著名人物提出“心理本体”的概念时,这时的“心理学”或者“心理”概念,就具有一种形容词的性质——它本身被价值化了,被用来表达某种价值情感和价值诉求。但在今天,在人们的期待视野和神话化当中发生认知扭曲的“心理学”,以及迎合这种“心理需求”的各种“心理专家”,确实已经看不清楚自己的限度所在。今天人们的问题,是生活在物质富裕的时候失去了大的目标方向、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是对于这个世界发展总超出其认知能力、不能理解其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愤慨”,是无所事事的矫情与无能的自怨自艾。这也就是说,今天人们的问题,可能大部分是精神问题,是价值观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这个关系,就好像是电视节目出了问题,而不是电视机本身出了问题时,天天找修理工来将电视机拆卸开来鼓捣,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但这或许正是当下“心理学”成为“热门学科”,而“心理咨询专家”“情感问题专家”深受欢迎的原因。
屈原选择沉江,是因为他相信他所坚持的价值理想远比其个体的生命重要得多。屈原是以燃烧个体生命的方式,来祭奠自己所执着的伟大理想。人们当然可以不赞同这种选择本身,但用心理疾病来亵渎屈原,就像用电子器件的故障来证明电视节目不健康一样荒谬。同样,人们对于屈原的怀念尊崇,是人们心中的自然感情、自然价值感的流露。这些才是人类生活与文明秩序、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按照尼采最初的理想,对于一种清楚自己从哪儿来、要做什么、要到哪儿去的健康、健全的文化生活,哲学起到的是护持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自然秩序、自然正确性的积极作用。从哲学所维护的自然价值秩序,到同质化、形式化、抽象化的大众心理学,这是激进启蒙主义的一个顺带结果。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极端诉求与消极后果,就是对于某种抽象的自由、平等的绝对要求,对于文化“民主”忽视其价值内容的形式关注。心理学肢解精神价值视野,但对它的极端推崇本身,却迎合或者要求着某种抽象“同质”与庸俗“平等”的绝对性价值诉求与价值观念:按照心理学所反映出来的启蒙主义价值序列,怎么思想比思想什么更重要,思想抽象平等的“独立”姿态与“民主”形式,比经由深刻思想而做出的价值抉择更重要。这样的“价值”立场人们耳熟能详,似乎很像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奉为圭臬的艺术主张,但思想或者哲学,应该是一种现代主义式的行为艺术的表演吗?
也许有人会问,尼采不是自称“心理学家”吗?尼采是这样说过。但尼采是一个具有“超人”视野和造物主高度的“心理学家”,他要告诉人们的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心灵构成与限度,以及它的种种病态。同样,如果人类彻底认同启蒙世界观,将启蒙的逻辑贯彻到底,则不应该对于尼采赋予人类的“畜群”这一“生理学”称谓感到愤慨。根据刘小枫先生十几年前的尼采解读,尼采以一副特别“启蒙主义”的面孔,将启蒙理性的逻辑夸张到极致,而后现代的知识人以为就此取得了尼采的真经,因而如癫如狂,奉尼采为“后现代”的教主,殊不知他们正是中了尼采涂满书页的致命“毒药”——这是一种精确的意象与譬喻。尼采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视野,恰恰是对于启蒙主义学理基础的釜底抽薪,它构成对于启蒙主义内在逻辑的悖谬及其夸张的人性自恋症的一种致命的打击。尼采思想当中的反讽与曲折结构是显然的,但如果要说这是一种“隐微教诲”的话,那就在于它不是通过智识可以索解或排遣的东西,而是必须用生命与生存来献祭或押注;反过来,尼采作为“心理学家”的“毒药”,也不只是导致思想上的迷失,而同样导致是“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效应:是让人真正面临或觉悟或不觉悟、或困窘或舒适的生不如死的生存绝境。
然而,一百多年以后,尼采笔下反讽性、批判性的“最后的人”图景,茁壮成长为眼前的现实:经过后现代“药理学”炮制,作为流行时尚的“心理学”变成了新型“毒药”的畅销品牌之一,这恰恰是因为它能够以将人变成心理实验机器的方式解构价值焦虑,制造“人人需求同一,人人也都一样”的“安逸的梦”与“安逸的死”,从而避免了屈原式的“心理疾病”,使得“崇尚健康”的“最后的人”在其中飘飘欲仙。它或许曾经是作为“精神贵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奢侈品”,但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消费品。而今天的“专业”知识分子,在事关国家、历史、文明、社会等方面的宏大话题上价值关怀的缺失与错位,使其进一步丧失了思考能力、发言能力,因此只能以坚持美国崇拜的“悲壮”姿态、坚持菜市场里被忽视的底层民众式的“愤怒”,乃至坚持讲各种“段子”甚至黄色笑话,来表明自己的“批判精神”与“独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