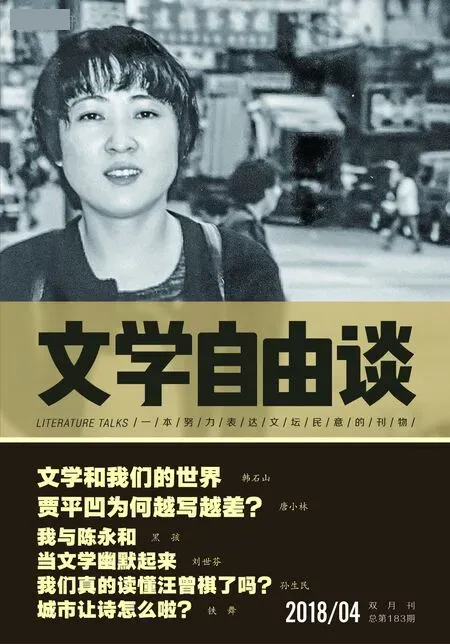皮肤主义(外一章)
2018-03-07郭建勋
郭建勋
有个想法,想找一个词儿概括一下我们的这种创作形态,或者,表达一下所谓的艺术主张吧。一直找不到。没错,这个词儿挺难找的。当然,换了高人,就很容易了,如那顶“打工文学”的帽子,就轻易地盖了我们的形态和主张,密不透风。不管怎么说,那是顶正确的帽子,至少到目前为止,非如此不足以概括和表达。文学是需要这样的帽子的,尽管这帽子至今有争议,有些戴了这帽子的人也不高兴。但有帽子总比没帽子好,我持是论。争议的事情不好说,一说,又要争议了。只说为何不高兴,归纳起来,大约两点,一是嫌其寒碜,二是怒其不争。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都是人性里的正常,反之,倒不正常了。
该说一下,我是差点有词儿了的。2012还是2013年吧,跟阿北在一起聊,我们弄个主张吧。聊的结果是,取名:湖畔。那时,我们住在福永的立新湖边。取名的那天晚上在喝酒,取了名字很激动,禁不住每人又喝了一瓶。在喝这瓶的过程中,我还拟了八个字的“艺术主张”:湖有点脏,所以在畔。第二天,阿北告诉我,湖畔这名字不是初创,1920年,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和冯雪峰4人在杭州的西湖边就成立了湖畔诗社。那是近代国内的第一个新诗社。他们的主张是:“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我说,我们弄我们的。阿北还真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开了个湖畔的网页,贴了些文章,也请朋友去跟帖,那一段,还稍有些热闹的样子。阿北有没有提炼点艺术主张,我忘了,记得的是,阿北公司运作的那个项目黄了,我们的湖畔也黄了。阿北离开了福永,去了公明,埋头写他的长篇小说《找北》。小说动笔前,我给他写了题记:在这个找不到北的鸟时代,我们努力地找着,直到找到找不到为止。《找北》后来易名《释梦者》,得了京东锐作者的大奖。书由作家出版社出了,我的题记赫然在印。这让我比自己出书还高兴。
湖畔找北,最后释梦,这似乎是个命运的谶。湖畔是梦,找北也是梦,一切皆梦。而且,后来想起来,湖畔的名字以及我提的那个“湖有点脏,所以在畔”的艺术主张都是揪了自己的头发要逃离地壳的虚妄。我们这种泥土里生长、泥土里挣扎的所谓作家,哪有资格嫌湖脏而寻找“在畔”感呢?永远的,我们就在那个脏湖中,甚至脏湖底,满是水草和淤泥。高人或可站在湖畔欣赏水光潋滟,我们的任务总是掏水草和淤泥。或者干脆化身作了水草和淤泥。
这样的警醒是有好处的。东汉王充看出了儒的虚妄的病,开出了“疾虚妄”的方子。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今世,虚妄一窝蜂又来了,鄙俗如我辈,竟也懵懵然地要“湖畔”起来,想想也真是汗颜。湖畔就此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间,低到尘埃里上班下班,亦低到尘埃里读书写作,吃得香睡得香,如是几年。
上个月,几个朋友吃饭聊天,忽又聊到概括和表达的事。戴斌说,我们的写作是用皮肤感知生活的温度。我随口说,皮肤主义。皮肤主义就此诞生。仔细想,还真是非用皮肤主义这四个字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创作形态和艺术主张。
其间,我忝作了睦邻文学奖的初评委。这些年,我做过不少次评委,有点滑稽的是,连普通话都讲不利索的我还做过一次演讲比赛的评委。既然写不好了,就做评委吧,我喜欢这个活儿,站着说话不腰疼。除了腰不疼,做这次评委第二个好处是,越到后来,我越欣喜地发现我的所谓皮肤主义的“理论”找到了注脚。扑面而来的针头线脑、鸡零狗碎、张长李短的邻人作品几乎篇篇都是“水草和淤泥”,具体而微地观照着这个城市当下的世道人心,成为精简宏大的主流叙事外满满塞塞的旁白与注解,一不小心,几成一卷凉热幽明的《清明上河图》。
那到底什么叫皮肤主义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共八条:“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皮肤主义没这么复杂,只有三条:一条,用皮肤写作,用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触摸生活的微凉与微暖,所有的温度通过皮肤传递到心灵。二条,写生活的皮肤,只写皮毛只写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形而上学的本质与真谛藏匿在感性的现象中。三条 ,直抵母语,剥除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华丽衣裳,回归中国话语。
很简单的三条,却也足以表明我们的主张。事实上,说的容易做的难,要做到,没那么简单,几乎是另一场“白话文运动”,光“直抵母语”这一条,就是胡适那场“白话文运动”的运动。原来的那场“白话文运动”固然是破了文言文的窠臼,但不得不说,它立了另一个窠臼,又跟翻译体等结合起来,成了一锅夹生饭。老实说,现在不少文章,比文言文还难懂难读。我们追求的母语是有温度的生活的语言。
要真正地实现皮肤主义是个难事,但我们愿意迎难而上。丢掉“湖畔”,回到“皮肤主义”,这或许是我们这种作家的使命,以水草和淤泥的姿态,用皮肤感知这世界这时代的温度,将我们感知的,告诉别人,也告诉后人。我们干不了别的,试着干干这个。期望更多的作家加入到皮肤主义的行列。
皂荚草
跟老友喝了一下午的茶。黑茶。出门,下雨了,落脑门上,冻冻的。真冬天了,上午冷风,下午冻雨。这个冬天有点冷。莫名的,由冷雨忽想起了一副联:
氷冷酒,一点两点三点;
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氷是冰的异体字。很多年前,在一本《绝妙好联》的书里读到这副联,我就觉得并不妙,上联差点,像薛蟠霸占了香菱。丁香花的句子是好的,戴望舒的巷子里结着丁香般愁的姑娘,缠着百头千头万头的缱绻。
我是想过以“水冰川”对“丁香花”的,但后面跟不上。之所以冒出“水冰川”,是有段时间喜欢过冷冰川的版画,那黑白二分表现出来的世界是如此宁谧且丰富,觉得很有禅的味道,虽然我不懂禅。
喜欢冷冰川是因了罗向冰。认识他时,他在《大鹏湾》做美编,他的版画深得冷冰川的神与趣,大多乡村题材,最有印象的是一幅:半边的黑是夜空,中间一钩变形的弯月;另半边是湖边的蔗林,蔗林里一具女人的胴体,毕加索的丰腴而夸张。我去大鹏湾》住的他的宿舍,他送了我一个书柜和一副版画。书柜很有用,装了油盐酱醋。那副版画夹书页里了,后来找不到了。他去了广州几年,再回深圳时办一本杂志,叫我写鬼故事。我写了个《柳树精》给他。稿费出来了,我请他在新洲路吃了个面。他的杂志不办了,我却一口气写了四五十则鬼故事,先命名《乡村野谈》。去年翻寻出来,觉得近50岁了,有资格说鬼话了,就换了名,叫《山村鬼话》。
罗向冰后来回雅安老家了。有一年,他给我寄过一包蒙山茶。蒙山茶很有名,他打电话问我茶怎么样。我说不错。其实我不喜欢那个茶,涩涩的。我只喜欢喝黑茶,老家的。人是恋乡的,包括它的茶、它的女子。有时候也想起罗向冰,那个半秃的头,笑起来两颊扯起布袋一样的纹,喜欢讲点黄色笑话。
有一天,看到又一副对丁香花的联:
皂荚草,七脚八脚十脚;
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初看有点小意思,细究又觉得也不好,皂荚草三字失之于雅。联是没对好,并非说皂荚草一无是处。它又称皂角,籽儿揉碎滤汁可洗头洗衣服,亦可入药,能催奶:“去皮,蜜炙为末,和酒服之”。还有诗:
妇人催奶法如何?皂角烧灰蛤粉和。
热酒一杯调八字,管教时刻笑呵呵。
洗头洗衣催奶,看来,皂荚草倒是专为女人生专为女人长的,倒像个男人。从这点看,这副联倒挺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