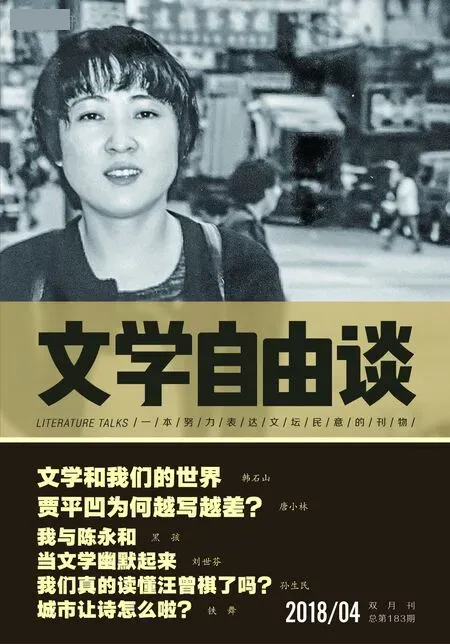我们真的读懂汪曾祺了吗?
2018-03-07孙生民
孙生民
大约在十年前,我曾经在《汪曾祺的意义》一文里预言说,汪曾祺的文学价值远没有得到重视,将来我们会有重说汪曾祺的时候。时间果然是伟大的魔术师,近年来,汪曾祺研究持续升温,汪曾祺作品一版再版,汪迷们甚至按图索骥寻找汪曾祺笔下的地方与人物。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汪曾祺的《受戒》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开启了一个文学新时代,让文学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了文学本身。现在,汪曾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已经经典化、固定化,逐步形成了一个符号象征:“最后一个士大夫”,承接了现代文学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的抒情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个优秀的作家总不会是如此单一的面孔。汪曾祺丰富的创作,一定不是什么流派所能规范了的,他的作品的意义也一定是多元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况味来,正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汪曾祺生前就十分反感某些评论家将他划归为“乡土文学”流派的说法。诚然,将一位作家划归某种文学流派,很容易明晰他的创作特征,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做也很有可能削足适履,从而遮蔽了作家创作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一般论者谈论汪曾祺文学创作,主要是以新时期文学他“复出”后的创作为主,如《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故里三陈》等等。这些故人往事,反映了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从这些怀旧的小说里,人们很容易看到汪曾祺“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看到汪曾祺“回到民间”“回到传统”“沉入于国民中”的姿态,看到闲适、淡定、从容、随遇而安的汪曾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的形象。
也许,人们对汪曾祺这样的定位也与他的“夫子自道”有关。986年,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里说
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同一年,他在《晚翠文谈·自序》里又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1991年,汪曾祺在散文《随遇而安》里又说: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其实,考量汪曾祺新时期“复出”以来的创作,也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和谐”“随遇而安”所能概括了的。他还有许多其他创作,如 《天鹅之死》《云致秋行状》《皮凤三楦房子》《尾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以及对《聊斋志异》里许多短篇创造性的现代改写等等,更何况还有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大量创作呢。我在《汪曾祺的意义》一文就曾这样说过,如果说汪曾祺先生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体现的是一种“和谐”,那么,他在40年代那些带实验性质的现代派小说创作,便体现了“深刻”的一面。
更何况,汪曾祺的创作历程与体裁并不如此简单。他是一个跨时代作家,40年代、60年代、八九十年代三个创作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品;考察其文学价值与创作特征,也不能仅仅只考察他的小说创作,他还有大量的散文、戏剧、诗歌、文艺评论、书信、书画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对一个真实的汪曾祺,才能面对汪曾祺这样一个丰富的存在。
即便如此,就是在面对八九十年代倍受大家喜爱、体现其闲适风格的《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们细读一下也不难发现,在洋溢着生之欢乐的田园牧歌式的故事里,遍布现实的却是人生之困顿。《大淖记事》里巧云平日的辛劳,兴化锡匠们为十一子挨打头顶香炉到县衙请愿;《受戒》里农人、和尚日常生活的匮乏,小英子对明海庄严受戒的不屑。也许大家感觉到小英子与明海爱情的纯洁与两小无猜,其实这爱情懵懵懂懂,多少有点如梦如幻、不太真实。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也许被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读到了秦观佳期如梦的意境,但其实更多是十一子与巧云的艰难处境。小说总是虚写爱情的遇合,实写尘世的困苦。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大多是困顿的,只是作家以梦幻的爱情或者人物相互之间的情义与节操,为我们提供了心灵伊甸园,只是这尘世上的天堂是脆弱的。
我们不妨回到新时期之初,回到汪曾祺创作这些作品的“现场”:
1977年4月,爸爸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当然是有人组织的,以后又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交代是不是“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反右”和“文革”初期,倒霉的人有千千万万,他只是其中一分子,受苦受难好歹还有不少人陪着;如今,大家都已翻身解放,心情舒畅,他却要再吃二遍苦,这使他十分委屈,更十分恼火。
爸爸受审查,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他多年来已很少画画,这次可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画的画都是怪里怪气的,瞪着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他是借画画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
这是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对当时情景的回忆。这个日常生活里的汪曾祺,苦闷、悲戚,在严酷的政治生活里茫然四顾,承继了故乡先贤“扬州八怪”及晚明清初文人抒发“不平之气”的方式。他自己就曾写诗明志说:“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边缘化的实际处境,被压抑的心绪,于是四十多年前的梦悄然出现了,慰藉着怯意丛生的汪曾祺。这样的处境与心绪,使得汪曾祺的创作远离了当时喧嚣的政治与文坛,回到了文学本身。
其实,汪曾祺始终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来描写村镇生活的,他笔下的靳彝甫、高北溟、王淡人、季匋民这些“士大夫”的生存境况,正好与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有了某种程度的暗合;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的重义轻利、急公好义、安贫乐道、甘于淡泊、注重心灵自由与宁静、追求独立的文人品质,也为知识分子建构一种自己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参照。汪曾祺的作品迎合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重构——自我精神的独立性。事实是,“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一称号就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或者悖论。平心而论,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有些是被重新“发现”的,如他身上儒道互补的人文传统,以及归有光及桐城派等作文传统等等,有些是在当下语境中被新近“发明”出来的,意在借他的创作来对传统与现代发声。所以说,汪曾祺创作或者说“汪曾祺热”,某种程度上曲折反映着新时期以来人们重建民族文化,以及对于传统或者说对于现代的暧昧态度。
然而,我要说的是,“汪曾祺热”有可能遮蔽了真实的汪曾祺。记得沈从文先生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作为沈从文先生的高足,汪曾祺曾于1982年在《沈从文的寂寞》里就引用过这段话,并且还说:“沈先生的重塑民族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
我们真的读懂汪曾祺了吗?我们是否忽略了汪曾祺作品里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呢?也许真实的汪曾祺正等待后人深入全面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