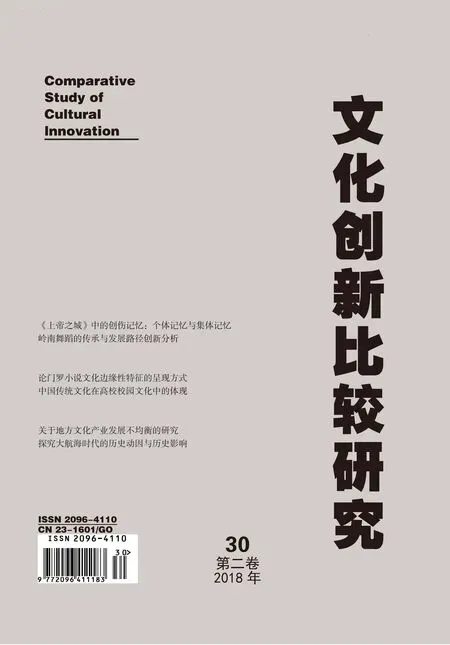论门罗小说文化边缘性特征的呈现方式
——以《快乐的影子舞》为例
2018-03-07赵晶侯君
赵 晶 侯 君
(沈阳大学,辽宁沈阳 110044)
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是当代加拿大文学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于 2009 以来多次获得国内国际重大奖项十余项。门罗的独特在于她集加拿大人、女性作家、短篇小说家等身份于一身,同时她的作品充斥着加拿大国家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特色。加拿大文化上的“边缘性”,也使加拿大人在伦理观上表现出相对主义的“整体含混性”。笔者认为,加拿大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具有双语、多族裔、区域对峙的内在异质性,但共同的“文化安全诉求”使得加拿大人获得了一种统一而不同一的文化妥协,即“边缘性”。
众所周知,加拿大属于后殖民主义国家之一。与美、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加拿大在外交事务中更多地表现出阴性品质——从属,顺服和被统治。英裔(新教)的疏离及英、法裔(天主教)之间的隔离与猜忌一直存在于加拿大国家内部;在国际上,加拿大受到美帝文化威胁,心理归属上居于中间无所归依。而对于门罗而言,尽管作者本身公开认可自己的女性小说作家身份,但实质上女性短篇小说家的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对于创作风格的选择。门罗对于“加拿大性”的文学贡献焦点主要体现在在对“被统治性”的表述。其实,恰恰因为这种“被统治性”,激发作者及有相似成长背景的读者内心升起“边缘感”。同时,在加拿大经验层面引发摆脱“阴性——被统治者”的身份诉求,在加拿大文化伦理层面引发模棱两可的整体含混观。
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里的加拿大性反映出加拿大历史上的一系列矛盾,在矛盾中加拿大为自己的身份做出最好的注解。加拿大的边缘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国际社会的边缘政治地位并赋予其挑战现行霸权文化的潜力。加拿大仍然保持着对母国的忠诚,不仅是因为自己祖先的背景与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些有着久远历史的文化中心亦貌似能为其提供与美国“文化侵略”相抗衡的有力武器。加拿大可以有选择地借鉴欧洲传统文化中的唯美主义,以抗衡美国现代文化的粗犷不羁,并博采众长克服其他霸权文化影响。
在《快乐的影子舞》一文中,门罗借助“圣愚”这一矛盾的非主流人物形象揭示了加拿大作为边缘国家的主流信仰。事实上“圣愚”主题在西方文化的历史、民间故事、文学及宗教传统中常被提及。基督教义中的圣愚传统始于St. Paul,他首先用“基督的愚人”的说法。纵观整个基督教历史,“圣愚”主题呈现的形式多样,但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有“从属”的特征。这种“从属”状态可以被认为是当人处于堕落和痛苦的境况下,有意识地成为基督面前顺服的羔羊。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塑造的“圣愚”人物形象即有孩子般的信任和单纯,这也正是一个完美基督徒的最佳定义。通过引荐“圣愚”这一人物形象进入小说,门罗甚至寻求到了远处北方的俄罗斯文化作为其文化同盟。俄罗斯的东正教义中“圣愚”形象深入人心。俄罗斯人不会忘记如何估量痛苦,他们感知其价值及带来的影响,品味苦涩的甜蜜。加拿大文化同样视痛苦为珍宝。但有一点与俄罗斯不同——她会同时强调感知和庆祝重生。这就是门罗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不同之处——她会永远在结尾留一抹亮色。通过“圣愚”这一角色,门罗将小说中的配角(年迈的哥特主义的钢琴老师和她天才又拖拉的学生写成了精神上圣洁的“圣愚”化身)。故事中,钢琴老教师玛莎拉小姐是卑微和高尚的结合体。她和她的姐姐是没落贵族家族的后裔,代表着逐渐消亡的“淑女”传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风尚和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窘困她们已经不再享有社会特权等等现状,两姐妹仍刻意选择视而不见。她们苦心维持的钢琴派对成了哥特主义的缩影。故事开篇即为玛莎拉小姐的钢琴派对定下了“过时落伍”的基调:玛莎拉小姐准备开一个派对(处于对音乐的正直追求或她内心对宴会的大胆渴望,她从未把这个派对称之为独奏音乐会。)在小镇人的眼中,这些钢琴派对在现代加拿大经济化和城市化进程背景下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老套落伍。而姐妹俩拒绝向周围环境屈服的这种做法使得她们在小镇的人际关系愈加边缘化,并且使那些乐于接受新世界的朋友亦陷于尴尬境地。正如小说中写道:“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我母亲自言自语道,不过她当然不能大声地说出来;她从电话旁转过头,看上去像受了刺激——就好象看到了一些脏东西但她却没法擦去——脸上流露出她惯常的同情。她答应会参加聚会;可以想象接下来的两周,她心里会不断地打退堂鼓,但她知道她最终还是会去。”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写出了小镇的朋友不得不为了维护玛莎拉小姐脆弱的“高贵”而尴尬的接受邀请参加这个派对。“玛莎拉小姐的聚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像是马脱了缰绳,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在你驾车驶入这样的聚会的时候,一个问题始终盘旋在你脑海:大家是否都会到场?谈到过去两三次聚会,最令人不安的一件事,就是聚会常客的队伍正在不断缩水,还有那些老学生,这些老学生的孩子可能就是马赛勒小姐所招揽到的全部的新学生了。每年六月,都会有新的一批人离开。”以上种种文字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这对“举止高贵”的姐妹成了爱丽丝门罗小说构建的小镇“圣愚”,她们的生活已处于小镇生活的边缘。
从《快乐的影子舞》中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出加拿大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导致了其文化焦虑,导致加拿大民众有种与生俱来的边缘感,并反映在加拿大文学的“小镇传统”中。加拿大心理中的孤独和彷徨是其边缘感的延续,表达了加拿大作为后殖民主义国家所承受的“失母”之痛。在《快乐的影子舞》中,玛莎拉姐妹与小镇居民的关系,即是“从属”概念与加拿大“后殖民”心理的互为关照,提出加拿大国民心理中天然具有对边缘者的同情。这种宗教中的“圣愚”形象寄托了门罗对于张扬“边缘人”力量的哲学想象,同时表达了加拿大经验中对自己独特身份与权力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