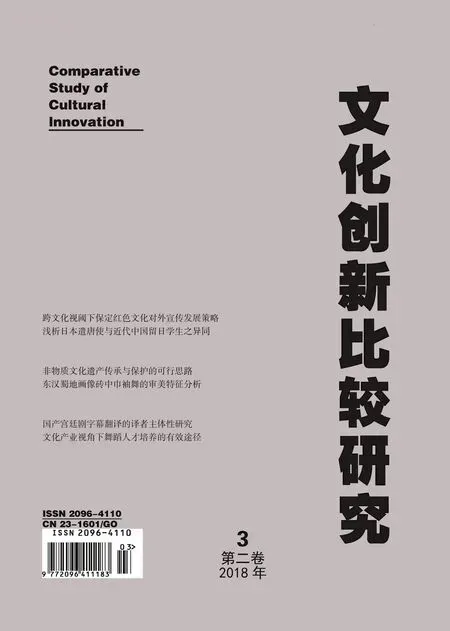恶作剧者的创伤与治愈
——以《自由的恶作剧者》为例
2018-03-06赵巧利
赵巧利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116044)
奥吉布瓦族作家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4-)作为美国土著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曾获得两个标志性奖项:2001年的美洲原住居民作家终身成就奖和2005年的西方文学协会杰出成就奖。他曾被莫马迪称为“也许是20世纪美国印第安作家中最优秀的讽刺家”。《自由的恶作剧者》为代表的系列“恶作剧者小说”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借用创伤与治愈理论,聚焦恶作剧者形象以此挖掘他们在主流文化冲击下所受的创伤以及自我治愈中所采取的策略。
《自由的恶作剧者》作为对美国主流文化强烈抨击的辛辣讽刺之作,植根传统,融入现实。小说题目自由的恶作剧者本是美国当权主张雕塑的自由神像,该神像雕至胯部位置便被丢弃了,通过创造这样一个情节,暗讽了主流文化中宣扬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假象并谴责了其对印第安人采取的种种歧视与压制。该小说由7个短篇系列合成,讲述了明尼苏达北部一个保留地上7个恶作剧者兄弟的故事。作者并非采取主流文化的惯用写作手法,而是着眼于土著人视野,将本民族语言与英语杂糅起来,以迥异的修辞措词手法,打破传统的散文叙事形式,戏仿后结构主义的散文模式,独创序言与尾声,中间以独立章节呈现小说内容的叙事模式。在小说的叙述上依赖于人物对话,结构整洁。表面来看,作者运用戏谑的语言,滑稽的恶作剧者形象讲述了印第安部落一个家族的故事。并且,透过这些人物描写可以看到作者对主流社会的猛烈抨击。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些人物表面看似滑稽、好色、叛逆,但也正是这些个性特征隐含着他们的心理创伤。透过作者的书写,从这些恶作剧者的语言行为便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历过创伤的折磨的,并且可以看到他们进行自我治愈时的挣扎。个体创伤与民族创伤是分不开的,在自我治愈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创伤的治愈。
赫曼提出了创伤复原的三个阶段。他认为遭受创伤的主人公可以通过重新建立安全感、追忆创伤事件和融入社会群体这三种形式来复原创伤。在第一阶段,受害者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再次的伤害,同时能够完全的掌控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生活。第一阶段的顺利度过代表着受害者的安全感已经初步建立了,这时受害者就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恢复——讲述创伤事件。受害人必须勇敢的面对过去遭遇的创伤,并且深入的分析创伤产生的原因,并试图将这种过程讲述给其他人以此来重建创伤故事。重建创伤故事不仅要对创伤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也应该对受害人创伤前人生经历进行回顾。在这个阶段,受害者往往由于缺乏足够的直面痛苦的勇气而选择性的回避一些伤害,这样的回避是不利于受害者恢复的,因此重建创伤故事必须是事实求是的叙述。如果受害者成功的进行了创伤叙述,她就已经通过自己的语言与外界建立了联系,同时也可以正视自己遭受的伤害了,这个时候,就来到了非常关键的第三阶段:受害人通过构建一个新的自我来面对世界从而重建其人生。在这一阶段,赫曼提出受害者构建新的自我可以通过重拾生活之乐趣,并积极的投入到社交生活中去来完成。《自由的恶作剧者》中的人物恰恰遭遇了这样的创伤并经历了创伤复原的过程。
在被殖民的历史长河中,印第安人遭受着白人主流社会各式各样的折磨与歧视,大到残酷的种族大屠杀,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蔑视与压制。但在杰拉德笔下,他们敢于正视历史,创伤得到了治愈。这些惨痛的历史经历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都有所体现。《自由的恶作剧者》讲述的是主人公鲁斯特・布朗,帕特尼亚的男爵,及其后代的故事。其后代就是恶作剧者形象的化身。其中,鲁斯特给孩子们讲述恶作剧者和创世故事,并教他们当情绪激动使,向“恐慌洞”里面嚎叫。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注重联想他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并且均获得了有特色的绰号,他们古怪的脾气和幽默的语言使得他们得以忍受悲剧文明的侵蚀。这些惨痛的历史经历都通过恶作剧者之口被讲述出来,看似只是在讲述故事,实则回忆过去代表着与自我内心世界的斗争,即在心理上遭受着创伤的侵蚀。独具特色的恶作剧者们面对创伤选择不一,但总体而言,他们所受创伤已治愈。
恶作剧者伊特娜・弗拉姆・布朗尼邀请三位僧侣参加参加部落典仪,在回去的过程中帮助了一位小男孩。这群僧侣姐妹戴头巾,穿黑色僧袍。具体来讲,她们在回部落的路上遭遇暴风雨,在风雨交加中听到一丝微弱的呻吟。经过探查发现,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跟随叔叔一起参加部落典仪,却被大树压住,动弹不得。伊特娜・弗拉姆阻止了要直接帮助小男孩的姐妹,而是不断地以语言鼓励小男孩,希望他以自身的力量摆脱困境。最后,在她的再三鼓励下,小男孩摆脱困境,最终从树下逃脱,站了起来。这里体现了恶作剧者语言的治愈力量。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创伤已治愈,否则是不能够发挥出这样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治愈他人的。
斯里波特斯・布朗尼是部落里最聪明的恶作剧者。他在大学里拿到了经济学和印第安研究的学位。在与银行投资者的对话中提到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借研究印第安人的饮食习惯和疾病之名去挖掘印第安人的坟墓,研究他们的骨头,但是考古学家却对白人死者表示尊重,这极大的损害了印第安人的权利,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造成了伤害。这里便体现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而在斯里波特斯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部落。但是白人政府却不允许他们发展飞机业务。可见白人对印第安人经济发展的压制。而斯里波特斯却没有进行反抗,而是转向投资动物医院。说明其依然受着白人至上,不可侵犯的观念束缚。证明其没有正确看待民族的被殖民史,自己的民族意识还没有觉醒。通过投资一家动物医院,治愈那些受伤的鸟类。这象征着治愈受伤的印第安人。
金瑟・布朗尼天生具有发现大蒜和人参的能力,这种天生的能力为部落带来了生意并获得了自我解放。由于印第安部落琥珀色的人参比外面的人参价值更高,因此吸引了很多前来采购的组织和商人。白人邮递员认为金瑟与中国人协商买卖人参是对美国的背叛。随后亚瑟便被该地区的联邦法院控告,认为其违反了多条包括保护濒临灭绝的种类在内的条约,因此他不得不暂停与中国人的贸易。在与白人法官的争论中,白人法官处处强词夺理,白人制定印第安世界的法则,对印第安人的权利进行限制,处处体现了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压迫。由此可见白人自恃高贵,只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抢夺印第安人固有的财产人参,还称对方不合法。由此便可以看出,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欺压。但是金瑟并没有默默忍受白人社会强加给他的罪名,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金瑟假装不懂英语,通过自己认定的翻译员与法官进行交流,最终通过恶作剧的语言游戏重新获取了买卖人参根须和种子的权利。
在《自由的恶作剧者》这部小说中,维兹诺塑造了鲜明的恶作剧者形象。恶作剧者是巫师,是滑稽的解放者,是语言上的治愈者。恶作剧者可以穿越边界的限制,挑战白人世界的规则和束缚。而且描绘了大量的印第安传统,例如口述传统,萨满教文化,典仪等。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对白人权威进行挑战,渴望印第安人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保罗・雷丁认为恶作剧者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他不分好坏,也没有固定的价值观,所有的价值都在他的行为中体现。正是这样的恶作剧者经历着心理创伤却又能以自己独特的智慧自我治愈。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恰恰是恶作剧者的自我治愈,带动了印第安族人的反思与追忆,促使族人们正视过去与现在,才得以促使印第安民族创伤的逐日治愈。
[1] Squint, Kirstin L. Gerald Visitor’s Trickster Hermeneutics, 107-122
[2] Madsen, Deborah L. Understanding Gerald Vizenor[J].Book Reviews,147-149.
[3]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4] 蔡满艳.西尔克《仪典》的创伤研究[D]. 泉州:华侨大学英语学院,2012.
[5] 陈文益,邹惠玲. 鬼舞:美国印第安小说中的批评隐喻[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1-42.
[6] 陈许.土著人的回归— —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小说中的人物身份探讨[J].盐城学院报, 2005(3):93.
[7] 丁文莉.走向第四世界: 印第安恶作剧者的朝圣之旅— —解读杰拉德・维兹诺《熊心》中的恶作剧者[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8-30.
[8] 方红.美国的猴王——论杰拉尔德・维兹诺与汤亭亭塑造的恶作剧者形象[J].当代外国文学,2006(1):58-63.
[9] 郭巍.美国原住民文学研究在中国[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4):57-63.
[10] 李婉.治愈创伤——从创伤小说角度解读《典仪》[D].重庆:西南大学英语学院,2008.
[11] 王卓.方寸之间的诗性舞— —论杰拉德维兹诺俳句的多元文化意蕴[J].当代外国文学,2013(4):37-47.
[12] 邹惠玲. 哥伦布神话的改写与第三空间生存— —评维兹诺的《哥伦布后裔》[J].外国文学研究,2013(5):8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