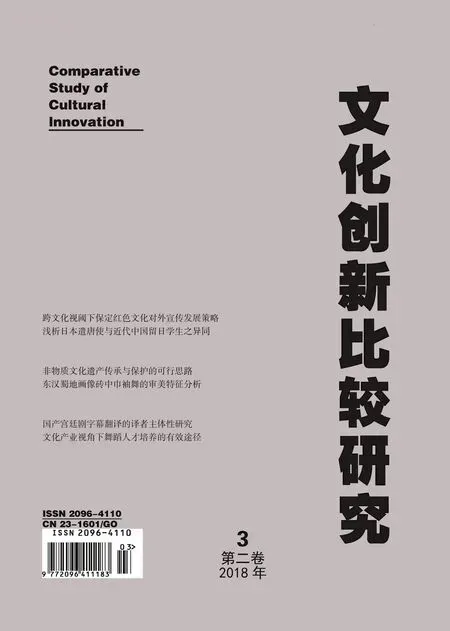《野草》中的生命哲学
2018-03-06王琬琼
王琬琼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 250100)
1 《野草》中的情绪转变
《野草》堪称鲁迅大量的作品中最为异色的存在,就文辞来说,大量晦暗诡谲的意象,含混不清的象征性表达,“消失于无地”这样陷于自相矛盾的话语,以及“水银色焰”、“一切冰冷、一切青白”、“青白的两颊泛出轻红,如铅上涂了胭脂水”,这仿佛带着金属质感的文字,正是最鲁迅式的表达。
我将野草分为四组。
第一组中,《秋夜》作为《野草》的第一篇文章,为整个《野草》的梦——噩梦一般的——奠下基调。《野草》是一场噩梦,人们终将从噩梦中醒来,而后又复沉入噩梦,再醒,再做梦,如此循环。
《影的告别》影没有归处,影不被任何一方所接纳,影亦不接纳任何一方。“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影认为自己不论去往哪里都将迎来终结,却绝不愿拖累他的朋友,绝不愿“占你的心地”,最终独自远行。
《求乞者》主角不施与,也不祈求施与,不宽恕他人,也不要求他人的宽恕。末尾,“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这又是极为鲁迅式的阐述,《求乞者》中本是冷漠与麻木的循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也没有理解,只剩下瞒和骗。鲁迅拒绝对这种虚伪的现象软化,他“一个也不宽恕”,同时也拒绝宽恕身处其中,不自觉与之一同食人的自己,因而不要求施与,却以这种不要求做消极的反抗,至少打破这冷漠的循环。纵然不能使“诚”多一点,也使“不诚”少一点,这样的反抗,鲁迅称之为“与绝望捣乱”。
《复仇》两篇,其一以自戮向看客复仇,虽然飞扬,虽然“大欢喜”,其实也并无甚可喜,反而显得空虚而荒凉。其二,人钉杀神子,神子目含悲悯,此时他仍是神。当他在痛苦中追问为何见弃于神时,耶稣成为人之子,而钉杀人子的人,同类相残、同族互食,比钉杀神子者尤为血污、血腥。
《墓碣文》死尸,“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无解的循环,没有出路的永恒轮回,《墓碣文》堪称鲁迅文中最深的噩梦。
第一组的风格是明晰的,暗色的基调,创始者(=作者)的冷眼,这冷眼甚至显得有些残忍。由告别起始,途中也曾求乞,也曾复仇,最终在本味永无得知的状态中走入坟墓。但这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灭亡,譬如《死后》的不得安宁,再譬如《墓碣文》的末尾:
“待我成尘时,你将看到我的微笑!”
死不是死,死是绝望。而希望为虚妄,绝望亦为虚妄,在存在彻底死灭之前,“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还是能够反刍自己的痛苦,然而,“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或许只有真正彻底的死亡,才能够终结这个绝望的循环。所以只有在成尘之时,死尸才会露出微笑。
第二组中,挣扎与反抗的主题渐强,从《希望》阐述鲁迅的核心哲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开始,鲁迅不是单纯地否定希望,他甚至同时否定了绝望,深知不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只是明灭不定的虚妄之况。
要如何打破这种虚浮的状态?鲁迅选择斗争,以行动本身为存在打下坚实的锚。“我思故我在”,我所能确定的唯一事实便是我在思考,而对鲁迅而言,绝望希望皆为虚妄,但行动本身是确实存在的,是足以确证的自我存在的证明。“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是鲁迅的辩证法,一种状态,必须经由另一种不同的状态,才能得到证明。
《雪》是一篇意象化极强的短文,也最富诗意。鲁迅虽然自幼在江浙一带成长,对北国的雪却别有一番体悟,鲁迅写雪,即是写自己,而如同朔方的雪一般,不论身处何种境况都不曾改变倔强、执拗的自我,正如在凛冽天宇下旋转升腾的雪一般,是足以徜徉于天地间的斗士的精神。
《过客》文中展示了鲁迅其时的精神状态,并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实在是不知希望,不知未来,而只能本能性地往前走,直至坟墓。鲁迅一边认定人类平等地走向死亡,迎接最后的破灭,一边又对途中的种种怀有希望。而在这行进的过程中,他拒绝善意,甚至诅咒给予善意的人,因为恶意会使人愈发冷酷坚硬,而善意会使人软化,软化并清醒的人在其时的环境中只能得到痛苦,无法前进。但,不论付出多么惨烈的代价,不论归途是怎样的虚无,鲁迅笔下的“过客”终究是头也不回地前进了。而这也是鲁迅的选择。
《死火》最鲁迅式的故事,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死火死而未僵,“我”的体温使死火苏醒(“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我”脱离冰谷,又被代表敌人的大石车辗轧至死,大石车也坠入谷中,而敌人再没有遇见死火、脱离绝境的可能,文章在同归于尽的快意中结束。
三组开始,鲁迅渐渐回归至我们所熟识的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或者说,正是从《野草》的这第三组文章开始,鲁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杂文。一卷《野草》翻阅下来,可以明显看出卷内文章象征性渐弱,对现实的直接针砭则愈强。直至最后的《淡淡的血痕中》与《一觉》,青年们的血激昂了鲁迅的心,像是终于从长梦中醒来,忽而找回了至坚的斗志。
可以说,是环境、现实唤醒了鲁迅,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是鲁迅,才会被这样的现实所唤醒。“环境的力量有多大!……然而,我们必须更清楚,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
至此,《野草》的旅途已经走到终点,鲁迅也找到了摆脱这泥淖一样的心境的方法:斗争。与绝望斗争,与现实斗争,不论何时何地身处何种境况,想要决然反抗不断沉沦的心境,唯有以行动抗争。精神与现实是对立并相辅相成的,要影响其中一极,必然要从另一极进行处理。从绝望中寻找出路,在我看来,这就是《野草》隐含的精神主线。
2 《野草》的生命哲学
先说关键的《题辞》。我认为《题辞》应该放在全书的末尾。与笼罩全书的诡谲气氛相较,《野草》的题辞中别有一番爽利在,比起对死亡与腐朽的诅咒,更多的是坦然的接纳,接纳自己的腐朽,接纳自己的残缺,纵然面目可憎,但自己终究是自己,而人最不能背弃的,正是自己。“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于是在这自我剖析、自我解读的漫漫长路中,鲁迅终于走到了足以开怀大笑的目标点。人在走入绝境之时,总是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鲁迅始终在与自己所深深厌恶的事物的斗争中生存,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极度的痛苦往往会转化为大欢喜,作为“永久的战士”的他,越是痛苦之时,越是可以畅快地笑出来!
明生暗,友会成仇,未来终将成为过去,人可以变为野兽,爱者也会成为不爱者,由此,生而后死,死而后生,“出生入死”,出土为生,入土为死,二者互相转换,本质上并不存在区别。“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正是在这样死生轮换、爱憎反转的精神状态下写出的《野草》,生极则死死极则生,如此循环往复,反复生死,不断枯荣。
死境很多,但绝非没有生的存在。如同绝望希望皆为虚妄,生死之间本来也是来回转换,轮转,这个过程是不曾止息的。他也一定是在以二者为两极的轴柱的反复回旋中,勉力在这个世界上维持着自己的存在吧。在于自己所怨憎的事物的搏斗中存在,以斗争保证自己存在的完整,自深渊中顽强地凝筑起自己的主体意识,也许这就是鲁迅为我们留下的最大启示,也正是他最为鲜明的生命哲学,或者说,永不磨灭的生命意识。
[1] 章衣萍. 《古庙杂谈》(5)[N].
[2] 鲁迅. 《野草》英文译本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