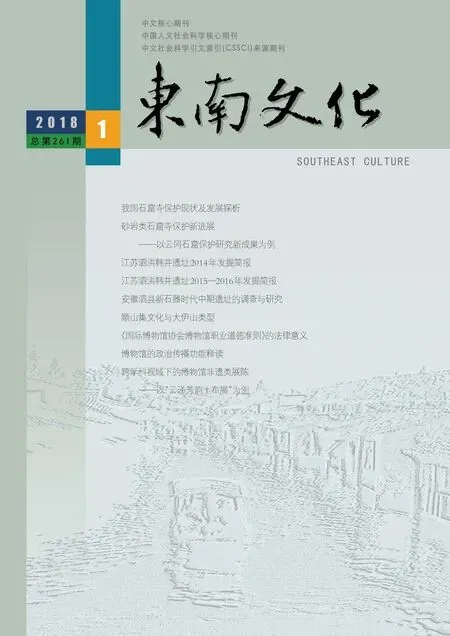江苏泗洪韩井遗址水稻驯化的植硅体证据及相关问题
2018-03-06邱振威庄丽娜林留根
邱振威 庄丽娜 林留根
(1.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2.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韩井遗址[1]位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韩井村(N33°35 43.20 ,E118°13 4.69 ,海拔20米),南距泗洪县城约20千米,西距顺山集遗址[2]约4千米。遗址的主体属于顺山集文化时期,面积约5万平方米。2014—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泗洪县博物馆合作开展韩井遗址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确定其为顺山集文化时期的一处环壕聚落。揭露的遗迹有顺山集文化时期的房址、成组分布的柱洞及灰坑、灰沟、水沟、大范围碎陶片铺设的活动面和水稻田等,大汶口文化时期少量灰坑及一些汉代墓葬等遗迹。
在发掘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堆积单位都采集了浮选和微体植物遗存分析土样。考虑较多堆积单位未发现与水稻直接相关的大植物遗存,本文通过微观视角进行考察,此处以植硅体分析和陶片显微结构观察为例进行介绍。
一、样品采集与实验
韩井遗址微体植物遗存分析土样的采集遵循针对性采样和自然梯度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注意观察采样部位的局部堆积形态。部分样品同步发掘工作及时采集,部分样品采用“剖面柱”预留方式采集(详见后文),样品信息详见表一。结合出土器物判断,此次分析的单位均属于顺山集文化一期偏晚和二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距今8450—8200年左右。其中仅H114①一个堆积单位来源于顺山集文化二期偏早阶段,考虑样品的偶然性和代表性,后文分析时仅以植硅体的百分比和浓度作为参照进行时间序列的比较,其他有关水稻植硅体和水稻驯化方面的讨论均系将所有分析单位作为整体考量。T3352k1为近椭圆形坑状洼地,T3354g1-g8系与洼地连接的水沟,二者是水稻田遗迹的组成部分。H172①层下“生土”(5~10厘米)和T3352k1②层下“生土”(26~30厘米)两个堆积单位作为实验参照采集样品[3]。
植硅体提取参考目前国内外从沉积物中提取植硅体的一般流程[4],并根据中国南方土壤沉积物性质略有调整。植硅体鉴定与统计参考已发表的一些标准[5]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收集的现代标本。采用加拿大树胶(沃凯Our⁃chem,CASNO[8007-47-4],折光率1.52—1.54)作为观察介质,在生物显微镜(型号:Nikon Eclipse LV100NPOL)下进行鉴定、统计和拍照。选取500个作为单个样品植硅体统计总量标准。

表一// 韩井遗址部分堆积单位植硅体分析土样信息
二、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植硅体提取情况
实验提取到的植硅体类型主要包括:扇型、方型、长方型、长鞍型、短鞍型、哑铃型、多铃型、横排哑铃型、平滑棒型、突起棒型、刺状棒型、尖型、帽型、齿型、木本型、莎草型、水稻双峰型等。另有少量导管、海绵骨针和硅藻(图一)。各分析单元的植硅体组合基本均以扇型、平滑棒型、哑铃型和帽型为主(表二)。鉴定出的植物种类主要包括:水稻(Oryza sativa)、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竹亚科(Bambusoideae)、早熟禾亚科(Pooide⁃ae)、莎草科(Cyperaceae)。

图一// 韩井遗址出土植硅体等微体植物遗存
实验提取到的水稻植硅体较为全面,既有来自稻叶的水稻扇型和横排哑铃型,也有源自颖壳的水稻双峰型,且其含量和浓度普遍偏高,尤其是部分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浓度甚至达到学者们提出的古水田判别标准[6]。类别上,所有样品几乎均是水稻双峰型占据主体(以T3354g2①、T3352k1②和H172①下“生土”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堆积单位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略多),水稻扇型次之,横排哑铃型植硅体则是零星出土。时间上,从顺山集文化一期到二期,韩井遗址水稻扇型和横排哑铃型植硅体的百分比和浓度(均值)均呈现减小的态势,而水稻双峰型则表现出相反的规律(表三)。堆积上,不同类型或同类堆积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同一堆积的不同深度(H114①)的百分比有随深度减少的趋势(图二、图三)。
值得注意的是,堆积单位T3352k1②(19~26厘米)的植硅体样品中可见大量炭屑和个别禾本科花粉,较之其他单位水稻扇型相对多于双峰型,而且双峰型大多破碎较甚,难以测量。
T3354g3①、T3354g5①、H172①和H173①出土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尤多,平均百分比和浓度分别达到了18.5%(11.6%~21.4%)和89274个/克干 样(56290~162614个/克干样)。水稻扇型植硅体浓度方面,顺山集文化一期的T3354g5①、H172①和H173①均达到甚至远高于5000个/克干样(5733~11119个/克干样);顺山集文化二期H114①堆积的三个不同采样梯度均值达到了4318个/克干样(3336~4928个/克干样),而且呈现出浓度随堆积深度递减而降低的趋势。
横排哑铃型植硅体在假稻属(Leersia)、菰属(Ziza⁃nia)等植物叶片中也普遍存在,所以其单独出现一般不能作为水稻遗存存在的证据[7],但其与水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体共存则强化了顺山集文化时期韩井遗址或周边有水稻生长的证据。
(二)水稻植硅体形状参数分析
针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参数的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水稻驯化过程。如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水稻扇型植硅体长(VL)、宽(HL)值渐增[8]。顺山集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长(VL)、宽(HL)均值在顺山集文化一期和二期分别达到了39.16μm和40.17μm(统计数量均为50个)[9],而同一阶段的韩井遗址出土水稻扇型植硅体呈现偏小的特点(表四、图四)。同属顺山集文化的这两个距离很近的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上的差异是水稻驯化早期的不稳定性使然还是分析对象来源偶然反映,抑或其他原因所致,尚需进一步讨论。

表二// 韩井遗址部分堆积出土植硅体鉴定、统计表(深度单位:厘米;其他单位:个)

图二// 韩井遗址部分堆积单位水稻植硅体百分比

图三// 韩井遗址部分堆积单位水稻植硅体浓度
目前,学界一般采用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形状参数[11]或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12]对水稻的野生与驯化类型进行判别。但是,囿于多种主客观因素,这两种方法很少被同时应用于同一批样品的分析,容易造成交互验证的缺失。韩井遗址出土的水稻植硅体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契机。然而,基于以上分析单位的水稻扇型、双峰型植硅体反映的韩井遗址水稻野生与驯化情况存在一定非协同性(图五、图六),即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给出的野生与驯化类型比例几乎均达到水稻双峰型判别结果的两倍。我们注意到,后者有接近45%的比例系介于野生与驯化之间的“中间类型”。因此,究竟是“中间类型”使然还是两种判别方法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表三// 水稻植硅体百分比和浓度均值、范围的分期对比

表四// 韩井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参数

图四// 韩井遗址和顺山集遗址不同阶段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对比
结合淮河下游顺山集,浙江钱塘江流域上山、荷花山、跨湖桥、田螺山等遗址的植硅体分析(图五、图六),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和水稻双峰型植硅体总体指向驯化长程于波动中进步,但两者同样呈现出非协同性现象。前者指示与钱塘江流域相比,淮河下游以韩井和顺山集遗址为代表的水稻驯化节点更具“进步性”;后者似乎支持相左的指征。
一般我们倾向将造成这些差异或异常的可能原因归于水稻驯化早期过程的不稳定性。但样品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观察、测量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以及统计分析的方法选择和主体误差均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尤其需要注意不同遗址统计分析的过程,如用于统计分析的植硅体总量、出土单位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等。
浮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多指标[17]表明,采集是顺山集遗址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水稻生产是生业结构的有效辅助[18],而这或与全新世早期的气候压力有关[19]。此类现象在淮河下游甚至长江下游地区是否具有普适性和时效性,尤为值得探究。
三、陶胎掺入稻壳反映的水稻栽培与驯化实践
在韩井遗址陶器整理过程中发现部分陶片内外壁、陶胎断面有不同程度的疑似稻壳羼和物或印痕存在,而且在夹植物陶器和泥质陶器上尤为明显,初步观察顺山集文化一期的堆积单位有T3350④、T3350⑤、H122①、H128①和H135①等。进一步通过微观结构观察与局部点位的植硅体分析,验证确系制陶过程中掺入的来自水稻秸秆与颖壳的植物残留。现以灰坑H135①出土具有较典型特征的陶片为例分别介绍陶片内外壁、剖面的显微观察和局部植硅体提取情况。
本分析的主要理论依托和技术手段是:显微观察可以初步判定水稻颖壳对应印痕的存在,再对疑似水稻颖壳的局部残留进行植硅体提取与分析,实现交互验证。

图五// 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个数视野下的水稻驯化过程

图六// 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形态测量视野下的水稻驯化过程
H135①出土的一件夹植物陶片,呈现外灰内红的特征,质地疏松,多孔结构。陶片外壁多见明显的稻壳印痕(彩插四),内壁和陶胎断面除此以外又见印痕处填充白色半透明状残留物。手术刀片刮取此白色物质并在生物显微镜下直接辨识出全部为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彩插五),或大或小碎片状。
目前的定性观察与分析,基本可以认定稻壳破碎后被作为羼和料用于韩井遗址的陶器制作。结合以上对顺山集文化一期和二期阶段韩井遗址水稻驯化程度的分析,这种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应是建立在水稻的栽培实践过程中对水稻认识程度提高的基础上。至于韩井遗址出土陶器的稻壳羼和料是否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要进一步增加观察单位、扩大统计基数,同时还要考虑夹砂陶与夹植物陶的本身属性区别、顺山集一期到三期夹砂陶向夹植物陶的演变以及稻壳羼和料与制陶业的关系等。
四、几个问题
(一)韩井遗址的生业形式
韩井遗址三十余个单位出土了炭化水稻,个别灰坑内发现了驯化类型水稻小穗轴,是水稻栽培和驯化的直接证据。在T3352③层和T3354③层叠压的水沟和洼地组合遗迹的填土(即S1①)中出土了较多的水稻植硅体,而且不乏驯化类型,结合这组遗迹的结构特点,笔者推测此组遗迹与人类栽培与驯化水稻的行为有关,很可能是当时的水稻田。目前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水稻田分布于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淮河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涵盖了距今七千年到四千年的时间范畴,其中淮河中下游的史前水田仅见距今四千年前的藤花落遗址。因此,韩井遗址发现的水稻田,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与人类驯化水稻相关的遗迹。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整理表明,哺乳动物以猪的比例最高、鹿次之,还有较多以鱼鳖类为主的水生动物。初步看来,水稻栽培和野生动物的利用在韩井遗址长期共存。

表五// “生土”堆积出土水稻扇型植硅体测量数据
中国的稻作农业在距今10000—9000年前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20]。贾湖一期的贾湖遗址[21]和八里岗遗址[22]浮选出土的炭化水稻和一定比例驯化类型水稻小穗轴表明,距今8500年左右淮河上游已经存在驯化程度较高的水稻[23]。地处淮河下游的顺山集遗址和韩井遗址出土距今8500—8000年前的炭化水稻、驯化类型水稻小穗轴和一定比例的驯化类型水稻植硅体,指示水稻栽培行为和驯化进程。结合黄河下游地区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24]和西河遗址[25]出土距今8000年左右的炭化水稻,再次印证了全新世大暖期以来的稻作农业由长江流域北扩的过程[26]。这一过程或与气候环境的有利因素、文化传播以及人群迁移有关[27]。顺山集和韩井遗址出土了水稻田、炭化水稻、水稻小穗轴、水稻植硅体、稻壳羼和料等水稻遗存,表明顺山集文化时期的淮河下游处于这次稻作农业北扩的关键时空位置上。
因此,韩井遗址水稻田等遗存的揭露有助于分析淮河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的形式与内容,为探讨中国水田稻作农业体系提供了更早的关键资料,更为研究东亚地区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以及中国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跨区域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此外,为了系统研究韩井遗址的生业模式,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有机残留物分析等多方面研究工作正在开展。随着生业经济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了解八千多年前的淮河中下游的社会以及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田野考古发掘与微体土样采集的协调
微体植物遗存分析土样的采集往往因较低普及性(远低于浮选土样的采集)和易污染性不易为一般田野发掘工作者所掌握,加之田野考古现场的发掘工作涉及一系列操作规程,故此一般微体土样的采集需要相对专业的人员进行操作。这样就容易产生田野发掘进度的要求与微体土样采集不及时之间的矛盾。结合韩井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微体土样采集的实际操作,我们提出“剖面柱”的概念与尝试。具体来说,在某一遗迹(如灰坑)内的堆积清理过程中,随着1/2或1/4方式清理的完成,完整暴露出整个遗迹的堆积构成后,选择其中代表性较强的堆积部分保留下来,形成20~30厘米见方的“剖面柱”(彩插六︰1),其余堆积完成清理和浮选样品等的采集工作。这样一方面对整个遗迹的文字记录、绘图、照相等田野操作基本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另一方面给微体分析工作所需样品提供了采集的缓冲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展采样工作前最好用封口袋或保鲜膜一类介质将“剖面柱”部分暂时“封存”,待采样工作完成后再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堆积记录工作。

表六// “生土”堆积出土水稻植硅体判定情况
这种方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田野发掘完整性与微体取样科学性之间的矛盾,实际操作性较强,可以尝试推广。
(三)“生土”与水稻植硅体的“矛盾”
两个作为实验参照的初步判定为“生土”的堆积单位 H172①下“生土”(5~10厘米)和T3352k1②下“生土”(26~30厘米)(彩插六︰3)中提取到含量较高的水稻双峰型和水稻扇型植硅体。H172①出土的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含量和浓度显著高于其下部的“生土”堆积,除此以外,这两个“生土”堆积中出土的水稻植硅体与其上部人为堆积的情况并无明显差异。
从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上看,H172①下“生土”(5~10厘米)出土可供测量者(8个)的长、宽平均值略高于本次分析人为堆积的对应值,而T3352k1②下“生土”(5~10厘米)出土者(3个)的测量值均偏低(表五)。
值得注意的是,“生土”堆积中出土的“驯化型”水稻双峰型和扇型植硅体均有很少量存在(表六),尽管数量很少但一定程度上却指示田野发掘现场对“生土”堆积性质的判定存在问题,或许将其定为“次生土”更合适。结合发掘过程中观察到发掘区局部剖面堆积的“裂隙”现象(彩插六︰2),应系土壤中的植物根系、虫洞或地质作用等所致,上部晚期堆积极易混入下部早期堆积。若是二者土质土色较为接近或者“裂隙”较小,在取样过程中不易发现也属常态。此处两个在发掘和取样过程中判断为“生土”堆积的植硅体情况,给我们今后的田野发掘和样品采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1]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江苏泗洪韩井遗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8年第1期。
[2]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编:《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3]这两个遗迹内的填土清理完毕后在其底部暴露出黄色黏土,发掘现场判断为生土或次生土沉积,即为此处表述的“生土”。本文以此两个样品为例,尝试对考古发掘过程中一般认定为生土或次生土堆积的性质与判断作一些论证或讨论。
[4]Lentfer C.J., Boyd W.E.A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fortheextraction ofphytolithsfrom sedi⁃men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8, 25(12);Pearsall D.M.Paleoethnobotany:A Handbook of Procedures.Academic Press,2000;王永吉、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海洋出版社1993年;Piper⁃no D.R.:《植硅石分析──在考古学和地质学中的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5]Pearsall D.M.Paleoethnobotany:A Handbook of Proce⁃dures.Academic Press,2000;王永吉、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海洋出版社1993年;Piperno D.R.Phytolith Analysis:An Archaeological and Geological Per⁃spective.Academic Press,1988;Piperno D.R.,Pears⁃all D.M.The Silica Bodies of Tropical American Grasses:Morphology,Taxonomy,and Implications for Grass Sys⁃tematics and Fossil Phytolith Identificati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Twiss P.C., Suess E.,Smith R.M.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grass phy⁃toliths.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Proceedings,1969,33(1);王才林、宇田津郎、汤陵华等:《植物蛋白石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吕厚远、贾继伟、王伟铭等:《“植硅体”含义和禾本科植硅体的分类》,《微体古生物学报》2002年第19卷第4期。
[6]宇田津彻郎、汤陵华、王才林等:《中国的水田遗构探查》,《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靳桂云、燕生东、宇田津彻郎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8期。
[7]Yost C.L.,Blinnikov M.S.Locally diagnostic phyto⁃liths of wild rice (Zizania palustrisL.) from Minneso⁃ta, USA: comparison to other wetland grasses and usefulness for archaeobotany and paleo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1,38(8).
[8]Fuller D.Q.,Harvey E.,Qin L.Presumed domestica⁃tion?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fif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Antiquity,2007,81(312).
[9] Luo W.,Yang Y.,Yao L.et al.Phytolith records of ric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Middle Neolithic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Huai River region,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6,426.
[10]同[9]。
[11]Zhao Z.,Pearsall D.M.,Benfer R.A.et al.Distin⁃guishing rice(Oryza sativaPoaceae)from wildOryzaspecies through phytolith analysis,II Finalized meth⁃od.Economic Botany,1998,52(2).
[12]Fujiwara H.Fundamental studies in plant opal analy⁃sis(1):on the silica bodies of motor cell of rice plants and their near relatives,and the method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Archaeology and Nature Science,1976,(9);Lu H.,Liu Z.,Wu N.et al.Rice do⁃mestication and climatic change:phytolith evidence from East China.Boreas,2002,31(4);Huan X.,Lu H.,Wang C.et al.Bulliform phytolith research in wild and domesticated rice paddy soil in South China.PLoS ONE,2015,10(10).
[13]同[9]。
[14]Wu Y., Jiang L., Zheng Y.et al.Morphological trend analysis of rice phytolith during the early Neo⁃lithic in the Lower Yangtz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4,49.
[15]同[9]。
[16]同[14]。
[17]a.同[9];b.吴文婉、林留根、甘恢元等:《泗洪顺山集二期聚落环境与生业的植硅体证据》,《中国农史》2017年第1期;c.杨玉璋、Li WeiYa、姚凌等:《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来源与石器功能》,《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7期。
[18]同[17]c。
[19]同[17]b。
[20]赵志军:《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21]程至杰:《淮河上、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22]邓振华、高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3]张弛:《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文物》2011年第3期。
[24]Crawford G.W.、陈雪香、栾丰实等:《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Crawford G.W.、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东方考古》2006年第3期。
[25]吴文婉:《中国北方地区裴李岗时代生业经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26]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