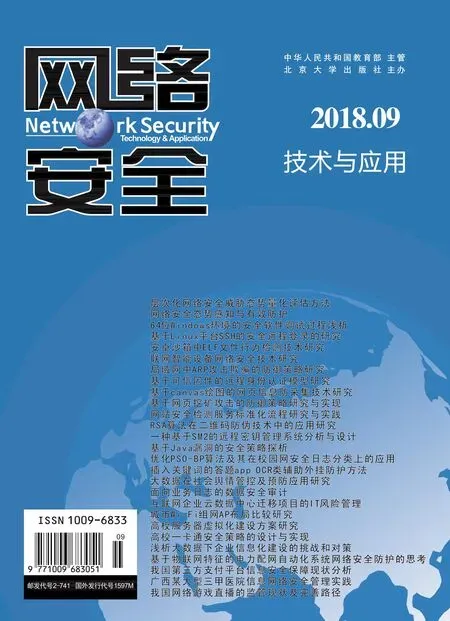关于互联网+软件平台模式打击传销的应用实践和探讨
2018-03-05高振林裴晓燕
◆高振林 裴晓燕
关于互联网+软件平台模式打击传销的应用实践和探讨
◆高振林 裴晓燕
(北海市公安局 广西 536000)
本文介绍了传销的危害,分析了传销发展的新形势,难以打击和消灭的原因。针对传销防范打击难的原因,提出了通过互联网+软件平台模式打击传销,建立打击传销的群防群治模式,实践效果明显。本文还探讨了该模式在打击传销方面的推广以及意义。
互联网+;软件平台;打击传销;群防群治
0 引言
传销害人害己,大多数参加者血本无归、流落异地、生活悲惨。由于传销人员发展对象多为亲戚、朋友、同学、老乡,其不择手段的欺骗方法,导致人们信任度下降,引发亲友反目,甚至家破人亡。
随着传销不断进化,结合“互联网”、电子产品等等,隐蔽性、欺骗性更强,范围更广,有蔓延之势。传统打击传销的手段一般都是依靠线人举报,工作效率低,身份也难核实。
1 传销犯罪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传销犯罪现状
近年来传销案件频发。2016年国内传销案件超过2800起,同比增加19%。目前在广西、安徽等传销重灾区,始终没得到根治。2017年,四川警方破获“12.18” 云数贸特大网络传销案,涉案金额5.2亿元,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1.2 原因难点分析
打击传销难主要有“三大原因”:侦查难、抓捕难、打击取证难。
(1)侦查难
宣传不足,民众认识不到位:认为查处传销不利于当地的稳定;或者认为传销对当地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进行地方保护等。
(2)抓捕难
传销组织行踪诡秘,极易“人间蒸发”。“互联网”传销发展迅速,出现了网络传销。传销具有扩张迅速、隐蔽性强等特点,难以抓捕。
(3)打击取证难
传统打击传销的手段一般是依靠线人举报,查处传销案事件时也多是用纸笔来登记,采集效率低,由于传销组织封闭性强,少有证人证明案件事实、指证传销头目。
2 互联网+防范打击模式实践应用
针对传销的发展形势,我们运用“互联网+”思维,研发了打击传销的软件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网站以及综合研判分析平台。
(1)微信公众号:用于实时推送打传信息、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传销的网站或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等信息举报;传销视频、照片、文字信息等线索上传。
(2)APP(警用版):用于传销信息(包括人,车,物)查询、录入、核实、研判等;APP(民用版):用于查询来访或租房人的身份,整治涉传出租屋,釜底抽薪剥离传销组织的“生存土壤”。
(3)网站:用于给没有安装微信的人群提供举报传销的渠道。
(4)综合研判分析后台。用于案件库、人员库、线索库的建设。
针对具体人群,有以下效果:
(1)针对警察,APP可以为警察提供传销信息(包括人、车、物)查询,信息录入、核实、研判,后台将信息汇总成证据线索,梳理传销人员等信息。
(2)针对社区、物业管理员,APP可以提供来访或租房人的身份查询,检验其是否为传销人员,同时将信息推送给系统后台,以便研判和抓捕措施。
(3)针对民众,通过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可以将疑似传销视频、地图定位上传;另一方面可以举报传销的网站等信息。
该项目实施以来,在多次打击传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系统协助检查出租屋4114 户,捣毁传销窝点3871处,同比增加21%,排查传销人员8900 余人,同比增加26%,后台采集录入涉传人员信息4万余条,数据670万余条(含涉传人员及“一日游”大巴车等相关数据),配合执法人员侦办了4.23自然元素、4.13五行币、5.25赛比安等一系列传销案件,提高了工作效率,打击了传销泛滥的嚣张气焰。
3 结语
为了提高打击传销犯罪的效率,建立“查、防、控”的打传模式,我们运用“互联网+”的科技手段,研发了一套互联网+打击传销软件平台,广泛收集线索,通过系统后台来研判、分析和审核,形成一套打击传销模式,实践证明通过此模式工作,能更好、更快地防范打击传销。
[1]Dan Vesset,AshishNadkarni,etal.World Wide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2012-2016 Forecast[R].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2012.
[2]赵文正,王在云,李阿芳.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相关分析[J].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018.
[3]马思婷.我国反传销犯罪的法律制度完善研究[D].宁夏:宁夏大学,2016.
[4]唐金权.大学生传销问题及其防治[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陆克威.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思考与侦查对策[J].华东政法大学,2012.
[6]Daryl Koehn.Ethical Issues Connected with Multi-Level Marketing Schem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1.
获2017年度公安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应用创新项目 (2017YYCXGXQT038),广西公安厅应用创新项目 (GAT2017-2)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