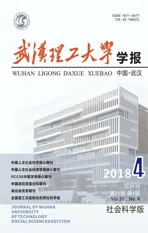论陆羽的饮茶观—以《茶经·六之饮》为视角
2018-03-03刘垚瑶
刘垚瑶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天津 300110)
《六之饮》在陆羽《茶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饮茶的意义、沿革与方式方法,集中清楚地体现了陆羽的饮茶观。
一、《茶经·六之饮》的形式与内容
(一)《六之饮》的行文结构与修辞
本文研究的对象——陆羽《茶经·六之饮》,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南宋咸淳所刊百川学海本《茶经》为据,该刊本将《六之饮》部分分为五个段落进行论述,其采用递进式的结构顺序,分别讲述了茶与酒、水的区别,茶作为饮料的起源及传播,唐代茶的分类及饮用方式,茶之九难,饮茶时茶碗之数量,进而并提出了“精行俭德”的饮茶观。
吴觉农在《茶经述评》中将《六之饮》概括为三个部分,即:“饮茶的现实意义、饮茶的沿革和饮茶的方式方法。”[1]陆羽将前五章论述的有关饮茶之源、具、造、器、煮五方面的内容,加上本章的“饮”,统一概括为“九难”,对前文的内容进行了强调和升华,并提出了自己的饮茶观。
《茶经》不仅描写了大量的“茶人”“茶事”,也极具语言特色,运用了比喻、排比、对比等大量修辞手法。在《六之饮》中主要体现在对比和排比两种修辞手法上。《六之饮》第三段中写道:“以汤沃焉,谓之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2]93这段话将用开水冲泡的茶和加了姜、栆等配料冲泡的茶进行对比,强调清水煮茶的清饮观。陆羽将这两种饮茶法进行了对比,由此可见其对茶之煮饮的严格要求。
在《六之饮》第四段描述“茶之九难”中,陆羽这样写道:“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擅鼎腥阮,非器也;膏薪厄炭,非火也;飞湍奎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邃,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2]93接连运用九个排比句,从“非”的角度强调了“茶之九难”,指出饮茶意在求精,每一步都要做到精益求精。读起来朗朗上口,在语义上也达到了强调的效果。
(二)《六之饮》的内容
1.饮茶“荡昏寐”。
《六之饮》中提到:“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2]93这句话将茶与酒、水,进行了对比,从而突出了茶可“荡昏寐”的功用,指出茶是一种兼具药理和生理作用的可以提神醒脑的饮料。茶同样在精神生活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茶可以清除昏昏欲睡的精神状态。现代科学通过提取茶叶物质可以得到证实的是,茶叶中含有茶多酚、咖啡碱、蛋白质、脂肪等维生素成分多达350多种,是非常富有营养含量的饮品,与此同时,还具有调节生理机能的作用,可以说有着良好的药用效能和保健作用。
中国民间有饮茶谣云:“早茶一盅,一天威风;午茶一盅,劳动轻松;晚茶一盅,提神去痛;一日三盅,雷打不动”,也可由此体会出“荡昏寐”的功效。在茶叶成分中,生物碱的含量约占3%到5%的比例,其中包含着咖啡碱、可可碱、茶碱和氨茶碱这些成分。而咖啡碱的含量最多,且咖啡碱极易溶解于水,用沸水冲泡时,茶水中的咖啡碱可以达到茶中含量的80%。如果一个人每天喝四到五杯茶,那么人体内便可吸收约0.3克的咖啡碱。咖啡碱的作用是能使中枢神经兴奋,从而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可以增进人体内的血液循环。饮茶可以刺激神经中枢,使大脑皮层兴奋,从而使人精神振奋[3]214。
2.茶之九难。
茶之九难是饮茶最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六之饮》中最核心的内容。
一是制造。陆羽在《三之造》中提到唐代采摘法,即趁着“凌露”采摘“颖拔”的枝叶,即趁着凌晨的时光去采摘茶叶。对于生长在土壤肥沃之地和贫瘠之地的茶树来说,其枝叶生长情况是不同的,要采摘生长的秀立挺拔的茶叶。如果在阴天采摘,夜间焙制,那么便做不出好茶。
二是辨别。同样在《茶经·三之造》中陆羽对制作饼茶的茶叶规格品质提出严格的要求,古时评茶主要依靠视觉,茶叶外形是否光滑,外形褶皱的,茶汁流失较少也是好的。色泽为黄色比黑色好,但黄色呈现的茶汤品质比黑色差。饼茶表面凹凸不平要比平整的好,因为茶汁流出少。但通过口嚼和鼻闻香气,无法做到真正的茶叶鉴别。茶叶的辨别在《茶经·一之源》中也有提及。现代评茶技术主要采用高科技手段,通过物理或化学鉴定来评判茶叶。
三是器具。陆羽在《茶经·四之器》和《茶经·二之具》中详细罗列了煮茶每一个步骤所用的器具,有风炉、灰承、火夹、锅、漉水囊、碾等等。每件器具都造型各异,设计独具匠心,但沾染了腥味的杯碗之类的饮具,不能作为煮茶的器具。
四是用火。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提到,烤煮茶汤,必须用冒着火焰的木炭,以木炭为最佳材料,用沾有油烟的柴和烤过肉的炭,不适合做煮茶的燃料。
五是选水。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提到,山上的池水和来自钟乳石的滴水是最好的水,江河之水次之,属井水最差,奔涌的急流和停滞的死水不适合做煮茶的水。
六是烤炙。《茶经·五之煮》中提到,烤茶对热量和时间都有讲究,要使茶饼受热均匀,不要烤焦,茶叶外熟内生是烤炙不当。
七是碾末。《茶经·五之煮》中提到,碾茶时要将饼茶分成小碎块放入碾钵,然后将茶碾磨的粗细适中,把茶研磨成青绿色的粉末和青白色的茶灰,是研磨不当。
八是蒸煮。《茶经·五之煮》中提到,煮茶有“三沸”要注意火候、烟气和气泡的状态,操作的不熟练或者搅动得太急,烹煮不出好的茶汤。[4]
九是饮用。这是最重要的环节,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进行了详细论述。作者特别提及茶要趁热喝,一般第一碗茶汤最好,但也要分茶,有的茶汤第一碗是要倒掉不喝的,从第二碗开始入味。只在夏天喝茶而冬天不喝,不能称之为饮茶。香高味美的好茶一炉只能煮三碗,次之是一炉五碗。若喝茶者有五人,那么就盛三碗,如果宾客达到七人,就分五碗,若座客有六人,便不需要计算碗数,按少一人计算就好,把原先留出来的茶汤留给所缺之人。
3.茶汤要“珍鲜馥烈”。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提到了茶汤要做到“珍鲜馥烈”,即在感官上达到一种完美。“珍”是指煮出来的茶汤要具有很高的品质,同样也就十分珍贵。“鲜”是指茶汤要是新鲜的、原汁原味的。“馥”是指茶香四溢,悠远绵长,给人嗅觉上的直观感受。“烈”是指在闻到茶香的同时,品出的茶味也要甘醇浓烈。陆羽喝茶讲究“品”茶,人们在品茶之前要先闻茶香,然后再小口慢饮。陆羽十分重视茶汤的色、香、味。“干看”要注意茶的色泽、气味、咀嚼茶叶并闻香气。“湿看”品茶汤是否醇厚,注重看茶汤表面“沫、饽、花”的形态。这一内容在《茶经·五之煮》中有详细介绍。
陆羽所强调的“品”,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所在章节描写妙玉泡茶款待宝玉中有所体现。小说描写妙玉笑说宝玉道:“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曹雪芹笔下的妙玉被视为嗜茶如命、孤寂清高的女子,妙玉认为饮茶一杯便已足够,饮茶的重点在“品”,而不是解渴。饮茶重在一种意境,鉴别茶叶的气味和口感,欣赏茶在水中的样貌,因此有言“三品方知真味,三番才能动心”。
二、《茶经·六之饮》的饮茶观及贡献
从《六之饮》有关“荡昏寐”、“茶之九难”、“珍鲜馥烈”等内容中不难看出,陆羽在采茶、制茶再到品茶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要求做到精益求精,并且强调以“俭”为主,且不是单纯的“饮”,而要去“品”,达到精神上的感知,因而是一种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饮茶观。陆羽的煎茶品饮之道,在自成体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饮茶风尚的传播。
(一)《六之饮》的饮茶观
1.“精行俭德”。
《六之饮》通篇向我们传达的,便是“精行俭德”的饮茶观,这也是陆羽衡量茶人道德修养的基本标准。所谓“精”,即所有的工序都要精益求精。《管子·心术》中说:“中不精者心不治”[5],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事如果做不到专心致志,那么他做事的心力就没有到位。前文提到的“茶之九难”,每一步都需要茶人做到精益求精,不然便做不出高品质的茶。所谓“行”与“德”,是对茶人道德品质的要求,陆羽认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操行的人,他在行茶事、品茶论道中也可以做得很好[6]。这一点在陆羽的《六羡歌》中达到了完美的诠释:“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者,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7]14。
陆羽所倡导的茶学精髓即是“性俭”。他从饮茶的数量和茶汤的性质来说明“俭”的重要性。我们喝茶时,水不宜过多,从保健方面来讲,茶的药效也会因此有损减。同样,喝茶的碗数也不倡导过多,因为目的不是解渴,而是品味茶汤的精华。除此之外,趁热喝茶也很重要,茶汤的“沫、饽、花”,只有趁热喝才能品味得更加深刻,也是茶味最“烈”的时刻,若是等茶凉了再喝,则无法体味这种味感[7]32。前文提到的“以汤沃焉,谓之茶”的清饮观,同样体现了陆羽对“俭”的要求。
据了解,现在很多功夫茶的壶杯都做得非常精致小巧,也是将陆羽“茶性俭”这一观点运用得淋漓尽致。而陆羽所提倡的“俭”,在煮茶用具中也有体现,要求茶具要用生铁制成,瓷质和石制的茶具经不起长久使用。如果采用银制,又太过于奢侈,这里所体现的“俭”是节俭之意。我们也可由此看出陆羽所具备的“俭德”,即为人廉洁,高雅朴实,勤俭节约[8]。
2.“天时、地利、人和”。
如今很多人的饮茶观多停留在品饮的层面,而陆羽的饮茶观在“茶之九难”中就得到了深刻的诠释,从茶树的种植,茶叶的采摘再到制作、品饮,是每一步都环环相扣,成体系的饮茶观。
“茶之九难”第一难是“造”,茶树枝叶的生长情况依赖于一定的自然气候条件,属于“天时”。光照条件好,茶树生长茂盛,茶叶呼吸作用加强,从而影响茶叶色泽和味道。雨量多、气温高时,茶芽生长迅速。所谓“地利”,即生长在土壤肥沃或贫瘠,向阳或背阴,陡坡或平川上的不同的茶树,生长状态,成茶品质是不同的。要采摘其中长势良好的茶叶,并借助多种制茶器具来加工制造,以期达到高品质的成茶。陆羽的饮茶观最重要的便是在达到“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要讲求“人和”,这里的“人和”不仅指茶叶采摘制造中人在其中参与采摘及辨别、加工和传承技艺、传播茶文化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一种“品悟”的心境,追求内心的淡泊与沉静,以期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3]262。
(二)煎茶品饮之道的“教科书”
陆羽详细地将自己实践调查的有关茶的采摘、煎煮、饮用等方法在《茶经》中进行了完整的论述,使得茶叶的生产发展有了完整的理论依据,也使得茶文化成为了一项学科。陆羽自创的“煎茶法”,可谓是茶叶煎茶品饮之道的“教科书”,不仅详细地列出了各类煮饮用具,而且记叙了详细的操作过程,其中,尤其以《六之饮》中“茶之九难”最为显著,其详细地介绍了“采摘、加工、鉴别、取火、选水、烤茶、碾茶、煮茶、饮茶”九大难点,成为了当时以及后世品饮的典范。明朝陈文烛在《茶经》序中称赞道:“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稷树艺五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茗而天下知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并祠可也。”不仅如此,《六之饮》中所倡导的“精行俭德”的饮茶规范,也值得后人学习。
(三)促进饮茶风尚的传播
饮茶风尚的传播在唐代达到了盛行阶段。《封氏闻见记》记载:“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9],反映出了当时唐代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到了唐中叶以后,茶叶的生产发展及消费日益增强。在唐代历史上,品茶赋诗、作文的风气在文人间广为流传,如白居易、李白、刘禹锡、温庭筠等人便是如此。这一时期陆羽《茶经》的问世,也使得茶道之风兴起,出现了大量赞颂茶的诗文。例如,白居易的《山泉煎茶有怀》诗云:“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盌,寄与爱茶人”。白居易的《谢李六郎中寄蜀新茶》诗云:“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鞠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10]。
此外,由于佛教戒律中要求有酒戒,便使得僧人们以茶代酒的现象尤为普遍,加之茶有使人精神振奋的效果,促使很多僧徒们养成了饮茶的习惯,并逐渐形成一套庄严肃穆的茶礼[7]41。中国的茶传到日本,也与来华留学的僧人们有关。并且,寺院多地处于名山大川的幽静之处,许多僧人在寺内种茶,并传播种茶技艺,也推动了很多优良的茶种得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
三、《茶经·六之饮》中饮茶观的局限
陆羽在《六之饮》中所提倡的部分饮茶观,只适应当时所处的社会,如果将其放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的一些观点即使是在当时看来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然,之所以会如此,这与我们当今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息息相关。
(一)关于茶叶的采摘
《六之饮》“茶之九难”中首先提到的是茶的制造,而制造最重要的前提是采摘。《茶经·三之造》中提到:“茶之笋者,竽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2]文中提到了“凌露”采摘的观点,即迎着凌晨的露水采摘茶叶,我们称其为露水叶。今天看来,露水叶的质量是不好的。因为,如今经化学检测,露水叶中的水含量可达84%左右,露水鲜叶的表面含水率约为20%,这些叶表所沾附的露水在茶叶杀青时要吸收大量热量后才能使水分蒸发掉,需要提高锅温才能保证杀青叶的品质,如乌龙茶鲜叶的早青叶(上午九点之前采摘)附着露水较多,会使得乌龙茶的香气较差等。因此,“凌露采摘”,只适用于唐代采摘的方法,已不适合当代。
另一个局限便是“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这一要求是基于唐代的饼茶蒸青和杀青方面对鲜叶附着水分需要控制这一方面来说的,但这一要求在当今茶叶采摘方面是不可行的。采摘茶叶需要严格控制采摘的时期,尤其是雨量多、气温高的时候,容易促进茶芽的生长,应该及时采摘。
(二)对茶的色、香、味的评判
“茶之九难”中“第八难”即为“蒸煮”,而煮茶的好坏直接与茶的“色、香、味”密切相关。《茶经·五之煮》中云:“其色缃也,其馨[上必下土右欠]也。其味甘樌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2]78分别说出了茶汤的色泽是浅黄色,茶香醇厚,茶味先苦后甜是好茶。
在现代科学技术检测中,茶中的芳香物质,按照有机化学的分类方法可以分出300多种香味。每一种茶香是无法用简单的词句去描绘的。按照目前大众所熟知的茶类可以粗略将其茶香简要概括为:黄茶、白茶的气味是清香;红茶气味是铃兰香、玫瑰花香或果香、甜花香;花茶为玫瑰花香或甜花香;乌龙茶为花香;黑茶为陈香;绿茶为清香和青草香。而茶色目前可粗略概括为红、橙、黄、绿、青、褐、灰、白、黑这九种茶色。茶味按照味觉感官反映可粗略分为酸、甜、苦、辣、鲜、涩这六种味道[3]194。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无法单纯按照陆羽评判茶汤的标准进行品鉴。
“色”的另一种评判体现在茶树叶的色泽上,为“茶之九难”第二难“辨别”,在《茶经·一之源》中所云:“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2]5,指生长在阳面山坡树荫下的茶树,以紫色的叶子为最好的茶叶,绿色的茶叶次之。茶叶颜色的不同与茶树的品种、所生长的土壤条件和覆荫等条件息息相关。茶嫩叶呈现紫色是因其接受紫外线光照强烈,温度升高,从而使得呼吸作用加强,促进了叶内花青素的形成。唐代制作饼茶时,对饼茶的苦味要求很高,紫色茶叶的味道要比绿色茶叶味苦,因而优选“紫者”[11]。但现今看来,单纯从茶叶的颜色来评估茶叶的好坏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生产实际了。
(三)对水质的评判
“茶之九难”第五难,即“选水”,在《茶经·五之煮》中提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原注:《赋》所谓‘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水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蓄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2]80由此可知陆羽评判水质的根据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在现今看来,这并不能作为评判标准,而且部分地区的水质污染较为严重,不可轻易饮用。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衡量水质的好坏,需要一系列科学的水质指标,如物理指标有水的温度、浑浊度、颜色等,化学指标有硬度、碱度、总耗氧量、氧气、二氧化碳等,生物指标有细菌总数、大肠杆菌、藻类等,放射性指标有总α射线、总β射线、铀、镭、钍等。
(四)清饮与调饮
“茶之九难”第九难为“饮用”,陆羽在《六之饮》中说:“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2]117文中所讲述的第一种煮茶法,是我们普遍所了解的煮茶、泡茶之法且广为沿用,我们常常称这样的饮用之法为清饮;而第二种饮法,加入了葱、姜、枣等调味品,这种煮饮方法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广为流行,只是煮饮时的器具和步骤略有不同,这样的煮饮方式为调饮。陆羽将第二种煮饮法做出来的茶汤称之为沟渠之水,在现今清饮与调饮皆盛行的时代,或者说在唐宋时期,都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在唐宋时期,清饮法与调饮法同时存在。一方面是按照陆羽的“性俭”观,在讲究饮茶艺术格调的品饮法中,是将其他佐料排除在外的,在调味中可以加盐。但在另一方面,调饮法在唐宋时期是十分流行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将这一种煮饮方式视为“沟渠之水”。如唐代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煎之。”宋代苏轼《次韵周禾童惠石铫》一诗就写道:“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苏辙《和子瞻煎茶》则云:“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老。又不见,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陆游《午坐戏书》写道:“贮药葫芦二寸黄,煎茶橄榄一瓯香”“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烹橄榄茶”等等[12]。
其次,在当代,清饮与调饮均十分盛行,多元文化的包容使得两种煮饮之法均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且同样在不同的地域流行。近些年来,很多茶艺表演多采用清饮法方式,如《九曲红梅》、《龙井问茶》等。在茶艺馆中,常见的还是清饮法,很多茶艺师也将清饮法的冲泡作为基本功。在国外的很多侨胞、华裔的家庭待客中和中餐馆中也以清饮多见。同时,调饮法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国内外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饮茶风俗中,如在俄罗斯,午餐喝茶时,要在茶中加入柠檬和砂糖等,招待客人时会在茶中加入果酱和蜂蜜,有时还会加入牛奶和鲜奶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调饮法尤为多见,如景颇族的“腌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傈僳族的“油盐茶”和苗族的“菜包茶”等。[13]另外,体现在保健茶中,现代很多美容保健品及罐装瓶装茶饮料中多添加了其他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