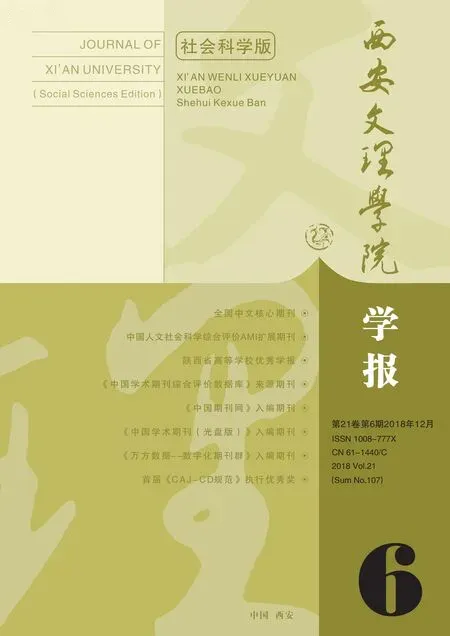汉代“三年之丧”的形态演进及其动因探析
2018-02-25唐紫薇
唐紫薇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611130)
一、“三年之丧”的基本内容
对于逝者的处理态度与表达方式,都体现着这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与理性自觉,在华夏文明圈内,以儒家的丧礼制度最为完善、普及。而关于丧礼的具体仪制,则是本乎经典顺势而行的。在《周礼》的五礼分类系统下,丧礼隶属于凶礼,“以丧礼哀死亡”,而《仪礼》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章节,则是从仪节细则、服制规定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叙述,是丧礼制度的坚实理论基础。而《礼记》一书则通过对于儒家思想的阐发论述的总集方式,从不同角度辨析了丧礼的仪式内容与文化内涵,如《丧大记》《问丧》等章节。而在丧礼制度中,依据丧服体系则可将丧期与服制相结合,划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其中“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1]1374,可谓礼之至隆者,具体亲属、尊卑规定使得“三年之丧”这一仪制有子为父服、诸侯为天子服、父为长子服、妻为夫服、母为长子服等情况,由此可将其分为两类:至亲之间及臣下对于君主。故而《礼记·大传》曰:“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1]910以血缘亲疏及政统地位为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这也是华夏文明伦理共同体的核心框架之所在,其余的服术都是由“亲亲”“尊尊”衍生而来的。故而“三年之丧”作为服制之最重、丧礼之至隆者,必然在社会实践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地位,从而在各朝各代展示其“称情以立文”的现实作用。在此则将目光集中在汉代,通过对统治者的官方态度及民间风尚的自觉性两个方面来讨论“三年之丧”在汉代的形态动态变化,并试图阐述其中的社会动因,以期更好地理解“三年之丧”这一重礼。
二、“三年之丧”的起源认识
关于“三年之丧”源流问题辨析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中,丁鼎先生的《“三年之丧”源流考论》和黄瑞琦先生的《“三年之丧”起源考辨》都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深刻而清晰地论述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多种认识,而最常见的主要有四种观点:“自古有之”说、殷商旧制说、周代制礼说、孔子制礼说。同时也有一些新论,如丁鼎先生的东夷之俗说、方述鑫先生的“周祭说”。在此就通过对这些不同观点的整理,试图厘清部分“三年之丧”的起源说认识,分别对其基本信息进行简单介绍。
(一)“自古有之”说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而有言礼起于俗。《荀子·礼论》中提出:人之争夺而无度量分界,致使乱象频出、物欲争斗,先王制礼作乐,使之知礼义文理之所以而养情。而最初的行为准则则来自于人们长期社交经验的磨合,这种能够清晰、明确、有效地表达的方式则渐而推广,成为约定俗成的礼。《仪礼注疏》:“此谓黄帝之时也。在《黄帝九事》章中,亦据黄帝之日,言丧期无数,是其心丧终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朴渐亏虽行心丧更以三年为限者。”由此可见,在黄帝时期还未有约定俗成的仪式,但已经有了“心哀”的意识,而到了唐尧虞舜之时则有“三年”的说法。因而对待死者的离世,表达出哀切的情感诉求,成为“三年之丧”产生的可能性猜测之一。即如《孟子·万章上》提及的:“《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1]1374可见古籍文献中记载着自古存有“三年之丧”的痕迹,但文献资料缺乏充足的考古证据,且由此风俗“三年之丧”服制仍未成形,仍属一种自发行为而不具备自觉性,因而尧三年丧后舜尤“葬于苍梧之野”。即如《仪礼·丧服》所载:“又案《易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2]许慎注《淮南子》曰:“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礼。”[3]9由此可见,“三年之丧”的礼制意识在三王时期还未成形。
(二)殷商旧制说
《论语·宪问》记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4]从中得知高宗,即殷王武丁,已有不言以表哀悼的信息。守丧制三年以为后世所表,由此孔子得出三年之丧为“古之人皆然”的结论,而前提必然是建立在殷商已有三年之丧的服制,又有清人焦循在《孟子·滕文公上》“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疏中说:“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滕文奉行……是皆商以前之制”[5],其后傅斯年、胡适亦持此说。然而此说也是在文献记录上的推论,郭沫若先生在《殷虚书契》中根据殷墟出土的四片甲骨卜辞,厘清了帝乙在其父文丁死后的时间线,由此发现文丁离世后在三年内帝乙主持举行了四次殷祭,如按照“三年之丧”的“居倚庐,寝苫枕块,哭昼夜无时”不为礼、不奏乐的居丧仪态,这是不对应的。由此推翻了殷商时期成制说。同时李民先生的《高宗“亮阴”与武丁之治》一文对“高宗谅阴”进行解读,以亮为谅,即是信的意思,解阴为措,即是默、不语的意思,由此得出“高宗‘亮阴’,乃是由于‘默以思道’、‘恐言之不类’。‘不言’是由于‘以观国风’,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行为”[6]。故而此说也许多加考量再予以定论。
(三)周代制礼说
朱熹提出“三年之丧”是由周公制礼而成,其观点附在《孟子章句·滕文公上》相关内容的注上,即关于“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7]一节的理解,其中鲁国先君已不行三年丧,不仅是对传统的抛弃,更是对德行修养的不利导向。由此朱子注道:“二国不行三年之丧,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8]朱子以周王制礼为前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而不行三年之丧,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康有为在其后也认为此制“承自上古,定自周世”。鲁在周公之后,周公制礼的传承当时做得更完整而谨守礼节,但“鲁先君莫之行”,由此滕国以此为宗“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则变成了相互矛盾的事实,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即是周公未有作“三年之丧”,由此鲁国也从未行之。
针对周公作“三年之丧”这一观点,黄瑞琦先生在其《“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中做了仔细辨析,其中运用金文材料“佳王元年三月,王在吴,各吴太庙。……王乎(呼)史赞册命师酉:‘嗣乃祖窗官邑人、虎臣、西门夷……’”[5]52,指出周宣王元年正月,册命师酉继承先祖去管理邑人奴隶的事。“如果西周有‘三年之丧’,新即位的君王应三年不问政治,特别是号称西周王朝中兴之主的周宣王,更不应该在即位的第一年第一月就远去吴地安排管理邑人奴隶的事。”因而可以认为西周制礼说也难以服众。
(四)孔子创制说
孔子创制说为廖平、康有为、郭沫若、钱玄同等经学家所赞成。而孔子大力推促的“三年之丧”,在《论语·阳货》有详细的论述,宰我提出三年之期太长,会致使生活节奏停摆,由此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回道:“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在丧期锦衣玉食良心安否?宰我坦然回曰:“安。”孔子为此深感不满:“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3]在这次论述中,孔子着重以家庭伦理的情感纽带为论点,但未论及他人行礼之典例,只从人性的普遍性和道德的价值取向铺陈,如前文所提及的《论语·宪问》中子张问孔子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前已廓清高宗此举多为政治需要,以不言而明察,故而这两次阐述都只从道德的一般性和宏观的历史性为立足点,由此可见“三年之丧”缺乏更确切的历史基石和理论依据,由此看孔子首制的说法的确有说服力。但黄瑞琦先生提出:“《左传》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21岁)五月,昭公母亲齐归莞,昭公不守丧,却在比蒲打猎,晋大夫叔向说:‘君有大丧,国不废冤,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成。’《左传》又说:‘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可见在孔子青少年时,社会上就有了‘三年之丧’的说法,而且成为当时所行之礼。”[5]由此孔子首制可能是完整的丧服服制体系,但“三年之丧”的概念在此之前已有远绪。
(五)东夷之俗说
东夷之俗说主要是台湾学者孔达生先生持有,他根据《礼记·杂记》所记载:“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息,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1]1074,由此提出“三年之丧”来自于东夷旧俗,而曲阜为东夷旧都,也是后来的鲁国都城,孔先生更是认为当地风俗即为孔子所倡导的丧制直接来源,章景明先生继承了“三年之丧”为东夷之俗的观点,指出《左传·襄公十七年》记晏婴为其父晏桓子服丧之事:“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而晏婴“可能也是个东夷之子”[3],这些论据还需要继续丰富、充实,故而三年之丧“东夷之俗说”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六)周祭说
方述鑫先生在《“三年之丧”起源新论》一文中提出了周祭说,并通过分析研究丰富的卜辞材料得出:春秋时期的叔向、孔子所提倡的“三年之丧”,其实也正是在殷代衣祀即周祭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殷人一直都在举行衣(殷)祭,即举行有系统的周祭,遍祀先王先妣。并且,在祖庚、祖甲时代,形、翌、弱三种主要祭法都已经具备了。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所谓的‘三年之丧’,其实即起源于殷代的这种周祭。‘三年’不过是一个虚数,是在一个实足的衣祀年”[9]。殷代于先公先王举行合祭,再进行先妣的祭祀。周祭亦即衣祭,有六祀统的规定,先有合祭再分祭,每个祭统一百一十天,合祭则长达六百六十天,分祭三年一次,五年一次合祭诸祖神主。这一观点有独特的视角,但也有待更多的探讨。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断的发展、完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对于“三年之丧”的起源论还需要更多的“地下材料”进行考证,由此也有待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但文献材料对于礼制文明的重要线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三年之丧”在汉代的不同呈现形态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作用,由此来分阶段论述在汉代“三年之丧”的发展、变化。
三、形态变化及其社会动因(一)汉初“短丧诏”的特殊历史背景
汉高祖马上得天下,但也承秦之弊,因前朝暴君污吏徭役横作,使得政令不信、公田不治、民不聊生而饥馑窘困。由此,开国之初必然会面临重建秩序。事实上,汉天下的新朝方立,一切皆沿袭旧制,希冀徐徐图之以恢复国民生机,但仍有不合民意、不服国情的制度,如秦朝施重服的丧制。《晋书·礼志》记载:“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10]527这样天下民众为君服三年,旦夕哭悼,长期严禁正常饮食与暂停社会运转,只会让民生衰敝的情况更加恶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及秩序体系的分崩离析。故而汉文帝发短丧诏,推行厚养薄葬,由此“三年之丧”改为三十六日,以日易月:“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者,纤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11]133。吏民表示悼念三日之后可除服,同时不中断正常的社会交往与生活节奏,哀悼离世者也不能使得现实世界停摆,由此简便丧服仪制,去除繁复的表达符号,如布车及兵器、哭无时等规定,使之变成合理限度下的情感表达,由此缩短了服丧的长期过程,成为了适宜、理性的制度化程式。这成为汉代丧葬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孝文帝再作居丧仪制,其后安眠于霸陵,“自崩至葬凡七日也”,的确有了切实的实践,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行短丧制度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动因,分别是:
其一,汉承秦制,需要建立合乎国情的礼法体系。正如前引,汉高祖立国之初诸事不备,遂继秦朝礼法体例,但秦二世而亡,不仅有统治者的执政理念问题,更有其严刑峻法、率意而行的制度规则,而在严酷的行政压力下,对于暴政的反抗被压制得越狠反抗得越激烈,而这个只延续14年的短暂王朝,也没有将严苛的制度合理化的机会。故而汉代传承的秦礼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因而《晋书·礼志中》记载:“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绖,进退无当。不敢奉诏。”[10]921短丧诏的推行可谓是从社稷宗庙、亿兆民众之生息着眼,随时顺势而制礼则再立规范,成为后世服丧的仪则,既是哀慕之情的完整表达,又能够投入社会生产,故而也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这是一种礼制的时代转化与历史革新。但汉文帝的短丧诏不仅是出于本身礼制操作性、合理性的考虑,更是以当前社会风貌与国情民情为考察。
其二,汉初百废待兴,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生机,因而黄老之说受到重视,推崇休养生息的国策。前秦大兴土木透支民力,连年征战和严苛峻法都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不利局势。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描述的:“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11]123远征四夷后又接连战乱,使得百姓本来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加恶劣,战争导致的流离失所更使得人们失去了自给自足的立身之本,这也导致了人间惨剧的发生。在这种艰难的社会背景下,首要的是避免过多的资源消耗,无论是物质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资源,使得力不足、财不赡的民众有了喘息的机会,故而文帝即位后,“躬修俭节,思安百姓”。如《汉书·刑法志》所记载:“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11]1005而以兼收并蓄、综合百家为特点的黄老学说更重视人本地力、养民节用,故称为汉初的主旋律,由此力戒“三年之丧”的厚重明器、陪葬仪制,缩短因服丧而终止生产的时限。
其三,文帝时期,社会生产回归正常轨道,但也逐渐生出人心浮躁的社会现象,追名逐利者见长。汉初经孝惠、高后的经营后,通过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逐渐呈现出“衣食滋殖”的“文景之治”的图景,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社会风气。《汉书·刑法志》引贾谊上《论积贮疏》内容,描述了文帝二年“背本趋末”的现象:“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11]1005为了遏制这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恶俗,更需要将民众从私利的追逐中拉回来,不能将社会价值置于物质财富的单一指标之上,尤其要抵制虚荣、奢侈的不良风气,改变人心浮躁的社会风貌,也推动了“以心哀悼”、不以繁复的表达为手段的短丧。
其四,匈奴屡犯,又逢自然灾害频繁,民生疾苦。虽是时已步入了恢复社会活力的正轨,民众的生存境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与自然因素的负面影响成为限制儒家“三年之丧”理想状态实施的客观原因。《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11]1124此仅有水旱之灾造成的破坏,事实上其他的自然灾害也不少见,岁恶无收,贩卖田宅、子嗣以求生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狼狈不堪,那么此时“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与此同时,匈奴的虎视眈眈也不容小觑,《汉书·天文志》记载:“孝文后二年正月壬寅,天夕出西南。占曰:‘为兵丧乱。’其六年十一月,匈奴入上郡、云中,汉起三军以卫京师。”外族的威胁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个仍需努力求生存的时期,无妄之灾的频繁“造访”无疑都是灾难性的,由此只有节衣缩食、短丧薄葬,因而可以认为短丧制度也是顺应特殊历史时期的仪制转变。
在汉文帝“短丧诏”这一历史节点后呈现了相互交错的两种情况,统治者既以孝道、仁心作为思想旗帜敦促社会风气,同时又以“三年之丧”为代表的久丧占用社会资源、离析行政队伍而不断进行限制,但这些状况都可视作同一个历史时空坐标上的不同点,故而可从“三年之丧”的一般实行情况与统治者的政策限制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西汉中后期的磨合、调整阶段
这一阶段是向正规化过渡的阶段,是社会效能与民风意愿相磨合、和解的过程,也是不断实践短丧恢复国力,探索最合乎民心的运行状态。文帝短丧诏后,汉武帝至后汉光武帝之间的这一长跨度历史阶段,有丰富的“三年之丧”践行例子,仅就杨天宇先生《略论汉代的三年丧》一文梳理中就有五十余例。在此则仅从不同年间由统治者、诸侯朝臣以及平民三个角度进行整理,列出有典型意义的文献资料。
从统治者的角度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汉文帝后,统治者对于“三年之丧”的赞赏、身体力行与明确态度表达就有两例:
《汉书·哀帝纪》记载:“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11]338《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11]4125
朝臣诸侯依礼行丧的典例更多:
西汉时期首位由丞相封侯的公孙弘,据《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11]2628:《后汉书·陈蕃传》:“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后遭母忧,弃官行丧。服阕,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以谏争不合,投传而去。”[11]2165《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11]3042
还有平民自觉遵循礼法的例子:
《后汉书·铫期传》:“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11]732《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不受赙赠,缞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11]1534
由此梳理出三个倡行“三年之丧”的时间点:
一是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此为汉文帝短丧诏之后有明确史料记载的首个服“三年之丧”者,且离短丧制度推行时间不远,可见民间孝谨之风气、哀悼之心情是不可被强行抑制的。尤其在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完毕,除服后又重回庙堂,任内史数年后又迁御史大夫,其对策疏文被武帝看后拔为第一,再拜为博士于金马门待诏,这种优待也可看出统治者对于不行短丧者的宽容,公孙弘去官在乡服丧三年,复起仍可得以重用,民间更可以此为典例,把握官方传递下来的讯号,但正面、主流舆论中,此时仍然倡导文帝短丧制。
二是汉哀帝以河间王良为宗室仪表、道德楷模,并行封赏增赐封万户,此举无疑是正面赞扬“三年之丧”孝道伦常的明确表达,可以视为短丧制官方态度的转化。而“三年之丧”作为一种内在蕴含着情感内容的行为规范,更清晰地贯彻了对于道德品行的崇尚,由此更是对于孝感文化的大力推广。与此同时,汉哀帝规定的博士弟子父母离世应“予宁三年”的规定,更开启了“丁忧制度”的开端,逐渐演化成为在朝官员如遇父母离世,须辞官服丧以表孝道,但这项规定同样导致了行政压力和人力资源的消耗,只是在汉代的首要着眼点和立足点仍然是对于“称情而立文”仪制的表达。
三是新朝王莽复礼的奉天法古运动,“开秘府,会群儒”以制礼作乐,并推崇儒家传统“三年之丧”的规定,平帝崩而征明礼者制定新朝规制,以“眩惑天下,示忠孝”,于是令天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吏皆服丧三年,从而延续了汉哀帝的丁忧制度,并将仪制和准入门槛做了进一步细化,使之有了具体的服从秩序。但如《功显君丧服议》所表达的,在其母功显君病逝后,怀揣着政治目的的王莽“但服天子吊诸侯之服,”加缌缞弁而麻环绖,一吊再会而已,令其子亦即功显君之孙为丧主来“服丧三年”,但王太后离世“莽为太皇服丧三年”。以己为入皇室继子,认文室皇太后为嫡母,狼子野心昭明于世,且借礼制儒风之大旗行无德不孝之实,但从客观角度观之,则也可称其以最高统治者的角度以身作则,向民众推广、倡导“三年之丧”以表哀情的仪制,也是汉文帝短丧诏正式被“驳回”的标志。
由此可见,西汉中后期的确出现了态度上的松动,追寻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则可看到两点:首先是思想领域上的儒风提倡,其次是选拔制度的道德要求,这从两方面共同推促了“三年之丧”的施行,既是对品性的确认,同时也成为士人晋升的坦途。
汉武帝遵从先王遗志施行短丧,官方态度从而下渗到民众之间,但同时随着汉朝国力的跃升及汉武帝野心的政治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再成为思想领域的主导理念,而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思想为大一统,置《五经》博士,推崇儒术,并着力倡导儒家的仁义理论与伦理价值,通过经典教化来陶冶德行,通过学术引导来整齐上下,由此提升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也有了修身为道的儒家治学理念,从根本上塑造忠义之士。“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本就注重孝道,在汉武帝时期更是采用了察举制为选人制度,《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11]184,兼绝“乱国政”之言。高祖立国之初选人制度袭前秦之制,也更同乎高祖“马上得天下”理念,即以“军功”论人,“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但夺天下易守天下难,“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其后,高后、惠文景时期增设“任子”“訾选”等制,“任子”即使诸有功者皆受封地为列侯,本质上是一种世袭制。“訾选”制则以财产规模为门槛,皆绝寒门平民入朝堂之途径,由此“臧于高庙,世世勿绝”,但这种垄断的选拔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无法扩大优秀人才引入的路径,其实高祖刘邦早于高祖十一年(前196)即发布求贤诏书,但具体的施行还是经过了多代的努力,高后始开“孝悌”“力田”初定为察举科目,“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景帝时,赞誉廉士之寡欲易足,又苦于求贤而不得,将訾以广求贤良。文帝其后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察举制直至武帝时才正式成形。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11]194重新从道德和品性两方面考察官吏,故谓“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1]194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选拔人才的高标准要求,而为了达此目标,以立言治世为理想的士人必须以此来丈量自己。此即成为西汉中后期“三年之丧”形态转变的两个具体原因。
(三)东汉复归居丧礼仪的反视阶段
民风多尚“三年之丧”以表达情真意切与品性崇高,同时自汉武帝始,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选拔人才的晋升之途的察举制,从两个方面都推进了“三年之丧”的施行与接受度的提升,但正如“夺服”之制所针对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行政链条脱节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对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有效稳定造成不利影响。由此东汉光武帝在遗诏中再一次颁布“短丧令”:“皆如孝文皇帝制度”。致使东汉甫立便又复归汉文之短丧制了,但这种官方表态并不足以熄灭盛行的民风民尚,且制度的调整也并不意味着对于孝道的颠覆,而是在合适的表达程式中更紧凑地安排丧礼,故而在此阶段产生了一种短丧令的号召下孝道醇厚的服丧制度与投机、功利心理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由此丧礼这一纯粹的礼仪符号,增添了教化的内容以及统治集团内部门槛标准的双重含义,而这种文化内涵的再创造使得“三年之丧”的性质又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了不同的审视态度,这是东汉阶段“三年之丧”形态变化的重要原因。以下从三个方面论述这种变化:
1.东汉时期官方态度的变化
东汉推翻王莽的新朝统治,光武帝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在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后也不得不恢复民力,休养生息;同时改革中央官职,精简体制,大兴儒学,这也可与同推翻秦朝的高压统治并再次整合国民经济的西汉初期相类比,在这种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首要仍是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社会组织内个体长时间脱节的可能性,由此丧礼行三年的仪制虽经汉哀帝与新莽的推崇,民间风气的盛行也需在此做出规制,返回简约、高效的丧礼仪式,以期维护社会秩序。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12]94如光武帝遗诏所要求,西汉中后期逐渐脱离汉文帝短丧诏牵制的“三年之丧”仪礼,又重新受到管制并回归约简的标准,而这也是同社会矛盾运动内在契合的,不以消耗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为“奠”,以助力于“储蓄”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提升资本,由此这项“短丧令”在立国初年尤具有现实价值。但光武帝逝世后,汉明帝并未如实遵循其短丧诏,《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了汉明帝仍为先帝亲服三年,其圣孝之心久在园陵,悲切之心无须言语,由此蔡邕以为“礼有烦而不可省者”,现在汉明帝行重服是彰明了先帝用心周密的礼仪内涵,并通过以身作则的实施成为万民楷模,扬德行于天下的有益政教活动。正如此举所显示的,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三年之丧”已被民间普遍接受并广为践行,如杨树达先生就从《后汉书》中《韦彪传》《鲍永传》《廉范传》《刘平传》《江革传》等章节考证出“三年之丧”存在的痕迹。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三年之丧”也更为大众所认可。《后汉书》卷三七 《桓荣丁鸿列传》记载:“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觽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12]1257由此邓太后以服三年丧为官吏进士的门槛标准,打破了汉文帝初立、光武帝复归的短丧诏规定,并以官方态度再次强调孝道与诚敬的立身之本,故而“三年之丧”的社会接受度与普及程度又呈现了积极倾向。元初三年(116),才有了“丙戌,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12]232。注疏亦云汉文帝短丧制定以来,多行简约遵仪制,而“至此复遵古制也”,也就解释了其中“初听”一词的缘由,可以看出在光武帝遗诏中所强调的仪礼须从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一旨的确得到了有力的贯彻,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是保持着上下统一态度的,而光武帝至孝安帝历经六世仍有余威,其执行意志也可见一斑。但仍可从统治者队伍内部的态度倾向中提取出“三年之丧”的政治作用,汉明帝以孝心感怀天下,邓太后以仁心德行要求官吏队伍,都是对社会风尚的方向引导,也更具备教化意义。
2.伪作姿态以服顺孝道民风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三年之丧”的时长要求与具体细化的仪式表达,从现实角度看的确是检验丧主是否诚敬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体现其哀痛伤感情绪表达的直接发泄途径之一,故而对“三年之丧”的执行与否或者遵循的程度表现都是可以直接衡量生者对于逝者的孝心程度与感情牵绊的深浅,不孝之人必然是不会遵从这种条条框框,具体到站位、哭时的仪,最明晰的例子即是昌邑王刘贺即汉废帝被罢黜之由,昌邑王虽典丧而服斩衰,但“亡悲哀之心”而“废礼谊”,先帝之灵柩还停殡于前殿,昌邑王便“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居丧期间不以仪制守丧,“弄彘斗虎”“击鼓歌吹作俳倡”与宫人厮混,不忌饮食“常私买鸡豚以食”,行事铺张、排场浩大,命掌管财物、珍宝的中御府令拿出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并“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这些荒唐行为都让朝臣上下无不为之“愚戆”反感,终被诸臣弹劾认为其不孝至极,不可承天道,即位二十七日而废。这即是“三年之丧”在政教方面重要地位的体现。
但在这种经久不衰的社会风尚推崇下,也逐渐出现了背离孝道、沽名钓誉、称奇标新的投机行为,这些目的不纯的伪作者只为功名利禄的谋取,而并没有内在的道德驱动,这样的行为为人所不齿。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其人:“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及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12]2165其行为夸张至极,安葬其亲而不封隧道,在其中“行服二十余年”,赵宣此举纯为邀誉以举孝廉,试图以投机心理铺就利禄仕途,果然“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并将他举荐给陈蕃,却不料通过了解其妻儿陈蕃才得知赵宣五个儿女都是居丧期间所生,此等欺上瞒下的“骗局”不仅损毁了以孝道服丧这一真挚情感内容的表达途径,更是对朴实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成为极为不利的反面示范,故而“遂致其罪”不予轻饶。陈蕃是东汉桓帝时人,此处也可看出此时并不严守丧期时月,而返归制礼的原意即对于孝道与品性的推崇,这种真实情感的展示也是统治者乐见其成、平民群众予以高度赞赏的。更有许多风采卓越的士人却不具备最基本的孝心德行,《后汉书·虞延传》记载了永平初年,新野功曹邓衍凭借外戚小侯的身份朝会,其容貌身姿趋步都卓然优越于众,汉明帝对他表示十分欣赏,甚至夸赞道:“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后乃诏邓衍拜郎中,又升至玄武司马。但这时了解到邓衍在职其间未为其父服丧,汉明帝听闻后不由得叹息:“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这也表达了即便是一表人才、风采出众之人,不能内在地具备良善的道德品质为亲人慎终追远的诚敬情感都是不被统治者及他人所认可的。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所书,汉安帝元初五年,赵惠王刘乾为其父靖王刘宏服丧期间,因其不守礼法、不能以诚敬的态度对待亲人的逝世,反而“私聘小妻”“白衣出司马门”,被坐削中丘县。这些对于不敬不孝之人的惩处都是非常明晰的态度倾向,也表明了“三年之丧”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最直接地体察无德无礼之人的方式,也是深刻反视自身品性的最好映照。
3.“三年之丧”崇敬理念的泛化
杨天宇先生提出,东汉的三年丧除为君、为父母服外,还有为太守服三年者,详参《桓莺传》《李询传》。还有故吏为其主官服三年者,如《杜乔传》《荀爽传》内容;以及为师服三年丧者,此举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儒学大圣先师孔子,在其离世后即被弟子诚敬的悼念,又说弟子皆居丧三年,还有认为子贡甚至守丧六年,留下一“子贡庐墓处”。但杨天宇先生据文献考证,发现西汉时期为师服丧更为有迹可循如《扬雄传下》,侯芭为扬雄服丧,及《李合环传》中为师心丧三年。与此同时,更有属民为其长官服三年者的形式,如《桓典传》中桓典为沛相王吉服丧三年。这四种特殊的守丧形式,都是基于内心崇敬与尊重的反馈,更多的是摒除人际张力,而纯粹来源于个人情绪体验所做出的行为表达,这种剔除了必然性的选择,大多数都应当是对良知和感恩的自觉,这也是“三年之丧”由原始含义上的宗法制经脉成为道德的映射符号与理性自觉的执行过程。故而可以认为“三年之丧”由制礼作乐,历经数朝数代的发展、完善,实现了一个礼仪再发现与礼制具体仪则可操作性的调整。
因而,“三年之丧”在后汉时期由于西汉的德性孝义的社会风尚,也出于较长时间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人们对于丧制的履践动机逐渐又复归回对于道德品行的礼义反视与倡导,由此不再限制“三年之丧”的施行,而给予民众自己充分的自主权,甚至在邓太后与汉安帝这一阶段还呈现出积极推行的明确表态,并成为官员表达仁心孝行的衡量尺度、进士考察的门槛。
四、余论
通过梳理“三年之丧”的来源,并将目光集中于汉代丧制的形态变化,由此可以发现,礼是人心理状态的外在表征,即便是汉文帝的短丧制度也需要“以日易月”,在规定的期限内展示丧主来源于内心无处宣泄的哀痛与伤感,这即是制礼作乐“称情以立文”的现实价值,由此在社会民生得到有效缓和之时,民间风尚便由简约的丧制做出了相应的自主调整,这样的民风民意也逐渐与上层统治者的意志相连接。由此短丧制度的几起几缓,都表达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礼的不同需求,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如何实现自身品性的有效呈现并表达出对于高标准道德的追求与理想呢?即是通过施行“三年之丧”,其中体现的毅力与诚敬便成了最好的佐证。但《晋书·礼志中》仍指出,文帝作短丧诏“后代遵之,无复三年之礼”,由此可见短丧的实用和简约价值,也并未被崇尚“三年之丧”表仁心孝行的风气所掩盖,而是有了各自的空间,故而“礼者,时也”,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变化有着不同的现实价值与社会动因,但在推进社会风尚与道德文明的过程中,却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动力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