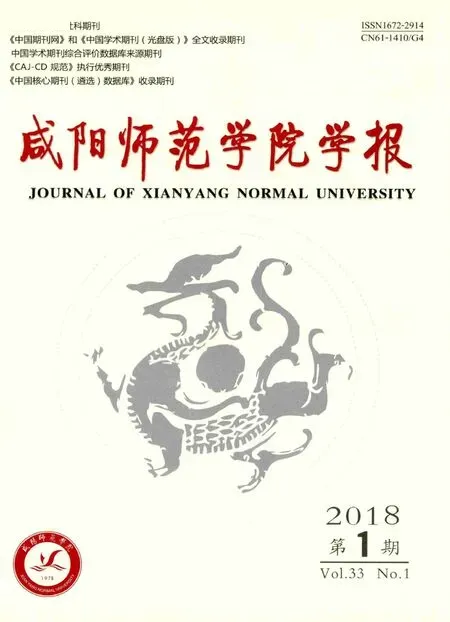天德王道:论刘古愚《大学古义》的诠释特点
2018-02-25单晓娜涂耀威
单晓娜,涂耀威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一旦社会发生大的变革,经世意识就会勃兴。清代后期,受时势的影响,经世风潮大兴。学者笃信程、朱是为经世,主张调和汉、宋者亦为经世,经今文派阐发微言大义同样有经世情怀。儒家经典《大学》成为学者阐明经世思想的重要文本,学人纷纷借《大学》以阐发自己的观点。[1]《大学古义》是刘古愚诠释《大学》的著作,在诠释上回应了时代的主题,反映出他的治学特点。
刘古愚(1843—1903),名光蕡,字焕唐,陕西咸阳人,清末关中今文经学与维新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被梁启超赞为“关学后镇”,[2]12康有为誉为“海内耆儒,为时领袖”。[3]86刘古愚精研经史,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主治今文经学。刘古愚生活的时代,“中国久积弱,屡被外侮,先生愤慨,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之,以为此学,亦以此为教”。[4]189他提倡实学,强调西学,主张改革,振兴教育,主持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多年,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治经重微言大义,不重训诂考证;在义理上与王阳明心学相近,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刘古愚以《大学》为“天德王道”,将心性与事功之学并重,反映出他的民本思想和对经济的关注,以及今文经学家以《大学》为政治哲学纲领,开掘《大学》微言大义的努力,在众多《大学》诠释文本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1 “天德”即天与我之“明德”
刘古愚提出了《大学》是“天德王道”之学的命题。他说:“天德王道,天下万世之人所当学,此篇以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括之而无遗,宏纲即举,而细目又极详密,故此篇言学,为古今有一无二之书。”[5]261
天德,是“真的自己”,道德本体,性之本然,《中庸》的“纯亦不已”。儒家认为,圣人天性浑全,实行仁义,习于本性,不假外修,谨慎要求自己,“含德之厚,比若赤子”,所适自无往而非道,故能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关于“天德”,儒家思孟学派已有论之。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对“天德”最好的诠释可能是《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的“性之”二字,也就是《孟子·离娄下》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6]371理学家认为“天德”就是“天理”,朱子曰:“有天德,则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无天德,则做王道不成。”又曰:“无天德,则是私意,是计较。后人无天德,所以做不成王道。无私意间断便做得王道。”[7]159-160“天德”,类似于西方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泰勒等人所说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本真性”(authenticity),是一种原始的、先天而来的道德意识,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直觉。“天德”是“天理”的认识,使得道德本体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根本。刘古愚以《大学》为“天德”之学,认为《大学》的“明德”就是“天德”,“天与我之明德”,[5]268所以有“《大学》一书只是个明明德”[5]275之语。
何谓“明德”,刘古愚认为,明德是天与人之性,是道德本体,自有之物,“此知为流动之灵明,必有实落凝聚处方可谓之德。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5]270-271“明德,性也。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以应万事者,即《孟子》万事皆备于我之义。以迹象言谓之物,以义理言谓之德……明明德,复性之学也。身心家国天下,皆是物;修齐治平,即是则。不违其则,即德也。”[5]264
对《大学》“明德”的诠释,刘古愚认为是天与人之本性,推及外物不过是不违其则,“物物有其则”,以天所与人之本性“明德”以应万事,使物物不违背自身规律;而“明明德”,即是复性尽性之学,恢复本体良知。这是天理之流行的认识,是典型的道德本体论,将“明德”与“天德”的意义相等同。
同时,刘古愚认为“明德”要与事功相关联,他说:“自古圣王莫不用力于明德,盖出全力以为之。”[5]269如何为之?要见诸行事,不能留于空寂,要扩充其量,实用其功,“明德不充其量,则遗弃民物,虚寂之学,非大人之学也。明德不实其功,则泛滥为知俗之学,非大人之道也”。[5]266他认为实用其功的对象在“民”与“物”,“入《大学》讲明道德,不过复完我得于天之性,我得于天者,万物皆备,故欲得我之性,不能离却民物遁于空寂自谓见性”。[5]264明德见诸王道,即在亲民,“亲民”与“明德”即为一物:“合明德、新民为一物,此有深意。人皆视明德、新民为二,故佛老之徒修身养性只知为己,无圣人成己所以成物之公心。……合德民为一物,一物而二名者,本末之形也,德民为一物,即明新为一事,事同而名异者,终始之迹也。”[5]263以“明德”与“亲民”同一,对“明德”的重视,也会重视“亲民”,所以刘古愚的《大学》诠释思想中,把“亲民”看成王道之学的重要部分,十分关注。
2 “亲”之一字为王道之本源
“王道”,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是“孔子以学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5]280王道政治是对西周文王、武王统治时期理想社会制度的概括,是推行仁政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8]56-57刘古愚认为《大学》与《春秋》一样,是针对君王而言的建立王道的政治学纲领,他说:“至于必同民好恶,辟则为天下戮;财聚民散,悖入悖出,拂人性则灾逮夫身等语,处数百年君民分定之世,而著民叛之事,为罪不在民,皆长国家者所深恶而厌闻者。”[5]281天德是体是本,王道是用是末,“有天德自能实为王道”。[5]277但二者不可分,一而二,二而一,关系紧密。在刘古愚看来,应参赞化育,视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德、民是一物,“明德”即是“亲民”,“亲民”即是“天德”的实践。由明德到亲民到王道,构成内圣外王之学的全部。亲民是连结天德、王道的中间环节,故在重视《大学》心性内容诠释的同时,刘古愚将亲民也上升到与明德同样的高度,认为亲民是王道之本源。
刘古愚认为《大学》之道生于民,亲民是“明德”的内在要求,“性分所固有”。学者必须成己成物,在德性修成的同时,对庶民之事给予足够关注,“《大学》之道,是由明德以亲民之路。明德不亲民,即无道。故《大学》之道,生于民,无民即无道。天地间万事皆起于有己有人,若天仅生我一人,则德不与人接,谁谓其不明,亦何贵于明哉?圣贤立学之意,凡以为民也。学者有志于学,须立地有民胞物与之量方可言学”。同时,他认为“明德”的效验必于亲民上见,无民即无己,“明德至善之地仍在亲民上见,不新民而空自明其明德,其明于何见之……盖己与民共立于世,无民即无己,无己即无明德可言,故为学以亲民为重也”。[5]262明明德于天下就是亲民,“明德是就本原说,天下是就分量说,明明德于天下即是亲民。……亲民之极,即是明明德之极”。[5]265
亲民是天德所见之在,也是王道的根本,与“王道”相对之“霸道”在刘古愚看来皆由视民不亲而生,“人惟视民不亲,故忍以法术愚民、刑威迫民”,所以才提出“亲之一字为王道之本源”的看法。他认为“亲民”之义精深宏大,已涵盖有“王道之作用”的“新民”之义,故不主张改“亲民”为“新民”。[5]262亲民所受于天,是王道之根本,有民才有国之富贵,而不是一家之私产,“帝王之富贵,以有民也。习之久而昧其初,不以民为吾所受于天之职分,其教养皆吾当尽之责,而以民为祖宗所留贻之畜产以供吾财用者,天子贵极富溢,日纵淫侈,积为风俗”。[5]278继承先王为政之道,教化、生养民众均为应尽之职分,是天德王道的内容所在。
刘古愚认为学《大学》之理就要见诸实事。他说:“何以为《大学》?立念以天地民物为一体,而学以讲明其理,然后实为其事,则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矣。”[5]261强调以变易思想看待《大学》,“夫子为书,既有感于当时而发,世移时易,理不变而法令不能尽同。学《大学》者,乌可不以己之身世习之而泥古法以治屡易之身世哉?”[5]280在对《大学》天德王道内容诠释上,可以看到刘古愚重视民生财用。他说:“财既生,仁者理之不偏重于一而周流焉,则家给人足,天下长享太平之福矣。……天下太平之成,自财用恒足始,则天下不平之端,必自财用足生。”他视财用为天德、天理,“财者,人之生机,即天之动机,无财用,则人事绝,天理灭矣”。
刘古愚论民生和工业,不囿于陈见,与时俱进,在注解《大学》“生众食寡,为疾用舒”时,他认为向来论财用,只是重本抑末,是理财而不是生财,而生财无有西洋工业之利多,“自汉以来,君相经营财用,亦知取则于此,然不过重本抑末,驱民归农食、节用时,示民以俭已耳。至今思之,仍撙节爱养,谓为理财之极则则可,非生财也,生财则须以人力补天地之缺陷……圣门论财用,未尝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机器,一人常兼数人之功,一日能作数日之事,则真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矣。《易》称黄帝尧舜之治归之制器。《大学》论生财未必不见及此,故吾反复此节,而知外洋机器之利。夫子必已见及而时未至,不能遽兴,故露其机于此,以待身逢其时者之取而用之也”。[5]279因此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业,“延外人以教中国之民,来百工之说也。振兴工学,以自制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之说也”。[5]280
刘古愚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工业,是其亲民思想的重要体现。受到晚清时势之影响,他也主张变革。不过,他以“天德”“天理”论“财用”,“中体西用”特点比较明显。
刘古愚认为礼是王道之纲纪,《大学》天德王道之学,具有立纲陈纪之用,是礼之本,故主张将《大学》升入《仪礼》,完全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四书》之《大学》,也异于清代以《礼记》解《大学》的学者。刘古愚说道:“礼者,人事之纲纪。王者之政,所以纲纪人事也。欲王政之行,必须人材。大学培养人材,以为立纲陈纪之用,则《大学》尤为诸礼之本。……予意以此篇为经,升之《仪礼》中,或置于首,或置于《冠昏礼》后,或置于末。置于首者,即《大学》为诸礼之本之意;置于《冠昏礼》后者,《大学》为成人之学也;置于末者,虞廷典乐,教冑子在礼官之后也。而以《学记》为传,如《仪礼》有《冠礼》、《昏礼》,《小戴》即有《冠义》、《昏义》之类是也。如此分为经传,似较与《中庸》同列《论语》、《孟子》中为稍胜也。”[5]272刘古愚对《大学》性质的认识,或是礼之本,或是成人之学,或是与《学记》性质相近,以经传相配而行之。这些论断没有多少文献上的依据,只是刘古愚认为孔子以学承三代为万世之法,必不轻视学礼;而朱熹作《仪礼经传通释》,也特别重视学礼;《大学》揭示的正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天德王道之学,而王道纲纪正是诸礼之本,孔子、朱熹重礼思想正是与其一脉相成。对《大学》纳入《仪礼》归属的判断,充分反映了刘古愚今文经学家的特点。
3 “天德王道”观的实现
刘古愚所论《大学》之“天德”与“王道”是紧密联系的,其义虽与内圣外王趋同,却没有内外之分,是天人合一思想与内圣外王框架的一个产物。明德是天所给予,民物是自己分类之事,明德必须亲民;王道是天德之显现。刘古愚在强调道德修养的同时,推及王道政治。“三纲领”中刘古愚以为只是“明明德”,明德之核心是诚意,格物、致知、正心不过是恢复天德之良知、意之灵明。亲民与明德同等重要。而具体如何由明德到平天下,刘古愚认为王道不外人情,只是要尽物之性,推平好恶之情,“明德,天理也;好恶,人情也。物物各就其矩,王道也。王道不外人情,君子平天下,平天下之情而已,情范于矩,则天理明于天下矣。天理从人情上见”。[5]277情是性之所发,情之正即为性为理,以絜矩之道推情于天下,“明德是性,好恶是情,矩是明德之形,即范好恶之道,絜矩即是知道而用以平天下也。……明德在我为性,达于天下,则其用在情。故诚意以好恶起,以民情民志结,见明明德于天下,正赖此情之无不同耳。……至治国章,推明人情之同,上下感应之理,见情之正者,即性也。……故曰人情者,圣王之田,而中国能为一人,天下能为一家也”。上古王道之政也不过如此,“自古王者之兴,皆先去民所恶而后能聚所好也。……若裁制万物,固是推吾心之爱,然物莫贵于民,民害不去,民利何由兴,故平天下由所恶推入,然后好恶并言也”。[5]276-277
总而言之,“天德”将“明德”建立在天的基础上,与“王道”政治相结合,使得道德本体有了普遍的意义,又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王道”的实现也反映了儒家所推崇的周代礼乐的仁政模式,使得事功成了“天德”的内在要求,而不仅仅是心性修养工夫。刘古愚的《大学》诠释思想,对“明明德”十分重视,将“明德”视为天德,又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进而视其为天理。更具体地讲,刘古愚的思想延续王阳明、刘宗周以心学解《大学》的思想比较多,在格物致知、诚意等概念范畴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毕竟王阳明强调良知、刘宗周强调慎独终究只是道德修养方面,在《大学》诠释中,对王道政治强调不够,而刘古愚在强调心性之学时,继承了关学源头宋儒张载立民胞物与之念,“天德”与“王道”并举,重民物而亲民。与朱熹一样,刘古愚也看到《大学》为大人之学、教人之法,讲心性修养论,但刘古愚还看到了《大学》为王道政治纲领的一面,所以朱熹家将《大学》收入《四书》,而刘古愚却主张将《大学》升入《仪礼》。对于刘古愚生活的时代而言,外侮内患,积贫积弱,他所处的关中地区风气未开,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刘古愚不得不借助对传统经典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他所关心的“王道”就是兴教育、办工业等兴民生措施,对财用的重视、对西方工业的学习,均是刘古愚面对时代主题而对《大学》思想所作的创新性诠释。
正如有论者认为的那样,王道重视礼乐,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特点。所谓王道,就是行政权力的建构与运作以社会公益为起点和枢轴;霸道则正相反,其建构与运作以一家一姓的私利为起点和枢轴。“王道出现的历史背景,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手段不足;又由于个人尚未从早期共同体中离析出来,社会以家族、宗族、部族为基本单位,利益尚未分化,所以,族群之间的结构关系或曰秩序,主要是建立在礼让、协商的基础之上;族群之内的结构关系或曰秩序则主要以‘亲亲’和‘尊尊’为原则,即建立在血缘关系以及内部分工的基础之上。……而《大学》所讨论的既不是抽象的认识论问题,也不是什么‘为学次第’的问题,而是关于王道政治之重建的某种系统理论。具体落实于《大学》,其首重‘明明德’,所讨论乃是一个促使‘明德’由潜而显其明政治实践问题。……‘明明德’首先是应唤醒自己神性自觉(责任感或使命感),顺信天命以行,具体而言就是应承继先王志业,以道化民。”[9]358-364刘古愚的《大学》天德王道说,无疑已经涉及了这些内容。“天德”、“王道”以及“天德王道”思想,是原始儒家伦理政治重要思想之一。明代吕坤有云:“天德王道不是两事,内圣外王不是两人。”[10]61近代学者熊十力先生就注意到王夫之每以“天德王道”总括六经之理要。[11]49刘古愚以“天德王道”总括《大学》也应是有所继承。
4 结语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理学家非常重视,近世论儒家道德实践哲学者多以“内圣外王”概括它的意思,以前五项为内圣之学,后三项为外王之学,而《大学》就是表述“内圣外王”的纲领。然而,“内圣外王”说,先秦只见于《庄子》,孔、孟并未言及,宋明理学家言之也少,用它来概括理学思想也不准确。实际的情况是理学“内圣强而外王弱”,在具体诠释《大学》时,理学家也是多重内在心性修养之阐发,而不重外王之学。朱熹说:“《大学》重处都在前面,后面工夫渐渐轻了。”[12]251因此他讲解《大学》,前面五条目不厌其详,后面三条目则轻轻带过。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八条目仅举前六项。以后王阳明争古本《大学》,认为八条目中“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前,所争也是在“内圣”之学方面。[13]2不过,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大学》只是一个‘空壳子’,其自身不能决定内圣之学之本质。”[14]350这要看不同的诠释者在诠释过程中的侧重,明代邱濬著《大学衍义补》本意即在补充“外王”之学。我们看到,刘古愚对《大学》“天德王道”的概括是《大学》诠释文献中,对《大学》性质与内容比较精当的论述,接近于“内圣外王”,可能更契合《大学》作为伦理政治纲领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传统。
参考文献:
[1]涂耀威.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J].中国哲学史,2009(4):98-103.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M].上海:上海会文堂书局,1925.
[3]康有为.烟霞草堂文集序[M]//康有为全集:第1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陈三立.刘古愚先生传[M]//散原精舍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刘光蕡.大学古义[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思过斋烟霞草堂遗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陈明.王道的重建:“格物致知”义解[M]//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陈荣捷.存养[M]//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杨高男.原始儒家伦理政治引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9]陈明.大学之道:为学还是为政[M]//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吕坤.说道[M]//呻吟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11]熊十力.读经示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黎清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姜广辉.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